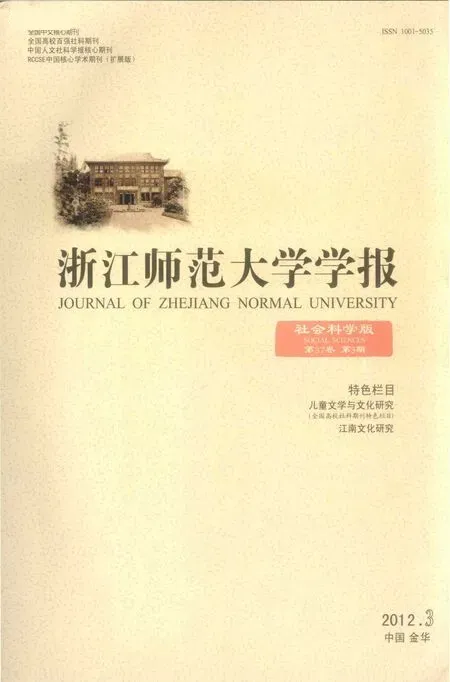论儿童汉字习得的美育功能*
章 辉
(浙江大学 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丁海东等将儿童精神的基本特质总结为“自我中心化、整体性混沌、潜意识化和诗性的逻辑”。[1]的确,儿童精神虽尚未发育成熟,理性尚未发达,然而在他们身上却潜藏着成年以后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始基。因此,抓住儿童阶段精神的特点,通过美育诱发儿童的诗性逻辑,促使其健康成长,为日后理性的发展和成熟创造互补的土壤,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历来的儿童美育中,一个很大的失误在于仅仅把美育等同于让孩子学习歌舞、绘画等艺术,而忽略了母语习得中的美育功能。这种美育上的忽略,遗忘了汉字本身的审美建构。马克思曾普泛性地断言“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事实上,人也遵循美的原则来建构语言。换言之,语言本身也是由人的审美意识和诗性思维所创造的。卡西尔曾指出:“我们日常的语词并非纯属语义的记号,而且还充满了形象和具体情感——它们是诗意的和喻意的表达,而非仅仅是逻辑或‘推论性’的表达。”[3]131汉字是建立在象形基础上的音义结合的语言系统,卡氏这一论断用汉字系统来加以印证尤其具有说服力。
人生识字始于儿童时期。19世纪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4]同样,对于儿童汉字教学,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认字的过程,而应使其成为唤醒学生美感和道德感,激发鼓舞他们人文精神的契机。儿童精神是潜意识化的,特别是在儿童早期表现尤为显著。如能在儿童阶段结合汉字中的审美因素来进行审美教育,将能起到潜移默化的良好效果,在他们将来美好性格的形成上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构建审美形态,启迪审美意识
历史上,汉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取向产生了丰富的审美特质。笔者认为,作为审美建构的汉字系统至少具有以下四种传统审美形态:简约、中和、神妙、气韵。
(一)汉字的“简约”之美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崇尚简约。纵观传统艺术构造,无不极为简约。比如二胡仅有两根琴弦,水墨画仅有黑白二色。汉字字形的建构也完全体现了简约之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但笔者认为,每个汉字都无非是由横、竖、撇、捺、点组合而成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五种基本笔画是汉字的字母,汉字是它们用“拼”出来的。对比其他语言,英语有26个字母,俄语有33个字母,而且每个字母还有大小写的不同,因此每个汉字的组合部件是极为简约的。不但书写结构简约,字音也同样如此。每个汉字的发音只有一个音节,且多为单辅音+单元音式,没有欧洲语言那样复杂的复辅音,非常清晰。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来说,汉字这种简单的构造元素更易于他们掌握。
史文霞认为:“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角度来看,语言艺术美的实质在于简约之美。”[5]汉字的简约美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例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汉字简约而不简单。正如二胡虽仅有两根琴弦,却五音齐备;水墨画虽仅黑白二色,却气象万千一样,在二维空间里,五种基本笔画却可以根据需要构建出几万个不同的汉字来,可谓潜藏着无限变化的空间。17世纪的莱布尼兹早已看到这一点,指出汉字“根据事物的可变性呈现无限多样的笔划”。[6]116此外,从字义来说,虽然书写、读音建构简约,但每个汉字却都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强大的构词潜能,这是其他文字很难做到的。所以这样看来,“语言的简约美……是语言发展过程中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5]
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教师可以因势利导,就汉字的简约之美启发儿童以少驭多的审美思维,提高他们掌握外部世界的能力和水平。
(二)汉字的“中和”之美
儒家美学尤其推崇中和,可以认为,中和是儒家哲学为灵魂的审美形态。“中和”即中正、平和,它首先基于这样的认识:承认对立,但更主张对立的统一、世界的多元化和思想多元化,学会包容正反两面意见加以融合,使事物始终处于合作、和谐状态。对此,抽象能力较弱的儿童是很难加以理性掌握的。而在汉字习得中,他们则能较容易地从感性上理解这种哲学关系。例如教师可以提示他们,汉字的基本笔画都是对立的,如横与竖、撇与捺、勾与提,都呈对立状态,而每个汉字却是由这些对立元素所和谐统一而成。这样解说,对立统一关系这个复杂抽象的概念就在童心的土壤里得到了感性的播种。
中正还含有节制、秩序、规范、对称等美学含义。汉字字形向来讲究布局控制、书写秩序与对称、呼应等关系。莱布尼兹认为,一种完美的文字应该以汉字为蓝本来创造,使它“具有汉字优点”,即“根据事物的秩序与联系将笔划完美地联系起来”。[6]116在书字教学中,教育者可以引导孩子发现汉字规范字形控制(每个字都呈方块形,并占据大小一致的空间),严格讲究笔顺等特点,以及明显的对称美,笔画的呼应关系,让他们在幼小的心灵深处体会儒家美学的感性特征。
中和强调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这一点在汉字里有鲜明的反映。卡西尔认为语言中具有一种直观的性质和意蕴,不过这种直观性在西语中并不明显。而汉字里大量的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形状的诗意欣赏与直观摹写。除了象形字以外,还有大量以象形字为部首的形声字(如大量以口、宀、山、日、水、火、田、石、禾、糸、月、舟、車、門、阜、雨等为偏旁的汉字),让人既知声又见形,从字形中见到自然万物。教师引导儿童发现这一特点,不仅能让孩子懂得汉字造型的理据,也有利于儿童理解中国传统审美形态中效法天地、崇尚自然的重要思想。
(三)汉字的“神妙”之美
在视觉形象的“形”、“神”关系上,传统美学重“神”而轻“形”。汉字作为诗意的语言系统,本身就是显现事物灵魂的艺术品。它在描摹事物自然形状的同时,更重视对其内在精神本质的勾勒,因此,它超越了形,达到了“离形得似”、“形神兼备”的境界。
例如,“悦”的本字“兑”,缩小简化了人的躯体和四肢,而突出了其上翘的嘴和嘴角的笑纹,将喜悦的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見”字的原始形象忽略了人体的上半身,让人看到的只是行走的两腿上一只张望着的硕大眼睛的形象,突出了人的探索、发现之神情。而“听”字的原始形象更只绘出了一只大耳朵和一张(或两张)说话的嘴。同样,动物字也贯彻了重神的思维,“虎”字突出其威严的身躯和大口,“兔”字突出了其长耳和短尾,而“牛”、“羊”字更加离形得似,造型干脆不绘身躯和四肢,只展现其头部,注意以其兽角的上弯和下弯特征来加以区别。《淮南子·说林训》提出,失败的造型艺术是“谨毛而失貌”,即小心地绘出了细微而无关紧要之处,却忽略了整体特征,也丧失了美感和意蕴。正如颜翔林先生所言:“如果符号形式直接简单地呈现艺术文本的意蕴,两者距离过于靠近,使欣赏者一目了然,就缺乏从容品味的余韵,造成艺术趣味的淡然枯燥;反之,如果符号形式和文本前者意义存在遥远的距离,使人在两者之间寻找不到任何逻辑联系,滋生不知所云的淡漠感觉,也是失败的艺术创造。”[7]历史上许多象形文字系统,因过于求形似而繁复、僵化,最终都被废弃。而拼音文字的符号和意义无任何理据联系,难以产生美感。只有汉字象形而离形、重神,其生命活力与美感保持至今。
苏轼有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这恰好说明了儿童在审美认知中重形似的局限性。席勒说:“一切的关键在于把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必然不沾染任何偶然。”[8]67笔者认为,汉字的重“神”,就是一种发现必然,不为偶然所拘束的表现。抽象思维是儿童缺乏的能力,所以,在汉字习得中为儿童辨析出汉字重“神”的建构思维,能启迪儿童在认识事物中抓住本质特征,破除偶然揭示必然,提高其通过形体展示精神的哲学思辨能力。
(四)汉字的“气韵”之美
“气韵”形态中的“气”指的是一股生命的活力。马大康认为:“如果说,口头语言更直接地归属于感性生命,它原本即生命的呐喊,那么,书写则更多地与理性、逻辑思维联系在一起,并因其媒介的间接性,在开拓了形上思考空间的同时,总难免与感性生命隔着一层。”[9]不过,马先生在张扬口语生命感的同时却忽视了汉字书写建构的生命特征。事实上,在汉字里充满了生命的迹象,呈现着普遍存在的万物生命。成千上万的汉字以艸、禾、木、竹、麦、麻、羽、鳥、隹、牛、羊、豕、馬、鹿、兔、犬、犭、虎、象、魚、豸、虫等象形字为偏旁,因此在阅读汉语时,字里行间处处可见草木鸟兽的感性生命。此外,传统美学的五行相生观和天人合一观,使我们倾向于对风、雷、雨、雪、天、日、月、星、水、火、电、土等自然物、自然元素和自然现象也赋予生命力的想象,认为它们也和人类一样有生命活力和自行主宰并生发化育他物的能力,由此在造字过程中大量以这些形象作为汉字偏旁。这样一来,整个汉字系统就流动着一股生命气息。
刘文典先生曾在教学中特意利用到这一点。据其学生记载:“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10]因此,教师如能在汉字习得中结合相关教育内容启发儿童体会汉字的生命美学意识,将会使儿童的身心和汉字的灵魂一样生气勃勃。
“气韵”的“韵”意味着一种类似于音乐的节奏性和规律性。语言的“韵”之美,首先诉诸于听觉。听觉美是东方语言的特质。卢梭在《音乐辞典》里赞美说,“东方语言如此响亮、如此富于乐感”,[6]309并将这种美归因于音调:“东方的语言……一切效果都表现在音调上。”[6]331汉字发音之美的确很大程度上来自抑扬顿挫的声调。不过,汉语的听觉美不仅仅表现在音调上,它还有更多独特之处。由于汉语长期以来以单个汉字为本位而不以词为本位,故而这里需通过词的层面来展示汉字的声韵之美。我们发现,汉语非常善于运用重叠的手段来造成节奏感。更为重要的是,汉字的音节简单,没有复辅音,使得双声词(如参差)、叠韵词(如从容)等形式易于形成,这样就使重叠不至于单调,使听觉美丰富而富于变化。笔者还认为,节奏是广义的,它主要诉诸听觉,而又不局限于听觉。从字音上看有双声词、叠韵词,而从字形上看我们也发现有双形词(即形旁相同,如络绎、惊慌)。它们造成一种视觉上的节奏感,使人体验到类于声韵的审美通感。更有趣味的是,双声、叠韵词大部分又同时是双形词(如澎湃、招摇),给我们带来一种视听觉双重审美意蕴。卡西尔说得好,语言活动“总是浸润着主体的、人格的生命之整体。言语的节奏和分寸、声调、抑扬、节律,皆为这种人格生命的不可避免的和清楚明白的暗示——都是我们的情感、感受、旨趣的暗示”。[3]138我们正应该好好利用“气韵”这种其他文字所罕有的美学特质,通过文本认读、书写、朗诵等形式,激发儿童的美感和乐感。
二、培养道德情怀,启思伦理自律
(一)汉字的道德培育功能
古代哲学家们高度重视美与伦理道德的联系。如我国儒家美学的“比德说”积极将自然美与道德美加以比附,而古希腊的柏拉图则强烈反对摹仿坏人坏事的戏剧和诗歌。康德则最终做出“美是道德的象征”[11]这一明确论断,深刻地指出审美活动的客观目的就是通过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的实现,将主体引渡到善的境界,从而实现审美和道德的精神合流。
我们发现,汉字的字形里传达着丰富的道德教训。比如“孝”字,从原始字形看,就是一个小孩搀扶或背负着一个头发稀疏的老人走路的形象,生动直接地体现了我国古代的伦理观念。再如“悌”字,意为敬爱兄弟,而字形从心从弟,即指明心怀兄弟为悌。又如“信”,人言为信的会意传达着言谈需要讲究诚信的道德教训。“崇高”的美学范畴源自西方,而在古代汉语里,则有“大、崇、巍巍、荡荡、汤汤、浩然”等概念与之大体相当。这里就充分反映出儒家“比德说”的审美思维了:“大”字让我们从人体的巨大去联想人格的伟大,“崇、巍”等字,让我们从山岭的巍峨中去体会人格的崇高,而“荡荡、汤汤、浩然”则从水域的巨大广阔里让人领悟崇高不可抗拒的力量。
当前的美育常常忽略了美与伦理道德的沟通,把美育简单地等同于形式美的教育。而童年正是一个人形成道德观念的最重要时期,如果教师能在汉字教学中点出其伦理美学意味,则儿童的德育无疑可以自然渗透,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就如席勒所言:“审美趣味对义务有利地调整我们的感性本能,使意志能够以比较轻松的道德努力来履行道德的命令。”[8]250
(二)汉字的伦理启思功能
古代伦理学基本等同于道德、品性之学。从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出发,近代伦理学突破了道德学的藩篱,把伦理学看作研究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的学问。正如伯纳德·威廉姆斯所言,伦理学是研究“我应该怎样生活”的学问。它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类的责任、义务,还更关注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和生活态度、自律规范等问题。对于有着未来人生无限可能性的儿童来说,伦理启思是极为必要的。大量的汉字从字形上就有着伦理的启思,即对“我应该怎样生活”的启思。例如,教师可利用“信”字“人言为信”的含义,启示儿童讲诚信,重口头承诺;可利用“武”字“止戈为武”的造型寓意来教育儿童反对暴力、爱好和平;又可利用“臭”字,启示儿童不可骄傲自大的伦理品行。这对于儿童今后伦理自律能力的形成,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伦理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文精神。在当今技术压倒人文,工具理性侵占精神家园的时代,儿童伦理教育中的人文思想内容尤其显得迫切,而汉字习得恰可助其一臂之力。人文精神思潮来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自身生命、尊严和价值的关切和追求。事实上,近世所谈论的“人体美学”和“身体美学”,就是人文精神在美学领域的显现,而汉字系统里就早已内涵有这种人文思维。汉字处处凸显了人的形象,表现了存在的自我意识,并把这种自身的存在当作最根本的审美观照对象。例如,汉字人旁(包括单人旁亻、双人旁彳,以及女字旁、子字旁)字很多,还常把人体构成部分的形象作为偏旁,如身、肉(包括月)、頁(头的形象)、首、面、手(包括扌、又)、足(包括止)、口、耳、心(包括忄)等等。莱布尼兹甚至认为,几乎大部分汉字的结构都很像人体。
雅斯贝尔斯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12]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汉字正可以启思这种“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在儿童汉字教学中,教师要能认识到这种汉字建构中的道德象征与人文内涵,在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经济、科技,道德水准滑坡,物质欲望膨胀而生命内涵遭到压抑的今天,这种教育将十分必要。
三、促进创造性思维,激发想象能力
(一)汉字建构与创造能力
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我国儿童最缺乏,也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汉字的审美建构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能力。
首先谈创造性思维。汉字习得,除了音义的掌握而外,还包括字形的辨识和书写。不难发现,拼音文字书写较为简单。以英文为例,只要掌握了26个字母的写法,书写习得即告成功。而汉字书写却远非如此,它是一个从儿童开始却近乎需要用一生去习得与提高的技艺。为何会有这样的特点呢?这是由汉字的形体结构决定的。
前文提到,汉字结构有中和之美,书写讲究秩序和规范。但同时,又可以有间架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和创造,给个人书写的创造性留下巨大的空间。正如李运富所言:“汉字的笔画和构件摆布在两维平面的方块内,每个字的空间相同,整齐,……便于匠心布局和变异书写,从而具有艺术审美价值。”[13]这种在规范与限制中的自由发挥余地,乃是书法艺术所得以产生的原因。它使书写能够承载和涵括丰富的个人风格,使得“字如其人”成为可能。在书写教学中,教师若能点出这一层面,让儿童的个性在书写结构和布局上适当有所发挥,可以培养他们的美学创造能力,避免千人一面的印刷字体和僵化思维。
(二)汉字意象与想象能力
汉字习得能养成儿童运用想象力的习惯。这是因为,汉字系统充满审美意象,而审美意象的生成需要想象力的发挥。
审美意象必然要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和哲理性,而这些都是汉字形体所具备的。M·V·大卫在1636年就指出,象形文字“是更优美更庄重的书写符号,比较接近抽象的东西。它们通过对符号或相当于符号的东西的巧妙结合,而将复杂的推理、严肃的概念或隐藏在自然或上帝心中的某种神秘徽章一下子展现在学者的理智面前。”[6]118这一论断用来诠释汉字的审美意象性极为恰当。汉字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庄义友认为:“汉字本质上是一套象征性符号系统。”[14]例如“尹”字,用手执权杖的形象来象征管理百姓的权力。又如“義”字(“义”的本字),用羊头挂在长柄的三叉武器上面,象征皇帝或贵族的威仪。黑格尔说:“真正的象征本身就带有谜语的性质,……(谜语)属于有意识的象征。”[15]谜语式的求解性是汉字的独特魅力。很多汉字看起来就像谜语,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猜测。例如“彳亍”一词甚为怪异,有人通过它和“行”字字形的关系来推测其义。而如“灭、忍、攀”等字,不少教师也常在教学中发挥想象力,从字形上为儿童做出拆分式解读。同时,汉字字形本身还表达着一定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也早就得到了国外学者的承认,莱布尼兹就指出汉字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如“鲁”字,本义是“美好”,它用嘴里吃到鱼的美味的形象传达了这样的艺术哲学观念:美首先是物质的感性存在,与人的感官享受不可分离。再如“福”字,是双手捧着大酒坛在祭台前求神赐福的形象,它表现了这样的人类信仰:幸福来自上天的赐予。
获取汉字的意象之美需要想象力。康德早就界定说,审美意象是指想象力所形成的某种形象呈现。其后黑格尔断言:“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性的。”[16]而萨特更主张用想象来界定美的本质。他说:“美是一种只适合于想象的东西的价值。”[17]292又说“审美的对象是某种非现实的东西”,“我所称之为美的,正是那些非现实对象的具象化”。[17]285-287即美不是客观实体,而是通过想象力产生的审美意象。
意象并非实在形象,而存在于想象之中。只有发挥想象才能领略汉字的意象之美。现代儿童教育学认为,儿童精神的感性成分占绝对优势,而感性精神成分是审美的、幻想的、直觉的、感悟的、模糊的、冲动的、热情的。故而,好的教师应当利用汉字的哲理性和象征性,积极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达到美育的效果。
四、结 论
我国当前教育界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善于发现教学内容的美,开掘出这些美,并在教学中显现这些美,在此基础上来创造美。”[18]对于儿童来说,发现适合教学内容的美并以此构思美育教学尤其是教师需要思索的问题。象形基础上的音义结合的汉字系统,是按照汉民族审美心理来建造的恢弘的艺术体系。美国诗人庞德曾感叹说: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的是诗的,相反,一大行的英语字却不易成为诗。诚然,形简意丰、中正平和、蕴涵生命、流动韵律、培育道德、启思人文、便于创造、激发想象的汉字系统,是一种充满诗意的高级审美形态。因此,汉字习得是从感性层面上接受美育的最佳途径之一。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将在认字中逐步开始生活于语言文字的符号世界。因此,要抓住汉字习得的机会,让儿童们感受美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接受美育。要让他们的诗性逻辑在汉字习得中获得养料,以期为儿童未来理性的发展插上审美与想象的翅膀。
因此,本文热烈呼吁,将儿童时期的汉字习得作为全新的美育道路。“童年不仅是人的根基,而且是人的核心。如同树木一样,那最初的年月被记录在年轮中最核心处,尽管它已被后来的岁月所包围,但那最初的年月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童年,就是人这棵树最中心的年轮,它是人这棵树的树心,仍然在默默地滋养人这棵树木。”[19]教师要善于开动脑筋,发现汉字系统的审美特质。在人的一生的核心阶段——儿童时期——这段可塑性极强的头脑中,构建审美形态,启迪他们的审美意识;培养其道德情怀,启思其伦理自律;促进其创造性思维,激发其想象能力;让儿童精神从一开始就得到最健康完美的滋养。
[1]丁海东,杜传坤.儿童教育的人文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26.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
[3]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4]袁锐锷,张季娟.外国教育史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65.
[5]史文霞.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与语言的简约美[J].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8(2):85-86.
[6]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7]颜翔林.怀疑论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63.
[8]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9]马大康.诗性语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4.
[10]励志.国学大师刘文典师[J].中国人才,2010(17):45.
[11]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01.
[12]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3.
[13]李运富.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6.
[14]庄义友.汉字符号象征性探解[J].语文研究,2000(1):23.
[1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57.
[16]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0.
[17]萨特.想象心理学[M].褚朔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18]周施清编.小学美育化教学与儿童创造性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24.
[19]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