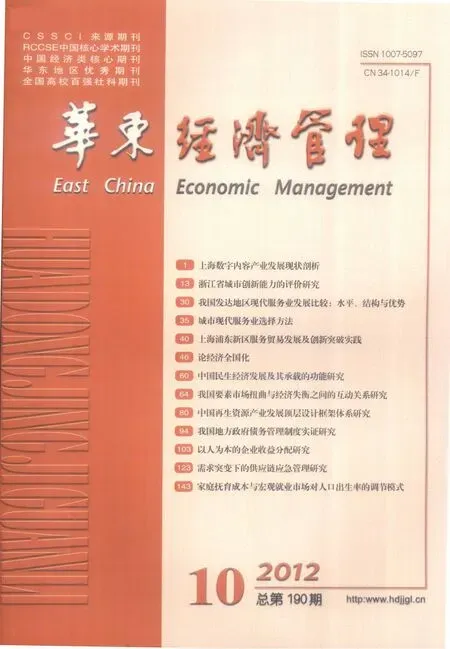家庭抚育成本与宏观就业市场对人口出生率的调节模式
李 哲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江苏 扬州 250007)
一、研究意义和背景
针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因素进行辨识和测定,即可以服务于劳动力供给的长期预测研究,也是优化和落实国家生育政策的基础。当前,我国要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关键在于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并将其维持低位均衡。我国自1972年进入出生率转变阶段(该年出生率降至30‰以下),人口出生率剧烈上升势头得到遏制,且这项关乎国策的重要指标变动总趋势是不断下降的。我国的1988年人口出生率甚至呈现出了下降趋势,与之具有天然联系的生育率也接近了更替水平。
研究背景在于,西方学者关于人口出生率和宏观经济的互动理论在过去不久的十一五期间掀起的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很好地补充了对计划生育政策作用效果的研究。该年波及广泛的金融危机诱发国内经济环境的暂时性转变,随之相伴的还有人口出生率的反弹式上升,这种趋势有逆于既有的人口转变过程,关涉到国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迫切需要利用科学的数理手段,取简去繁地获取未来出生率变动的判断途径,辨识主要因素,并预估其对人口出生率的长期影响效应。从经济逻辑上看,随着我国的巨大经济飞跃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我国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促使老龄保障、社会保障等制度日趋完善,从而弱化了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考虑到生命周期以及需求无限性的特征,确保新出生婴儿的生存需要必须被作为基本需求,这种不可或缺的低层次需要包括吃、穿、住、行等等。由于衣、食、住、行的成品来自于父母劳动所提供的资源。所以,只有当父母对婴孩的物品供给处于安全阀内,才能保障家庭后代获取有效的生存性物品。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上对如上逻辑和事实加以归纳,并将人口出生率归结于经济景气度与现代化进程的双重作用,把人口转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如经过兰德里和诺特斯坦等发展、完善形成的“人口转变调试理论”,其表达的核心观点即人口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互动。
理论意义在于,要探究人口出生率波动的经济因素,则要在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外,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和抚育费用等序列的时间变化,以及它们与中国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单向作用和影响程度。在当代中国,除了政策规范和生育观念的影响,经济水平是引起人口出生率降低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生育国策构建后的前一阶段中,经济发展促使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有助于缓解我国人口压力过大的问题。在后一阶段里,社会保障的完善和育子功能的变化,昭示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即将演变为一种趋势。若出生率长期持续负增长,则有可能促使我国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匮乏。由此导致的人口红利丧失将制约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其关联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将由之显现出来。
二、文献回顾和述评
本文旨在从经济学的“效用-成本”角度考察出生率短暂回升的背后原因。父母为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会在生活质量和孩子数量之间考虑优化配置方法[1]。处在法定婚龄期的男性和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几近全部属于适龄劳动力人口,使得抚育能力、抚育成本与社会人口出生率保持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既有的文献仅表明,在人口转变进程中,法定婚龄期人口或适龄劳动力“生儿育女”的传统意愿会逐渐弱化源于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对自身发展的需求。但金融危机期间及其过后的数年内,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短暂的回升,则可能由于实际抚养成本的升高而减少了家庭对于子女的预期收入。以往的生育研究已经显示,在现代化进程和家庭人均收入上升的同时,不断提高的即有生育成本、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即Leibenstein提出的“抚育资源成本”,如生活费用、教育费用等;也有间接成本,即Leibenstein提出的“时间-劳动力成本”,如父母为抚养孩子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Leibenstein,1957)[2]。然而,不断降低的有孩子的预期经济效用、保险效用[3]。此外,上学难、上学贵、就医难、高房价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使得“少生”成为一种理性行为。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出生数量取决于处于结婚年龄和具有生育能力的成年个体,成年人的实际收入会影响生育数量。马尔萨斯研究了人口出生数量的两种控制方法,一种是以“道德控制”为标示的主动控制;另一种是以“非理智控制”未标示的被动控制。达尔文对于人类生育率的自然选择论也是基于马尔萨斯的理论,优胜劣汰的另外一重含义即是有能力者多生。这种能者多生的观点同样蕴含着“成本-效用”论的某种意义。斯宾格勒正式提出了影响家庭规模的“成本一效用”理论,用成本与效用分析家庭人口的最优规模。贝克尔将经济学引入家庭及其生育领域,他考察了影响成年人生育偏好和实际选择的若干因素,认为子女是一种消费品和生产品的有机集合。家庭中子女的出现不但能够满足父母心理需求,还可以提供货币支持,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家庭效用”。其中,贝克尔特别强调货币支持对于父母养老的作用。
模型构建的机理在于:经济效用取决于家庭偏好,而家庭偏好又受限于社会和经济因素,即收入、物价、信仰、种族、年龄等因素[4-6]。特别是受家庭收入、扶养成本及子女提供的。抚养子女带来收入增加和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家庭对子女的需求,如果孩子干家务或在市场上劳动,则必将贡献于家庭收入,即生育孩子增加了家庭的整体收入潜力,减少了后期抚养净成本的总量。也就是说,子女效用的不断增加和扶养成本的不断降低会刺激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表示,除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之外,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造成人口粗出生率下降的更为重要的推动力。家庭对孩子由数量需求转变为质量需求,这意味着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大大提升。他所估算的从孕产期到孩子结婚之间,父母所投入的成本约需要49万元,进而得出结论“不是育龄人口不想要,而是因为他们养不起”[7]。
综上,可以用家庭偏好表示追求子女提供的经济效用最大化,同时假设家庭根据相关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子女数量。即可以利用贝克尔的相关约束理论,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分别分析了家庭生育的偏好以及对于质量和数量的选择[6]。古典经济学派的若干代表(Malthus等)进行家庭收入无增长的模型中,给定的核心假设也为人口的增长源自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虽然当代的人口增长理论着重于研究“人均收入得以持续增长”的现代经济。该理论的核心假设为控制技术发展的作用,人口增长是外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影响人口增长,但是马尔萨斯指出了关于经济发展对于人口出生率的间接影响路径,很好地契合了如今经济危机过后的出生率波动特征,即全社会规模不变(或递增)的发展水平能够导致家庭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故而经济环境和家庭效用理论可以对当今社会生育动机及行为选择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经济增长影响十二五期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采集及时序平稳性检验
此处采用的出生率及宏观经济指标分别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与历次人口普查(含人口抽样调查)原始资料。
为构建粗出生率和抚育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着重保证了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具备平稳性。平稳序列围绕均值上下波动,并具备向平均数收敛的趋势,避免了非平稳数据可能致使的统计推断失效和模型结论偏误。
为了检验解释变量是否稳定,此处采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中的ADF方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首先,分别在水平状态和多阶差分下对时间序列数据做反复的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原检验H0设为:序列中含有单位根。经尝试所选的水平状态下原检验未遭拒绝,却于一阶差分之后接受了备择假设,故而认定其服从一阶单整过程I(1),即序列中有且仅存在一个单位根。再次,检验回归中是否仅具有截距项或兼具趋势与截距。本文应用了ADF的单边检验,即查验滞后因变量的t统计量,发现其小于临界值,故而拒绝原假设,否定单位根的存在。
本文对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CBR)、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就业比例(EMP)和职工工资指数(PAY)四列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表明,原水平序列CBR的ADF检验值大于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存在明显的单位根,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序列表现出非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序列ΔCBR的值小于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表现出平稳的特性,即一阶差分序列服从一阶单整过程,即I(1),变量之间符合协整关系的条件。

表1 模型中各变量的ADF 平稳性检验结果
(二)变量说明和假设前提
利用所选指标构建转移函数模型,对出生率的年度数据进行回顾拟合和前瞻性预测。首先,从定义回归模型中的变量入手,设定三个解释变量,分别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职工工资指数PAY、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EMP;然后,检查模型的残差并且对之用ARIMA模型进行拟合;最后,对回归—时间序列组合模型(转移函数模型)的所有参数进行同时估计。其中,对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步骤如下:
变量CBR(人口出生率或粗出生率)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数的比率,计量单位选为千分率,即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其中,出生人数指活产的胎儿数,而此处的年平均人数为年初和年末人口的算术平均,而变量CPI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在模型中,用于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的儿女抚育成本的影响程度。变量EMP(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获得采用如下公式计算: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经济活动人口/总人口数)×1000‰。变量PAY表示职工工资指数,指某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得报酬的总额与此地区人口总数的比值,以“元/人”为度量单位。以上一年为报告期,计算公式为:职工工资指数=(本年工资总额-上年工资总额)/上年工资总额×1000‰。
转移函数模型构建的假设条件为:人口出生率与解释变量间的关系为线性关系,解释变量之间是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建立的模型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出生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职工工资指数等,其他因素归入随机干扰项。
(三)转移函数的模型构建及估计检验
本文选取了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模型样本,从人口出生率的回归模型开始。将历年活产婴儿数与同期总人口的生存人年数之比作为该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千分比表示为CBR。
变量CBR是非平稳的,但它的对数序列是平稳的。由CBR的时间序列可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转变被划分为几个阶段:1970年之前的高出生率阶段、1970年代的下降阶段、80年代的波动阶段和80年代以来的低出生率阶段。下降过程可进一步细分为: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转变,人口出生率由高水平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90年代的第二次转变,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8]。
本文希望对回归模型进行拓展和变形,即构建转移函数模型来模拟和预测我国人口出生率。为探究基本模式,须利用1978年至2010年的数据对该方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散点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初步发现出生率与CPI、就业水平、工资指数存在弱线性关系。

图1 人口出生率与其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对选取的三个经济类解释变量中进行Frisch逐步回归,发现解释变量PAY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具有共线性,舍去PAY后能够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则设序列:

附加误差项反映了不可解释的变差,即消费指数和就业水平之外的作用于出生率的影响因素,比如少年人抚养比、教育程度等等。最小二乘法的结果如下,其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对应参数估计的t值。


图2 传统逐步回归模型:出生率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
图2反映了结构回归模型(2)式中人口出生率的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正如我们预料,经济活动人口比重与出生率增长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该指标可以作为父母抚育子女的时间替代品,代表了育龄夫妻对于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反馈。因而,该变量应该对人口人口出生率有反向影响。然而在公式中,物价指数与出生率增长水平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与现实不符[9]。因为,物价水平直接影响抚养成本,是育龄夫妻不得不考虑的经济要素。
注意到,图2中的残差呈现出高度的正自相关,也反映于上式中较小的杜宾-瓦尔森统计量。残差序列的一个来源应是附加的噪声项,而噪声项的未来变动难以预测。虽然,对残差存在的一阶自相关进行广义差分校正可以显著地改进预测效果,但是原回归模型对整体的拟合较合理,只是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拟合效果较差。我们在下文将采用转移函数模型进行修正。

图3 回归残差:样本自相关函数与偏相关函数
图3显示,残差的样本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前者稳定趋于零,证明了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图4显示,一次差分后的残差样本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系数,其所有的自相关系数接近于0。然而,通过反复试验,我们仍先对无差分残差序列建立模型,然后将原回归方程的误差项用ARIMA模型代替。在使用该方程预测CBR时,也可以得到误差项ut的一个预测,借以反映回归方程中的经济解释变量所无法解释的那部分变差。

图4 回归残差的一次差分:样本自相关函数与偏相关函数
经过模型调试可以得到的残差序列Residual(ut)的转移函数模型形式是ARIMA(8,0,1),估计结果如下:

可知自由度为32-9-1=22,而q统计量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故不拒绝ARIMA模型的残差为白噪声的原假设。
从精确地角度来审视,虽然如上ARIMA残差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考虑到无法同时估计所有参数将导致精确度的降低,需要采用转移函数模型进行多元自回归——移动平均的结合,即同时估计回归-时间序列组合模型所有参数。该转移模型由三部分构成:出生率及其滞后项,原有的两个解释变量和可以实践序列模型部分地解释的误差项。将其一般形式设定为:

其中,多项式v(B)、ω(B)为需要确认的模型结构部分;多项式φ(B)、θ(B)为需要确认的时间序列部分,估计下列具体模型的参数:
可以发现,经过变形的转移函数模型的R2较优且D.W.非常接近于2,该方程拟合前期的残差样本自相关系数接近于0,倾向为白噪声模式。

图5 转移函数模型效果: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
图5显示,截止到2010年样本期的拟合值、实际出生率以及残差序列。残差序列在0附近形成无规则波动,且在样本期后端趋于稳定。图6显示,(偏)自相关系数未现明显的周期式跃高,表明残存的时间周期模式经模型转换已消除。

图6 转移函数模型残差效果:样本自相关函数与偏相关函数
(四)利用转移函数模型进行模拟和动态预测
将样本期数据构建的转移函数模型分别应用于长期和中期两个时间段的延展模拟和动态预测,图7显示了1986-2012年间的27年出生率模拟和预测结果(该预测的前23年为事后模拟,后4年为动态预测期),由希尔不等系数的三项构成的分配比重可知,模拟值在总体上与实际值很接近。
四、模型结论和讨论
研究出生率的作用要素对于理解和贯彻国家十二五期间的生育政策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10]。本文就改革开放后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期构建了转移函数,以对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进行甄别和测定,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事后模拟与动态预测,得到以下结论:

图7 转移函数模型:人口出生率的中长期动态模拟与预测
(一)就业水平、物价水平为人口出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虽然就业水平、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都影响着人口出生率的高低,但由于消费指数和工资指数之间的共线性,工资对于出生率的影响被削弱。就业水平、物价水平为人口出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化的突飞猛进促进了生育偏好及其行为的革命性调整,在那些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比较高、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比较多的地区,生育率和生产、生活、交往的货币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经济、文化、功能三个维度或者三个变量中,经济约束条件和经济变量是最主要的变量,解释能力最强。故而经济效用模型比文化概念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金融危机前后的出生率波动。
(二)家庭保障的预期效用逐渐弱化,引致“少生晚生”的理性行为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上升1单位时,人口出生率将降低0.0158单位,即是说抚育子女成本越高的时段,夫妻生育愿望越低下。在家庭人均收入上升的同时,生育成本,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养子弃工”的机会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在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和国家计生工作的双重控制下,抚养成本中的教育投资也随之高企。育龄夫妻工资面对的就业市场景气程度和物价水平都影响后代的资源投入,特别是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减速程度增加虽然诱致了夫妻生育时间的增多和生育意愿的增加,但并不必然导致人口转型的终止,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取决于经济发展对生存条件的改善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使“少生晚生”成为理性行为。
(三)业余时间多少和工作压力大小影响着出生率变动
模型显示,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每增加1单位,出生率将降低4.6017单位。出生率变动依赖当地人的业余时间和工作压力,工作节奏越快的地区,出生率越低。首先,我国存在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特征为工作不稳定,收入水平低,其经历理性博弈后的选择常为推迟结婚或晚婚晚育。其次,作为生育孩子的载体,职业妇女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生活节奏加快,结婚年龄普遍推迟。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达地区的高龄妇女队列生育的大幅减少,原因在于女性广泛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从而大幅推迟生育年龄,导致该时段生育数量显著减少。因此,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地区应该放在那些就业率相对较低的地区。
(四)人口基数的扩增潜在地抑制着人口出生率
构建过程中,发现人口出生率呈现出最佳滞后阶数大于或等于8,移动平均阶数为2的序列。说明前期的中国人口基数得到了扩增,潜在地抑制了人口出生率,普通家庭对孩子由数量需求转变为质量需求。进一步地,有经济学常识可知,在经济发展在经久的高增长态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将呈现下滑态势,进而诱发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同时,在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将会加重养老负担。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消极影响的滞后作用,人们的就业机会预期下降,工作替代成本减少,致使生育意愿有所上升。综观模型结果的内在涵义,在我国经济启暖的初期,即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初期,出现的人口出生率的短暂抬升并不会长久持续。面对经济环境和家庭抚育成本给计划生育国策造成的内在影响,需要政府机构重新审视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配以相应的统筹调整,防止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社会人口环境。
[1]Bongaarts,John,Susan CottsWatkins.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emporary Fertility Transitions[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Review,1996,22(4):639-682.
[2]Leibenstein H M.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J].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1957,89(1):1-31.
[3]Martin 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1999,(3):99-107.
[4]Zhang Junsen.The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on Population and Output Growth[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5,(1):440-450.
[5]徐达.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模型与实证[J].财经科学,2012,(4):15-23.
[6]蒋正华,陈松宝.中国生育率变化及人口发展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1985,(10):2-8.
[7]穆光宗.超低生育率阶段的区域人口发展战略[J].人口学刊,2008,(6):3-9.
[8]尹文耀,钱明亮.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35-45.
[9]陈卫.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J].人口学刊,2009,(3):3-8.
[10]查瑞传.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