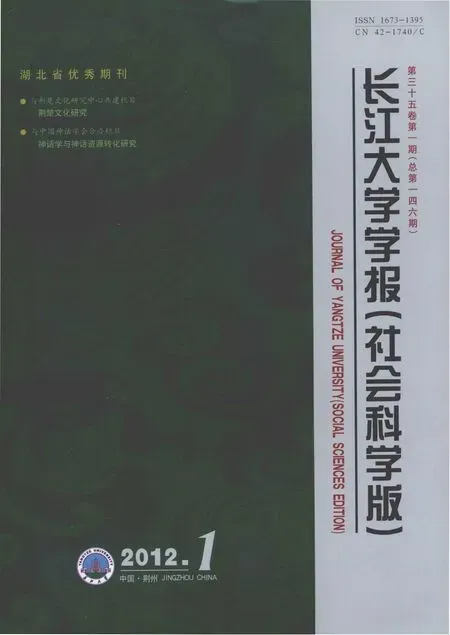中国诗学与诗道
刘 勉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中国诗学与诗道
刘 勉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中国诗学应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诗道概念为核心。中国诗学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是人有我精、玄妙神奇的风格诗学。
中国诗学;诗道;道家哲学;本体建构;风格诗学
诗学概念,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涵义是多种多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如下几种。第一,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的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1](P2)第二,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我的‘诗学’概念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即有关诗歌的学问。……‘诗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诗学’是Poetics的译名,意味着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狭义的‘诗学’是中国固有名词,即诗歌理论。”[2](P10)第三,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诗学)是用来指称诗歌创作实践体系的一个高度概括的术语,当然也包括由这个实践体系所引出的诗歌理论和批评。……其主要的承载体是实际的诗歌创作,而非纯粹的理论和批评。现代‘诗学’,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其主要性质是作为一种学科存在,这是其与传统诗学最大的差别所在。”[3](P278~280)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蒋、钱二位的意见是值得听取的。蒋寅强调文类学立场及其理论品质,钱志熙则强调实践性特征,边界都比较清楚,但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这就比较符合中国诗学的实际情况;从比较诗学研究出发,文类学基础及其理论品质与实践性特征相结合也能够充分地显出中国诗学的文化特性。如果以这样一种眼光从事中西诗学的比较,无疑比以西方传统的诗学概念(文艺学或文学理论)为基准来展开比较研究更富有建设性。
诚如钱志熙所言,中国传统语汇中的“诗学”一词自唐代就产生了,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实践性内涵,在他所举的两个语例中①晚唐郑谷《中年》诗:“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晚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商隐字义山,诗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第265页),“诗学”一语是指关于诗的涵养功夫和操作能力,并不表现为理性知识。可是,过分强调主体实践性特征,诗学经验便似无从认识、总结、交流,也无法参与理论形态的概念、命题之比较研究。好在宋代以后便有了不少径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如《宋史·艺文志》著录范处义《诗学》一卷及《毛郑诗学》十卷,金元之际元好问著《杜诗学》一卷,元代范德机撰《诗学禁脔》,明代周叙等编《诗学梯航》一卷,宋孟清编《诗学体要类编》三卷,《清史稿》则著录有钱澄之撰《田间诗学》十二卷,陆奎勋撰《陆堂诗学》十二卷,徐时栋撰《山中诗学记》五卷,顾广誉撰《诗学详说》三十卷,汪师韩撰《诗学纂闻》一卷。值得注意的是,范德机所撰《诗学禁脔》又称为《诗格》,依此例,唐代诸多《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作均或可称之为《诗学》,也就是说在“诗学”一词产生的时候,诗学著作也出现了。上述著作的性质,有的属《诗经》之学,有的属诗法之学,不管属于哪一类,起码具备了知识的形态。但是如果从思理绵密和理论品质方面看,这些著作似不能与亚氏《诗学》相提并论,所以朱光潜在1942年《诗论·序》中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就是从这一点立论的。朱先生曾钟情于《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和逻辑严密,但同时又认为其中所讨论的问题超出了诗的范围,似乎不便算作诗学。
朱先生当时并未考究中国“诗学”一语的名义,他对诗话之诗学性质的否定主要是诗话过于“零乱琐碎,不成系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的缘故。[4](P3)显然,朱先生能够抛开单纯的“正名”思维,从理论品质方面看问题,但同时他又受限于西方传统的科学逻辑的思维模式,从而忽略了诗话中“片言中肯”的诗学命题及其理论价值。朱光潜心中的诗学观念显然包括文类基础、理论品质和系统逻辑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正是在最后一点上,他否定了中国诗学的存在。
以西例中,自然不易丝丝入扣,但中国古有诗学却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古之诗学与今之诗学,西方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是否应该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换一种说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中国传统诗学的知识形态、存在方式和民族特征。
一、中国诗学的名与实
中国传统的“诗学”一语,大致有三种涵义。第一,从汉代经学中分化出来的《诗经》之学,如范处义《诗学》,《毛郑诗学》,钱澄之《田间诗学》,陆奎勋《陆堂诗学》,徐时栋《山中诗学记》,顾广誉《诗学详说》均属此意。目前国内学者一般都不认为此类著述属于诗学范畴,可是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一本论著中却肯定地认为,作为经学文献之一的《诗大序》就是古代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原创性的诗学著作。[5](P18)第二,供童蒙入门的诗法之学,如范德机《诗学禁脔》,周叙等《诗学梯航》,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汪师韩《诗学纂闻》即用此意。这类著作入不了大多数学者的法眼,往往被认为是三家村夫子之言,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透过看似粗浅、琐屑的格、式、法、术等程式化的准则、规范,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诗学义理。第三,指诗家独得妙悟的心法功夫,即庄子所谓不可言论,只可意致的“物之精”,亦即《白石诗说》“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的涵养之学。此意用例不见于著述名目,只是在诗人非理论话语中有所体现,如郑谷《中年》诗:“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宋宜《分类集注杜工部诗·序》:“陈君可谓笃于诗学者矣。”《清史稿·庞垲传》:“垲嗜吟咏,与同里边汝元以诗学相劘切。”上述三义,前两项中有部分命题探讨诗歌的义理、功用、方法,与西方诗学讨论的某些问题比较接近,第三项大体指诗歌创作不可言说的心法妙谛,属于对诗歌本体(本质)的最亲切的实践性把握,如果从学理逻辑上看,这些偏重内心体验的内容是不能称之为“学”的。
但是,就是这不能称之为“学”的“诗学”,却是中国诗学的命脉所在,最能体现中国诗学“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根本特征。不过能真正表达这一涵义的理论术语通常不是“诗学”,而是“诗道”。“学”的概念与“道”的概念在古代哲学中显然不属于同一层次,《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因此,与“诗学”相比,“诗道”概念显然更具有形而上的理论品质和涵盖特性,作为一种实践修为功夫的“诗学”实际上只是诗人主体对“诗道”的涵养和把握,而“诗道”才是真正关于诗歌本体、规律的理论思考和概念表述。中国诗学体系的成立和展开就是建立在“诗道”概念基础上的。
最初提出“诗之道”概念的是东汉郑玄的《诗谱叙》:“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始)于此乎?”郑玄视《虞书》“诗言志”诸语为“诗道”的初创,与朱自清先生“开山纲领”之说同一机杼。
“诗道”一词也屡屡出现在唐代,孔颖达《毛诗注疏·关雎正义》:
诗之所陈,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诗之道则兴,幽、厉不用诗道则废。
又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语:
诗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诗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诚,精诚之至,以类相感。
指出“诗之道”实现的基础是“精诚之至,以类相感”,这后一句话明显是源于庄子“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孔氏所谓“诗道”,大体上还属于儒家诗学范畴,其意旨不外兴、观、群、怨,比较注重诗歌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干预和教化作用,但由于融合了庄子的某些思想,将孔门传统的功能论建立在道家思想的道性论基础之上,使儒家社会学的诗学观念,带上了道家形上哲学的色彩,显示出传统诗学观念潜流暗转的新趋向。①准确地说,在诗学理论中融合儒、道,并不自孔颖达始,此处只是就“诗道”概念的分析立论。中唐以后,“诗道”概念更多地涉及创作、批评理论,如刘禹锡《董氏武陵集序》: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
在刘禹锡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工于诗”指实践能力,“达于诗”指理性认识,“二者还相为用”则正是“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变相说法。实践能力与理性认识相互为用,方能真正体现“诗道”。稍后的韩偓,在《春阴独酌寄同年虞部李郎中》说:“诗道揣量疑可进,宦情刓缺转无多。”指出“诗道”的精进乃“揣量”使然,这就为后来严羽的“妙悟”说开了先河。
宋代以后“诗道”概念广泛为诗论家所使用,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刘克庄《敖茂才论诗》:
诗道不胜玄,难于问性天。莫求邻媪诵,姑付后儒笺。至质翻如俚,尤癯始似仟。吾非肝肺异,老得子同然。
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
世之言诗者,好大好高,好奇好异,此世俗之魔见,非诗道之正传也。体物著情,寄怀感兴,诗之为用,如此已矣。是故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二言足以尽诗道矣。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
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
叶燮《原诗·内篇》:
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其道在于善变化。变化岂易语哉!……夫惟神,乃能变化。
刘熙载《艺概·叙》:
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
从上面征引的文献看,“诗道”概念统率下的诸多命题,有涉及到诗歌创作论的,有涉及到诗歌本体论的,有涉及到诗歌功能论的,有涉及到诗歌风格论的,有涉及到诗歌流变论的,其中对本体和规律性的关注探讨,完全摆脱了对单纯的格、法、式等方面的热情,显示出对诗歌“进乎技”的形上义理的追求。这一部分内容散见在各种著述中,但细察却不无脉理,若综合起来,完全符合现代学科意义的诗学概念。因此,考察中国传统诗学之有无,辨析其理论品质的高下,不能仅仅停留在“诗学”一语的涵义上,也不能停留在有关著述中的知识排列是否具有缜密的逻辑上。
二、诗道成立的哲学基础
毋庸讳言,论及传统中国哲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哲学,比起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具有更为深刻而且深远的创生意义。原因很简单,儒家学说只是一种社会伦理思想,一种实践精神,不是一种通观天人的思辨哲学,缺乏哲学应有的深刻品质,不能统摄世间万物,也不可能对世间万物做出深刻而圆满的说明。《论语·公冶长》中子贡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儒家学说的思维偏向和哲学局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儒家学说显然是在回避对人性的分析和对形上问题的回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孔子的一番感叹,更可以形象地说明儒、道学说的分野:“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学说停留在可罔、可纶、可矰的现象世界、知性世界,而老子道的哲学是龙,优游于天地之间,不可罔,不可纶,不可矰,其卓越的形上品质决定了它明白四达的穿透力量和涵盖能力。它不受可知世界一事一物一理的限制,能够做到无知,但它在超越知的同时又执着于对天地根的追寻,对常道的终极之知。老子对常道的关注,使他能够更加真切地了解万事万物的始初状态及其存在依据,获得对包括人类文明在内的一切文化现象的透彻认识。①《老子》第二十一章:“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学界一直有一种错觉,以为老子不如孔子关注人类文明,对人文现象多持否定态度,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对传统文化艺术观念的建树和影响远不及儒家思想大而远。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在整个诸子时代,所谓人文,其范围不外包括周公建立的礼乐人文制度及其观念,以及作为这种制度、观念记载和表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在《道德经》中曾对作为人文观念和实践方法的圣智、仁义、巧利等做过深入的剖析: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王弼解释说:“圣智,才之善也,仁义,行(“行”原作“人”,据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改)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在老子看来,圣智、仁义、巧利三者作为“文”的表现,有着重大的先天缺陷,这种先天缺陷就是无所属,也就是说缺乏本体论依据。在《老子》第18章中,他对作为有周以来人文标志的仁义、智慧等做了更为彻底的否定:“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指出仁义、智慧是大道本体缺失的产物。老子对人文的关怀是一种终极关怀,他所提出的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秩序重建原则,究其实质,就是要解决人文本体依据的缺失问题。“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看似采取了一种颠覆的态度,实际上却是对病态文明的根基的修复,其中充满了极大的爱的热忱。
在《庄子·天运》中,还记录了老子与孔子的一次交谈,第一次涉及到老子对六经的具体看法: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老子十分尖锐地指出,作为人文记录和表现的六经只是“迹”,只是文明的外在表象,而不是“所以迹”,不是文明成立的内在依据;孔子误以“迹”为“道”,并没有把握人文的本体依据,所以老子不无揶揄地说:“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孔子关于文学艺术的看法多体现在对《诗》、《乐》的具体评价中,所以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国诗学的大源在儒不在道,或者儒为主道为辅,或者中国的艺术精神至庄子方才确立。老子关于六经为“迹”而非“所以迹”的评价,实际上也包括了他对《诗》、《乐》的根本看法。六经皆“迹”而非“所以迹”,不仅直接导出了后代六经皆史的史学命题,还开启了后代诗学中的通变论,而老子对人文本体的追寻,也使得以宗经为重要思想的刘勰必须首先考虑原道的基本命意,才能求得对文的本体依据的终极阐明。
老子关于人文本体的追寻思路,在先秦时期就为诸子所继承。孔子关于“绘事后素”的意见,似乎可以看出老子“见素抱朴”以有所属思想的一些影子;子夏“礼后乎”的感悟,则分明让人想起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深刻见解。稍后主张非乐的墨子,与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老子似乎更多一些因缘,虽然他们各自立论的根据有所不同。墨子在《非命》中对言谈、文学之道有过一段颇为深刻的说明: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柰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他所制定的“三法”,先本原而后功用,因本原而明作用,显示出对言谈、文学本体的高度重视,后来刘勰《原道》、《征圣》、《宗经》中的主要思想似乎就是从此发端。
老子哲学中的人道思想仍与他的天道本体论有关,“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不过他所谓的“圣人”,即同于道者或善为道者,主要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国家治道,属于政治生活层面中的人。而庄子笔下的“至人”、“神人”、“圣人”已经转向个人的精神生活,逍遥、齐物、养生,“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德充符》),“将磅礴万物以为一”(《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老子强调人对道、自然的取法,客观上人还是外在于道,外在于自然的,庄子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为人可以“物化”,可以“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的观点,肯定了“道”在人的精神领域中的现实存在,即个人精神可以有“外天下”、“外物”、“外生死”的独立价值。庄子多次强调“游心”:
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人世间》)
游心于德之和。(《德充符》)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
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
游心于无穷。(《则阳》)
将作为宇宙本体的“天道”落实在“心”中,在汗漫无待的逍遥之“游”中,完成“道”与“心”的合一,从而创出独具特色的心道本体论或人格本体论①李泽厚将此概括为“人格本体论”,我觉得“心道本体论”更为合适,故两存。李说参见其《漫述庄禅》一文(《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这就为后世的种种“师心”之说奠定了哲学基础。江总在《庄周画颂》中写道:“玉洁蒙县,兰薰漆园。丹青可久,雅道斯存。梦中化蝶,水外翔鲲。出俗灵府,师心妙门。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笼樊。”以“物化”、“师心”为庄子哲学的核心,对庄学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本体论的重点转移,使得老子的天道哲学,经由庄子的心道哲学逐渐走近诗道哲学,后来刘勰讲“道心惟微”(《原道》),讲“师心独见”(《论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讲“雕缛文心”,盛赞为“心”之美妙(《序志》),司空图论《实境》“忽逢幽人,如见道心”,刘熙载说“艺者,道之形也”,说诗是天地之心,又是民之性情,“诗为天人之合”,无不有着庄子心、道一体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其最终的根基,仍是老子“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的基本命题。
不过,庄子所谓“至人”、“神人”、“圣人”是无己、无功、无名的,因而也是无情的。这种心道本体论对“情”的不加考虑似乎不利于文学艺术。然而,庄子的“无情”概念乃另有所指,“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德充符》),“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因为在庄子看来,道是“有情有信”的,因此,“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生》)。显然庄子追求合乎自然之道的真情,而这种合乎自然之道的真情,是“精诚之至”,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它意味着对矫伪之情的修正,对世俗之情的超越。应该说,庄子关于有情无情的看法,在哲学上是彻底的,但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日常世俗之情的合理性,在诗学中却并不算彻底。②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诗有灵襟,斯无俗趣矣;有慧口,斯无俗韵矣。乃知天下无俗事,无俗情,但有俗肠与俗口耳。古歌《子夜》等诗,俚情亵语,村童之所赧言,而诗人道之,极韵极趣。”这个问题一直到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理论上才有新的突破。
曹魏之时的刘邵虽不是严格意义的玄学中人,但其《人物志》中的人论思想却是沟通儒、道,连接老庄与玄学的重要环节,而在道家天道哲学向下落实为诗学的过程中,其理论价值也不容忽视。在庄子那里,人是“道与之貌,天与之形”(《德充符》),人可以做到“以天合天”(《达生》),在精神上达到一,但人的肉躯和日常情感是不在其中的。而刘邵则说: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
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有血气者”),是以性情为本,以元一(即“道”)为质,元一之“道”是内在(“含”)于生命存在的。《人物志》所讨论的重点并不是性情的基本理论,而是以识才、选才为目的的人才之学,但其中树立的理论前提却是道家的自然哲学思想。“情性之理”即“情性之道”,“微”和“玄”也完全套用老子的话语,其所标榜的“中和之质”的圣人,也就是老子肯定的“微妙玄通”、善于“守中”的“为道者”。与庄子不同,禀承“中和之质”的圣人不是优游于“无何有之乡”的神人、至人、大人,他是入世的,这一点与老子的圣人观相通;与老子不同,刘邵笔下“平淡无味”,却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的圣人,乃禀阴阳以立性,是“阴阳清和”的结果,不是“致虚极,守静笃”、“营魄抱一”、玄览守中的结果。如此看来,刘邵在哲学上以老庄的自然之道为基础,而在人皆自然这一点上却发展了老庄思想;而且,后来何、王等人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探讨,在“变化应节”一语中也已经埋下了伏笔。
刘邵对情与性两方面的理论关注是有所偏重的,《人物志》重点在性而非情,其思维逻辑是因物以论体,因体以论性,因性而观才,因才性而定德用,因此,有五行(即五物),即木、金、火、土、水;五体,即骨、筋、气、肌、血。五质(即五性),即弘毅、勇敢、文理、贞固、通微;五常,即仁、义、礼、信、智;五德,即温直而扰毅、刚塞而弘毅、愿恭而理敬、宽栗而柔立、简畅而明砭,从自然基质到人体构成,从人物气质到道德素养,一一对应。在刘邵看来,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也不是“五”所能穷尽的,因此他说:“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九征》)
本着因性而观才观德的逻辑,刘邵对人物类型做了区分。他将人分为三个等级:兼德、兼材、偏材。《九征》中谈到的圣人属于兼德,明白之士、玄虑之人属于兼材。他在《体别》中又举出十二种偏材: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惧慎之人、凌楷之人、辨博之人、弘普之人、狷介之人、修动之人、沉静之人、朴露之人、韬谲之人。三等之外,还有末流,包括依似和间杂两种类型。刘邵从自然禀性方面指出了人的差异性,又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肯定了差异的合理性,特别是对偏材的具体分析,客观上正视了圣人之外,日常众庶才性、情感的合理价值。《人物志》对于诗道成立的意义,一是肯定了人的自然性情的本体性质,刘勰论立文之道,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情文,五性是也”,《晋书·乐志》认为“生于心者谓之道,成于形者谓之用”,均本此立论;二是具体分析了各种偏材的特点,正视了所谓偏材的差异性及其合理性,后来个性风格诗学中的“才性异区,文体繁诡”之说即以此为根据;三是因性而观才、观德的思维方法,客观上为后世诗学中的本体论与功能论的统一提供了个体心理依据。
三、自然之情的本体建构
如上所述,《人物志》对性的关注更甚于情。情的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加以讨论是玄学面临的任务。玄学对人的现实情感合理性的探讨,同刘邵一样,最初是以圣人为考察对象的,其中也包括对普通大众情感的隐性论述。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王弼则认为: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何、王的结论虽不相同,但他们的前提却有某种共同性,即普通之人都有世俗五情的这一事实。何晏的具体论述已不可考见,王弼的看法显然更具有合理性。在王弼看来,圣人与普通之人相同又不相同,相同的是都有日常的应物之情,不同的是圣人有情感反应却能不为情感对象所累,具有超越日常世俗之情的能力。显而易见,王弼对圣人之情的看法与庄子的“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一脉相连,差异在于庄子齐生死,强调道的有情有信,客观上忽略了生之情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王弼则更多立足于生来讨论情,肯定了圣人生之情的自然合理性。王弼说:“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哀乐之情乃是生命存在“不可革”的“自然之性”,普通大众如此,圣人也不能免俗。
与王弼同时的竹林之士,对人情之“不可革”的体验和论述更为充分具体。阮籍《达庄论》认为: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
将人的个体生命存在视作一个身、性、情、神的有机系统,性、情是其中重要的构成成分,同为自然禀赋,具有先在的合理性。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则更多地从情欲与礼教的对峙来考察情欲的自然之性,并本着“全性”的思想肯定了情的合理性: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论情更强调生的意义:
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
嵇康之友张邈《自然好学论》论情则立足于不教而能的本能特性:
夫喜怒哀乐、爱恶欲惧,人之有也。得意则喜,见犯则怒,乖离则哀,听和则乐,生育则爱,违好则恶,饥则欲食,逼则欲惧: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论所云,即自然也。
值得注意的是,竹林之士在探讨自然之情的合理性时,已经初步意识到性、情、欲三者的联系和差异,虽然三者在他们的文字中也常常混淆,但以他们日常行为中“任情”而不“纵欲”的种种表现与之参证,可以肯定,竹林之士对自然之情的看法重点在于“情性”而非“情欲”。与名教主张“节之以礼”不同,嵇康等人多从“全性”、“致和”的人道高度来讨论情感的和谐与提升问题。换句话说,庄子的“以天合天”的命题在魏晋时期被赋予了谐调内在生命情感的新的涵义。嵇康说: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
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养生之正度,求之于怀抱之内,而得之矣。(《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正是由于立足于“怀抱之内”情性的谐调和提升,庄子哲学王国里“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神人,一变而为现实人生中“气静神虚”、“体亮心达”的君子。如果说“气静神虚”还有老庄思想的影子,那么“体亮心达”则完全是竹林优游之士的人生体验。不难看出,嵇康“情不系于所欲”的思想与王弼“应物而无累于物”的观念有着哲学上的一致性,但嵇康的论述更加明晰,更容易落实为一种现实人生态度和日常生活方式。从差异方面看,王弼的所谓圣人是一种社会理想人格。而嵇康的所谓君子是一种个体理想人格,王弼的圣人观从传统资源中来,也从社会需要中来,嵇康的君子观也从传统资源中来,却未必从社会需要中来,君子较之圣人,明显多了一层人生体验。在嵇康看来,“不系于所欲”的君子之情,能够超越低贱粗俗的欲望,达到“通物情”的高贵纯净之境,而这种状态中的任何彰显个性的“任情”表现,无论是阮籍的穷途而哭,还是刘伶的纵酒放达,无论是嵇康的俊侠刚烈,还是王戎的悲不自胜,都是“合道”的自然之情。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竹林之士在对情感的认识上,悬置了圣人之情,屏弃了小人之情(即欲),大力彰显“我辈”的君子之情,通过深刻的哲学思辨和分明的个性标榜,将情感从神圣拉回到人间,又使情感摆脱凡俗而趋于高贵,任情而不主故常,合道而不失多样,将老子的“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的哲学义理落实到现实的情感世界之中,完成了自然之情的诗学本体建构。其后,无论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还是刘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论断,无不以此为契机和依据。魏晋以后种种诗本情的观念也都以自然合道的君子之情为基本内涵,而其中对礼教和凡俗的双重超越也显示出传统诗学精神的独特价值。
不言而喻,从本体的确立到诗道的展开甚至诗道概念的提出,也还有一个过程。如前所述,诗道概念的出现,严格说是在唐代,诗道的具体展开也是唐及唐以后的事。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诗道概念明确提出之前的情况。
道的概念移之于艺文,自魏晋始,先是涉及音乐书画艺术。始作佣者仍然是放胆敢言的嵇康,其《声无哀乐论》首先屏除儒家礼教思想,论及“声音之道”,认为声音之道在于“和”,随后王羲之《书论》论及“书道”①《全晋文》卷26王羲之《书论》云:“结构圆满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峙立如鹤头,郁跋纵横如古隶,尽心存委曲,每为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书道毕矣!”,宗炳《画山水序》论及山水画“含道暎物,澄怀味像”的画道。齐梁之时,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以“道”论文,强调本于自然的“道之文”,进而延伸到内涵更加具体的“立文之道”②《文心雕龙·情采》:“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别出形文、声文、情文三道。从“道之文”到“文之道”,其论旨的转移对于后来文道、诗道的形成和展开,意义尤为重大。另外有一点值得特别留意,《文心雕龙》虽然意在“弥纶群言”、“论文叙笔”,但《神思》以后所论多以诗歌为准的,也就是说,《文心雕龙》最有价值的理论其实是一种潜隐诗学。唐朝以后,诗家更是着力于对诗道的研究,皎然《诗式》一方面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给诗道的最高表现以明确的定义,另一方面又说“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一举揭破诗道的终极本体性质,由此诗道概念终于成立。
四、道不自器,与之圆方
一直以来有一个困惑,就是中国诗学中哪一方面的理论最能代表中国的民族特色?刘若愚先生曾对中国文论的各种理论观点有过系统的阐述③刘若愚将纷繁的中国文论分为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见《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并没有指出哪一种理论是人无我有,或人有我精,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多年之后我终于若有所悟,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应该是,而且必然是精妙神奇而又令人困惑、令人叹服的风格诗学。理由可以简单陈述如次:有坚实的中国哲学基础,绝非纯感性、纯印象批评;产生早,魏晋之际就有了风格审美意识和基本理论;内容广博,涉及个性风格论、文体风格论、流变风格论、地域风格论、文本风格论、审美风格论、品评风格论、语言风格论等诸多分支;风格类型概念极为丰富灵活,足以应对丰富多样的诗歌创作实践;充分体现了“有物混成”、“妙造自然”的最高艺术价值观念;本着道器合一、体用不二的原则,以其双重的实践性(创作实践、批评实践)推进诗歌艺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唐之前,虽然也有卓有成效的风格批评实践及相关理论,但中国风格诗学的成立,应该以唐代为标志。根据一是此期有了严格的风格定义,二是开始立足于文本阐述风格的整体美感特征,提出了一系列风格类型概念,三是确立了以道体自然为原则的理论前提和逻辑思路,并以之观照众品,考量得失。
风格是什么?唐代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刘勰论及体性时,以体指代风格,但体又是什么呢?刘勰没有说明。皎然说,体就是“风律外彰,体德内蕴”,简言之就是“体德风味”。虽然这个定义与刘勰“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思想(《体性》)有直接关联,但立足点不同,刘勰讲的是个性与风格的关系,皎然讲的是风格的构成和性质。司空图关于风格的定义仍然沿用了皎然的基本思路,《雄浑》首句“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同样适用于后续诸品,可以视为他的风格定义。皎然、司空图所谓内、外原本是在文本范围之内所做的区分,但是,他们并不强调内外的严格划分,而是主张用一个字、一个词对风格做综合概括,或用一种状态来指陈风格的美感特征。
《二十四诗品》专谈理论,不涉及风格批评,是典型的诗学。让人疑惑的是司空图所采用的表述方式。其实人们只要想想老子论道的表述方式,就不难发现司空图论诗的表述方式就是中国哲学,准确地说,就是中国道家哲学的表述方式。对道家特有的表述方式的选择,似乎让人隐约感觉到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否也如老子之道一样,是一个难以言说的问题呢?还有一点也使人疑惑不解,司空图分列诸品,存在一些诸品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譬如“希音(声)”或“希”,论“冲淡”说“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论“实境”说“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论“超诣”说“诵之思之,其声愈希”,这种相似性使人意识到司空图分列的诸品似乎缺乏严格的界定。其实,这样的感觉是就品论品时“执”的表现。老子说,道“不可执也,执者失之”,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各品中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正是司空图风格诗学的要义所在。执而未超,自然不得其道。
如果以不执的眼光来看《二十四诗品》,就不难发现司空图的风格诗学以道的观念为核心;如果进而再以执的眼光看待道,其具体内涵又包括着三个层面。
第一层,风格本道。这里的道即情性,也就是经过玄学确立的自然合道的本体君子之情,这从《二十四诗品》中多以高人、畸人、幽人、隐者、佳士比喻论品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二十四诗品》中“情性”、“情”一类词语出现不多,仅两次,一次是《自然》一品:“薄言情悟,悠悠天钧。”一次是《实境》一品:“情性所至,妙不自寻。”仿佛《老子》中的“道隐无名”,又不得不强为之名曰“道”、“玄”、“深”、“大”、“微”、“远”。“情性”在《二十四诗品》中,常以“真体”(《雄浑》)、“真与”(《自然》)、“真宰”、(《含蓄》)、“真力”(《豪放》)、“真迹”(《缜密》)、“真素”(《劲健》)、“真取”(《疏野》)、“道心”(《实境》)之名出现,此外还有“微”、“灵”、“素”、“真”、“性”、“神”等,也都含有近于合道“情性”的意思。司空图反复强调“真”,与老子论道所言“其精甚真”有很大关系。他几乎在每一品中都指出“真”的重要性、本根性,最后又借《流动》言此意彼地总结说“夫岂可道,假体如愚”,隐括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大巧若拙”以及庄子“若愚若昏”(《天地》)的思想,意思分明是说,诗之风格不可道,依凭真体道心就是大智慧。这实际上又可以转换成这样一个具体现代意义的命题:风格本道。
在强调风格本道、本真的同时,司空图还非常重视情性的本色自然的特色和自由无羁的表现。他在《雄浑》中说“持之非强”,在《疏野》中说“真取不羁”、“与率为期”、“若其天放”,在《自然》中说“真与不夺”,在《飘逸》中说“如不可执”,语言表达虽有些差异,意思却完全一致,无非是要说明,作为风格本体的情性要取一种自然、自由的状态。与此相关,司空图还特别提到了本体情性的生机问题,如“生气远出,不著死灰”(《精神》),虚静问题,如“虚伫神素”(《高古》),以及浑朴问题,如“脱然畦封”(《高古》)。
如果把老子“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朴散则为器”的思想向下落实,把司空图论“委曲”的“道不自器,与之圆方”的命意向上提升,使之交会在风格本体论的平台上,就不难发现《二十四诗品》中存在着以真体、真宰为道,以二十四品为器的思想逻辑。这种思想逻辑的基础就是老子的道器、体用哲学。鉴于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诗歌风格的左右圆方根本上就是“朴散则为器”的结果。
第二层,风格即道。此处的道意指一种浑朴自然的生机存在。老子说“有物混成”,庄子说“惟道集虚”,司空图则集二家“混”与“虚”之意,说“返虚入浑”(《雄浑》),单看其间术语概念的因袭关系,就可以变相地为风格下一个定义。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有物混成。有物表明它是一种存在,混成表明它是一种浑然不分的整体存在。“返虚入浑”虽然只论“雄浑”一品,可是尚虚重浑的思想却贯穿众品,成为司空图风格诗学的重要观点。“超以象外”(《雄浑》)是虚,“脱有形似”(《冲淡》)也是虚,“由道反气,虚得以狂”(《豪放》)、“是有真迹,如不可知”(《缜密》)、“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流动》)依然是虚;“天地与立,神化攸同”(《劲健》)是浑,“浅深聚散,万取(读作趋)一收”(《含蓄》)也是浑,“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更是浑的极至;至于“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高古》)则是既虚且混。虚与浑本不可分,是一体二面,老子一面说道是混成之物,一面又说道是冲虚之气。虚本于老子无的观念,浑本于老子有的观念,有而不分就是浑。司空图以“万物”、“万象”来形容“有”,又以“脱然畦封”来说明不分之浑,将老子的道体哲学落实到诗境之中,借以阐明诗歌风格的构成和特征。刘勰在《神思》中也表达过“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意思,但主要是针对创作心理而言,不是对文本整体风格的描述。
浑朴虚廓而又富有生机的诗境存在,其理想化的形态是妙造自然。换言之,风格完美的标志,不仅仅是模写自然之物,也不仅仅是表现自然之情,而是融二者为一,达到道的自然之境,即在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之间别开一诗性自然。这或许就是司空图“妙造自然”的深层底蕴。
第三层,风格归道。这里的道指诗歌风格中蕴涵的希声远韵,与司空图论诗之“象外之象”、“味外之味”款曲相通。《二十四诗品》中多次使用“希声”、“希音”、“希”之语,很显然,这些用语本于老子“大音希声”和“听之不闻名曰希”的道体观念。司空图之前,殷璠就曾论及储光羲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皎然《辨体有一十九字》论“远”字云:“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似都包含有希声远韵的意思。但殷璠、皎然只论诗中一品,没有视之为众品的共同特征,司空图却把这一特征上升为多种风格的共同要求,如论“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论“冲淡”:“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论“纤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论“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论“实境”:“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论“超诣”:“诵之思之,其声愈希。”论“飘逸”:“如不可执,如将有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论“沉著”一品:“如有佳语,大河前横。”郭绍虞先生认为“大河前横”即“言语道断之意”,其实用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意来解释这两句更加明晰。显然,司空图认为沉著的风格也应该具备希声远韵的特点。
司空图从老子五千言中拈出“希声”之语来讨论诗歌风格的审美品质,确实有以道论诗的理论意图。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重温《老子·三十五章》中的一段文字: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文中谈到道的性质:无味、无形、无声。其中“听之不足闻”即“希声”之意,但老子接着指出无味、无形、无声之道却有无尽之“用”。因此,司空图借用“希声”一词,既是要说明风格的审美性质,更是要说明风格不尽的审美之用。诗之用,在司空图看来,不是白居易等人的美刺比兴,而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不尽大用,与这种希声之用相比,儒家的兴观群怨之用多少有些老子所谓多言数穷的局限和尴尬。
道之所及,当然不止风格一域,但在风格诗学中影响最大。司空图之后,姜夔论诗之“气象欲其浑厚,韵度欲其飘逸”,与《二十四诗品》尚虚重浑,追求希声远韵的风格之道有直接关联,严羽论“诗之入神”与司空氏“妙造自然”之说也不无前后因缘,至于明代陆时雍说“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清代王渔洋论诗之神韵,莫不以司空表圣为关捩,因道以论诗歌风格的本体及美感品质。
[1]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钱志熙.“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A].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2002.
[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5](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王字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Chinese Poetics and Shi Dao
LIU Mian (School of Literature,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3)
Chinese poetics is based on Taoist Philosophy and is Shi Dao-centered.Among Chinese poetics theories,the one that is richest i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style poetics,which is refined,mysterious and magical.
Chinese poetics;Shi Dao;Taoist Philosophy;ontology construction;style poetics
I207.22
A
1673-1395(2012)01-0006-09
2011 -10 -12
刘勉(1961-),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唐诗及中国诗学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