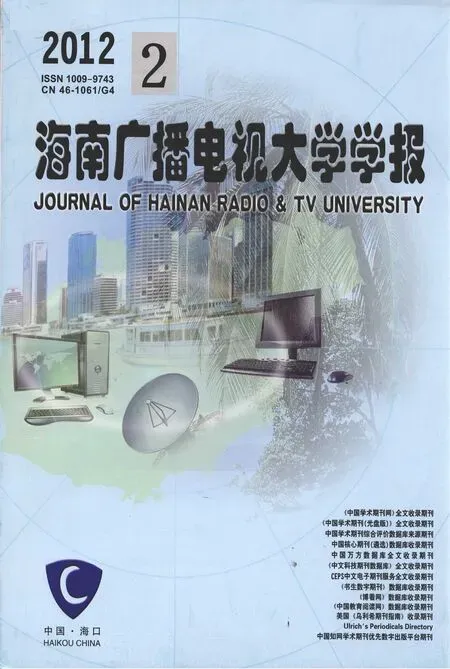塑造新民族:从城市消费看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觉醒
曹 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北京 100000)
塑造新民族:从城市消费看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觉醒
曹 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北京 100000)
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引领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塑造了中国国民新的民族意识。要分析这一变革的产生,就不能忽视消费的作用。处在上海特殊的国际化环境中,民众在与西方的对比中审视、反思自身,由此成为现代新国民。
上海;城市史;消费;民族主义;广告;现代化
近代的上海,是首屈一指的远东大都市,是中国金融与工商业中心。中国各地移民云集于此,世界各国洋商穿梭往来经营商贸,造就了一座多元化的城市。“沪江财富甲瀛寰”,财力由四面八方汇集到上海,使其发展出中国最发达的商业系统,“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①《申报》,1872年5月22日。转引自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第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种土壤使上海铸就了新的城市性格和市民意识。毫无疑问,消费革命对于这一变迁的巨大影响是令人侧目的。
上海成为远东传奇都市,是以商业发达为前提,而商业发达又是以鼓励消费为前提的。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消费模式可以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场变革还局限于上层社会小范围之中,而1920年以来,随着上海工商业高速发展,“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的市民得以摆脱日常油盐的困扰,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②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第1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场革命席卷上海,令其迅速从传统走向现代生活方式。新时代的消费是大众的消费,许多过去只属于显贵绅士的高档消费品由于产业和商贸的发达,广泛进入普通市民的消费领域中。
在程步高1936年指导的著名影片《新旧上海》中,我们可以对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窥见一斑。汽车夫起早贪黑去上班,薪水微薄,但也已经开始用牙粉刷牙;丝厂因为经济不景气停工,丝厂的袁先生几个月没有收入,只得借债,又典当了太太的手表戒指还债,如此拮据的光景下袁太太还不忘烫个头发,并买节礼送人以维持关系;袁太太买航空奖券中奖后,看到百货公司的大减价广告,又去买了许多新式产品;东家不用车的时候,汽车夫及其太太邀袁太太等坐汽车兜风娱乐。
这种情况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上海市民自由消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对西方现代文明耳濡目染,承认自身的不足,认为中国也应不甘落后地建设文明的新生活。这使得民众的现代民族主义日益成熟。本文重点讨论此消费变革中的民族主义因素:这里的民族主义不仅指狭义的爱国主义,也包括了对现代化的新国民精神、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塑造。
一 民族危机中被强加的现代化
自十九世纪上海开埠以来,随着口岸的开放和外国资本大批涌入,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活方式。各国租界的建立,使上海成为一座华洋杂处的城市,西方居民的各种现代生活习惯和配套设施令上海民众大开眼界,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但这种向现代化的转型,最初是被强加的外来之物。显而易见,是列强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进行殖民活动和商品、资本的输出,才使西方工业文明推动了上海的崛起。这一过程开始是十分苦涩的:租界、法律、市政、社会组织、工厂企业、生活内容等方面,都服从西方的要求而被强加而来,是伴随着屈辱的①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但是,尽管列强是通过殖民活动将现代化强加于上海社会生活中,不可否认,这种移植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市政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适应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租界为中心的新式道路一开始即以数倍于老县城6米小巷宽为标准,实际建造时又有突破,主干道最宽有18-21米,一般也多数超过30英尺宽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871年,第19-23页。转引自上书,第370页。。而咫尺之隔的华界逼仄不堪,强烈的反差造成国人心理失衡,“顾行于洋场则覆道坦坦,而一过吊桥便觉狭仄,兼多秽恶,实令人有天堂地狱之慨!”③《申报》1880年4月25日。转引自上书,第371页。这真是两种城市体系的鲜明对照,国人由此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市政缺乏治理,且无卫生习惯可言。华界急起直追,至1911年共筑新式道路10条;1914年拆除城墙,商品流通的需要改变了华界、租界彼此隔离的格局,两者联为一体,更加剧了西方文明对华界的影响。到1927年,南市、闸北新建马路百余条,基本形成今天的市区范围,其影响直到今日。
上海最初只是被动接受现代化进程,但逐渐发展到开始回应,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民族的生存已经受到挑战。国人目睹种种外来文明的示范,产生了认同并积极仿效,萌生了以西方现代方式振兴我族、救亡于危难之中,使中华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想法。这就构筑了近代上海矛盾的形象:一方面是列强势力掠夺、压榨中国人的典型象征,它再繁盛也只是帝国主义吮吸国人脂膏的吸盘,“上海一天天的繁盛、扩大,中国便一天天的凋零、衰落。上海成了天堂,中国遂如地狱”①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第61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转引自《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第42页。,是一种应该毁灭的邪恶;但另一方面,民众又认为帝国主义剥削统治崩毁后,上海将是“民族重生的物质基石”,成功的民族革命将把它重建为自己的城市,以自己民族的方式重塑上海的都市景观。“假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抬头,那中国怒吼的第一声定是从上海发出”②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第39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转引自《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第42页。;这是1933年新中华杂志社就“上海的将来”主题征稿时普通读者来稿的看法。
由此可见,上海这座特殊的城市对西方列强带来的现代化进程的接受、追赶,始终和民族主义情感密不可分。而无论是国民追求新的、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还是提倡国货、号召以商业消费救国图强,新消费方式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是上海塑造新民族风范的一个窗口。
二 市民新生活:走向现代化
晚清以降,上海民众由“臣民”变为“市民”。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华洋杂处的耳濡目染、繁荣的各种媒体的集中影响,现代知识在市民中间空前增长。新价值观与社会生活的转型,造成了上海不可逆转的都市现代取向。
《申报》上纷纷撰文,对中外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承认了西方人生活的文明进步性,认为国人在生活习性的许多方面应该向西方学习。如娱乐消费,“西人游行固不惜重费,然其所费者,不过舟楫车马舆夫宴饮等事而已,华人之耽于逸游者,则往往所好在嫖赌。”至于饮食消费,“西人所食者皆实惠足以适口,足以果腹如是而已;华人所食则但取鱼翅燕菜贵重之品,何者值价最巨即以何者为上品,而其味之果佳与否,不之计也。”服饰消费上,“西人则取其适体而已,华人则必以绸缎纱绢,且五色陆离,光彩炫目,此何为者也?”③《申报》1885年8月22日,转引自《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第230页。婚娶上,“西人之婚嫁乃子女自主之,父母不问也。……中国不然,俗语有云: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即此二语误尽苍生。”④《申报》1886年10月26日,转引同上。在礼仪上,也对国人传统作出了深切反思:“盖华人所尚者礼文仪节之繁缛,而诚意固不及西人也。昔人有言失礼则求于野,今则求于野而不得,且将求之于外洋矣。夫外洋之风土人情其不及中国者亦殊不乏,惟此诚与伪之所分,则似乎胜于华人。”⑤《申报》1885年1月5日,转引同上。以上观点,对中国几千年来不合理的传统消费观、生活观进行了批判,这种观念的转折不能不说是革命性的,跳出了以往闭关自守、天朝上国的观点,来客观讨论如何采用科学合理的新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成为新文明之邦。此外西方人在文明卫生方面给国人印象十分深刻,不断有人呼吁国人建立新卫生习惯,在居家饮食、保持公共环境上学习西方,以讲文明讲卫生为美德。
要分析这一新潮流在民众中的影响,就必须要提到这一时期的各种广告。众所周知广告是针对受众设计的,目的是契合受众的需要,以吸引受众的认同,从而成功劝说受众消费该产品。而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告,多是被各种现代西方健康生活方式、科学观念所武装的,可见民众的兴趣所在。如《大公报》1929年6月15日号上雀巢麦精粉的广告:“此粉为唯一滋补饮料,用最优等牛奶和麦精制成,经五十年之研究始臻完善,故能强健身体且易消化也。”①《 大公报》1929年6月15日第9版,转引自《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第439页。可见上海市民对洋商的产品已经有了一定认同度,接受了西方保健食品。又如乐口福麦乳精广告:“强身补血,益脑安神。营养成分最充足,滋补功力最伟大”②益斌等编:《老上海广告》,第30页,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美国黑人牙膏:“以热带洁齿植物素制成,比众不同,白齿、灭蛀、除臭,功效立见。”③同上,第43页。东方大药房四合一洗面粉广告:“天热时的男女应该用新发明之美容剂;”④同上,第47页。冠生园月饼广告:“冠生园最可人意的中秋月饼,科学烘焙无生熟不均之弊;”⑤同上,第48页。,德国拜耳药厂阿司匹林:“打败一切疼痛”,等等。这些产品多数是过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事物,现在却走进平民百姓家,如《新旧上海》中汽车夫早起后先用牙粉刷牙;这表明西方现代科学的产物已经更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使其更卫生、健康、科学、便利。
从二十年代末到1935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上海工人的生活程度和家庭生计进行了数年的跟踪定点调查,在考虑到职业、年龄、人口、区域、收入、消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因素的情况下,对3口至7口的工人家庭进行了系统的抽样调查,这便是《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在工人家庭各项支出中,杂费支出值得注意。杂费支出是工人家庭在保证基本生活所需开支外的消费支出,作为发展所需费用,一般认为杂费比例增加意味着生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的现代性比例的增大。这些杂费支出包括教育、卫生、嗜好、娱乐、医药、迷信、利息、水费、储蓄等等。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杂费支出年均112元,占总支出24.6%,居然高于德国的21.6%和英国的14.9%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1-84页。转引自《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第334页。。虽然统计上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但也能说明上海平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由于上海工商业繁荣,上海工人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比其他内地城市都好得多。在抽样调查中,除了鱼肉蛋菜,上海工人家庭还年均购买牛奶、奶粉若干斤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83页。转引自《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第339页。,而同一时期在北平的调查显示购买鱼、蛋的工人家庭寥寥无几,牛奶更是一家也没有⑧同上。。(发现339)显然,西方现代生活的营养观念对上海影响颇大,使上海普通家庭的营养结构远超过内地,提升了上海市民的身体素质。
在这个时代,上海人的消费已经由仅仅满足于生存本能上升到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市民取得了消费的独立性,自我奋斗、自我决定命运,而不像旧时代服从于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这种变革冲破了传统社会性格和生活方式,使市民得到自由与解放,这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点,也是社会继续发展的动力。在这一基础上,甚至有人在《申报》上公开挑战中国传统的“崇俭”观念:“裕国足民之道不在乎津津讲求崇尚节俭,盖自有其道也。”此“道”即是“奢靡消费”,“此实利国之奥妙……行之何害,禁之何为?”①《申报》1877年2月28日,转引同上,第349页。可见上海人不仅乐于消费,还认同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国民消费促进生产,生产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因此消费是现代化的一大推动力。
但上海人也不是一味宣扬奢侈消费,许多民族实业家便认为应视国家发展需要调整消费观。他们深知上海生活奢靡,而创业艰辛,提倡节俭度日,以进一步积累资本投入产业的后续发展。荣德生曾说,“看得洋场风气,奢靡成风,教育无方,殊非久传之道。”聂云台更是力主节俭,认为这和国家兴盛紧密相关,他曾著《廉俭救国说》,推崇美国华盛顿、林肯的节俭,将西方思想家、科学家甘愿淡薄生活、摒弃物质享受的态度,并把日本的自强也归功于节俭有方。他规劝众人在三十年代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勿再贪图享乐,“克除私人欲望,而后一切建设有可期。”②同上,第355页。这也能看出,民族资本家们普遍对消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
在三十年代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各报刊也开始提倡节俭,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如《申报》的《论节俭在今日市面不景气下之我观》《洋货与排场》《应倡节俭》,并在1935年12月推出《新年送礼专号》,请各界名人与市民讨论送礼问题,刊发《怎样送礼》《谈谈送礼》《新年送礼与国货》等几十篇文章,希望市民改掉传统观念推崇的愚昧奢靡消费,指出“送礼真不在厚薄与多少上着想,应注意适用与需要”③《申报》1935年12月26日,《新年送礼专号》,“我来谈谈送礼”。转引同上,第357页。。这种看法又和提倡国货联系在一起,又有《排奢倡俭应从使用国货做起》《反对奢用洋货、倡用国货》等文章。这不但用西方现代的“适用”观念规劝市民抛弃传统的不合理的消费观,为经济持续发展着想,更站在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上,呼吁市民以消费来助民族工商业一臂之力,摒弃不必要的奢侈消费,令国家富强。这便是新国民精神的表现:欲救亡图强,首先要养成现代的科学的文明生活方式,使我国民成为充满力量、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新国民。
三 国货:以民族主义为名之消费
在茅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小说《虹》中,来自四川的梅女士坦言在四川生活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国家的概念,但在上海这座半殖民城市仅仅数月,她“却渐渐看见了”。看见洋人在上海的强势,她“想起自己是中国人,应该负担一部分的责任,把中国也弄得和外国一样的富强”④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第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1933年新中华杂志社征稿集《上海的将来》序言中说:“上海是世界第六位的大都市,是中国第一位的大商埠;是国际帝国主义对华经商的大本营,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滋长的根据地。”⑤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第1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转引自《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第41页。正因为在上海洋商力量一目了然,西式文明的优越性近在眼前,不仅警醒国人反抗侵略,也激励他们要将中国建设得一样强大。在上海人对现代化的认同轨迹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少数人到全面追求现代化的全社会实践运动,爱国民族主义始终是国人发奋图强的主动力之一。美国学者詹姆士·哈里森认为,传统中国的自我意象可以用“文化主义”来定义,“它强调一种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对某些信仰的共同接受”①同上,第44页。,使中国人聚合在儒家思想体系周围,并自认为拥有无可比拟的文化优越感,如此创造了一个能够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共同体,将各族各地人统合在其中,获得了强烈的“中国性”。但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碎了这一“天朝大国”的文化优越性神话,使中国人被迫进行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近代转型,逐渐产生了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上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切入点,在民族主义的形成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而消费方式则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材料。民族成员的消费行为同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契合是其形成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在本文前一部分已经进行了分析。民族主义的消费不仅体现在建立文明科学的新生活上,更直接体现在对国货的消费上。二三十年代,国货运动席卷上海,从广告中可以最直观地看到它对民众消费的号召。
20 世纪初,国货广告在上海报纸上尚属罕见,刊登广告的主要是洋商。1927年成立的国货团体上海机联会认为,国货的表现未尝不如人,而洋货之所以长期独占鳌头,“实因平日利用广告宣传,而国人忽之也,长此以往,制造虽有进步,推销不谋发展,国货将日蹙于市场”②张爱平:《在民族的土壤上,下工业的种子——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货运动》,载《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4期。。于是1929年机联会组织国货联合广告,1930年后更是加大宣传力度。“国货”在此是一种商业运作手段,其首要目的是销售商品,为广告主——民族资本企业谋取利益,因此利用广告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整个民族利益等同起来;但国货广告能取得如此大的宣传功效,必须归功于迎合了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这一时期,各报刊上大量的国货广告都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引导市民的消费方式,促进了市民在消费过程中形成民族认同。
例如1920年6月3日《申报》上的中法大药房的人丹广告,将“人丹”二字镶嵌在“富国”二字中,寓意用人丹使国家富强;5月31日的广告用无数小字“国货”组成“人丹”二大字,并说:“此人丹,是国货,内务部,化验过。”③《申报》1920年5月31日,转引自王儒年:《国货广告与市民消费中的民族认同——<申报>广告解读》,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可见“国货”概念本身就是卖点,具有极大的广告效应,甚至要内务部化验以证明其是真国货。这就如同我们今日的广告强调服饰的时尚、食品的美味,或是强调某产品的功效是得到国家认证的。
又如1922年8月27日《申报》上海裕昌祥毛巾广告:“救国不尚空谈,请大家喝的,吃的,穿的,用的都要用国货。”这无疑是宣称,用国货就等于爱国,是爱国的实际行动。因为国货是为了振兴工商业、挽回利权生产的,所以消费国货就是为国家富强出力的行为,又比如1920年9月3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长城牌香烟广告,将秦始皇头像、长城和长城香烟排列在一起,说:“诸位先生,你知道上面三个圈子里,画的哪些故事么?第一个圈里画的,乃是统一中原、征服匈奴、建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帝。第二个圈里画的,就是抵御匈奴的万里长城。第三个圈里画的,就是保护我国利源的长城牌香烟。”①同上。这不仅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精明,也侧面体现了这一时期民众对爱国图强这一主题极其关注,所以民族企业能够以此种广告吸引民众消费。1922年9月《申报》上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为华成厂和中华工业厂产品做的广告,标题为“如何为爱护中华民国者,如何可以救国危亡”,答曰:“如何为爱护中华民国者,如何可以救国危亡,这两句话大家的眼光非提倡国货不为功。这是国民受的刺激深了,才有此一致的觉悟。提倡国货,只须大家不用劣质货,多用国货就是了。”②转引自《国货广告与市民消费中的民族认同——<申报>广告解读》。这是迎合民众对救亡图强的急切心理,将“用国货”夸大为唯一有效的救国手段。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马占山将军在东北抗日有功,举国上下视之为爱国英雄。1932年1月,《申报》上出现了上海福昌烟公司出品的“马占山将军香烟”大幅广告,占据一整版,云:“爱国民众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香烟,因有以下四种原因:一.全国一致景仰马占山将军;二.每箱有慰劳金国币十元;三.色香味悉能抵抗舶来品;四.破天荒精美卷听,由华商康元制罐厂特制。”并有黄金荣题词:“愿人人都学马将军”,还附有醒目的马占山照片,烟罐上也印有马占山像③益斌等编:《老上海广告》,第25页,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这可视为爱国主义广告的典型,将抗日英雄马占山的高大形象用来打造香烟品牌,号召民众一致改吸此烟,暗示吸此烟是如同马占山抵抗外敌一般的爱国行为,且此烟色香味都不比舶来品差,连精美烟罐都是华产,这向消费者传达了该产品是民族骄傲的象征的意味,寓意在民族危机中中华力量与文明仍能屹立不倒;劝说若消费者要参与这一民族主义行动,就要吸此烟。
除广告以民族主义之名吸引消费外,三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还发动了一场“航空救国”运动,旨在发展中国航空业,鼓吹帮助中国航空业发展是爱国情怀的直接体现,鼓动市民购买政府彩券机构每隔两月发售的50万张航空彩票,称投资十元就有机会赢得50万元奖金④《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第184页。。这便是《新旧上海》中袁太太所买的航空奖券。虽然袁太太买彩票显然不是为了表现爱国心,而是由于家用拮据,但政府的爱国号召在广大市民中产生了很大效果:其成功利用了市民对爱国运动的关注。
结语:塑造新民族
前文已经说过:欲救亡图强,首先要养成现代的科学的文明生活方式,使我国民成为充满力量、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新国民。与从前的“文化主义”不同,这才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引领了这一历史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塑造了中国现代化的新民族。在这一进程中,消费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消费,不仅民众逐渐采纳了现代化生活方式、实际体会到了科学卫生的生活习惯的优势,也在外来现代产品、观念的推动下,认识到传统思想和国民素质的不足,从而对国民性进行了反思。这一寻求改良的一致性民众需求,就是一个新民族形成的关键。
在民族危机的大环境下,上海的消费更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上海民族工商业力求与洋商相抗衡,使中国工商业发展壮大,因而号召市民贡献力量,投入这一爱国大业。这一方面是华商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客观助长了民族风潮。在民众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民族工商业号召市民若是爱国就用国货,实际上是鼓动民众:并非只有英雄、显要人士才能为救国出力,平民百姓以消费为武器一样是为国贡献、保卫国家命运的行为。这对普通百姓长期存有的他们与爱国事业有何关系的困惑作出了解答,使他们在进行日常消费的同时,将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归属感凝聚起来,形成了国民责任意识和自觉的国民精神。从市民到国民,有了这些,才有新的中华民族的形成。
A View from City Comsuption on the National Awakening in Shanghai’s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AO Ran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Beijing 100000,China)
In a sense,Shanghai,which occupies a remarkable position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leads the process of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and meanwhile helps mode the new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This transformation was partially caused by the trends of city consumption.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of Shanghai examined,criticized and adjusted their lifestyles so as to become the modern new citizen.
Shanghai;City history;Consumption;National Awakening;Advertisement;Modernization
K 26
A
1009-9743(2012)02-0030-08
2012-03-22
曹然(1986-),女,汉族,吉林长春人。硕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史。
(责任编辑:陈 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