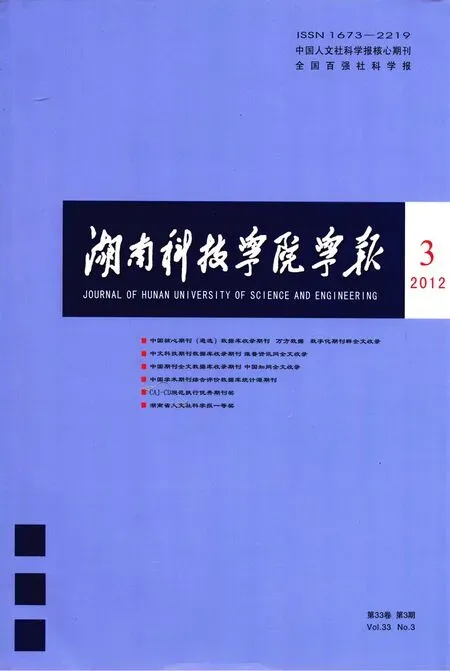《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女性主义解读
王 玫 马 燕
(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 基础部,安徽 合肥 230031)
《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女性主义解读
王 玫 马 燕
(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 基础部,安徽 合肥 230031)
托尼·莫里森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的作品深切关注着美国社会中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和身份危机。在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该文对莫里森的首部小说《最蓝的眼睛》进行了解读,并指出处于白人世界边缘状态的黑人女性一直以来受到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多重压迫,尽管她们努力地去迎合着白人的种种价值观,却始终被白人蔑视和忽略,从而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托尼·莫里森;黑人女性主义;多重压迫;身份危机
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欧美的兴起,女性主义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传统的女性主义运动被认为是白人中产女性为了获得与白人男性在就业、教育、家庭等方面得到相同报酬和认可而进行抗争的产物。事实上,这种白人女性主义运动并没有把有色人种妇女的权利包含进去,长期以来,黑人女性一直处于“他者”地位[1]。“所谓他者妇女就是那些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她们声音的女性,黑人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妇女的地位上——一直处于无言状态”[1]P157。正如玛吉·休姆(Maggie Humm)所说:“简单地说,黑人妇女不是白人妇女涂上颜色。白人女性主义批评不能框定和领导黑人女性主义。”对此,托妮·莫里森曾在一次访谈中也表示出她的担忧:“女性主义起源于(白人)民权运动,因此在妇女运动中忽略了黑人和少数族裔的解放,并把黑人女性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即不得不做出欺骗性的选择:为黑人运动或女性主义服务”,奥伊·莫瑞声称“白人女性主义最终还是没有考虑到种族问题,没有考虑到政治和社会因素给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带来的伤害”[2]P5。戴伯·金则用了“多重危险”来表明黑人女性要承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三重压迫[3]。
一 多重压迫下身份的迷失
身份的迷失是黑人女性长期遭受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的结果。拒绝接受自己的黑人形象,千方百计地模仿、迎合白人,最终导致心理扭曲,自我身份迷失的除了主人公佩科拉外,还有她的母亲鲍琳和布拉德利。
年轻时的鲍琳非常爱去电影院,好莱坞电影极力宣扬的美的标准让她自惭形秽,于是她模仿电影女影星,把头发从旁边分开,盘起来。而电影里宣扬的浪漫也让她羡慕不已。在电影里,白人男性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对女性体贴呵护,他们往往住在带有浴缸和马桶的干净宽敞的房子里。电影中的这种生活总能给她带来许多快乐,可却使她越来越无法回到现实中的家庭,接受自己的丈夫。她越来越讨厌这个贫穷、破烂和肮脏的家庭,越来越无法接受丈夫、孩子和自己的黑人形象。因此,当她成为一位白人家庭的保姆时,她处处维护白人雇主的利益,俨然把自己当做白人家庭的一份子。她越来越忽略自己的家庭、丈夫和孩子,对她来说,他们只不过是[4]“睡前的一点遐想,一天当中的清晨和黄昏”而已。更过分地是,她要求丈夫和孩子称她为“布瑞德夫人”,而白人雇主则亲切地称她为“鲍琳”。对她来说,这种称呼拉近了她和白人世界的联系,摆脱了和黑人任何有关的羁袢。
布拉德利则是来自另一个黑人社区的女性,她和她的朋友只关注与白人有关的事情,竭尽所能地抛弃一切与黑人身份有关的任何东西。为了远离黑人,她不上黑人学校,按照白人的方式做饭、装修房子、教育孩子。像鲍琳一样,她把头发拉直,从旁边分开,甚至睡觉也要像白人一样把胳膊交叉放在胸前。最可笑的是,她自认为是“有色人种”,否认自己的黑人身份,并对儿子解释有色人种和黑人的差别。在她看来,两者的差别一目了然,[4]“有色人种整洁而安静,黑人既肮脏又吵闹”。在盲目追随白人价值观的同时,布拉德利也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对黑人的歧视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的歧视。
二 多重压迫下扭曲的母爱
黑人妇女所受的压迫除了来自阶级和种族之外,还来自女性自身。[1]“深受父性制文化毒害的女性会自觉地将男性对她们的要求变成她们对自己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使她们自己安心于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且还会充当她们的压迫者的同盟,成为压迫其他妇女的一股势力。”[1]P179长期以来,在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下,黑人与自己的家庭形成了一种扭曲、病态和疏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切正常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被颠覆、被践踏,没有了朋友之爱、邻里之情,甚至连最神圣、最纯洁的父母之爱也被践踏得体无完肤。鲍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与其她女性不同,鲍琳自怀孕起就不喜欢自己的女儿,而产房里的一幕则加剧了鲍琳的憎恶感。当撕心裂肺的疼痛来临时,白人医生并没安慰她,也没有教她如何减轻疼痛,反而对其她人说:“这些女人们,你根本不需要烦神,她们不感到疼,生得很快的,就像马一样。”[4]P125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鲍琳的心,她感到了难以名状的羞辱。不去憎恨那些羞辱她的白人医生们,鲍琳却把所有的恨都转移到了自己女儿佩科拉的头上。她认为正是女儿的黑和丑造成了现在的一切。当别的孩子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无私的爱、认同以及带来的安全感时,佩科拉却接受着来自母亲的憎恨。最让佩科拉伤心的是发生在母亲的白人雇主家的一幕。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浆果饮料,自己也受了伤。没有查看女儿的伤口,呵护女儿受惊的心灵,鲍琳却冲向白人小女孩,连声抚慰并更换弄脏的衣服,还大声抱怨女儿搞脏了整洁、干净的地板。“大傻瓜!哦,我的地板!瞧你干的,滚出去。哦,我的地板…地板。”[4]P109
希尔·克里斯曾在《黑人女性主义思潮》一书中指出,“黑人母亲有义务把自己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生存的日常生活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女儿。”[5]P102,为了更好地让女儿掌握这些生存技巧,“母亲们要把确保女儿能生存下来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展示给她们,比如为她们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在危险的情况下提供保护,也就是说帮助女儿比母亲自己走得更远”[5]P184。但是对佩科拉来说,她没有得到来自母亲的任何教育和帮助,即帮助她认识和了解黑人女性世界,尤其是如何爱自己和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在这方面,她的认识是片面的,无知的,甚至是错误的。相反,她得到的是母亲转嫁给她的憎恨和自卑。在母亲的眼里,佩科拉是“丑陋的。虽然她有着满头漂亮的头发,哦,上帝!她可真丑”[4]P126。因此,芭芭拉一针见血地指出,佩科拉的不幸不在于她的“贫穷和疯狂,而在于她缺乏母爱”[6]。
三 结 语
虽然《最蓝的眼睛》出版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但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读起来仍然让人振聋发聩。直到今日,还有不少黑人盲目地以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来审视自己,妄自菲薄;有的甚至带着蓝色的隐形眼镜来企图掩盖自己的种族特征。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从不敢懈怠身上的责任,通过对黑人女性生存中的痛苦和忧伤以及对自我认识的迷茫的刻画,呼吁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黑人群体,尤其是处在社会最底层,承受着来自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多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
[1]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Mori,Aoi.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9.
[3]King,Deborah K.“Consciousness:The Context of A Black Feminist Ideology”[J].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88,(1).
[4]Morrison,Toni.The Bluest Eye[M].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70.
[5]Collins,Patricia Hill.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0.
[6]Rigney,Barbara Hill.The Voices of Toni Morrison[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I106
A
1673-2219(2012)03-0037-02
2012-02-10
王玫(1974-),女,安徽宿州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马燕(1979-),女,安徽滁州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学和外军教育。
(责任编校: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