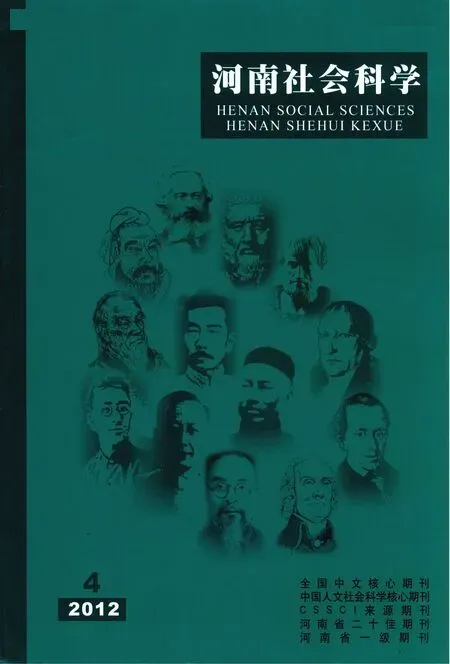文人身份与中国古代赠序和远游诗的兴起
石中华,孙文宪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文人身份与中国古代赠序和远游诗的兴起
石中华1,孙文宪2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赠序和远游诗,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词达到巅峰的唐宋期间。表面看,这好像是经济和文学发达时随之产生的自然现象,但深究起来,人们却发现其中有许多从文学现象本身出发难以解释的地方。要回答这些疑问,以往我们惯用的审美视角显然无能为力,须得结合其他方面来读解,方有可能弄清楚作者的本意。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必须从文人身份这个维度出发,才能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而对其进行现代阐述。
古代;文人身份;赠序;宦游;远游诗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含有大量的赠序文和远游诗,从这些文字和诗歌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件非常美好、带有浓厚人情味的事情,然而,深究起来,你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无限美好的状态下其实含有许多辛酸的成分,友人写赠别诗前常冠以序文,并非完全是絮叨友情和家常,而是有着其他目的的,诗人的“远游”也并非是简单地游山玩水,而很有可能是迫不得已去“旅游”。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演变成果,也是受到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所以,须得从审美之外的角度去重新读解。本文选择了文人身份这个维度,试图从阐述中国古代文人的特殊身份开始,逐一论述对于其对中国古代文学中赠序文、远游诗兴起的影响,以唤起人们对于文人身份这个因素对文学作品形成的影响的重视。
一、中国古代文人的特殊身份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就他们的文学创作及成果来看,他们被称为“作家”绝对当之无愧。用“知识分子”来称呼他们或许更合适一些,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则认为用“知识人”来称呼可能更严谨,因为“知识分子”是个外来词,它来自西方,并且出现得相当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很多,也十分严格,但大致说来都主要包含有以下两种内涵:首先,一个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个读书多的人,还需要有精神上的追求,如具有某种理念或价值观;其次,知识分子必须对现行社会具有某种责任感或义务感。所以,知识分子在现代常被人称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①。抛开某些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近乎苛刻的定义,我们只取前面说到的两种内涵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国古代是有一大批此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只不过,这种“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士大夫”。
“士大夫”是“士”与“大夫”的合称,它们原是分开的两个等级,同属商代至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战国时期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动,“士”的地位有所下降,它从贵族阶层中剥离出来,降至“四民之首”,这在《梁传·成公元年》中有清楚显示,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②由于有贵族不断下降为士,特别是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性质也起了变化,已不复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而是多呈“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在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这就产生了一个所谓“仕”的问题。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③,因此,战国时期的游士颇多,有学问有能力的士人便能得到君主“礼贤”,并获得较高的职位,成为“大夫”。但“士大夫”之称真正兴起却是在两汉,是伴随着“士”的落叶生根开始的。先秦游士居无定所,但他们在社会中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故汉高祖刘邦初起颇有鄙士之举,最后还是实行了“安抚”制度,允许这些游士置下产业,安顿下来,让他们有入“仕”的途径,进入社会管理层。因此,他们的家族开始壮大,人心也开始稳定,不会再因为“居无定所”而造成社会动荡,而是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两汉期间也因此出现了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名门望族。自汉武帝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便几乎以一枝独秀的姿态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近两千年,并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他们被委以重任,出现了世界史上少有的“文官”占据大半天下的统治局面。尤其是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一些有文化的士甚至平民有了入“仕”的途径,“士大夫”集团更进一步得到了扩展。这些以孔子为代表的新兴“士”阶层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他们自觉做“道”的承担者,以改善社会为己任,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士”文化,这与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内涵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中国古代文人并不等同于现代“知识分子”,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士大夫”的身份。中国古代有文化的人集中在“士”这个阶层,相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身份来说,他们的身份则比较固定。“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目标和追求,而察举和科举制度又让他们有了做官的途径,获得了“士大夫”的身份,因此,作为知识阶层的他们不仅是文学写作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社会管理者、领导者。其次,独特的身份确认。士大夫最明显的特征则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孔子这个新兴“士”阶层的代表被他们尊称为“先圣”,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其“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做“道”的承担者的这种核心思想,被他们奉为人生信条和行为目标,中国两千多年的“士”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士大夫们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身份确认,这与现代以来的文人是不同的,后者虽然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却没有这样的身份确认。再次,写作面临的对象。士大夫主要是为士大夫和帝王写作的,他们的写作不面对普通老百姓;现当代作家则是为公众写作的,有的作家也可能面向精英写作,但他们在面向精英写作的同时也面向公众,而且他们缺乏士大夫那样的身份确认,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集团。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所以如果对他们的作品单从审美方面去理解和阐述,显然有欠完满。
二、文人身份对赠序、远游诗兴盛的影响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创作是与时代大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的,而文人持何种社会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的创作,因此,要深入研究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必须首先考虑到这个因素。前面已论及中国古代文人是以“士大夫”身份出现的,那么,作为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混合体,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必然也会表现出与他们这种复杂身份相伴的身份话语,下面将要论到的赠序和远游诗即是他们身份书写的某种表征。
(一)“举荐”与赠序的中兴
赠序,是在初唐兴起的一种散文化程度很高的特殊文体,是中国古代序文中的一类,常于离别时作“赠言”用,是文人间约定俗成的一种“馈赠礼”。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向来重视礼尚往来的馈赠文化,而赠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礼品,在民俗文化中颇具典型性。一般来说,它是文人在与文人之间往来时借寓抒发文人情怀或某种志趣的行为方式,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馈赠方式中的一种“赠言”文化。但在这些赠序中,有一类赠序却并不是仅仅作为馈赠礼品那么简单,它因其功用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致使赠序这种文体在某个时代的数量突飞猛进,这就是赠序所具有的“举荐”功能。
这种具有“举荐”功能的赠序也被称为“请赠序”,多是受人之托或是被命赠的,主要用于科举之时一些有名望的士大夫受人之托向自己正在做科考官的朋友推荐某个“学而优”的学子,或是在某人即将远行时向自己位居高官的朋友推荐这个人,希冀委以官职。这与唐时的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唐朝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和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许多人为此前赴后继,每年集合于长安的举子,大约有1600人,但录取名额却很少,如进士名额只有30人左右,这样中榜的机会可以说非常渺茫。然而唐代又流行一条捷径,那就是请人“举荐”。试前举子可以自行投文于当时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名公大卿(这些人也多半是由科举登第而来),名曰“行卷”,如果能够得到名公大卿的青睐,后者便会向知贡举者推荐人才,因而举子能否得第,有没有人举荐延誉就大不一样了。因此,每年科举之时,大量举子聚集京畿地区,千方百计地交结权要、名流,以期获得延誉和举荐,为其登科加重砝码。这是许多“学而优”的“士”子成为社会主流、改变命运的首选。如皇浦的《送王胶序》,就是为王胶将赴长安应进士试而作的,他在文中先是极称其才,接着又说“今侍郎韩公,余之旧知,将荐胶而未具,于西行,叙以先之”④。皇浦这篇序文的主旨就是向韩愈推荐王胶,韩愈此时在长安贵为侍郎,且享大名。能够得到这样一封介绍信,足以使王胶在众多考生中引起韩愈重视,而后仕途便通达了。这正是一般文士、举子向名人求谒的目的。也因此,每年科举之时,赠序数量都会激增。另外,赠序“举荐”功用中的推荐官职功能也大大地推动了赠序的发展。唐朝时除了通过科举这一途径获取官职外,有才能的人先入主幕府为事,后再受幕主举荐进而升职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在科举制度不能完全解决文人出路的情况下,他们纷纷入主幕府做文职幕僚。而入主幕府,除了少数享名在外的文士外,大多数人还是要靠名士推荐的,因此,有名的文士便再一次成了众人请托的对象。当然,这里面也并非全是文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人情”之辞,有许多人也是确有其才,是朋友之间的真心推荐,这种举荐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补充了朝廷选拔之不足。如元结《送孟校书往南海并序》云:“平昌孟云卿与元次山同州里,以词学相友,几二十年……云卿声名满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云卿何事不可至,勿随长风乘兴蹈海,勿爱罗浮往而不归。南海幕府有乐安任鸿,与次山最旧,请任公为次山一白府主,趣资装云卿使北归,慎勿令徘徊海上。诸公第作歌送之。”⑤诗人的举荐之意和殷殷真情是最明白不过了的。玄宗朝著名的文人宰相张说和张九龄,以好提拔下层才士的声名垂入青史,赠序也成为他们荐举文人的一种工具,故他们所作的赠序数量非常多,也就是从他们开始,唐人创作的赠序数量就逐渐多出其他序文的数量,达到兴盛,并渐渐脱离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存在。不能不说,正是赠序所具有的这种举荐功用,对于赠序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世的文人延续了这一特殊馈赠方式,所以在宋、元、明、清的文人结集中也常常能见到此类赠序的出现,这种赠言文化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宦游”与远游诗的兴起
做官是士人理所当然的职业,也是唯一值得终生追求的目标。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如果一个人不愿做官,他也不可能去从事工商业,因为从事工商业在明末以前是被人看不起的。士人的理想与出路是参加科考出仕,一旦考上,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家中原本贫穷的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就是科考制度中最低层的生员,只要考中,也会免去全部赋税,所以,科考出仕吸引了许多莘莘学子为之前仆后继。但是,科考出仕给中国古代文人带来的并非全都是好处,实际上,它也有着许多苛刻的条件限制,比如它的职位变动非常缓慢,经常是在某个职位上任满之后,还要过好几年才能得到另一个职位,升迁也极其缓慢,而且,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地位的巩固之目的,常常要把他们派到离自己家乡很远的地方去任职,更有甚者,大半生都在外漂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宦游”。著名诗人王勃曾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提到过这种“宦游”:“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西汉时的士大夫稍好一点,因为士族根基未稳,不劳统治者“费心”,但到东汉末年就不同了,士族开始变得庞大,家族势力一度扩大到几乎无法统治的局面,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就是当时士族扩大的力证。因此,到了唐代,统治者为了律法的公正性,也为了防治这些士族“结党营私”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便制定了一个“本籍回避”制,即所有官员都必须到离自己家乡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而且唐代还有所谓“守选”制度,“唐人每任一官,都有一定期限。除了特殊情况,一般都在四年左右,不能长久连任”⑥。这就导致了任期短、迁转频繁的情况,也意味着唐人必须经常为了迁官远行,这是唐代士人做官不可避免的命运,宦游也因此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大内容,书写宦游的诗也就极多。如诗人高适,于天宝八年(749),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后弃官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安史之乱,升侍御史,拜谏议大夫。肃宗朝历官御史大夫、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又任彭州、蜀州刺史,转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后为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从高适的这一系列官职上可以明显看出唐代士人为官的频繁迁转和需辗转各地赴任的社会现实,也因此诗人所创作的作品大多都是奔赴各地时的忧愤之作。所以,在他50岁刚到封丘县任县尉时,就写了一首《初至封丘作》,提到离家在外做官的心情:
可怜薄墓宦游子,独卧虚斋思无已。
去家百里不得归,到官数日秋风起。⑦
钱海燕有时很想抱抱周启明,但周启明坚决不让他抱,他说:“我就像个放射源,虽然可能残留得很少,但万一还有呢。”
诗作写得沉痛有力,诉尽在外宦游的苦闷。大诗人白居易一生四处做官,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他对宦游的体会更加深沉。他三十多岁时,被派至长安附近的一个小县任县尉,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便已在《县西郊游寄赠马造》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宦游的厌倦:
我厌宦游君失意,可怜秋思两心同。⑧
这恐怕也是唐代许多在外宦游做官的人的共同心声。到老年时,他更写了一首《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诗,总结他一生的宦游经历:
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
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⑨
意即他做了20任官,却宦游了30年。这就是唐代士人典型的宦游生活经验。除了宦游诗,唐代大量的送别诗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种宦游的频繁,以写边塞诗著名的岑参就写了大量送友人赴任的诗作,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送裴校书从大夫淄川觐省》……可以说,唐朝时的官制是间接导致文人大量创作送别、远游诗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唐代这样,唐以后的统治者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官制,士人做官仍然常常需要远游,以宋代大诗人苏轼一生的“宦游”经历为例,他自20岁初试礼部并高中后,就一直处于宦游当中,在其为期近四十载的宦游生涯中,官历26任,除了在被贬的杭州和惠州时间待得稍长之外,大多数时候任期都很短,有的甚至不满一年,如《宋史·苏轼传》载其元七年,徙扬州。……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苏轼为官迁转之频繁和每职任期之短在现在看来让人惊叹不已,其中虽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宋朝官制与唐时一样,士人每每为了做官不得不东奔西跑,难以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扎下根来,所以苏轼的诗词中也有大量的远游题材,如《初到黄州》中写下“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等自嘲诗句。到明、清时这种制度虽有所放宽,但许多官员仍需离开自己家乡去“宦游”,这从《红楼梦》中的贾政几次到外地任职都可以看出来。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诗词中的“远游”题材并非仅仅是游山玩水这么简单,或者以为是经济繁荣的表现,其背后蕴藏着的恰恰是与他们官员身份相伴的离开家乡的苦闷和忧郁。而且,他们家乡的基业往往因此而被迫放弃,有的人甚至到老了才能还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的诗句描写的是当时许多士大夫文人的真实境况。韩愈说“中古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⑩,正是这种景象的写照,这也直接导致了在汉代兴起的士族大姓、族群在中世纪开始衰落。
三、创作中文人身份的重要性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人身份对其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拿赠序来说,如果不是科举便没有“请托名家”写赠序来提升自己的做法,如果不是要做官赠序也不会成为文人间的推荐信。那么赠序大可以像“游宴序”或普通送别诗前冠以序文以抒发离别之情的散文一样,成为文人间礼尚往来的特殊赠品。但正是赠序的举荐功用,使得它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大量涌现,成为一种不平凡的“礼品”,字里行间彰显着士人集团的特色。远游诗也一样,如果没有官员这种身份,他们就不必去宦游,如果只是普通的一次旅行的话,他们的诗中透露的应该是期待、兴奋和自豪,诗文也应该充满了诗情画意,友人也大可不必郑重其事地设宴饯行,写下诸多伤感的离别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宦游不仅刺激了远游诗的大量出现,赠别诗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流行元素,自唐初开始,往后一千多年的文人莫不受其影响,他们创作出大量此类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其实不仅仅是赠序和远游诗受到文人身份的影响,中国古代其他题材的作品也与此有着密切关系,限于篇幅,此处不详论。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文人身份对他们作品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一个人持何种社会身份,决定了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而环境对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也决定了他会以何种身份和话语进行书写。文人身份问题是前现代主体性研究发展到后现代的产物,并进而被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重视,提出了“作家身份话语”这个研究主题。赛义德在《东方学》中特别强调文学作品中的“东方”形象出自西方作家的个人想象,它与真实的“东方”是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差异的。因为许多西方作家并不曾到过东方,没有实际接触过,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是从别人的小说、传记、电影、新闻等中形成的,所以东方人在他们笔下往往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而西方作家之所以会这么写,除了他们未曾到过东方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西方在殖民时代累积的财富使他们形成了一种“霸主”的心态,总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俯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霸权话语”也随之出现。很明显,这种“霸权话语”是受到其身份影响的,这种身份同样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所以才会出现赛义德提到的不真实的“东方形象”。这不仅说明了作家只有深入实际生活、了解生活,创作出的作品才会真实感人,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众人的推敲,同时也可以看出,了解作家身份和读懂其身份话语,对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是多么重要。
注释: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②陈戌国点校:《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四书五经》,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550页。
③[宋]朱熹注、王浩整理:《论语·子张》,《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④[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六八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25页。
⑤[唐]元结:《元次山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4页。
⑥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9页。
⑦[唐]高适撰、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⑧[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一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5页。
⑨[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三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3页。
⑩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送杨少尹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责任编辑 姚佐军
J0
A
1007-905X(2012)04-098-04
2012-01-10
1.石中华(1980— ),女,湖北恩施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2.孙文宪(1947— ),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