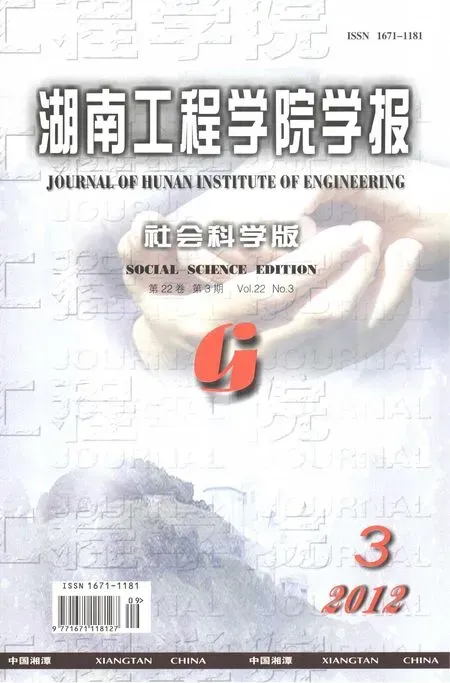形神理论源自道家考
马汉钦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形神理论源自道家考
马汉钦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通过对中国古代形神理论的发展源头进行追溯,可以认为早期道家的“器”与“道”关系论就是形神理论的源头;到了庄子,形神理论在哲学里已趋成熟,并开始了它向人的转化,至此,中国古代形神理论则已经完全形成。
中国古代形神理论;道家;庄子
一 早期道家:“器”与“道”—“形”与“神”关系论
“形”“神”作为一对紧密相连的范畴进入中国哲学领域里,始于何时?这是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遍览群书,笔者最终找到了早期道家的“器”与“道”关系论。
“道”,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名词,与动词“行”通义,有行走而四通八达之意。后来从“行走”创造出“道”字,《说文解字》释曰:“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人昂首朝一个目标走去,“一达”也。因此,“道”的本义就是人走的、四通八达的道路。《诗·小雅·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通向周的都城的大路,平坦得如磨刀石,直得像一条箭杆。
道路通向何处,是有它的规定性的,有明确的走向,人沿着道路而行,运动不息,于是我们聪明的先人便产生了联想:天上的日月星辰昼夜不息的运行,是否也在沿着一条无形的道路在行走呢?春秋时代的天文学家便提出了“天道”的观念,运用“天道”一词表述日月星辰的运行有它们固定的轨道,何时在何种位置出现,都有严格的规定性,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又显示出它们运行的规律性,尤其是季节与气候的变化,更有人们难以真接把握的奥妙事理在其中。《国语·越语》中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天道”就是日月运行周而复始的不变的规律,“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就是“天道”运行的内容,它们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因为日月星辰运行引起昼夜、气候的变化,继而引起自然界一切生物包括人生死盛衰的变化。于是,当时一些思想家又用“天道”来说明世间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变化的总规律。如《左传·庄公四年》记载楚武王伐随,武王夫人邓曼知此行凶多吉少,说:“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后来,《左传·哀公十一年》中也记载了伍子胥同样意思的话:“盈必毁,天之道也。”这些议论都说明,上古时代的先人已经意识到,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一切现象的呈示,都像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发展到了顶点就必然走向它的反面。
以上“道”与“天道”的观念,都还停留在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停留在直观的阶段,但他们的感性认识已开始向理性认识飞跃,如对“天道”就有“盈虚”变化的体认,并用来附比王朝政事。但是,将“道”上升到哲学的范畴,并赋予其纯理论的色彩的,则是老子。
老子“道”的观念不但超越了道路之“道”,还超越了“天道”。《老子·二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143
这个“道”,实质上就是宇宙的本体,因为它是“天下母”,所以日月运行的“天道”亦从它而出;这个“道”,囊括了“天道”、“地道”、“人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1]144
日月运行是人的眼睛可以见到的,天气变化是人体可以感觉到的,总之都是可以名状的。但是,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却是超感官、超名相、超理性,只可体悟而不可言说的实体、实在: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锲;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十四章》)[1]82
在老子看来,“道”的本质就是“无”,就是“虚”,“道”既包容一切又不见一切。没有颜色故“视而不见”;没有声音故“听而不闻;”没有形体故“搏之不得”,大得无终无始,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无法形容它,人们的感官根本不能把握它,因此,只能把它叫做“无”。
这个“无”,不是空无一切之无,它只是无任何具体的可由人的感官直接把握的属性。但它又包容无限,“湛兮,似或存”(《道德经·四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经·六章》),虽然这“无”是不可凭感官感知的,是一种实存、实在。“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一章》),在虚无之中,实际上在孕育着万物,“无”中生“有”,即“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四十一章》)。若按老子这一观念序列,日、月都是属“有”的范畴,为‘无名之道’所生。当然,这个“无”就是“道”,而这个“有”就是“器”,“有”由“无”生,而“道”为“器”之所本,正如《道德经·二十八章》之所云:“朴散则为器。”此处的“朴”,即是“道”的一个别名。在这里,“器”—“道”的关系就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因果关系。显然,早期道家的“器”—“道”关系,即由此处而衍生出来。
我们知道,“道”是无形的,而“器”是有形的;将有形之“器”与“形”挂起钩来并非难事,而无形之“道”是怎样和“神”挂起钩来的呢?窃以为,就是“道法自然”这句话,为它们走在一起埋下了伏笔、创造了条件。
“道法自然”出自《道德经·二十五章》,这句话也算是该书的总纲。但是,这个“自然”不是我们常说的物质的自然界,这个“自然”是指一种没有主观意志的客观存在。这“自然”的表征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它是对“无为”的一种规定,也是“无为”的一种结果。“道”生成万物没有意志,不待勉强,一切听其自然而不施加任何干涉。这样说来,“道法自然”的“道”也就是“自然之道”,因有此意,“道”终于和有着“客观规律”之意的“神”建立了对等关系。
就像从天道盈亏引申出世间各种事物变化的规律一样,老子也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因“自然”这一特质,引申出宇宙万物变化的总规律,他对这个总规律的表述是: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1]288
“道”作为这个总规律的代称,在这里终于在两个层面上通过“器”而得以彰显:
一是在“物”的层面上。所谓“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是也。作为自然规律的“道”,既是万物所遵行的法则,那么“道”在万物之中,是必然有所体现的,得“道”之人也正是从大自然具体的物象中,才得以悟出这玄妙而深幽的“道”的。“道”以“器”显在这个层面上,就因此可以成立了。很显然,作为客观规律的“道”,是完全可以用有着“客观规律”之义的“神”来替换,而作为彰显“道”的“器”,用“形”来替换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以“器”显“道”、以“形”显“神”的逻辑关系,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是在“人”的层面上。所谓“道生之,而德畜之……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是也。原来,有“德”之人的身上,是可以“畜”这个玄妙莫测的“道”的。那么,有“德”者是靠什么来“畜”得了这个“道”的呢?老子指出,自然之“道”既是“无为而无不为”,人若以此为法,则即为有“德”之人,而“道”自然就可以为他所持有了。这个意思,《道德经》中是反复强调的,兹举二例以明之:
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三十七章》)。[1]211
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道德经·六十四章》)[1]346
老子还对如何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得“道”的境界作了反复的说明: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道德经·十六章》)[1]95
可见,只有“致虚极,守静笃”,方能“观复”而“知常”,“知常”者,明“道”也;反之,则是“妄作凶”。
再看老子对有着“无为”之“德者”的描述:
我独泊兮,其未兆,屯沌兮,如婴儿之未孩。(《道德经·二十章》)[1]115
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二十八章》)[1]168
老子认为,人只需保持婴儿那样素朴本性,则必有“无为”的处世原则,从而可以得“道”而“无不为”了。在这里,有“德”之人作为“器”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就可以得以彰显那无形的“道”了。显然,有“形”之人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器”,在他彰显作为客体之“神”的“道”时,其主体之“神”已与“道”冥合了。“形”“神”关系在这一层面上表现得更为曲折而深邃。
要之,在老子那幽深的“道”与“器”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无论自然万物还是人类自身,都处在一个“形”与“神”的范畴之中;所以可以这样说,形神理论的构建,其实在老子的那里已经发端。
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个发端,如同一棵小小的细苗,如不细细打量,是看不出来了。我觉得,这层薄薄的窗户纸,老子本人也似乎很想捅破——可惜只破了一丁点:那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把“神”和“道”联系了起来。老子用“神”凡八处,有七处是言神鬼、神灵之意,惟有《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原为山谷之义,此取其虚义,指道体虚无深藏;“道”之玄妙莫测就是“神”,“神”是“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然而,到了老子的后继者宋尹学派,则把这层窗户纸完全捅破了。《管子·内业》云: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2]129
无形无声的“道”,虽不可见,却可有形有声地藏身于万物之形中。既如此,“形”中取“神”,亦自然之理也。《管子·内业》里还有这么一句话:
抟气如神,万物备存……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2]134
“精气之极”就是“道”,“道”的状态也就是“抟气如神”,从而“万物备存”。一个形神关系的逻辑链条,在这里已是很分明了。
作为特殊之“器”的人,宋尹学派也把他看作一个形神兼备的实体。《管子·内业》云: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2]135
这里的“形”—“精”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形”—“神”关系无疑了。由此可见,形神理论向人的转化,在此已显端倪,从而为庄子形神理论向人的完全转化,打下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宋尹学派也认为,“道”也是可以借着“德”之人得以显明的。《管子·内业》云:
凡道无所,善心安处……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2]130
那么,得“道”之后呢?《管子·内业》对得“道”后的状态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2]133
由此可见,有“德”的“圣人”在其得“道”之后,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形态表现的;而正是这种有“德”者的形态,可以折射出那客体之“神”—“道”的独特光芒来。正如《管子·内业》开篇所说: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2]128
因而,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有“德”圣人,皆是“道”的载体。至此,早期道家的“器”与“道”、“形”与“神”的理论,也就略具雏形了。
二 庄子:形神理论向人的转化
如果说宋尹学派的形神理论只是存在一些迹象的话,那么到了庄子的手里,形神理论则已经完全形成。
也许有人会说,庄子在他的著作中不也时常使用“鬼神”一词吗?是的,庄子确实在不少地方是按照其原本意思使用了“鬼神”这个词的。如《庄子·人间世》中说:“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只要我们耳不外听,目不外视,收视返听,又弃绝心计智谋,则得入自然无为之境,如此,则鬼神也就不可怕了,人间的祸害就更算不了什么了。再看《庄子·天地》中说:“道于一面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缮性》中说:“阴阳和静,鬼神不扰。”请注意所有这些话语,或明或暗地都是把“鬼神”放在了人的权力之下了。当然,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人,并非一般的人,乃是得了“道”的人。可见,在庄子的眼里,得了“道”的人,是要比鬼神更厉害的;既然如此,则“鬼神”何为“鬼神”哉?这其实和老子所讲的“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完全是一个意思。所以,可以这样讲,在老庄二人那里,“鬼神”其实是被他们虚化了,这和他们那个时代较浓的人本主义思想氛围是息息相关的。
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并无二致,而老子的“德”在庄子那里则渐渐变成了“神”。如,庄子在《逍遥游》里面,就把得“道”之人称为“神人”。可见,庄子其实也就把“生于道”人的精神,当作了天地之间唯一的神妙之物。这个意思,在《庄子·知北游》中的一段话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突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3]324
可见,在庄子的眼里,人的“精神”是生于“道”,而形体生于“精”。“精”为何物?“精”即精气也。人的精神是从宇宙的本原——自然之“道”而生,以老子的推理看待,庄子在这里讲的人的“精神”,也就是老子的“德”无疑了;而人又是有形体的,有“德”之人的形体作为载“德”之物,亦未尝不是载“道”之物了。于是,“道”与“德”的关系,在一个有“德”之人即得了“道”的人那里,也就具体化为了一个“形”“神”关系了。他的这个意思,在《德充符》中庄子与惠子的一段对话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3]84
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得出来,庄子所说的“情”,是“无人之情”,其实也就是与“道”相通的人的“德”;而惠子所说的“情”,则与庄子的有大不同,他是指人辨析名理的聪明,而这在庄子看来,是“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的毁“德”之物,是对人的自然情性的严重损害。可见,人的“形”—“神”关系,是依照天地的“道”—“德”关系才得以理顺的;庄子正是在老子的哲学基础之上面,才使“形”—“神”关系从老子的哲学领域里走出来,而实现了它向人的完全转化。
因为“形”—“神”关系是从天地“道”—“德”关系那里衍生而来的,所以,“形”之于“神”,一如“德”之于“道”,是一种从属性的关系,这几乎是先天性的。所以,庄子的形神观,毫无疑问就是“神”尊于“形”和重“神”轻“形”的。人之“形”,在庄子那里简直到了被视而不见的地步。这个意思在《德充符》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
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
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
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淑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3]76-77
叔山无趾“形”虽残,而自知“犹有尊足者存,吾以是务全之也。”尊于足者是“德”,即其“神”也,其“务全”,是以“德全”为追求。但孔丘不理解,以为不过“学以复补前行之恶”,并“宾宾以学子为”,执于名迹。故无趾以为不可救药:“天刑之,安可解!”“形”之被刑,尚有尊于“形”者存;而“德”之被刑,真是不可解了。足见庄子对人的“形”的轻视和对人的“德”的推崇,这里的“德”,也就是人的“神”。再看另一段: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汜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豘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刖者之屦,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这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呼!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3]78-80
哀骀它外貌奇丑,“以恶骇天下”,却能“未言而信,无功而亲”,是因为他是“全德之人”。在这里,庄子借孔丘之名,极为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庄子的形神观。豘子(小猪)爱母,“非爱其形,爱使其形者也”,母死,形存而“使其形者”不存,故“弃之而走”。这“使其形”者,即是“神”。“神”使“形”,“形”使于“神”,这就是以“神”为主导的形神观。
闉跂支离无脣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 謷乎大哉,独成其天。[3]82-84
此二人形体穷天地之陋而全其德,故说卫君而卫君悦,说齐君而齐君喜。形体“眇乎小哉”,故“形“可忘;道德“謷乎大哉”,故德必长。“形”“神”之小大、轻重,在这里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因而,庄子之“神”,指的是人的内在心灵,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在的思想感情,而是指的“生于道”的自然之神,此“神”按其哲理上的意义即称为“德”。“形”“神”理论在庄子这里,终于有形有体地在“人”的身上站住了脚跟。
应该说,庄子的形神观,是一种重视人的内在心灵、而不重视人的外在形迹,重视人的内在之美、而不重视人的外在之美的形神观。这种形神观,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认识。因而,道家的形神观,对于以表现人主体心灵为重心的文学艺术而言,是有着重大的意义。
[1]张松如.老子解说[M].济南:齐鲁书社,1998.
[2]管子[G]∥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1.
[3]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Concerning the Textual Resear of Appearance-spirit Theor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MA Han-q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0,China)
By means of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ancient appearance-spirit theory of China,we think the“substanceway”relation theory of early-stage Taoist is its theory source.Appearance-spirit theory began to become ripe in philosophy and transform to human being up to Zhuang Zi,up to this point,the ancient appearance-spirit theory of China had completely formed.
the ancient appearance-spirit theory of China;Taoism;Zhuang Zi
B223
A
1671-1181(2012)03-0071-05
2012-03-19
马汉钦(1966-),男,湖北洪湖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