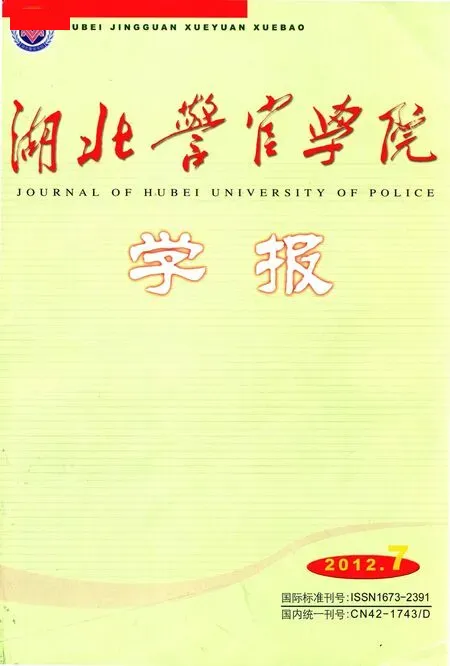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
赖彦西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646000)
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
赖彦西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646000)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上的创新之举,但该制度并未赋予指导案例的法律效力,未能完全发挥它在克服成文法缺陷、保障司法统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屡屡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统一性、稳定性、公正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目前,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条件已基本具备——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成功尝试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悠久的判例传统提供了历史借鉴;我国法院案例指导的实践提供了实践基础;判例机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运作的技术条件。
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可行性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首次以文件的形式确定要在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是指在刑事司法领域选择典型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并赋予这些案例法律效力,使这些刑事案例对法官产生强制性约束力的刑事司法制度。由此产生的“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不同于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性案例”仅仅对法院的裁判活动具有参考或知道价值,它将对法院处理同类案件的裁判具有强制约束力,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引用到判决文书中。
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不尽相同。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只能在制定法绝对缺失(不存在)或者相对缺失(过于模糊)的情况下才能创制,产生法律效力,其所包含的裁判规则在法院处理同类案件时才可以被直接引用;而在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中,判例产生法律效力不以成文法的缺失作为前提,判例一经创制立即产生约束力。[1]是否可以在中国建立判例制度,是一个争议话题。判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其作用有目共睹。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判例制度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特殊表达,其构建条件已基本具备。
一、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成功尝试提供了经验借鉴
为了弥补成文法自身的缺陷,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建立了判例制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德国,判例在司法审判活动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法律规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具有正式的约束力,对联邦及各州各级法院有严格的约束力,如果下级法院作出与之相反的判决,那么该判决就是非法的。另外,德国法律中规定了背离判例报告制度,该制度规定当法院要背离判例另行判决时,必须向上级法院报告。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保证了判例在事实上的约束力。[2]可见,德国虽然只赋予了联邦宪法法院判例正式的法律效力,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判例,仍然受到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对法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通过这种判例制度,德国法典不断受到司法判决的扩充和改变,使之变得更加充实和完善,适应了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法律体制本身的发展以及国家司法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国虽然不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基于成文法的传统,与大陆法系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陆法系国家推行判例制度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经验借鉴。两大法系基于各自的优缺点,相互借鉴,共谋发展是大势所趋。判例将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活动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所用,我国不应该碍于传统约束,在司法制度方面不敢尝试变革。
二、我国悠久的判例传统提供了历史借鉴
我国虽然是成文法国家,但考察我国刑事法律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判例制度自古就存在。
早在奴隶制时代,判例制度就开始萌芽,从“皋陶(舜时的司法官)造律”的传说中可以推断这个时期是“法生于例”。西周时期,刑事司法施行的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审判方式,不预先制定成文法典,而是选择以往的判例作为审判的依据。因为“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没有成文法,老百姓便无法根据法条来预知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犯罪应当受到何种刑事处罚,从而使得法律对百姓有更强的威慑力。[3]从秦代开始,历代相继制定了繁多的成文法典,但是,并没有抛弃判例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廷行事”(法庭成例),这正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例。汉代判例制度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即经最高统治者确认后可以用作裁判依据的典型案例,它与“廷行事”相类似,种类和适用范围更多、更广。唐代之后,以《唐律疏议》为标志,中华法系趋于成熟,在判例的适用上,遵循“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可见,判例是作为制定法的辅助形式,并通过制定法条的形式被固定下来的。在元代,《新元史·刑法志》中提出了“断例则因事立法,断一事而为一例”的主张,“断例”甚至优先于法令,出现了“以例破法”的现象。[4]明朝,朱元璋不仅重视立法,组织编纂了《大明律》,还亲自指导制作了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汇编——《明大诰》,要求司法官吏断案时必须参照援引大诰中的判例作为判案依据。清代,判例被定为条例入律,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北洋政府时期,大理院汇编判例有3900多件,这些判例成为各级法院处理案件必须遵循的“先例”。国民党政府时期,成立了“判例编辑委员会”编纂判例,要求全国各级法院遵循。
判例制度一直伴随着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与成文法典一起承担着维系法律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职责。如果将其抛弃,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将这历经几千年的判例制度传统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历史借鉴,将以例辅律的传统融入到当今的法治建设之中,才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应有的理念。
三、我国法院案例指导的实践提供了实践基础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通过颁布司法解释、做出司法批复、刊登典型案例的方式,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196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法院总结审判工作经验,选择案例,指导工作。一直到1985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内部下发了许多案例,用来指导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于1985年1月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公报》是公开介绍我国审判工作和司法制度的官方文献。在《公报》创刊早期,其公布的典型案例后面都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有关该案指导价值或借鉴功能的按语,明确表示“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开始出版《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主要内容是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中选择出来的,在认定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和定罪量刑等问题上具有研究价值,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疑难案例,并重点对裁判理由予以权威的阐释。[5]
2000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决定有选择地向社会公布裁判文书。
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确定要在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二)地方法院的判例探索实践
我国一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判例指导司法裁判方面也进行了探索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2年7月26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先例判决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是地方人民法院首次将判例制度运用于司法审判当中。该规定赋予了先例判决对司法裁判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力。当然,这种约束力并不是法律上的,在依据先例裁判时,并不能直接援引先例,先例在此仅仅起到参照的作用。
2002年10月9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民事审判中实行判例指导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暂不含涉外、海事)推行判例指导,这是该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明确提出了实行判例指导制度。这里的判例也只是具有指导作用,没有法律约束力。
2005年4月1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示范性案例评审及公布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较郑州的《规定》和天津的《意见》更为详尽。该《办法》指出,经审判委员会确认的示范性案例对全市法院办理同类案件具有指导、参考和借鉴作用。
各级地方人民法院是我国法院系统的基石,它们在判例制度上所进行的探索活动,为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累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探索活动的推进,判例制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判例机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的法学理论界对判例制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崔敏教授指出,应当确立“判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将推行“判例法”作为完备我国法制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也指出要在我国实行“判例法”步伐不能过快,要缓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6]宋晓明法官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分析了判例对于我国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判例可以成为成文法的补充并且可以减少法官因为自身素质不同而产生的量刑轻重悬殊现象,指出应当将判例法纳入我国的法律渊源。[7]武树臣教授认为,法律分为黑色的法律、白色的法律和灰色的法律。黑色的法律是指成文法及司法解释,白色的法律是指司法解释中的批复及被赋予典型意义的判例,灰色的法律是黑色法律与白色法律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法律形态。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是黑色的法律过于强大,要铸造灰色法律就要对白色法律予以扩充,这就涉及到要在我国发展判例制度,淡化“判例不是法律渊源的观念”。[8]研究者们来自于宪法、法理、法制史以及各个部门法领域,全国性的判例专题学术研讨会也时有举办,特别是在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后,这种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质的飞跃。这些理论研究为我国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运作的技术条件
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民法院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采取了切实措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人民法院信息网络系统建设。绝大多数高级法院完成了本单位的计算机局域网络建设,初步实现了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辅助管理、司法档案管理、司法统计管理、办公和司法行政管理等计算机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在积极开发法院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此外,全国法院系统已建成计算机广域网,初步实现了审判信息和其他管理信息交换、资源共享。这使得纸质判例形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使所有判决都能通过电子网络查看。借助于计算机软件,可以进行相似案件的对比工作,也可以输入特定的选项,查找到与待裁判案件相关的案例内容,并且可以及时更新发布生效的裁判。这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1][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25.
[2]岳志勇.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J].法制与社会,2009(7):45.
[3]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1 0-112.
[4]曾宪义.新编中国法制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43-46.
[5]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
[6]崔敏.判例法是完善法制的重要途径[J].法学,1988(8):22.
[7]宋晓明.判例法应纳入我国法律渊源[J].政治与法律,1990(1):34.
[8]武树臣.铸造灰色之法——再谈在我国发展判例制度的重要性[J].法学研究,2000(1):37.
【责任编校:陶 范】
D915
A
1673―2391(2012)07―0062―03
2012—04—05
赖彦西,女,四川泸州人,四川警察学院侦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