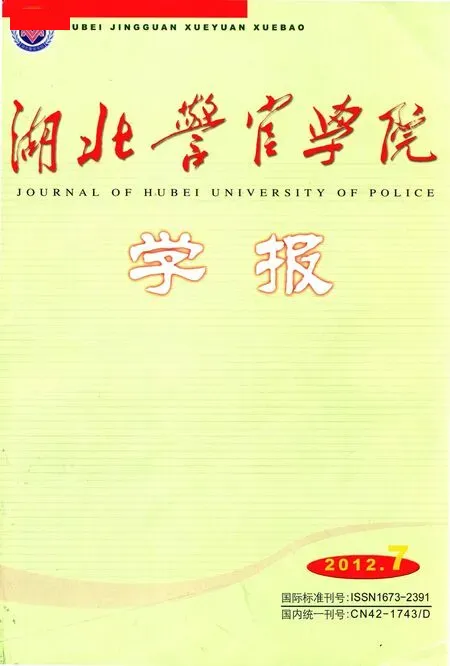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规范与扩展
吴加明,李 飞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0135;2.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四川 成都610041)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规范与扩展
吴加明1,李 飞2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0135;2.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四川 成都610041)
被害人救助工作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现行规定对检察环节的被害人救助限定过严,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而部分被害人通过申诉信访,迫使检察机关予以救助以求罢访息诉。当前申诉信访过程中被害人的救助缺乏规范性、稳定性。亟待建立统一有序的救助机制,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共同开展检察环节中的救助工作。
检察机关;被害人救助;对象;上访
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确立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规范。据此,最高检于2009年4月下发了针对检察机关开展被害人救助工作的专门通知,对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对象、条件及程序等作了规定。
一、当前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工作概况
据统计,2009年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共救助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285人,救助金额666.87万元。①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刑事被害人救助案件情况通报》(内部文件)。被害人救助工作已成为检察环节重要工作内容,在全国各地得以开展。
(一)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工作重要性得到充分认识
检察机关作为查办刑事案件的职能部门,直面各类被害人,是被害人救助工作的直接承担者。如果说几年前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工作尚处于理论探讨层面,实践中推行被害人救助的检察机关也屈指可数,2006年以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检察系统高层和学界的共识。最高检机关刊物《人民检察》刊登了关于被害人补偿的一系列文章,执笔者既有检察系统相关领域主管人员,又有学界权威,均对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给予了充分论述,这一系列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检察系统及学界相关领域对该制度统一认识的重要标志。②参见孙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实践意义及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6年9月(上);尹伊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载《人民检察》2006年9月(上)。其中作者孙谦时任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作者尹伊君时任最高检刑事申诉厅副厅长;作者王牧、赵国玲均为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其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被害人救助工作得到最高检的大力推广。其后,各地检察系统陆续开展了各项被害人救助工作,尤其是2009年4月,最高检针对被害人救助工作的专门文件下发后,检察环节中的被害人救助工作得到了充分重视。
(二)及时制定规范性文件,确保救助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公开的资料查询,从2006年起至今,全国各地已有数十家检察机关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各地检察部门以最高检的文件为依据,结合地方检察工作实际,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以规范本地救助工作。如河南省检察院制定了《河南省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被害人救助办法》、上海市政法委等部门共同出台的《上海市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实施细则》等。然而,上述规范基本是以中央政法委及最高检的相关文件为蓝本,结合本地实际做一些细则操作规定,对于救助对象扩展、救助程序简化以及如何与公安、法院、司法、民政等部门协调配合等救助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无实质性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积极推动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立法工作,其起草的《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由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200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例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法规,不仅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还解决了困扰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的诸多实践问题,其经验值得借鉴。
(三)申诉人以闹访等方式迫使检察机关予以救助
根据中央政法委及最高检相关规定,检察环节救助对象前提条件是案子不起诉,且案件类型局限于故意伤害、杀人等侵害人身权案件。然而,检察实践中不起诉案件并不多,不起诉案件中人身伤害类型的被害人更少。严格依照中央政法委的《若干意见》和最高检规定,对被害人救助的案件十分少见。实际上,大多数地区检察机关的被害人救助缘起于被害人的申诉、信访。即被害人对法院刑事判决不满提请检察机关抗诉,并请求检察机关予以救助,其所涉案件均已起诉,且往往不局限于侵犯人身权的类型,不符合现有规范设定的救助条件。
但面对申诉人的不断上访、闹访,甚至演化为冲击国家机关的群体事件,作为负责刑事申诉的检察机关往往被迫予以救助,或出面协调法院、公安等部门共同救助,以求罢访息诉、案结事了。如我院2010年办理的三例被害人救助案,均不符合“不起诉”的前提,所涉案件既有故意伤害类案件,也有诈骗、抢劫等侵财类案件。在检察实践中,被害人救助类型已突破了上述限定。这也是当前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背景下,检察机关为了罢访息诉、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无奈之举。
二、当前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被害人救助政策是以司法手段救济弱者的一项利民措施,检察机关在被害人救助工作上历经几年摸索,也发现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一)有关规定限定的救助范围过于狭窄
根据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制定的《若干意见》及最高检的贯彻意见,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接受救助的前提之一是“决定不予起诉的案件”,这是根据中央政法委《若干意见》做出的规定,也是出于公检法分工负责的实际,由结束刑事诉讼的部门负责相应救助工作。
本系统的显示部分由2.8寸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模块来显示,分辨程度较高,分辨参数为320×240、16位真彩色、自带触屏,LCD的接口16位8080并口方便用户观察环境参数,可以对设备进行操作。
在实践中,以检察院不起诉终结刑事追诉的案件并不多见,不论是绝对案件数量还是相对比例数均很小。而且检察机关有限的不起诉案件中,“相对不起诉”占很大比例,相对不诉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也就是说很多不起诉案件,被害人已经获得了加害人一方的赔偿,再由国家介入救助既无必要也不符合规定。
救助对象的另一限制是“因暴力犯罪导致伤残”,这就将实践中占很大比例的财产犯罪、经济犯罪中的被害人排除在外,这类犯罪也往往导致被害人陷入经济困境而无法获得赔偿。
综上所述,对于检察环节救助对象的种种限制,实际上将诸多确实需要救助的被害人挡在了公正的大门之外。
(二)救助程序繁琐、救助资金有限,削弱了救助申请的积极性
目前的救助规定要求符合条件的被害人提供“家庭经济状况证明”,须由其居住地或暂住地基层组织审核,由乡镇政府或街道办出具证明。囿于种种原因,有的申请人几经周折无法获得上述证明,外来人员还需往返奔波,使本已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根据现行政策,申请人即便申请成功,获得的救助金也不高,与遭受的损失相比可谓杯水车薪,难以有效解决实际困难。
另外,如果严格按照最高检的救助条件,必须待案子最终做出不起诉决定后方可申请赔偿,而依照刑诉法相关规定,审查起诉期限一般以一个月为限,特殊情况的退回补充侦查或延长,最多可能耗费几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很多暴力犯罪被害人医疗费用、手术费用没有着落,急需救助,却囿于该限制无法提起。也就是说,被害人在最需雪中送炭的时候,检察机关却爱莫能助。即使向其他司法机关申请救助,也可能因为案子倘处于检察阶段而被拒之门外。
如“诈骗被害人俞某等三人申请救助案”,该诈骗案发生在2006年前后,三被害人2010年才发觉被骗报案,但由于证据不足,侦查环节已几经周折,直至2011年1月才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我院经审查,认为该案证据不足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截止目前还在办理中。前后时间持续已近五年,被害人一家几乎陷入绝境,如严格依照上述规范,检察机关救助的大门也将被无情关闭,被害人将无从寻求救助途径。
因此,严格的程序限制和少量的救助所得,客观上影响了被害人申请救助的积极性,致使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工作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三)申诉信访接待过程中的被害人救助缺乏规范性、正当性,并可能滋生新问题
申诉过程中予以被害人救助缺乏操作规范,或者规范层级较低,显得较为随意。实践中,刑事被害人救助最初往往源于信访问题或特定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其救助性质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救助金额的多少也不确定,闹得厉害就多给一点,闹得不厉害就少给,不闹的就不给。比如某基层院办理的“杨某、郭某救助案”,该二人系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被害人父母,因对司法机关处理结果不满,加上得不到加害方的经济赔偿,便组织其老乡数十人到各级检察机关上访,甚至以聚众冲击检察机关等极端方式扩大事端,造成恶劣影响。最后在政法委协调下,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承办此案的公检法各方共同给予一笔不菲的救助金,才实现了平访息诉。这种救助虽然能够解决个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被害人实际困难,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无法推而广之①参见白金刚,王新,吴锋:《问题与制度设计:检察机关开展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之研究》,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还可能滋生其他社会问题。
另外,这种权宜之计的正当性值得反思。其一,国家的公款来源于纳税人,每一分钱的花销均需接受人民的监督,没有正当依据的救助毕竟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和民众的追问。其二,从司法的公正性角度看,对部分信访申诉人予以救助,而对类似境遇的其他人不予救助,其公正何在?对部分申诉人予以较高的救助,对其他人予以较少的救助,其公平又何在?
此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实,将会给今后的信访申诉接待工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如若老实本分者屡屡吃亏,如若乖张折腾者次次得利,理性上访、依法申诉将成为奢谈,取而代之的将是层出不穷的暴民和乐此不疲的闹访!
最后,根据中央政法委牵头制定的《若干意见》,判决之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救助的责任机关为法院,申诉环节的案件一般均已由法院判决,依此规定应由法院负责被害人救助。申诉环节检察机关对被害人予以救助有越俎代庖之嫌。如若严格执行“一次救助”原则,检察机关的僭越救助可能导致该申诉人无法再寻求法院救助。
三、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工作扩展与规范——以“无锡模式”为例
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与维护被害人合法权利的统一,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理想状态。当我们终于把目光投向以往一直忽视的被害人救助时,需要探讨的是如何设计更加完善、更加公平公正的救助制度,让被害人救助的司法理念得以贯彻。2009年10月1日,全国首例地方性被害人救助法规《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以下简称《无锡条例》)正式实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笔者认为,借鉴“被害人救助无锡模式”,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工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一)救助对象扩大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所有案件,申请救助与主动救助双轨并行
与中央政法委牵头制定的《若干意见》不同,关于被害人救助公检法之间的分工,《无锡条例》采用的是根据案件不同阶段,分别负责被害人救助,实现了刑事司法活动中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无缝衔接”。即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负责,提起公诉阶段由检察机关负责,审判及判决执行阶段由法院负责。《无锡条例》对于拟救助对象遭受侵害的犯罪种类并无限定,即只要遭受犯罪侵害、经济困难、无法获得加害人赔偿、工伤、保险赔付而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均可以申请救助。①参见《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2009年4月29日无锡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9年5月20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这就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检察环节救助对象范围,只要案件进入起诉阶段,被害人确实经济困难又无从获得赔偿或赔付的,即可以纳入救助对象。这样的规定更符合客观事实。是否应予以救助,不在于被害人是遭受何种犯罪侵害,更重要的是要判断其是否确实处于困境而无法获得其他救助。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与财产犯罪的被害人遭受侵害的犯罪种类不一,但只要确有困难的,没有理由只对前者予以救助而排除后者。因此,笔者认为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对象可以放宽为公诉阶段的所有案件、被害人确有困难而无法获得其他救助的,赋予救助机关更多的酌情甄别权。
借鉴《无锡条例》第十九条,检察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确实符合救助条件,而被害人没有提出申请的,检察机关也可以直接提出救助意见和救助金额,并办理相关手续,发放救助金。
(二)将被害人的救助拓展至申诉访接待过程中
将申诉信访接待环节纳入检察机关被害人救助范围,是现实需要,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能所在。在一定意义上,对申诉人予以经济救助是解决其信访、闹访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基于当前的社会现实,基于检察机关受理控告、申诉的法律职能,应将检察环节的被害人救助拓展至申诉接访过程中。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在申诉访接访中的被害人救助需要规范,避免随意性。必须根据既定规范,严格把握是否符合经济困难的救助条件,严格审查救助额度标准,对于是否救助、救助金额多少等环节,应有科学明确的标准,避免一味花钱买平安。
此外,为防止公检法对同一被害人救助申请重复救助或相互推诿等情形,应在政法委协调下建立相互之间救助信息通报机制,对于已经获得救助或救助申请已经提交其他机关正在办理的申请,及时予以排除。
(三)应由地方立法向全国立法、由低位阶法规向高位阶法规迈进
被害人救助工作涉及刑事司法各个环节、各个部门,需要整合全社会资源,最终实现救助工作的规范有序。针对当前实际,检察机关可以采取由地方向全国、从低级到高级立法的过程实现被害人救助工作立法制度化。
笔者认为,先由基层检察院自行制定院级规范性文件,系统地开展工作,并结合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断完善。再由基层检察院联合同级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通过文件会签形式建立联动机制,扩大刑事被害人救助覆盖面,待时机成熟后由同级人大制定规范性文件,如《无锡条例》,在区域范围内全面开展,然后再推动更高层级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直至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被害人救助法律规范。
D630
A
1673―2391(2012)07―0171―03
2011—03—19
吴加明,男,福建龙海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校:郑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