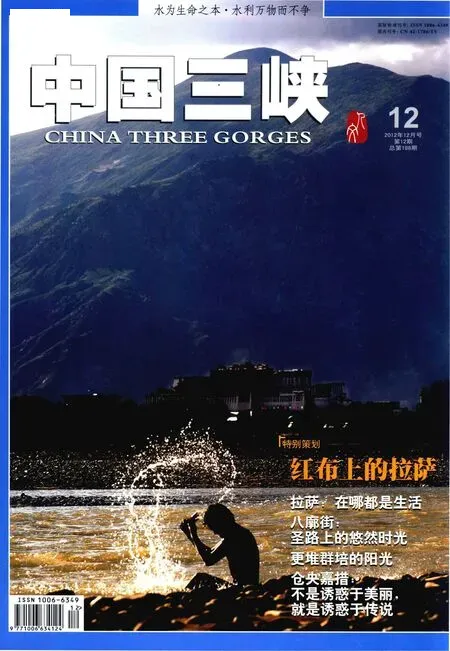昭 君 思 旅
文/罗婧奇 编辑/任 红

香溪河。 摄影/黎明
香溪地
关于王昭君的籍贯,《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南郡人”,文颖注《汉书》称昭君为“南郡秭归人”。宋代记载更为具体,《太平寰宇记》载:“兴山县,本汉秭归县地……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村连巫峡,是此地。”《归州图经》提到昭君的乡人因思念她,就在她的家乡香溪立昭君庙纪念她。这里提到的秭归和兴山,现在是不同的两个县级行政区划,但就其地域而言,山水毗连,且古代时曾并为一个行政区划,所以暂且按今天的县制认为王昭君是宜昌市兴山县人。
也有别说。东汉蔡邕的《琴操》说昭君是“齐国王穰女也”,认为王昭君是齐人;《安陆县志》“昭君村在荆门州”和《一统志》“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的两种说法是根据杜甫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附会而来,认为王昭君是荆门人;更有认为其是蜀中之女的看法。但根据多数史料、史籍的记载——除前面提及的部分,还有宋《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清同治版《兴山县志》等,昭君是兴山香溪溪畔的女儿是最为可信的说法。
还记得小时候,外婆家就在老兴山县城,小城不大,景点很少,去得最多的玩耍之地就是昭君村。传说昭君为解村子的河患之苦,曾带领乡亲在村口修了一座石拱桥,桥体似一面琵琶,名曰“琵琶桥”。
石拱桥本是传说,从我记事起香溪河上便是一座吊桥跨立,连接了村子和外界,钢铁拉索已没有了石质材料的古朴,沾染了现代气息,但踏上它时那种微微的晃动感,似乎应和着涓涓水流在念道那历史的久远。正因为这种沧桑之感,一切的认知也只能凭借留存的物事和自己的想象而来,真假之间似乎有了某种调和。
陆游《入蜀记》载:“去江岸五里许,隔一溪,所谓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绿于品,色碧如黛。”这弯弯的溪水,有过昭君的童年和少女时光,而清波几许,从她浣衣、打水的素手中流过,正如她和家乡的缘分渐渐滑走,她终将带着一脉夷陵女儿的清香,踏上了出塞之路。
水流为何叫“香溪”?有的说是因为昭君出生时,贫瘠的土地面貌翻新,刚种的粮食已可收获,而村边的那条溪流的水变的清澈、甘甜。也有说法称,某天昭君在溪中沐浴,不慎将一颗珍珠遗落水中,从此溪水变得等清透明、香气四溢。《妆楼记》则载:“王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尽香,今名香溪。”
香溪中有美丽珍奇的桃花鱼,指节大小、色泽透明,体若伞状,游动时像伞那样收张,每年三月时浮游于碧波上下,与岸上的桃花相映成趣,我也曾在溪中捞了一些放进玻璃小瓶中作观赏之物。
“桃花鱼”名称的由来也源自于昭君的传说。昭君出塞前,汉元帝特许她回乡省亲,探亲期满、告别亲友时,正是桃花三月天。感伤从此永别家乡的昭君乘舟沿香溪而出,泪如雨下,泪珠落入溪中,与水面落花相合,化为桃花鱼。
凭记忆,过桥后是一方宽敞的平地,正对着的是十几级台阶,隐约已可看到村内那座汉白玉的昭君像。拾阶而上,有一个土台,台上有个小拱门,上刻“梳妆台”三字,据说是当年昭君梳妆之处。又有一楼为“望月楼”,是昭君读书、弹琴和绣花的地方。昭君出生时恰逢皓月当空,她又生得脸似银盘、肤类月光,其母称是月中仙子入腹而妊娠,所以才称“望月楼”。楼前有菱花状的水井,是昭君小时与女伴担水洗濯之地,名“楠木井”。
以上这些都是真实遗迹,昭君正宅是依照古图重建的,高墙大院、门楼巍峨,内有昭君纺纱、父母接旨等蜡像,门外有仿制的农具可供游人把玩。近看昭君玉像,微微侧脸、神情淡然,体态丰腴、衣裙飘逸,是一派温婉女子的形象。院内还有一个蒙古包,表示昭君出塞的史实。
清山绿水中长成的女子是怎样承受住了北国肆虐的风沙,我们都不得而知了。只是印象中不屑贿赂画师以希君宠,具有绝世才色而不被汉帝知遇,最后毅然自请出塞和亲的女子,她的才情、她的见识、她的坚强,都化做看见院中那三十三棵青松时的感叹——她找准了自己的立足点,可毕竟生命只走过了三十三年的岁月,时间都嫉妒她的精明,抑或是她的命途本就不幸。

春韵昭君。 摄影/丁川华
风沙路
一个农家小女走出山林踏入深宫,又凭借与不俗的见识走出深宫,去到大漠中找寻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意义超越了本该是“嫔妃”的地位,而有了民族大义的色彩,使后代之人再也不可能忽略掉“昭君”这个名字。
昭君出塞是“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传》),是她自动要求出行的。而之所以使她产生这样的念头,是因为“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后汉书·南匈奴传》)。因是良家子而被迫入宫,入宫后却长时间孤凉地呆在“掖庭”,眼见命途要像很多白头宫女那样,为着一个男人可以见自己一面而将青春和生命消磨在无尽的等待之中,昭君选择了积极自救的一条路。
正好有消息传进宫,“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汉书·元帝纪》),汉匈民族关系是国家大事,后宫中人均有机会看到讨郅支的“图书”,所以昭君可以听到要和亲的消息,然后作出应诏的举动。可见昭君有着其他深宫女子所没有的气性高远,知道在劣境中为自己打算的坚强自主的性格。
在正史之中,昭君是这样一个形象——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宫,为了个人的命运和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自愿充当汉族的“和亲使者”。但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加入了作者的主观因素。譬如蔡邕在《琴操》一书中,伪作一首《怨旷思惟歌》,写昭君哀叹自己背井离乡、孤独的远嫁异族。还有南北朝梁朝的吴均,在《西京杂记》中捏造了反面角色画师毛延寿,他因昭君不肯贿赂他而把她画得丑陋,使昭君不得君王召见,为昭君的出塞找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原因。马致远的《汉宫秋》更写元帝和昭君产生了爱情,而昭君又不得不出塞,所以倔强如她在行至黑河时投水自杀,对正史的改动可谓更大。
野史不足为信,自古文人写史为真正史家们所批判。但不可否定,这些野史中的昭君形象更为人性化,可以说是挖掘了正史宏观叙述掩盖下人们所不断追寻的细节。昭君只是一个山村来的小女子,虽然不甘屈服于即将埋葬在深宫中的命运,但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肯为民族大计牺牲自己在宫中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去嫁给一个当时人认为的“蛮夷”,去忍受风沙等恶劣的环境,去遵循为汉伦理文化所不齿的原始胡俗。这些野史的文学创造,站在一个小家出身的女子的角度,剖析了她身不由己而离开故土、远走塞外的悲怆心情,更丰满了为何一代美人不得君王召幸的原因,或是将历史的主角贴上爱情的标签让经典更富有传奇的色彩。

昭君出塞。
不论出塞的动机和原因是如正史中说有大义凛然的成分,还是如野史中说完全是处于对自身命途的不平凡的把握,昭君出塞都是做出了伟大牺牲的。她如花容貌、年轻身心却委身于一个已经在衰老的单于,并在他死后为着和亲的大计要违背内心汉家的伦理道德律从胡俗而下嫁给他的儿子,还在匈奴过着艰苦的本不适应的生活。所以,即使历史上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且大多都是位高身贵的宗室公主,她们的事迹却多数随着历史的走过而消逝,只有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王昭君却名留千古。
琵琶情
所谓“诗词千首咏昭君”,古今作品中有对昭君的生动描绘和歌颂,有怜惜她远嫁、为她悲感者,还有的叹红颜薄命、因国家之大命而牺牲了自己的小命,等等,为我们展现了多面的昭君形象。
各种诗词文赋中,叹其悲凉的还是居多。如北周庾信的《明君词》情重词清,“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胡风入骨寒,夜月照心明”,同情昭君一路风霜之苦,还感其思乡念国之情。李白的杂言古风《王昭君》:“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出塞的路途孤寂,只有明月相送,而月亮明日还照亮这里,出塞的人儿却已经行至远方、不会再回,李白以明月比人,形象深刻、意境全出。杜甫《咏怀古迹》言“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直言“怨”“恨”。
以上所举这些都是哀怜昭君的远嫁之作,感慨她孤身一人去至大漠、终不得归。但也有诗反映昭君内在精神和心态,很有独见。虞集诗曰:“天下为家百不忧,玉颜锦帐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离离永未休。”(《题昭君出塞图》)此诗认为昭君之嫁不可悲,好过埋藏在深宫中,像其他女子那样虚度年华。唱别调的还有王睿《解昭君怨》,其中一句曰“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认为昭君的留名正是在于出嫁匈奴,借出塞而出宫免于流俗,不应悲凉反而应该庆幸。而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反过去普遍对画师毛延寿开骂的态度,而批评了帝王的好色和自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则不再存有大民族的偏见。

昭君墓景点之一“和亲铜像”,为昭君和呼韩邪单于的骑马铜像,下书蒙汉两种文字的“和亲”二字。 摄影/罗婧奇
去年春日,有机会去呼和浩特,特意去了昭君墓。记忆中晃晃悠悠走过香溪河上链桥的感觉犹在,面对昭君墓周边独特的民族风情,充满历史大气的出塞景象浮雕,以及竖立的功德碑文和山包上的独墓、题词“大德”,只觉恍如隔世。思旅只能是思旅,再如何回忆、感叹,伊人是远久的牺牲,拥有跟随她的不能自我主宰的归宿。只能立足于客观的历史,品味想象加工后的文学,再去她的生地、归处走一遭,在脑中勾勒出一个生动的昭君形象。走进昭君墓的大门就能看到熟悉的汉白玉昭君雕像,原来这和昭君村的那尊雕像是双生子,暗示两地友好,也昭示了昭君一生的完满。
不知是不是因为昭君故乡人,心中总有莫名的感慨,我走过她生与死的地方,也算是完成了某种敬礼。昭君墓的门票很有特色,是一张印有昭君风姿的明信片。我写上了家乡的地址,寄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