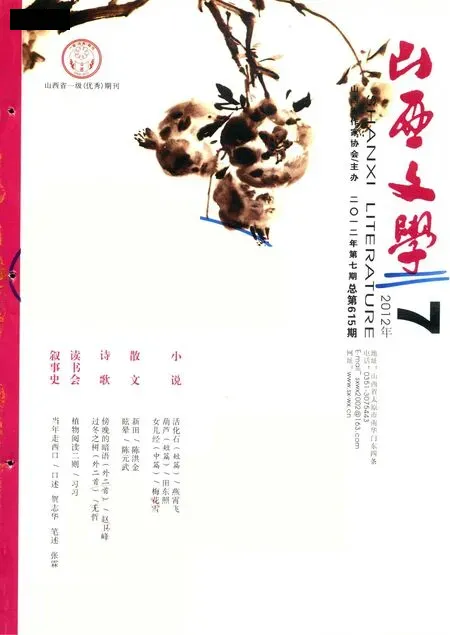当年走西口
口述 贺志华 笔述 张霖
编者按:张霖先生是内蒙古巴颜淖尔市一名非常普通的乡村知识分子,祖籍山西省浑源县。张先生热心民间艺术,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民俗、民风和民歌颇有研究。多年来,他利用带领二人台戏班子下乡的间隙,默默无闻地做着一项工作,就是收集整理老一代人走西口的家族史和个人史。到目前,已经记录了近三十位老人的讲述,蔚成大观,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壮举。现摘发其中一节,以飨读者。
我的家族我的大
我老家在陕西省府谷县贺家脑包,村子就在黄河畔畔上,黄河上去一个山坡坡。河这头是府谷县,河那头是山西的河曲县。
小时候时常听我大给我们说,我家在我老爷爷手上,还是一家有钱人家。出门坐轿,家里头雇长工,在方周二围三十里二十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家。也不知道因为甚,我的老爷爷下世以后,到我爷爷手上,家里头就破落得不行了,穷得连他们这辈子也裹络不住。家里头不光是没了长工短汉,就是弟兄几个也是扭股裂梆,闹不在一搭搭。弟兄几个都成了趴皮货,穷光蛋,反倒给人家打工,自个儿再种几亩地,就成了这么个汤水。
村子里头有个姓贺的教书先生,公家给发的衣帽蓝衫,不用交公粮水费不说,打官司还不用下跪。家里头女人烧茶煮饭,打狗喂猪,一个八岁的儿子,光景过得还可以的。
村里头山坡坡上扔的个碾轱辘,用得太年长了,细了,就舁得扔在那里,废了。有一天,一群娃娃在那耍,耍的是推碾轱辘,有的站在坡坡推,有的站在坡坡下推,摇来晃去。推着推着,碾轱辘忽摇忽摇动弹开了,站在下手的娃娃赶紧往开躲,教书先生的儿子没躲开,一家伙让碾轱辘推得跌在崖底下,跌死了。口里那地方我没回过,听我大说那崖有几十丈深。
儿子跌死了,教书先生的女人当下就疯了。疯跑。闹得教书先生书也教不成,每天就团弄这个疯老婆。后来亲家六人就跟教书先生说:
“人常说,羊群里丢了羊群里寻,她没了儿子,就得给她再闹一个儿子,她有了儿子了,说不定她就不疯了。不过,当下是养不下个儿子来,就是捏泥,一会儿两会儿也干不了哇,该想个甚办法?”
商量过来,商量过去,就把我大抱养在教书先生门下,给人家当了儿子。两头都姓贺,是本家,倒是出了五服。
把我大抱养过去以后,慢慢价,我这个疯娘娘(陕北地方称祖母为娘娘)的病也就好了。将那会儿,我娘娘对我大也倒是挺亲。不过,过了二年养下了我二爹(二叔),再过二年养下了我三爹,又过了二年养下我四爹。就这么几年时间,我娘娘扑溜扑溜,赶天连地又养了三个小子,两个女子,连我大,家里头就六个娃娃了。
自跟有了自个儿养的儿女,我娘娘就不亲我大了,动不动,照住我大的腿上就“嗤”——攮一针锥子。家里头我娘娘当家,教书匠爷爷不管事,也不说让我大念书。我大一辈子大字不识一个,连自个儿的贺字也写不来。其实我大是个挺聪明的人,虽说是没文化,还挺会说话,赶死时候也是精精明明,话说得啷啷价。亲生的娘老子那头家贫,顾不上招护我大,这头还不放,就教给当小长工,娃娃家也做不了多少营生,倒是受不完的气,我大是苦在心上了。
大十五岁那年,我那个教书匠爷爷死了。他这一死,灰下了!衣帽蓝衫也叫人家拿走了,种地还得拿害债,捐税一样不免。那会儿种洋烟了,洋烟的害债越大。我娘娘得惯这便宜了,说成甚也不交。从前我爷爷活的时候不交公粮水费,村子里头的人早就眼气得不行,这会儿我爷爷死了,众人就给囔灰话。公家左一次右一次催,我娘娘软磨硬泡,就是不交。有一天,衙门里头来了两个人,往我大脖颈上拴了一根铁绳,就把他闹在衙门里头,因为我大是家里头岁数最大的男人么。就这么着,人家年年催,我娘娘年年不交,隔个三月两月来一趟,把我大逮上走,关上个一月两月,就又放回来。年年如此。
我大二十岁那年秋天,有一天在地里头锄庄稼,天气热,他赤脚光头,上身光膀子,就下身穿的一条裤子,正撇汗流水在那锄地,突然来了两个衙门里头的人,往我大脖颈上扔一根铁绳,就把他拉走了。
走到半路一个村子里头,那两个人把他两个手往树上一吊,脚板子将能着地,人家吃饭歇晌去啦。这个时候,村子里头有个人圪凑在我大跟前,悄悄跟我大说:
“你看你这个后生,真是那铺上豌豆睡觉了——苶在心上了。从古至今,就是养儿当兵,种地拿粮,你妈不给公家交公粮水费,人家能饶过你们?明明知道你妈不亲你,就拿你顶杠子,就这么顶下去,甚会儿是个头?倘若哪天人家着了狠,把你一板子打死,不是完了?叫我看,三十六计,走是上计。你二十来岁的人了,走到哪,给谁家动弹他不给你一碗饭吃?他还能拿针锥子扎你?”
大一听,觉着说得挺对,就说:“是啊,我要是漏开空,就离家呀,跑狗的呀!”
“嗨,你这娃娃,要是打好主意想跑,我这会儿就把你放下来,我不怕这干锅油气,他能把我咋?你不说,我不说,他倒知道是我放的?”
当下,这个好心人就把我大放下来了。我大赤脚挠头,上身是个光不溜,就下身穿的一条裤,手里头提的一把锄,一蹦子倒跑狗的了。
一跑跑在后套
好心人把我大从树上放下来,我大抹开蹦子就是个跑。往哪跑呀?他心里头也没个数,就是个瞎跑,跑在哪算哪,反正跑得越远越好。
跑啊跑啊,看见路上吱吱扭扭几挂二饼子牛车,就走上去打听。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也是些府谷人,他们拉的枣啊、核桃呀、果子呀,相跟上去后套换粮去。我大就跟人家说:“把我也拉引上哇,我能给你们做营生,给我一口吃的就行。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你们说合得给我寻个吃饭处。”又把自个儿的遭际榫长卯短、一五一十的学说了一遍。这些人看见我大挺可怜,就把他引上了。白天,跑前跑后给人家赶车,黑夜喂牲口,反正是一路上脚不彻地做营生。
就这么,白天走,黑夜住,七拐八绕,一路上的辛苦就不能提。从府谷起身,拉拉溜溜,摇筛着硬硬走了有二十来天,走在了后套四坝的杨柜。掌柜的叫杨米仓,是河曲人,跟我们就隔得一条河。人家走口外走得早,倒在这地方立站住了。
住下以后,这个人给掌柜的送点儿核桃、枣儿,那个人给送点儿葡萄、果干,为的就是通融掌柜的能买点儿东西。掌柜的把东西收下了,他们才跟人家说:“掌柜的,你看我们也挺可怜,家里头也没个甚收成,过不了,这么远从府谷拉上些儿这东西,想换点儿吃的,看掌柜的能不能帮办一下?”掌柜的心眼儿不赖,说:“那行了哇,你们那么远从口里来在口外,我也知道你们艰难。不说了,说起来咱们还是亲戚。”
这是怎的回事了?他们来在杨柜上以后,掌柜的就一个一个问询,你姓甚叫甚?家是哪的?他姓甚叫甚?家是哪的?我大说我是贺家脑包的,姓贺,就问我的老爷爷叫甚,我爷爷叫甚。闹了半天,我家跟掌柜的还是挺远挺远、兔儿棒也打不住的个亲戚,也不知道几辈子扯拉下的亲戚。实际上谁也不认得谁,那就搬都甲,我们家是崇宁都九甲。攀清了辈数,掌柜的就跟我大说:“咳,后生,你可是该叫我姑父哩。”
掌柜的挺好,这个三斗,那个五斗,都给换了一些儿粮食。
他们临走的时候,就跟掌柜的说:“掌柜的把这个后生收留下哇,你们柜上多少人伙雇哩,这是多大的桩马!反正是从外头也得雇人,雇谁不是个雇?收留下他,给他多少算多少,我们也就不用再领他了。再说你们还是亲家了,他还叫你姑父了。”掌柜的挺痛快:“行了行了,这么还不行?雇谁也是个雇么,留下哇。”
就从这儿,我大就在后套扎站下。我大活到这这会儿是一百零九岁了,他那年二十岁,这是八十九年以前的事了。
就这样,大留在杨柜上,那一蹦子没白跑,总算跌落在个地方了。一个人来在后套,是单膀孤人,少亲没故,只有柜上是他的点儿靠。他也就一心一意好好给人家做营生,掌柜的教他做甚,他就做甚。
年年起来,从春天到秋天,就在地里头动弹。到了冬天就赶上牛车,拉上白面呀、胡油呀这些东西,给柜上往包头送,回来时候再拉上东西,反正人家叫拉甚就拉甚,人家柜上在包头街上有买卖字号。后来,我大当了二头儿,长工头儿,领导长工们动弹,他也动弹。除了工钱,二头儿每年能多挣五亩捎种——所谓捎种,就是掌柜的给你五亩糜子地,秋天这五亩糜子不管打多打少,都是你的。
我大来在后套第八年秋天,快到冬天了,他往包头给掌柜的送东西,突然在包头碰见了我三爹跟我四爹,也就是他底下的三兄弟四兄弟,弟兄两个拉的瓜桃李果来后套换吃的。我大离家那会儿,我三爹我四爹也倒十四五、十五六了,虽说是分开七八年了,一见面就认了出来。弟兄三个抱头就哭。
我三爹说:“自从叫公家把你弄上走了,只估划你叫公家害死了。妈妈思谋咱们不给人家拿害债,把你左一次右一次铁绳拴走,叫你受了不少罪,还丢了命。妈妈一到时分八节就给你烧钱挂纸,哭得,说把她小子害死了。”
我大就把他在家时候怎么艰难,怎么来在后套,给两个兄弟跟头至尾学说了一遍,说实在是熬炼不出来,才想起跑到后套刮野鬼。把裤子抹起来叫他们看,腿上一个一个,尽是叫锥子扎过留下的肉疙瘩。
二爹,三爹,四爹,都是些儿老实人,都不会说话,弟兄四个还就数我大会说话。兄弟几个从此拉扯开,只要一来后套,就来找寻我大,互相也有个照应。
半道捡下我的妈
有一个甘肃的买卖人,专门做羊羔皮生意,每年过完年就来后大套,跑羔买来杀了卖肉,留下皮子专门加工,再卖给做跑羔皮生意的。他年年来后套,跟好多羊主家都挺熟。年年不等羊羔羔产下,事先就跟羊主人家定好了。他给的价钱比大羊还高。杨柜上有一百多个大羊。一来二去,成了杨柜上的老熟人,不管甚时候,来了就住,不想住了就走。慢慢地,这个人就起了灰心,他把老婆娃娃丢在甘肃,长年住在杨柜上不回家了。
民国十七年,甘肃遭了灾,那年不光是甘肃,好多地方遭了灾。他老家有老婆,还有两个儿子,没人管,眼看的就要往死饿,家里头最值钱的,是两个骆驼,两头毛驴。岳父怕把闺女外甥饿死,就搬上这一家三口人上后套来寻女婿,把行李驮在骆驼上,大人娃娃也骑在骆驼上。来在后套杨柜上,就说:“女婿的,老婆娃娃我是给你领来了,骆驼毛驴我也给你拉来了。咱那地方往死饿人哩,你这老婆娃娃,不管不行,管,我连自个儿也顾不下。你就把你这老婆收拾上,活,是你的人,死,就是你的鬼,甚会儿你不想要了,你看往哪扔往哪扔,不能给我扔下。”把闺女外甥安顿好,岳父就回老家了。
老婆娃娃来了,他也没蛋弄了,他的老婆,他的娃娃,他不收揽谁收揽?掌柜的一看这事儿,就跟我大说:“你去场面,把那个看场房子收拾收拾,叫他们这一家住在那儿吧。”
不想,这家人在这个房里头连头带尾只住了四十天,男人就得了个出水伤寒,三下五除二,就把个人死了。
他死了,掌柜的就跟我大说:“我说元亨,你看你遭际这么苦,叫我说,你就把这个女人搂揽上哇,总算是一家人家。若不然你混一年又一年,这倒来了八九年了,终究不是个事。”我大思谋,就凭自个儿揽长工挣这几个钱,谁家敢把闺女给你?二十大几的人,闹不好敢打一辈子光棍。事到如今,就不能说那丑俊、岁数大小、有娃娃没娃娃了。怕是过了这村,就连这店也没了,管毬他,我这会儿还能说那声和名?
掌柜的又跟这个女人说:“你看,你的男人死了,你在这地方是又没亲、又没靠。回老家吧,那么远的路程,你娘们三个怎么回?就是回了老家,那地方遭了灾了,还不是个往死饿。要是留在这地方,该叫谁收揽你们?你这是天不收、地不留。唉,正好我这儿这个引工头儿也是一个人,你不如就跟他格络成一家,他的命也挺苦,不过,养活个你是不成问题。”其实这个女人,男人一死就犯了愁了,知道老家难回,后套住下,吃甚?喝甚?这一家三口算是困在干滩上了。如今好容易掌柜的给说这个男人,这倒是个坎门儿,甚不甚,三口人饿不死了。
没有新铺新盖,也没有典礼仪式,更没有吹吹打打,就这么着,两个苦命人把烂行户往一搭搭一搁,就成了两口子了,就在那个场面房房里头。
这就是我大,我妈。那年,我大二十八岁,我妈二十九岁。
我大我妈成了一家,两个苦命人凑在一搭搭。我妈觉得自个儿走到这个地步,我大不嫌她半老徐娘有娃娃,不仅救了她,还挺体贴她。我大呢,虽说是有亲娘老子了,弟兄好几个,偏偏儿把他抱养给别人,走到哪家都是个多余的,他挺记恨他那亲娘老子。抱养到那家,娘不亲便罢,还时常用锥子攮,老子倒是对他好,偏偏死了。如今总算有了自个儿的家,不用再受别人的气了。又遇上这么个好掌柜的,遭逢了两个娘,还顶不上一个掌柜的杨米仓。两个人这就一心一意刨闹这个穷光景,作务好两个娃娃。
掌柜的给我大指了一片地方,说:“元亨,你这也算有了家口了,从今以后就立起锅灶了。你套上牲口开地去,开多少算多少,种地也不用你拿害债,要是缺短甚家具,你就上这儿来。”这就够好了吧!受苦人么。
后套那时候满滩都是红柳、哈苜儿、枳芨,我大就没明没夜掏这红柳、枳芨、哈苜儿,开了有四五十亩地。打起堰坝,挖下沟渠,把地一耕,撅起屁股刨闹了一春气,浇了一水,紧赶慢赶种上了热水糜子。
我大在地边上盖了个茅庵房,全家就搬在这儿住。我姐姐就是在这个房房里头生的。住在这儿,虽说是新开的地,庄稼也还可以的。就是吃水不方便,人畜口吃水,每天都得去三四里以外担挑。最麻烦的是,每年还得去给公家应差,我大一走,家里头这四口人就没人管了。
那时候我娘娘、我二爹、我三爹、我四爹也来在后套了,住在了李七圪旦,那里有我娘娘的侄儿子,算是我二爹的姑舅。我二爹、我三爹在口里就问过媳妇,我四爹是在李七圪旦娶的媳妇。我二爹劝我大搬家吧,看搬在李七圪旦行不行。在四坝住了三年,全家就搬在了李七圪蛋。
李七圪旦在四分滩对过的黄河南面,村子里头有三十来户人家,也种地,也放牧。这个地方的人情不好,欺负外路人,我们那些亲家没有势力,帮不了忙。我大的姑舅说:“不行,你们在这儿住不成,搬家哇,搬在河对面的郝家圪旦吧。”在李七圪蛋住了还不到一年,又搬在了郝家圪旦。
郝家圪旦跟李七圪旦对打对,一个在河这面,一个在河那面,都在黄河畔畔上,这儿的黄河不宽,有一里多二里宽。郝家圪旦离四分滩、黄济渠不远,这个地方在沙窝里头,叫倾塔毛沙窝,满眼尽是红柳、枳芨、哈苜儿。
在这里住下,收拾盖房。那会儿,盖房就是用土坷垃垒摞。土坷垃好说,遍地都是寸草滩,齐管你拿锹裁,裁起来把底子铲平,就能碴墙,要多少有多少。碴墙也省事,不用焊泥,坷垃垒摞成个墙,再往墙墙上抹上一层泥就行了。那地方到处都是红柳、河柳,拣那粗点儿的做檩子,细点儿的做椽子。房上先铺柳条子、枳芨,上头再铺上一层麦秸子,一抹泥就行了。用红柳条子编了两个片子,两个片子当中填上些儿麦秸,这就算是门了。因为没有长点儿的檩子,盖起的茅庵房房是有长没宽介,长有一两丈,宽才六七尺。不过,这就够好的了,不管咋说,一家人总算有个住处了。
刚刚在郝家圪旦住下没二年,我妈就死了。
有一天,我大哥在野滩里头放牛,走到一个小土地庙跟前,瞄见小庙里头住着个野猫。他就慢慢、慢慢凑小庙跟前,把野猫儿盯在小庙里头,一顿放牛棍,就把野猫儿打死。
那会儿人穷,吃不上肉,我大哥就把死猫提溜回家,炒吃猫肉。那天正刮大风了,风把门窗刮得哗啦哗啦,我大哥就拿被子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炒猫儿肉的烟气也跑不出去。我妈正害汗病,一个多月了,拉拉溜溜不见好,一闻这油气病更重下了。从这开始,我妈病得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重,五天头上就殁了。
我妈咽气时候,我还在我妈的奶头上吊着,是别人硬把我揪下来的,那年我才三虚岁。
穷得要甚没甚,哪能闹上棺材?寻了两片囤笆子,枳芨编的。两条囤笆子,一条在上头,一条在下,把我妈放在当中,上下再拿草绳一捆,就算是棺材了。我大和我大哥两个人把我妈舁上,我二哥拉的一把锹,在后头跟的了。舁在沙窝畔畔跟前挖了个洞,就这么把我妈埋了。
唉,真叫黄土埋人了,我妈殁那年三十九岁,来在人世上走了这么一遭,养了四个儿女,一辈子就挣了两片囤笆子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