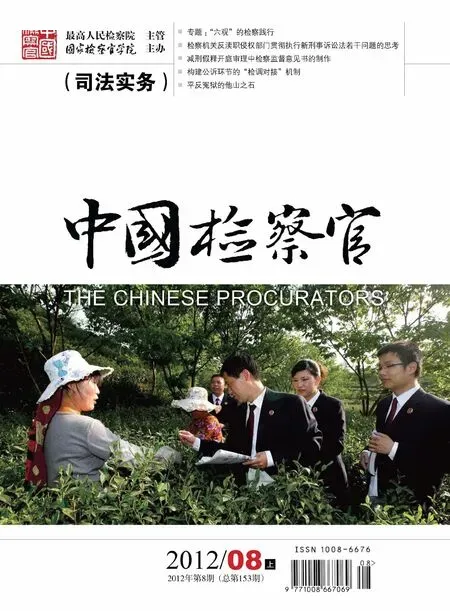论存在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
文◎陈 刚*
论存在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
文◎陈 刚*
任何法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处在一定的有机联系当中,并由此产生了关于法条之间关系的理论。法条竞合关系即是其中的一种理论,它是刑法适用中的一大难点,在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思考过程中运用较多。本文中笔者试在构造自己的法条竞合理论体系,以求理论能够正确指导实践,也为司法工作者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法条竞合的本体
(一)法条竞合的概念特征
所谓法条竞合,是指刑法典中存有两个或数个在理论上或个案中犯罪构成具有包含关系的法条,当一行为在形式上同时触犯了此种具有包含关系的法条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当然排除适用其它法条的情况。现将概念中反映出来的特点总结如下:第一、行为人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法条竞合是罪数理论一罪分类中的实质的一罪,实质的一罪要求要求行为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否则不发生法条竞合的问题;第二、形式上符合数个不同的犯罪构成,这是法条竞合与单纯的一罪的根本区别;第三、数个犯罪构成在理论上或仅在个案中具有包容关系。包容关系是此理论的核心,也是本文的基石。

包容关系可以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包容关系是指一个罪名的外延是另一个罪名外延的一部分,并且外延宽的罪名的犯罪构成内容已超出外延窄的罪名的情形。用图例表示包容关系的部分,既是图1的情形,而不是图2(交叉关系)、图3(分离关系)的情形。体、犯罪主观方面的任何一个或几个的包含与被包含。必须明确的是,除了有包含关系的部分以外,其他部分必须一致或高度一致,不允许有交叉或分离的关系。如271条的职务侵占罪和382条贪污罪,二者的犯罪主体不同;再如270条的侵占罪和264条的盗窃罪,二者的主观要件等方面不同。此两组罪名不可能是包含关系,而是交叉关系或分离关系,此二种关系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内容。此种关系罪名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但是,笔者认为在理论中不具有包含关系的法条有可能在个案中具有包含关系,进而形成法条竞合。如266条的诈骗罪和279条的招摇撞骗罪,理论中二罪名在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行为方面是交叉关系,如果个案中的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的不是地位或其他,而是骗取钱财,则在此个案中二法条就形成了法条竞合关系,应适用法条竞合的处断原则。因此,讨论法条竞合就必须在个案中进行。
综上,在法条竞合中,行为人的一个犯罪行为要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构成,其诸种事实特征必须在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基础上有过剩部分。而对另一个犯罪构成来说,其诸种事实特征正好完全与之相符,就是说另一犯罪构成恰好是对该一犯罪行为的最全面、最恰当的法律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某个案中另一犯罪构成就必须囊括前一犯罪构成及其过剩部分,从而产生包容关系。
(二)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
哲学上要认识一个事物,除了深入了解其本质以外,还必须在与其他类似事物的比较中从该事物的侧面进行认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是比较相似的事物,要深刻认识法条竞合,本文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简要的区分:第一、犯罪构成要件不同。法条竞合只有一行为、一罪过和一个刑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被侵犯;想象竞合是一行为、数罪过和数个刑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被侵犯。第二、竞合成因不同。法条竞合形成的原因是刑法规范本身,想象竞合形成的原因是个案中犯罪行为的特征。第三、处理原则不同。法条竞合是实质的一罪,只有一个法条才是对行为最全面、最准确的法律评价;想象竞合是处断上的一罪,任何一个法条对其进行评价都可以,为保障罪行相适应,其在处罚上采用的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二者的区分标准是我国刑法理论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在相似概念关系问题上,本文赞同“不可能划清界限的,我们不必重视他们之间的区分标准,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他们之间的界限”这一说法,越是所谓界限模糊的概念,越不宜讨论二者的界限。因为越是界限模糊,越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复杂、难以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关系即是如此。但如果忽视这种区别,从理论的二者的争议中解脱出来,放眼个案的适用过程,或许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考虑到在不违反罪行相适应的情况下,许多个案在适用二种竞合的处理原则时都有极大的相似性 (如法条竞合的重法优于轻法原则与想象竞合的择一重罪处断原则),在确保论述合理性的前提下,若忽视二者的细微差别,以处断结果为标准,在复杂的个案中以“大竞合观”来分析显然能简化思考过程,并且殊路同归[1],更符合现代刑法的价值和发展趋势。
二、法条竞合的种类
考察我国刑法分则各罪名,笔者认为我国的法条竞合——准确地说应该是法条竞合中的包容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一)因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逻辑关系而形成的法条竞合
这是指当两个刑法规范之间具有特别法和普通法关系时形成的法条竞合。根据通说,所谓普通法,是指在一般场合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特别法则是指在普通法规定的基础上所作的特别规定,以适用于特别场合的法律法规。二者是相对而言的。
刑法中有许多具有此种关系的规范。如刑法第140条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第141条的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第115条第2款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264条的盗窃罪和127条的盗窃枪支、弹药罪,277条的妨害公务罪和368条的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397条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398条至419条的各类故意性渎职罪,等等。
(二)因具有整体法与部分法关系而形成的法条竞合
这是指当两个以上刑法规范之间具有整体法和部分法的关系时形成的法条竞合。根据通说,所谓整体法,是指当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刑法规范,这数个刑法规范之间具有吸收关系时,能够全面充分地评价该一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文;部分法是指在数个刑法规范之间具有吸收关系时,被吸收的内涵小的法律条文。二者也是相对而言的。一般情况下,整体法包含了两种以上法益的保护;部分法则只包含有一种法益的保护。
如363条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与364条的传播淫秽物品罪;238条的非法拘禁罪 (并致人重伤或死亡)与235条的过失致人重伤罪、233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194条第1款的票据诈骗罪和266条的诈骗罪,382条的贪污罪和384条的挪用公款罪,等等。
如何区分法条之间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还是整体法与部分法的关系?笔者认为,运用形式逻辑的知识能够较好地解决此问题。在形式逻辑的概念分类中,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集合体,可以分成集合概念和类概念。类概念说明的是对象的数量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类概念与单独概念的关系是普通与特殊的关系。集合概念说明的是集合体由若干个个体组成,集合体与个体的关系相当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2]。笔者认为,运用上述概念的分类基本能解决此问题,但它还没有说到二者的本质区别,为使大家更好地理解,笔者尝试用一句话概括集合概念和类概念的区分标准,即:看是否需要抽象思维。如果需要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概念,则是集合概念;反之则为类概念。例如“树”是从“杨树”、“松树”等概念抽象出来的概念,因而它是集合概念;而“森林”相对于“树”来说是具体的概念,无须抽象把握,因而它是类概念。下面笔者将结合几组相关罪名,尝试运用上述知识来对法条竞合理论中的两组概念——普通法、特别法与整体法、部分法——进行区分。
对于第345条的盗伐林木罪和第264条的盗窃罪,笔者认为其同时符合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特征和整体法与部分法的关系特征。因为从犯罪对象来说,“林木”与“物品”是个体和集合体的关系;从犯罪客体来说,“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活动和林木的所有权”与“物品的所有权”是类和分子的关系。同理,如194条第1款的票据诈骗罪和266条的诈骗罪等,也是这种关系,而无论适用下文中的哪种处理原则,都是殊路同归,在本文理论体系下不会产生矛盾。
我们习惯了遇到何种情况遵循何种原则以解决何种法律适用难题,却时常忽视之所以运用此种原则的道理,以至于碰到复杂的案件时不知如何运用法条和正确说理。追根溯源,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正是区分标准问题。处理好了这个问题,在个案中运用处理原则就变得容易多了。
三、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
根据上述论述,法条竞合是实质的一罪,只有一个法条才是对行为最全面、最准确的法律评价。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法条竞合犯“虽然呈现出只是符合复数构成要件的外观,但是由于其构成要件具有相互的逻辑上的包含关系,实际上不过是受到其中的一个构成要件的评价”。考察成文法和刑法理论,笔者认为我国法条竞合有以下三个处理原则:
(一)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
其中的法理是为了遵循刑法特别保护的社会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当特别法不能够完全包含一行为的全部特征时,才能够考虑适用普通法,此时普通法类似于一个兜底条款。面对个案,当不能适用特别法时,司法工作者要重新考察犯罪构成要件,“目光不断往返于行为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分析认定普通法是否合适,不能不经考虑一律兜底适用。
(二)整体法优于部分法原则
其中的法理是刑法应全面评价一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当一行为同时触犯整体法和部分法的法律规范时,部分法只能评价其对一种社会关系的侵害,而整体法则可以评价其对多种社会关系的侵害,此种个案中适用整体法更为合适。
(三)重法优于轻法原则
其中的法理是为了贯彻罪行相适应原则。一般情况下,刑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就已经处理好了罪行相适应,上述二原则也能够体现出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但在个别情况下,由于刑法制定的复杂性或出现所谓的立法疏漏,也会出现适用上述二原则后违反刑法原则的情况,此时应适用第三个原则。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适用。
这里的“特殊情况”是指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法律明文规定按重罪定罪处罚。其成文表述一般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149条第2款。第二、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按普通法条定罪量刑,但对此也没有作禁止性规定。但当刑法成文规定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时,禁止适用普通法,如266条的规定。或者虽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从刑事立法精神来看,明显只能适用特别法条时,禁止适用普通法条。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会出现适用第三个原则,是有些个案会出现适用特别法处罚偏轻的情况;而笔者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整体法处罚偏轻而部分法处罚偏重的情况。
为了使刑法的适用具有国民可预测性以及司法的规范性,刑法和司法解释也不乏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具体成文规定,例如2010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行为人实施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此规定是第三个原则的直接成文表述。在此,我们也可以解构解释者在制定第五条时的思维过程 (以225条的非法经营罪与140条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系为例):首先,依据形式逻辑和刑法理论,225条与140条的关系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能够实现罪行相适应;其次,特殊情况下,在数额超过某一数量时,认定此罪会导致处罚偏轻;最后,为实现罪行相适应,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由此可知,这三个原则的适用不是平行的,而是有层次的。应首先适用第一和第二个原则,当不能达到能罪行相适应并且没有禁止性规定和不违反刑法精神之时,才能运用第三个原则。某种程度上说,第三个原则充当的是一个矫正的功能,起补充的作用。现在许多著述已经把“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列为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之一了,司法工作者也应该具备这种理念,在没有成文规定的情况下,也能运用理论知识很好地正确适用刑法和深刻说理。
注释:
[1]此思维方向未尝不可创建一个新的学说,有待学者继续探讨。
[2]出处同上。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检察院[51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