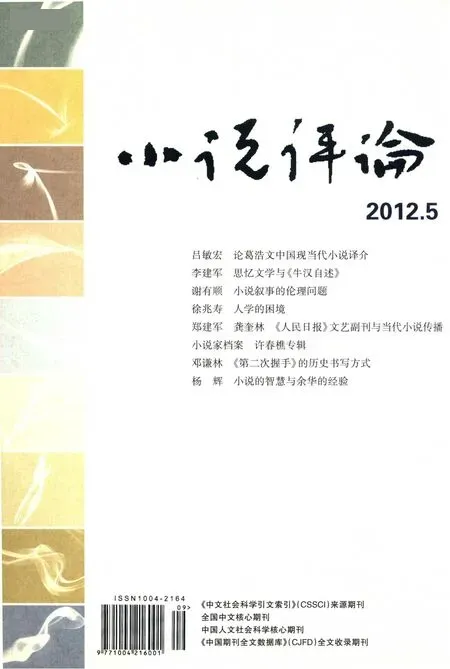论葛浩文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
吕敏宏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可根据译者的母语和经历分为本土、海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三种译介模式。本土译介,由于译者母语为汉语、大多生活在国内,外文创作的功力有限,对国外阅读市场缺乏深入了解,其译文难以吸引国外读者,不能在国外阅读界产生真正的影响。由于近年来华裔学者多集中于学术研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学者日渐减少,以林语堂为代表的海外华裔学者译介模式也逐渐式微。而汉学家译介模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加入这一行列,甚至在美国形成一股热潮①。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便是汉学家译介队伍中的头号人物。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已译介了中国大陆及港台的近30位作家的40多部现当代小说,夏志清称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②。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喻其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接生婆”。“在他翻译之前,那些有意于探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读者不得不忍受那些失去了原文生气的呆板译品”③,他所做的工作被认为对其后继者具有“启示性”④作用。那么,葛浩文如何踏上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之路?取得了哪些业绩?他的译介采取了怎样的原则和策略?本文将对葛浩文译介中国现当代小说做一述评。
一、葛浩文生平简述
葛浩文,美国加州人,生于1939年。1961年毕业于美国加州的长滩公立学院,获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半年,在完成了军官学校十六个星期的训练后,他被派往台北服役。服役之余,葛浩文把学中文、看书当作最大的消遣。就在这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葛浩文慢慢认识了台湾,爱上了中国文化,他的中文也提高了很多。1964年2月他离开台湾,一年半后再度回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正正规规学了约一年的中文。此时的台湾已俨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1968年葛浩文因父亲过世回到美国。茫然中,他又踏入旧金山州立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1971年他毕业于该校,获得硕士学位。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汉语教师后,他又进入印第安那大学东亚语文系博士班继续深造,师从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柳无忌先生。学习期间,他涉猎了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最终以萧红研究为其毕业论文选题。1976年,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专著《萧红》(Hsiao Hung)一书,由波士顿的Twayne Publishers出版社出版。1985年,这部专著由他的朋友、旧金山州立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郑继宗翻译成中文,以《萧红评传》为名,由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评传资料详实、论证充分,浸透了作者的心血和情感,成为研究萧红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文献之一。2011年6月3日,在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举行的首届“萧红文学奖”评选中,葛浩文以其《萧红评传》获得萧红研究奖。
葛浩文1974年从印第安那大学博士毕业后,受聘任教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1984年他创办了学术性刊物《中国现代文学》,做了15年该杂志的主编。1988年,他到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任教。之后,他又在圣母大学做教授,讲授中国文学、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他还以编委的身份参与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一些中文文学、文化出版工作,同时亲自主编、参编了数种汉语或英语语种的有关中国文学的图书。并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泰晤士报》(The Times)、《时代周刊》(Times)、《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二、扎实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常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先在国外“火”起来,然后才在国内“走红”。我国新文学时期的女作家萧红便是如此。由于种种原因,萧红在我国文学史上长期名不见经传。第一个研究萧红及其作品,并肯定其重要价值的学者竟然是一个外国人,他就是葛浩文。他是出了名的“萧红迷”,自称萧红是他“隔世的恋人”⑤。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文学研究在美国还相当冷场,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与当时中美关系的僵局以及当时中国文学的萧条状况均有关系),更别说关注萧红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葛浩文自己也觉得在美国研究中国新文学颇感“孤独”,力量单薄,他借用萧红的同名作品声称自己的努力仿佛是“旷野的呼喊”,无人听得到,并感叹道“不但我所认识的同行朋友们只有一、两位曾经读过《呼兰河传》,连夏公(指夏志清)的力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只提过萧红的名字一次”⑥。如果说,与萧红同时代的鲁迅发现了萧红的天分与重要性,那么可以说,是葛浩文还以了萧红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英国汉学家詹纳(W.J.F.Jenner)在其《中国可能有现代文学吗?》一文中认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除了“巨人阶级”鲁迅外,还有一些新近才被发掘出来的“新”作家,颇具现代性,其中一位便是萧红。詹纳特别在注释中说明,葛浩文把萧红带到西方世界,功不可没。与葛浩文交往甚密的刘绍铭教授(Joseph S.M.Lau)则补充道“其实……葛浩文在推介萧红作品给她同胞所做的努力,也一样功不可没”⑦。博士论文的完成和出版只是葛浩文中国文学研究的起点。从那以后,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由萧红再到以萧军和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继而转到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直至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身在美国,葛浩文更加关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状况。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从美国学者的研究情形谈起》一文中对比了美国七十年代以前和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由于政治原因,七十年代前期与后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差别较大,1972年2月中美关系恢复,在美国重新引发了“中国热”。正如葛浩文的研究所示,美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日益兴盛起来:研究的人数及研究的成果逐年增加;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活动也是“非常热闹”;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活跃起来,已有系列译本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刊除了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又增加了《中国现代文学通讯》;学术刊物上也时常可以见到一两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在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事情”。
但葛浩文也敏锐地看到了“热潮”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大部分当代作家的成就还没有评定,美国学者研究的作家和作品大部分是三十年代以前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如沐春风,生发出勃勃生机,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小说,到先锋派文学,中国文学一路走来,逐渐摆脱了十七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开始回归“人学”的文学之路。葛浩文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也随之从中国现代文学转入中国当代小说。通过对中国当代小说及其在美国传播状况的一番研究,葛浩文越发清晰地看到了在美国译介中国当代小说的作用和意义⑧。首先,从中国作家的角度出发,他认为,通过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推广,能够使中国当代作家观照到世界文学的趋势,写出顺应世界文学思潮的作品,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承认,也可以使中国当代作家深深感受到自己将被重视,自己的作品也将成为世界性作品,从而产生强大的创作欲望;其次,从西方读者的角度出发,他认为,通过学者们对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和推广,可以使西方读者渐渐地喜欢中国文学,并在他们心中扎下根,从而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当今的生活方式和状态。
同时,他以一位多年研究中国文学和喜爱中国文学的外国朋友的身份,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诚恳而谦逊地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建议,不仅要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及重要作品的研究资料,还要鼓励当代作家积极创作,提高当代作品的质量。葛浩文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事业之初,便确立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原则,他认为“任何一位学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论是对作家,或是对作品,乃至于翻译,绝不是仅凭着个人的好恶,其选定必然经过多方面的考虑⑨,他还明确提出学者研究、翻译中国文学的四条基本原则:第一、这些作家的成就;第二,这些作品的水准和风格;第三,这些作品翻译后是否有相当的读者;第四,当前世界的文学思潮。这些原则也成为他后来进行小说翻译的准则。
葛浩文对文学极为敏锐,对作品的理解也十分深刻。从其翻译的《干校六记》(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Downunder”)的《译后记》中,即可看出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功底。他非常欣赏杨绛平淡的写实风格,他认为,杨绛的这部作品反映了文革时期的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却很少直接提及任何与文革有关的人物或事件。他不仅能够体会出杨绛幽默而又辛辣的笔调,甚至还能够读出文中隐含的意义。比如,他能品味出该作品细腻且富含寓意的风格(subtle,almost allegorical style)。他认为该作品不像一般的“伤痕文学”那样,并不在文字表面提及任何敏感字眼,然而对时事的针砭与讽刺却深深地隐藏在文字背后。作品从不提及“四人帮”的字眼,只是偶尔的暗中指涉,比如,他认为Tigre Mountain一词指涉江青,因为《智取威虎山》是江青的样板戏之一,很多国人也未必能从这一地名做出此番联想。因此,在他看来,《干校六记》是一部寓意极为深刻的作品。他说“如果说杨绛的风格低调,这种说法本身低估了这部作品;如果说杨绛对这一时代的重大事件避重就轻,则完全误解了这部作品。诚然,书中所描述的完全是个人遭遇,而且似乎显得十分平凡。但是,正是这种平淡,加上偶尔的几段辛辣而又一针见血的议论,才使得文章具有如此感人的力量”⑩。应该说,他对杨绛的风格及作品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对于一位外国人来说更是难能可贵。他还能够从作品中读出诸多的主题,如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社会和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浪费;中国乡村的落后;“运动”的本质,以及牵涉到此运动中的人们的行为举止。由于身份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他甚至还能够抛开作品的时空性,看到作品更富人性的主题,即夫妻之间的深厚感情,因此,他认为《干校六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部爱情小说,可谓见解独到。
葛浩文用英文或中文撰写文章,有时也会把自己的一些英文文章翻译成汉语。“中国现代小说概论”一文便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前言中说明,此篇长文是应杨力宇和茅国权之邀,为他们所编撰的《中国现代小说——历史及鉴赏指引》⑪一书所撰写的一章,该书由美国郝尔公司(G.K.Hall)出版。原文共分三个部分,葛浩文自己翻译出前面两部分,收入《弄斧集》,“供爱好中国现代文学者参考”。该文以时间的发展脉络为线索,以文学团体及作家为单位,分三个时期介绍了从1917年到1949年的中国文学思潮及文学作品 ,即 肇 基 期(1917-1927)、成 长 期(1928-1937)以及抗战和内战期(1938-1949)⑫。该文最大的特色是,文后附录了非常详细的资料索引和参考书目及相关史实的详细注解,内容详实、论点清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精湛程度,令人感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自译还体现出他扎实的中文写作功底。下面以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学派”和“文言文派”或“学衡派”之间的论战的一段评议文字为例:
在此期中的大多数加入文学论争的作家中,大部分古文造诣甚深,但由于他们对新思想的热中(衷)和献身,使他们觉得只有全盘否定正统固有文化才是唯一解救中国文学之路——即使壮士断腕都在所不惜”⑬。
文中的“古文造诣甚深”、“全盘否定正统固有文化”、“壮士断腕”、“在所不惜”等字眼不仅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还透出一股中国新文学时期的措辞意味,若不知道,还以为是哪一位中国学者用母语写就的一段文字,而那股中国新文学时期的“味道”,恐怕与作者长期阅读、研究中国新文学时期的作品有相当关系。
三、卓著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业绩
葛浩文的研究和翻译相辅相成,始终跟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二战后,由于 宾 纳(Witter Bynner)、潘 恩(Robert Payne)、韦利(Arthur Waley)等人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美国学界和民众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1945年以后,美国的一些大专院校开始开设有关中国文学的课程;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限的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本在美国一版再版⑭,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还非常少见。在70年代之前,除了葛浩文所在的旧金山大学等极少数高校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可能得益于柳无忌在该校任教)之外,美国的各大学校几乎都没有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葛浩文曾经根据美国现有的图书资料,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英译状况作了一番认真的调查,并将这些英译本一一列出。面对一份数量甚少的译本清单,他不无感叹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成就是那么高,作品是那么多,于七十年代以前,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流传的却只有这样的极少几本,而《骆驼祥子》和《八月的乡村》更是早期完成的,实在是少了些”⑮。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遗憾,葛浩文开始尝试着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1975年,他与郑继宗合译了东北作家萧军的《羊》(Goat),后来他又翻译了萧红的若干短篇小说。70年代末,他与台湾著名的文学杂志《中国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的创始人殷张兰熙(Nancy Ing)合译了台湾小说家陈若曦的短篇小说集《尹县长》。很多读者通过这部译作,第一次认识了葛浩文。该小说英译本的标题标榜“中国文化大革命小说集”,1978年出版后书评如潮,一些相当有影响力的刊物如《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都纷纷发表了书评。那时,正值中国从十年浩劫中清醒过来,中美外交关系也刚刚恢复不久。这些都大大地激发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
1979年,葛浩文翻译的《呼兰河传》与《生死场》合集英文版出版,他在“译者前言”中,特意说明了译文所选用的版本问题。版本的差异是翻译《生死场》所遇见的问题之一,当时在手的两个版本,一个是1935年的原版本,另一个是1957年的香港再版本。他认为后者的编者对原版本进行了肆意的删改(bowdlerizing editor),其中的许多更正和声明与原本不符,因此,他的翻译采用了1935年原本。他认为,由于战乱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有时变得很混乱,如果能够整理全部的作品是最好不过的,如若有困难,至少应该整理重要的作品,这样不会造成研究上的失误。他认为,这一点对于翻译尤其重要,“如果选用被有意篡改过的本子,那就不只是白费气力了”。
80年代初,外文出版社约他翻译了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Heavy Wings)。自此,他开始接手翻译更多的中文小说。他坦言终于找到他能干好的一件事情,也许是唯一的一件事情。他觉得自己很幸运。1993年,英国伦敦的Heinemann公司和美国纽约的Viking公司同时出版了《红高粱家族》英文版。该书自第一版至今一直没有绝版,不仅为国外读者所喜爱,也成为美国各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必选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版图奠定了基础⑯。其次,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My Life as Eemperor)和莫言的《丰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的英译本相继出版,并引起了国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于2005年5月9日在《纽约客》上发表了题为《苦竹》(Bitter Bamboo)的长篇评论文章,由此引发了美国、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一些文学评论界的热烈讨论,扩大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影响。2008年,由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Wolf Totem)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大陆发行。据企鹅有关人士透露,《狼图腾》英文版截至2011年5月销量已达几十万册。
截至目前,葛浩文已翻译了30余位中国大陆及港台知名作家的40余部现当代小说,其中大陆作家有萧红、萧军、老舍、杨绛、张洁、王安忆、古华、贾平凹、刘恒、李锐、莫言、苏童、王朔、阿来、姜戎、王蒙、汪曾祺、阿城、毕飞宇等,港台作家有陈若曦、白先勇、黄春明、王祯和、李昂、施叔青、虹影、朱天心、朱天文、西西、袁琼琼等。葛浩文曾两度荣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颁发的翻译研究奖,1985年获美国翻译中心罗伯特·佩恩杰出 翻 译 家 奖(Translation Center Robert Payne Award);他与妻子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合译的朱天文的《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获美国2000年度国家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还获得了1999年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评选的年度好书奖。亚洲最大的文学奖——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至今已产生四届获奖作品,其中三届获奖的中国小说,均出自于葛浩文之译笔⑰。2010年9月葛浩文还获得了第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葛浩文的译本不仅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拓宽了了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视野,还无意间为非英语世界的汉学家及译者提供了便利。赵毅衡曾诙谐地说:“当代中国小说最杰出的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往往被其他语言的翻译者用作‘参考’。西方的汉学家,英文还是比中文好读,尤其是文学作品。至少两相对照,省了翻中文字典(一项很耗时间的劳作)。葛浩文为全世界的译本垫了底,却毫无报酬,因为凡是有点自尊的出版社,绝不会承认从英文转译中国小说”⑱。在美国,文学翻译的报酬少得“令人痛心”⑲,译者是不可能单靠翻译谋生的,葛浩文在多次访谈中也谈到这一点,但他却把一生大多数的时间奉献给了翻译事业,因此常常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从事翻译这么一个没有回报的事业,葛浩文这样回答道:
因为我热爱这项事业。我喜欢读汉语;我喜欢用英语写作。我喜欢它的挑战性,歧义性,不确定性。我喜欢创造与忠实之间的张力,更有不可避免的妥协。当我时不时地发现一部令我激动的作品,我的心头就萦绕着一种想要把它译成英语的冲动。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我知道自己能忠诚地为两族民众服务,这给了我一种满足感,它激励我快乐地把好的,坏的,或不好也不坏的汉语作品翻译成可读的,能理解的,当然,还能满足市场的英语作品⑳。
为什么?因为热爱。这是怎样的热情!古稀之年的葛浩文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在推进中国当代小说“西进”的事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译故我在”,如果说文字的书写是自身价值的认同,葛浩文正是以翻译的重写证明了自身价值。
四、译者素养
葛浩文译介事业的成功源于以下三个因素,其一是认真的翻译态度。他说,翻译必须“用心去做”。莫言曾盛赞葛浩文的严谨作风,“他(葛浩文)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与我反复磋商,我为了向他说明,不得不用我的拙劣的技术为他画图。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21]。葛浩文持有读者本位的翻译理念,但始终坚持认真严谨的翻译态度,从来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随意“归化”原文。他的翻译字字句句落到实处,直译的信度和意译的灵活相融合,从而呈现出不落俗套的译笔。
其二优秀的双语能力。葛浩文的中文功底厚实,可用一笔洒脱的汉字撰文。他的老师柳无忌先生为他的中文论文集《漫谈中国新文学》写序,曾这样称赞他,“最使我惊奇的,他不但用他本国的文字写作与翻译,他更用他修习的、也是他第二语言的中文,来发表文章。……在传统的西方汉学界中,学者们于中国语文,及经典书籍,有造诣,能做深邃的研究,成绩斐然,颇有其人;但是他们中间能讲中国话的不多,更谈不到能以中文撰写而在刊物上发表。……美国学者们讲说中国语言的能力,已比一般的欧洲学者为强,但能写作中文的人,依旧稀罕得有如凤毛麟角。至于以若干篇中文著作,收成集子而出版的,除葛浩文外,更不易发现了”[22]。刘绍铭曾经这样评价葛浩文的中文功底,“‘老外’朋辈中汉语修养奇高的大有人在,但能以写中文稿来赚烟酒钱的,只有老葛一人。……他的白话文虽未到诈娇撒野的程度,但确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23]。
翻译的过程是理解和表达,一般人以为翻译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解,即解读原文。然而,葛浩文认为,理解往往是容易处理的一面,可以借助外力来更好地理解原文,而母语表达倒是一个译者的内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译者母语的写作水平才是翻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他的很多同仁译家们花费大量时间研读汉语,以至于丧失了对英语的感觉,翻译时过于唯原文是图,往往使译文大失文采。他一直保持阅读优秀英文作品的习惯,以使自己的英文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他呼吁翻译同行多读优秀英文作品,磨砺英语语感[24]。葛浩文深厚的英文功底不仅在他的译作中有所体现,从他的文学评论及文学翻译评论文章中也能窥见一斑。在《罗体模〈旋风〉吹坏了‘姜贵’:为迈向世界文坛的中国朋友进一言》一文中,他严肃地批评了罗体模对台湾小说家姜贵的作品《旋风》的不负责任的翻译,文笔犀利又不乏幽默。在罗列出几十条“略加检视”便能发现的误译之处后,他引用美国著名文学家吉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的一句话“一本坏书只是一个错误,将好书翻译成坏书,却是一项罪恶”,十分尖刻地说“如此《旋风》英译本稳可角逐今年文学‘罪恶’奖”,并感叹道“如果将来有人再翻译这本书,我们希望下一个‘播风’者要能‘收获’(reap)旋风,而不是‘强奸’(rape)旋风”[25]。
其三,深厚的文学修养。多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经历,造就了葛浩文犀利的文学眼光和深厚的文学修养。他非常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尤其注重作品的文学语言特性,以实现风格的传译。为了使译文能最广泛地赢得读者,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在语言、文化、文学审美等方面的精髓,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取有舍。作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葛浩文的舍弃是有原则的。比如,他处理语言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分析某一语言现象是作者为了某种效果有意为之,还是由语言自身特点所导致。后者可变通处理,前者要尽力维护,以增加文本的陌生化,延长读者的审美体验过程。
就小说翻译而言,葛浩文认为译者的语言必须具有习俗性和时代感(idiomatic and contemporary),而不是华而不实的虚饰(flashy)[26]。此言真亦!小说体裁,再现生活,不连贯之思维、不合“法”之言语、方言等随处可见。这样的作品才会贴近生活,使人触景生情,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中国译者的汉译英作品,每一句话都是漂亮的英文,挑不出任何语法错误,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但是读来就是呆板,没味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够习俗化,没有时代感。葛浩文还非常注重词汇的选择,很少随意删去原文中的谚语、俗语、谐音,并以最大的努力在英文中再现类似的情景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凭借丰富的想象力,选词精当,使得译作的语言准确、形象、生动,创造出良好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读葛浩文的翻译小说仿似读英文原创小说,却并无置身于美国社会的感觉。葛浩文优秀的双语能力和深厚的文学修养不仅使其译文,“写得有个性、有气派、有文采”[27],也使他的译文“在审美价值上完全与原文匹配,和原文一样优雅、生动、充满活力,甚至有的地方胜过原文而又不失准确”[28]。小说翻译,乃至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正在于此:一国之文学经翻译后成为异域文学,从而真正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
五、易化原则
葛浩文十分注重译文可读性,尽可能地在保持原文原貌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手段简化原文,增强译文可读性,我们姑且称之为“易化原则”。其易化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省译,包括某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敏感词汇。
(二)通过事件重组,对小说结构进行局部调整。
(三)删减非叙述评论,使小说情节单一化,结构更加紧凑。
(四)通过对句子的长短、段落的长短、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关系的调整,调整小说节奏,使译文表现出一种普遍适应的节奏,以适合各个层次的译文读者。
(五)通过增加解释性文字,力求小说情节前后贯通。从某种程度上说,前几条或多或少也是为了情节的贯通,增加小说的趣味性与流畅性。
我们看到,葛浩文的“易化原则”力求遵守传统的叙事规约,即采取各种手法保持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连贯性、逻辑性。首先,从主观上讲,葛浩文这一原则取向依据于读者阅读的“优先原则”。所谓读者阅读的“优先原则”,是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籍由文化决定的优先规则(preference rule)在叙事文本阅读中的运用[29]。就小说而言,人们在阅读小说时,习惯上期待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是一个按自然顺序排列的故事。无论小说如何空间化,读者总是希望以最快、最省力的方法建构出一个按自然顺序排列的故事。可见,在建构故事方面,作者和读者处于一种反向的构思方式,也正是这种反向的张力带给作者和读者各自的快乐和趣味。葛浩文的易化原则其实也是他自己遵循阅读优先原则的结果。由于他将自己以优先原则阐释之后的文本付诸笔下,减小了译文读者阅读理解的难度。但是,说他因此减小了译文读者的阅读兴趣却不尽然。毕竟,译文的读者是西方读者,尤其是那些不知有汉的普通英文读者,他必然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其次,翻译的“易化原则”也是市场操作力的作用结果。葛浩文曾坦言,他选择作品翻译的条件只有两个:其一“我喜欢且适合我译”;其二“要考虑有没有市场与读者”[30]。在美国,如果一部书在三个星期内卖不完,就要下架退给出版社,或折价处理,甚至被烧掉。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无疑会影响到出版社和译者。葛浩文承认,他更喜欢有文学价值的严肃作品,但考虑市场需求,也会选择一些轻松娱乐的作品。因此,要想让一部小说译作进入西方阅读界,译作的趣味性、娱乐性也是译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为了让国人更多地了解一个与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首先要让国人“好之”。当初林纾翻译西方小说时,无论是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还是从叙事结构上均通过删节、增加等手段对外国小说作了大量的更改。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外国小说适应中国历来已久的叙事传统,以更好地为国人接受。葛浩文采取易化原则的目的与清末我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颇有相似之处。葛浩文也常常略去小说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卫星事件,使故事紧紧围绕在纵向主干事件的叙事线条上,突出故事的发展脉络,加快小说的叙事节奏,以赢得更多的外国读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很不平衡,我们拿来的多,送出的少。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依然缓慢,中国文学在国外阅读界的影响有限,国外读者的数量仍然很小,葛浩文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他的中文小说英译本的读者群更多的是西方汉学界或学习汉语的人,如西方各个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译中”近三十年来异常火爆,改革开放使得西方的现代文学思潮通过各种形式输入中国,封闭多年的中国文学好像一个被关在狭小空间、快要窒息的人,突然打开了窗子,便开始贪婪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一样,开始大量学习、模仿西方各种文学形式,包括各种小说技巧。对于这一点,葛浩文曾经风趣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作家从没有抄袭(plagiarized)过,他们只是临摹(copied)了不少[31]。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不在于小说技巧,而在于内容和主题。
葛浩文的易化原则使得其小说译本从叙述结构到叙述话语更加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难免与原文作者的创作理念有所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多元文化系统中,西方主流诗学对中国文学的边缘化。然而,文化传播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尤其是小说,趣味性是它的生命力。葛浩文曾经说美国人不喜欢看翻译作品,很多出版社甚至不愿意在作品的封面上注明translated by的字眼。他还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这些作家的英译本在美国的接受状况并不容乐观,首先它们大多由美国的小出版社出版,其次,它们的流传依靠“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很难真正流传”[32]。因此,中国当代小说要真正进入美国阅读界,葛浩文的易化原则也许是某种权宜之策。
综上所述,优秀的双语能力、深厚的文学修养、严谨的翻译态度造就了葛浩文良好的译者素质。凭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精深功底,葛浩文以学者的判断力解读中国现当代小说,又采用文学重写的翻译策略,以作家般的译笔,延续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文学性,以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表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的状况。他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挚爱和坚持不懈的译介,使得更多的中国小说真正进入了英美阅读界,赢得了海外读者,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注释:
①Heller,Scott.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N].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8,2000,47,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A22。
②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第22页。
③④[24][26][31] Lingenfelter,Andrea.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Full Tilt.Issue 2。
⑤这是葛浩文对自己的称号,见“访萧红故里、墓地始末”,《弄斧集》,1884,第97页。
⑥葛浩文:《中国大陆文坛的“萧红热”:萧红传记资料拾零》,《弄斧集》,台北:学英文化事业公司,1984,第66页。
⑦[23]刘绍铭:序《弄斧集》,台北,学英文化事业公司,1984。
⑧⑨⑮葛浩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从美国学者的研究情形谈起》,《弄斧集》,台北:学英文化事业公司,1984,第230-232,225页。
⑩Goldblatt,Howard.Translator’s Afterword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downunder”.Yang Jiang,trans.Howard Goldblatt.Seattle:Univ.of Washington Press,1984.p101。
⑪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History and Appreciation,Winston L.Y.Yang and Nathan K.Mao ed.Boston.Mass:G.K.Hall,1980。
⑫葛浩文文中没有译出第三部分,但他文中有说明,他的分期参考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分期。这里,笔者根据葛浩文的说明为其第三期命名。因为夏志清的第三个分期为“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以后”。
⑬葛浩文:《中国现代小说概论》,《弄斧集》,台北:学英文化事业公司,1984,第279页。
⑭Eugene Chen Eoyang,“‘Artificesof Eternity’:AudiencesforTranslationsofChinese Literature”,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x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p69。
⑯Hampton,Wilborn.Review:Red Soghum[N],by Mo Yan.trans by Howard Goldblatt.New York Times,April.18,1993。
⑰这三部小说分别是姜戎的小说《狼图騰》(Wolf Totem,2007年)、苏童的小说《河岸》(The Boat to Redemption,2009年)、毕飞宇的小说《玉米》(Three Sisters,2010年)。
⑱赵毅衡:《何打倒英语帝国主义?》,《书城》,2002年第8期,第72页。
⑲Daniel Simon.Why We Need Literary Translation Now.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03,19(3),p48-51
⑳Goldblatt,Howard.The Writing life.Wasinton Post,2002-04-28(BW 10)。
[21]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小说界》,2000年第5期,第170页。
[22]柳无忌:序,葛浩文,《漫谈中国新文学》,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80,第3页。
[25]Howard Goldblatt.Book Review on Chiang Kuei by Timothy A.Ross and The Whirlwind by Chiang Kuei and Timothy A.Ross,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2,No.2(Jul.,1980),pp.284-288。
[27]欧怀琳:读翻译 学英文,http://bbs.cenet.org.cn/html/board92525/topic73808.htm。
[28]Rong Cai.Review:My Life As Emperor,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
[29]Jahn,Manfred.Frames,Preferences,and the Reading of Third-Person Narratives:Towards a Cognitive Narratology.Poetics Today.1997,Vol.18,No.4,p446。
[30][32]罗屿:《中国好作家很多,但行销太可怜》,《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10期,第120-121页。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