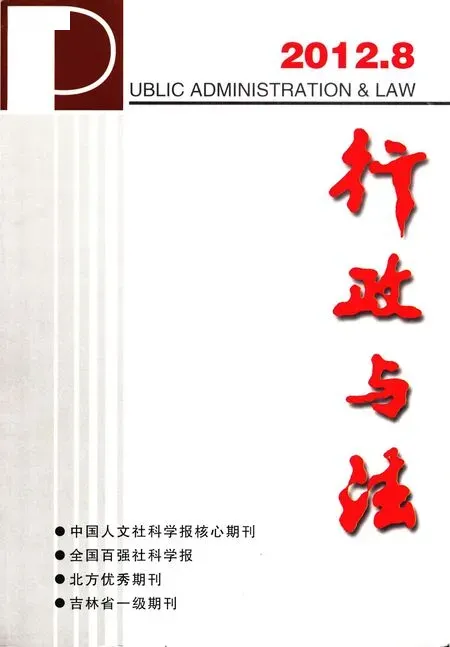浅析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
□ 荀福峥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浅析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
□ 荀福峥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应追求自由、秩序和正义的价值,以实现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遏止。但现实中,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因行为的多发性、饮酒的习惯性和制裁的限制性而存在一系列困境,因此在司法实践操作中,需破除对刑罚威慑作用的盲目笃信,在刑法与行政法的顺畅衔接和危险驾驶罪增设资格刑的同时,仍需社会力量的配合。
醉酒驾驶行为;法律规制;危险驾驶罪
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机动车数量巨增,这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并至。醉酒驾驶行为的高发就是其一。当下,因醉酒驾驶行为所导致的恶性事件的发生率呈上升态势,而相关法律法规未能适应现实变化,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制不力,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鉴于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2011年2月25日和2011年4月22日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以下简称 《刑法修正案(八)》和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定作出相应改变,①《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之一,予以刑事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将第91条关于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进行了修改。以加强对其规制的力度,从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秩序。
一、醉酒驾驶行为法律规制的价值追求
(一)外在价值
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应适应社会现实、社会心理与社会诉求,体现对自由、秩序和正义价值的追求。首先,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显现了法律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醉酒驾驶行为的发生,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如不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则作为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便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法律规制醉酒驾驶行为是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也由此彰显了法律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其次,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能够维护公共安全。醉酒驾驶行为针对不特定人的生命和健康具有抽象的危险性,其行为对公共安全形成威胁。对公共安全的维护是构建秩序的核心要素,“在我们的社会中,成年人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1](p199)法律规制醉酒驾驶行为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秩序。最后,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有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提倡。醉酒驾驶行为不仅是需要法律规制的行为,而且是为道德所非难的行为。而作为引起醉酒驾驶行为原因之一的酗酒,同为道德非难的对象。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是对道德非难酗酒和醉酒驾驶行为的一种保障。法律通过发挥它的评价和指引作用,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实现正义价值。
(二)内在价值
自由、秩序和正义的价值是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所追求的外在价值,除此之外,尚有对内在价值的追求。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所追求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遏止。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使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能够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利益,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增加了社会的风险,使人的安全感愈发降低,因而对于安全的诉求更为强烈。醉酒驾驶行为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多,它的多发性迫使人们考虑如何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能确保自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于是,人们选择法律作为兼顾二者的强制性保障。法律规制醉酒驾驶行为追求自由、秩序和正义的外在价值,而这些外在价值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实现。法律规制醉酒驾驶行为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是能够遏止醉酒驾驶行为的发生,这便是其内在价值,也是实现外在价值的方式。“法律的内在价值服务于法的外在价值,并接受外在价值的检验。”[2](p195)法律通过实现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遏止来达到对自由、秩序和正义的追求,而且对醉酒驾驶行为遏止的效果如何,要通过实现自由、秩序和正义的程度如何来检验。由此可以看出,自由、秩序和正义价值是一种目的性、目标性价值,而实现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遏止是一种手段性、方式性价值。虽然实现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遏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但由于其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更具现实意义。因此,醉酒驾驶行为法律规制的主要价值,便是实现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遏止,降低醉酒驾驶行为的整体发生几率,而非仅仅注重对个案的处罚。
二、醉酒驾驶行为法律规制的困境
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实现其所追求的价值的过程中,尚存在一系列困境。虽如此,也不能因困难的存在对醉酒驾驶行为听之任之,应注重实践操作中的具体方法。
(一)醉酒驾驶行为的多发性
根据公安部的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8月15日至12月10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2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3.2万起。因酒后驾驶引发交通事故1382起,死亡600人,受伤1573人。”[3]该数据表明,当下醉酒驾驶行为具有多发性。但此数据并不能代表全国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数量,一是此数据是在公安部的一次专项行动中统计的,某些驾驶人员畏于检查可能会收敛自己的行为。二是尚有未被查处的案件。因此,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数量要多于统计数字。笔者认为,导致醉酒驾驶行为多发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多,致使驾驶人员基数增大,发生醉酒驾驶行为的概率随之增大;第二,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按照心理强制说理论关于刑罚的内容映射于整个处罚体系,违法人在进行利益衡量后,或将选择违法行为;第三,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检查存在极大的盲区,某些驾驶人员以侥幸之心甘冒风险。醉酒驾驶行为的多发性使得醉酒驾驶行为的发现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未发现,自然无法谈及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罚,而未对个案形成处罚自然也不利于发挥法的指引与教育作用,从而阻碍遏止醉酒驾驶行为的实现。因此,醉酒驾驶行为的多发性成为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第一个困境。
(二)饮酒风俗情感的习惯性
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第二个困境,是基于饮酒的风俗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情感惯性难以剔除。饮酒至醉是醉酒驾驶行为的前置原因,而我国又是一个具有饮酒风俗文化的国家,由此形成的这种情感惯性对于遏止醉酒驾驶行为具有极大的阻力。譬如,我国有节日饮酒的习惯,而饮酒者可能又是车辆驾驶者。驾驶者出于节日习俗的考虑,或自愿或被迫饮酒,饮酒后很可能会驾驶车辆出行,当驾驶者的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达到一定标准后,便被认定为醉酒驾驶。再譬如,商业洽谈常于酒席之上进行,并业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此处抛开道德评价不论,单从此行为与醉酒驾驶行为的关系而论,显然,前者是引起后者的重要途径。洽谈者因商业习惯和交易利益而迫于无奈,最终选择饮酒,从而引发醉酒后驾驶车辆的可能性。在司法审判中,存在法官的个人情感与公正审判之间的矛盾问题,普通公民与法官相似,同样存在着生活中情感因素与守法之间的矛盾。情与法的矛盾体现了人的思维过程中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力一般可概括为三种可能:一是情感强化理性;二是情感反向削弱理性;三是情感横向干扰理性。从传统的视角看,情感对理性虽具有强化功能,但更多的是影响理性的正常发挥。”[4]当车辆驾驶者守法的理性受到情感的干扰时,便容易选择饮酒后的驾驶行为。因此,此种情感惯性是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另一个困境。另外,驾驶者的饮酒行为并非自愿能否作为阻却其违法犯罪的事由、对于无帮助驾驶者实行违法犯罪意图的劝酒者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均有待研究。
(三)法律制裁手段的限制性
法律在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规制时,其制裁手段对于克服以上两个困境显现出一定的限制性。法律制裁手段的限制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裁手段内部的限制性。现有的法律制裁手段对于遏止醉酒驾驶行为显得方式较少,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应有作用。二是法律制裁手段与其它手段外部的限制性。如果仅仅依靠法律的制裁手段来遏止醉酒驾驶行为显然具有较大的限制性,其它手段未能充分调动与利用,既浪费社会资源,又不利于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制。内部的限制性主要体现在立法上的限制性,而外部的限制性则主要体现在司法与执法上的限制性。因此,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需解决各个环节的限制性因素。
三、醉酒驾驶行为法律规制的实践操作
(一)破除对刑罚威慑作用的盲目笃信
醉酒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指向的重点并非对个案的处罚,而是降低行为的整体发生率。在此基础上,会出现一个实现此价值追求的途径,即将醉酒驾驶行为全部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实行醉酒驾驶行为的犯罪人予以刑罚处罚,从而达到威慑潜在犯罪人的作用,进而实现一般预防。威慑刑作为人类刑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存续时间极久。①邱兴隆教授将刑罚的进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复仇时代、威吓时代、博爱时代与科学时代。威慑刑即存续于第二个时代的刑罚方式与刑罚思想,其时期大体相当于人类的封建社会时期。参见邱兴隆.刑罚学[M].群众出版社,1988.16-26.威慑刑的历史时期虽已过去,但由于其历史久长,特别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漫长,导致威慑的思维依然存续。不可否认,要实现犯罪的一般预防,刑罚的威慑作用依然发挥着功效,但一般预防的实现如果全部寄托于刑罚的威慑,则不但不能收到一般预防的良好效果,而且会陷入重刑的泥潭。“用刑者不是从犯罪之存在与再生的必然性与刑罚对于遏制犯罪的作用的局限性中寻找失败的原因……制刑与用刑陷于失败——加重刑罚——再失败——再加重刑罚的无限往复之中……呈现出愈来愈严重的恶性循环。”[5]再具体到醉酒驾驶行为,基于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对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行为本身就不能予以过重的刑罚。“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严惩主张转嫁到司法裁量上。”[6]因此,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首先要确立一个理念,即破除对刑罚威慑作用的盲目笃信。进而可以得出结论,不能单纯依靠刑法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规制,应利用其它手段,而其它手段首先要考虑法律内部的手段,这就自然涉及到刑法与行政法在适用过程中的衔接问题。
(二)刑法与行政法的顺畅衔接
⒈刑法与行政法衔接适用的实然状况。《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33条后增加第133条之一,增设危险驾驶罪,并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该罪,法定刑是拘役,并处罚金。新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2款和第4款分别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修改之前,对此有如下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00元罚款”。通过《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前后的比较可以发现,修改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包括拘留、暂扣驾驶证和罚款,而《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其法定刑将原行政处罚中的拘留和罚款上升为刑罚的拘役和罚金,《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后,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取消了拘留和罚款,仅仅是吊销驾驶证。针对此种状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发现醉酒驾驶行为时,在法律适用上,刑法与行政法并用,在对犯罪人判处拘役和并处罚金后,再吊销其驾驶证。显然,针对醉酒驾驶行为,行政法成为了刑法的附属,失去其独立性,此种处罚方式不符合刑法和行政法的适用结构。
⒉刑法与行政法顺畅衔接的应然表现。刑法是其它部门法的保障法,只有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才会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内。法律对某一行为进行规制,首先需经刑法之外的其它部门法的调整,如适用其它部门法依旧无法救济权利,此时才会进行刑法的调整。因此,刑法与行政法的适用是一个双层次结构,而非主从结构。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删去原有的拘留与罚款,导致《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调整需依附于《刑法》。刑法与行政法顺畅衔接的应然表现是《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规定关于对自由与财产的处罚,不能因为《刑法》已经规定了拘役与罚金的法定刑,《道路交通安全法》便不需要规定拘留与罚款的行政处罚。《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包含醉酒驾驶行为,“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司法人员只需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即可……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7]可见,发生醉酒驾驶行为并非一定构成犯罪,“司法者把醉驾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时,必须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排除在犯罪圈之外。”[8]当醉酒驾驶行为未构成犯罪时,尚需行政法的调整。
(三)危险驾驶罪资格刑的增设
在刑事犯罪中适用行政处罚的法条依据是《刑法》第37条,其适用对象为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犯罪。即首先认定犯罪的成立,但由于情节轻微,可适用其它非刑罚性处置措施,行政处罚便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并不等同于法定刑较轻的犯罪。因此,对于法定刑较轻的危险驾驶罪而言,如果未出现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则适用拘役和并处罚金的刑罚。然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意在对醉酒驾驶行为予以刑罚处罚的同时,附加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上文已谈及,此种处罚方式不符合刑法与行政法的双层次结构。但是,如果不对犯罪人的驾驶资格进行限制,则会影响对其进行特殊预防的效果,进而影响一般预防的效果。对此,笔者认为,解决途径是增设危险驾驶罪的资格刑。与不能因为《刑法》已规定拘役和罚金的刑罚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就不需要规定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样的道理,不能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已规定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而《刑法》就不需要规定相关的资格刑。“我国刑法也并未因为行政法中已有行政拘留和罚款的规定,而不在刑法中规定拘役和罚金这样的刑罚。”[9](p242-243)针对危险驾驶罪中醉酒驾驶行为资格刑的增设,可以移植外国刑法中关于“禁止驾驶”和“禁止执业”(针对驾驶营运车辆)的规定。
(四)社会力量的多元配合
遏止醉酒驾驶行为不仅需要法律的制裁手段,更需要发挥社会力量。首先,基于上文所提到的醉酒驾驶行为法律规制的困境,醉酒驾驶行为极易引发社会越轨,“从功能论角度看,越轨不仅具有损害社会利益、破坏社会制度、导致社会功能失调的负作用,同时也具有澄清与重新定义社会规范、增强群体团结的正功能。正功能是伴随着负功能的出现而出现的,越轨行为总是以一个破坏者的身份首先登场,当它通过合理的途径得到有效解决的时候,负功能才会转化成正功能。”[10]因此,需要建立起一个社会的普适价值体系,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手段实现社会控制。其次,社会力量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道德力量,道德力量虽不具强制性,但却因其广泛性与习惯性,成为了配合法律适用的重要力量。醉酒驾驶行为是为道德所非难的行为,通过社会道德的提倡与普遍正义的彰显,可以约束醉酒驾驶行为的发生。对于法律规制的盲区,同样需要以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来配合法律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制。最后,社会力量还起到了监督的作用。社会舆论既可以直接对潜在的违法者进行监督,也可以间接对法律规制违法行为的过程与效果进行监督。只有通过此种监督,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制才会形成常态化。
[1][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公安部.全国3个月查处酒驾21万余起,11月份酒后驾驶导致的特大事 故 上 升 [EB /OL].http: //www.mps.gov.cn/n16/n1252 /n1837 /n2557 /2226063.html,2009-12-10.
[4]曹英.司法裁判与情感[J].柳州师专学报,2009,(01):54.
[5]邱兴隆.威慑刑的理性反思[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9,(01):114.
[6][8]赵秉志,张伟珂.醉驾入罪的法理分析[N].检察日报,2011-05-17(3).
[7]张明楷.危险驾驶罪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N].人民法院报,2011-05-11(6).
[9]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0]刘悦.当代中国社会越轨问题的成因与解决途径[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02):82.
(责任编辑:王秀艳)
Analysis on Drunk Driving’s Legal Regulation
Xun Fuzheng
Drunk driving’s legal regulation follows the values of liberty,order and justice.It also wants to achieve the containment of drunk driving.Due to the common incidents,habitual drivings and limited’s punishiments,drunk driving’s legal regulation is a difficult question.In the practice,drunk driving’s legal regulation needs to break the blind faith on penalties’ deterrent effect.Excepting for the crimi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s convergence and the qualification penalty’s addition on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are important,besides,it needs society’s power.
drunk driving;legal regulation;Dangerous Driving Crime
D922.296
A
1007-8207(2012)08-0105-04
2012-05-10
荀福峥 (1971—),男,吉林白山人,吉林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