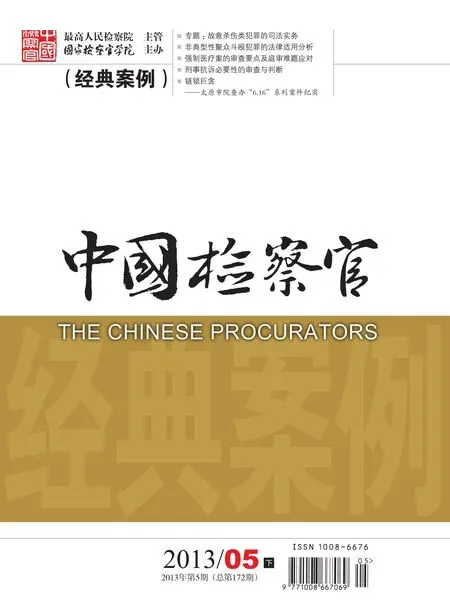非典型性聚众斗殴犯罪的法律适用分析*
文◎樊华中
现行《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另又规定了多次聚众斗殴、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持械聚众斗殴四种加重处罚情节。司法实践对符合典型特征的聚众斗殴案件认定一般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在一些场合则非常困难。主要包括: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另一方不知情及事后反击型;数人约定互殴,但因一方人员未到而使人数达不到聚众斗殴人数要求的不达标型以及无事先约定的临时起意型。现对此三类非典型特征的聚众斗殴如何适用法律进行以下梳理。
一、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并实施殴打及事后相互殴打行为的认定
[案例一]刘某开车至某村公路,遇张某一家三口在砍树,倒落的树将路堵住,双方遂发生口角。张某全家将刘某的车砸坏。后刘某纠集数十人手持砍刀等回来报复,声称“将张家房屋烧掉,小孩杀掉”,张家三口人被动应战,打斗之中,刘某纠集的数十人中有被张家人砍死。
对此案实践中共有三种法律适用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一伙数十人具有斗殴故意,应当认定为聚众斗殴,张家三口人因主观上没有聚众斗殴的故意,故不构成聚众斗殴罪,属于防卫性质,其致人死亡明显超出必要限度的应承担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纠集数十人殴打张家人,属于小题大做,应当定性为寻衅滋事罪,张家三口人出来应战,也可以视为寻衅滋事。在寻衅滋事中将人砍死,转化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一伙数十人虽有斗殴故意,但张家三口人主观上不具有斗殴故意,因此对刘某一伙人可以定故意伤害罪,张家三口人在殴打中致人死亡的,直接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论。
(一)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并实施殴打行为的定性
从目前看,仅有两个地方性法律适用意见对单方斗殴行为作出了规定。如2009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发布了《关于办理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江苏意见》)中规定“一方有互殴的故意,并纠集三人以上,实施了针对对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殴斗行为,而对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对有互殴故意的一方也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再如2011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司法局办理聚众斗殴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 《天津纪要》)中规定单方聚众斗殴罪,认为“一方有斗殴故意,并聚集三人以上,殴打对方一人或多人的,有斗殴故意的一方构成聚众斗殴罪。”
笔者认为,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并实施殴打行为的,对双方都不宜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这是因为:第一,从语义解释看,聚众斗殴中的“斗殴”与寻衅滋事罪中的“殴打”、故意伤害中的“殴打”有本质区别的。“斗殴”是指双方对打,而且是双方均有意识的相互争斗。“殴打”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击。因此,行为人具有的斗殴故意应含有与对方对打的内容,而不应是单方的打击。第二,从聚众斗殴罪所保护的法益看,聚众斗殴行为是一种严重影响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其危害性在于双方均目无法纪,用聚众斗殴的方式向整个社会进行有意识的挑战。社会秩序遭受破坏是双方相互有意争斗的行为共同促成的。因此,双方斗殴故意缺一不可。第三,从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动机来看,行为人实施聚众斗殴双方均是出于好勇斗狠、逞强好胜、寻求刺激等动机,只有双方均在具有上述“超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况下,伤害他人身体的主观方面才能与故意伤害罪主观方面、寻衅滋事罪主观方面区别开来。第四,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实施的斗殴行为解释为“殴打”行为而不是“斗殴”更具合理性。因为另一方不具有“斗殴”的故意,自然就不会形成“争斗”局面,当然更不会共同促成共同破坏社会秩序这一法益。即便是江苏省级机关公布了关于聚众斗殴的统一适用规定,有江苏地区司法一线人员在实证基础上认为 “法院适用聚众斗殴的条件较为宽松”但 “单方聚众斗殴其实施斗殴行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身体权,不是对整个社会的公然挑战,故此种情形完全不能体现聚众斗殴本质特征”[1]应当从严撑握。
笔者认为,从聚众斗殴罪所保护的主要法益“社会秩序”来说,应对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并实施殴打行为的从严掌握。如何定罪处罚应当在综合分析单方具有斗殴故意人群的主观故意与犯罪行为基础上综合评价。首先,单方具有斗殴故意的情况下,不论其出于什么动机,其所“斗殴”的对象均是特定的,这一点与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性”所要求的对象不特定是不符的,因此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其次,斗殴其实就是双方殴打行为,而殴打从实质理解上就是伤害行为,因此对单方具有斗殴故意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单方具有伤害故意的行为。再次,将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并实施斗殴行为的定性为故意伤害,也符合常识常理。从本质上来说,斗殴行为与伤害行为并无实质差别,只是刑法出于罪名分章及历史原因的考虑将多人相互伤害的行为单列出来。而且在现阶段,我们传统理解的为争霸一方、好勇斗狠而专门聚众打架的流氓团伙已经不大见了[2],一般性的伤害他人却是一直存在。最后,即便是上述规定了单方聚众斗殴罪的地方规范中,也明确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区分。如《天津纪要》又规定“在单方聚众的情况下,要严格把握聚众斗殴罪的法律适用标准,特别注意从主、客观方面与多人实施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相区别。”《江苏意见》又规定 “但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与共同伤害和共同杀人的界限,对于一方有明显的伤害或杀入故意的,直接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处理。”此规定可以看出,在实践中确实很难将单方聚众斗殴与故意伤害进行明显的区分。因此,对于单方具有斗殴故意的行为并实施的,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处罚并无不妥。
(二)另一方被动殴打后予以回应的行为定性
笔者认为,在单方具有斗殴故意而殴打另一方,另一方被动殴打后予以回应的行为如何认定,应当根据其行为反应的时间、地点、行为方式、程度分清情况分别定性:
第一,另一方被动殴打后予以当场、即时以暴力回应的,如果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并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另一方被动殴打后予以当场、即时以暴力回应的,如果行为超过必要限度不构成正当防卫的,应当根据其伤害结果及主观心态定过失致人重伤、死亡或故意伤害罪等。
第三,另一方被动殴打离开现场后,隔一段较短时间又纠集多人以暴力回应的,如果其针对的对象仍然是彼时单方具有斗殴故意的群体,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理由有二,一是另一方被动回应的,其必然在主观上形成了报复的动机,具有预谋性,这与我们理解的故意伤害罪并不矛盾。二是对于另一方隔段时间后又纠集多人以暴力回应的,对另一方以故意伤害定罪处罚是一般标准,但当双方的犯罪故意与客观行为、危害结果又符合聚众斗殴罪的,可以聚众斗殴定罪处罚。
如果被动殴打后纠集人员所殴打的对象并非原先单方具有斗殴故意的群体,而是原单方斗殴的部分人员甚至并非是先前单方具有斗殴故意的人群的,属于犯罪对象认识错误,但仍然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可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当然,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需要达到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对于达不到的,不宜以犯罪论处,也不宜以寻衅滋事罪替代处罚。
二、数人约定互殴,一方人员未到而使人数达不到聚众斗殴人数要求的认定
通说认为聚众斗殴罪在强调双方均具有斗殴故意的基础上,还必须满足双方人数均为三人以上的对偶性要求,如此才能构成“争斗”。但理论上也有观点认为“不要求斗殴的双方都必须为三人以上,一方一人或两人,另一方三人以上进行斗殴的也成立本罪。但一方一人,另一方两人的不宜认定为聚众斗殴。”[3]还有意见认为“聚众斗殴双方人员之和达到聚众斗殴罪即可,不必双方均达到三人以上。”[4]在地方性规定上,《江苏意见》认为“双方均有互殴的故意,斗殴时一方达三人以上,一方不到三人的,对达三人以上的一方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对不到三人的一方,如果有聚众行为的,也可以聚众斗殴罪论处,如果没有聚众行为的,不以聚众斗殴罪论处,构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论处。”笔者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已经突破了人们对聚众斗殴的对偶性理解,在实践中容易造成认识混淆。
(一)双方均纠集人员斗殴,双方人数不符合对偶性要求的情形
[案例二]2012年5月16日19时许,A1因要争回面子,打电话给 B1约架,B1答应。 A1约 A2、A3、A4帮忙一起打架。B1纠集了B2,两人赶赴约定地点。在约定地点相互殴斗。
针对此案,有观点认为既然起因是争回面子,说明双方相互认识,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随意性要求,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也有观点认为,A1、A2、A3、A4构成聚众斗殴,B1、B2不构成聚众斗殴,因为人数未达到三人以上,但可以考虑成立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行为类型中的“随意殴打他人”不但可以包含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实施的殴打行为,也可以包含双方具有殴打故意实施的互殴行为。
笔者认为,聚众斗殴罪虽然与寻衅滋事罪同样脱胎于流氓罪,但是聚众斗殴与寻衅滋事罪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聚众斗殴罪处罚对象针对的是那些在相互认识的人群之间因好勇斗狠而进行殴斗的行为,寻衅滋事罪处罚对象针对的是那些随意殴打不特定人的某个人或一群人。对于在聚众斗殴人数不符合对偶的条件下,不能将其降格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因为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斗殴罪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的,具体来说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随意既是殴打的客观要素,也是主观判断要素。随意殴打不仅仅是行为方式、行为对象的客观修饰,也是主观方面的限定。聚众斗殴的双方之间相约打架,说明在人数对偶的情况下,双方具有斗殴的意思联络,但从另一角度讲,双方之间是具有预谋性的。相反,寻衅滋事罪在犯意的联络下是单方性的,但在主观故意上是临时性、即时性的。
第二,随意体现在对象的选择上,而对象的选择又印证了主观上的随意。“随意殴打”表明行为人在殴打行为之前并无具体的目标、对象,只是在见谁不顺眼时就即兴打人。显然,聚众斗殴的双方对象并不符合随意所要求的“不特定性”,聚众斗殴的双方人员之间均是相互认识的,且相互之间有“过节”,因有“过节”要一比高下。
因此,综合这两点来说,在双方均纠集人员斗殴的场合,双方人数不符合对偶性要求,在不能认定为聚众斗殴的情况下,也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不过,根据斗殴人员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表现,可考虑构成故意伤害罪。
(二)双方纠集多人到场,但纠集到的部分人员仅仅围观,参与打架人员不足三人的情形
[案例三]A1和A2在酒吧玩,碰到了A1以前爱慕的女性C,其上前打招呼并拥抱,此过程被爱慕C的B1看到。随后吃醋的B1伺机将A1推到墙上,争吵中互相称看对方不爽,双方约架。后B1纠集B2、B3、B4,双方发生殴打,但在殴打过程中,仅仅有A1与B1对打,A2、B2、B3、B4 未参与殴打。
笔者认为聚众斗殴罪与寻衅滋事罪之间具有以下明显区别。首先,在犯罪故意上,双方之间互有联络,不符合寻衅滋事罪即时兴、单方性的要求。其次,在殴打对象上,也不符合寻衅滋事随意性所要求的对象事先不确定。在聚众斗殴难以认定的情况下,不应当考虑认定寻衅滋事罪,而应当考虑构成故意伤害罪。
至于纠集了多人,但是到场后打架的人总共仅有两人,或者说单方人数均未突破三人,其他人员仅仅围观的,应当严格依据聚众斗殴的构成要件进行认定。聚众斗殴罪中“聚众”与“斗殴”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两个要素的组合使得聚众斗殴罪具有明显的复合行为性质。不但斗殴的人员要有聚众意识,而且要有斗殴行为,这也是聚众斗殴罪的犯罪主体“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决定的。因此在纠集到的部分人员仅仅围观,参与打架人员不足三人的,对于打架的人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对于围观的人应当视情况而定。比如围观的人仅仅是围观的,应当严格依据聚众斗殴的复合行为要求,认定其不构成犯罪。但是围观的人如果不仅仅是围观,而且使用言语教唆,如“狠狠打”、“打死他”“弄死他”等言语助威、挑衅的,则应当将“言语暴力”视为斗殴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其对殴斗行为的进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双方各自约人,但一方约人未成或人员未到的情形
[案例四]甲1与乙系隔壁宿舍新邻居。某日,甲1到乙宿舍拿了一个枕头后又放回去。案发当晚,乙便质问谁动过枕头,二人言语不和,便约定打架。甲1让甲2、甲3过来帮忙打架,乙未叫到人,甲1、甲 2、甲3到乙房间后,甲1、甲2、甲3一起殴打乙1,乙构成轻伤。
笔者认为,双方各自约人,对于那些约人未成或约了人员,但打架时被约的没有及时赶到而单枪匹马应付的,除强调双方均具有斗殴故意外,还必须满足聚众殴打行为的对偶性要求,如此才能构成“双方争斗”,也才会对法益造成侵害。否则,只能考虑将双方认定为故意伤害。另根据伤害结果,如果有致人重伤、死亡的,应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自认为单枪匹马或一两个人即可应付的,双方发生互殴后,造成轻伤结果的,以故意伤害论处,未对另一方造成轻微伤的,可予治安处罚。
三、无事先约定的临时起意型
一般情形下,聚众斗殴罪典型案例中都有事先纠集、组织和策划的准备行为,且双方均有聚众斗殴的故意。但应当注意到,实践中也有不少聚众斗殴是临时起意的突发性斗殴。如在公共场所,一方本就多人在一起,另一方也是多人在一起。刚开始双方并无斗殴的故意,只是因为机缘巧合身处同一公共场所,后因一方某一成员与另一方某一成员因琐事发生矛盾,继而双方多人一拥而上,相互斗殴。此种情形就是临时性“聚众斗殴”。
[案例五]某建筑工地上,钢筋工人王1、王2、王3、王4,木工符1、符2、符3、符4系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两方人员均系各自姓氏老乡,某日因钢筋工王1将木工符1等人设置的水平线弄断,双方发生口角并扭打起来,随后王 2、王 3、王 4与木工符 2、符 3、符 4等持扳手、钢管等工具加入互殴,双方均有损伤。
笔者认为应将临时起意而相互争斗的情形定性为聚众斗殴罪。司法中通常认为聚众斗殴罪的客观方面包括“聚众”和“斗殴”两个具有关联性的行为。“聚众”行为一般发生在斗殴前有一个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和纠集多人的预谋准备阶段。对于临时、即兴加入他人打架队伍中的行为,解释论上的关键在于弄清 “聚众”一词。我们通常理解的聚众为有一个牵头者,组织、策划、指挥和纠集多人,即由A牵出 B、C、D、E、F等。但这样理解太过狭隘,将“聚众”理解为前期的预谋,而将后期的即时起意排除在外。在笔者看来,“聚众”不应当限定在A牵出B、C、D、E、F的传统理解,还应当包括A、B、C、D、E、F 共同形成犯意的过程,换言之,临时、即时加入他人打架斗殴,在主观上认识到他人的打架行为,也意识到自己加入后会有更广泛的危害后果,而执意加入或罔顾事实放任不管的。因此对临时起意型的,或者临时加入的他人打架行为中而达到聚众斗殴犯罪构成的,当然应当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注释:
[1]汪敏、王亚明:《聚众斗殴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基于规范实证的视角》,载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王然、温少昊:《聚众斗殴罪法律适用问题探究》,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5期。
[3]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768页。
[4]高铭暄、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