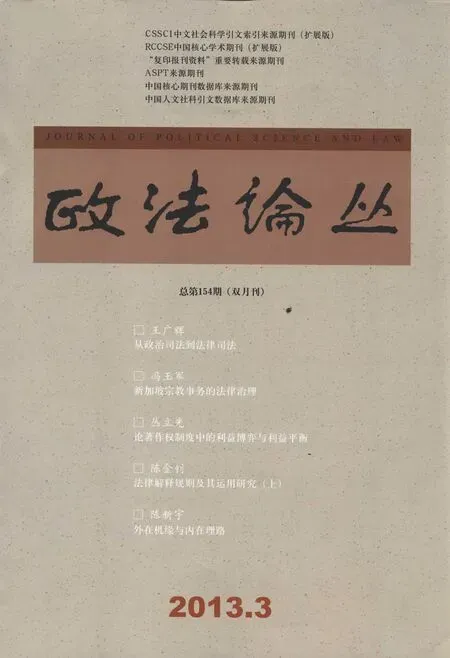论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演变*
魏胜强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论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演变*
魏胜强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通过考察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中华法系代表性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可以发现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规律,即法律解释权的基本概念从模糊走向明确,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目的从集权走向分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从多元走向一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从神圣走向世俗。深入分析影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内在因素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是左右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总体框架,法律状况是制约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具体条件,解释原理是支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内在规律,历史事件是改变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直接动力。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规律给人们的启示在于,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遵循法律解释原理和规律,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与法制状况相适应,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结合现代法治精神。
法律解释权 配置 演变
罗马、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分别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属于不同的法系,在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它们都属于所处时代中法律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而且对人类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它们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进行历史考察,会发现它们尽管差异显著,但仍存在一些共同的方面。①
一、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演变规律
纵观这些国家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到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基本演变规律,这些规律体现在法律解释权的基本概念、配置目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可以用四个“走向”来概括。
(一)从模糊走向明确——法律解释权基本概念的演变
从不少国家的历史来看,在法律发展的早期,法律解释权几乎没有被当作一个问题,至于法律到底由哪些主体来解释,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例如在罗马的王政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僧侣团和法学家先后掌握法律解释权,而法、德、英、美诸国在国家形成之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都很模糊。随着法律的发展和法律纠纷的增多,法律解释权问题才引起应有的重视。罗马帝国时期,法律解释权首先由皇帝授权的法学家公开行使,后来转到皇帝手中。法、德、英、美等国家或者在立法中公开宣布法律解释权配置给某些主体,或者某些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得到国家的认可。中国的统治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法律解释权虽然有一定的关注,但并没有完全明确,直到清末才学习西方而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最高司法机关。这一漫长的过程表明,法律解释权的基本概念从模糊逐渐走向明确,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解释权的称谓从模糊走向明确。法律解释权尽管一开始就存在,但在早期它仅仅是在事实上被一些主体行使,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没有意识到他们握有宣告法律意义的权力,其他社会主体也往往把法律解释权理解为法律执行权,或者只看到法律执行权而忽视法律解释权。罗马皇帝明确授予一些法学家对法律的解答权,可以称得上是法律解释权在西方最早具有的明确的称谓。后来,一些国家的法律中陆续出现了解释法律的权力,法律解释权逐渐在称谓上获得法律的明确认可。
第二,法律解释权的地位从模糊走向明确。法律解释权的称谓从最初的模糊走向后来的明确,也意味着它在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它的地位在逐渐提升。罗马皇帝授予一些法学家法律解答权,说明罗马皇帝注意到了法律解释权对于法律实施的重要性。后来罗马皇帝干脆从法学家手中收回解答权,更说明了法律解释权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商朝后期的商王亲自占卜,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都意味着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近代欧美国家法律解释权的演变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威,很大一部分来自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
第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从模糊走向明确。早期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是模糊的。罗马曾经由僧侣团、法学家、法官等主体掌握法律解释权,中国曾经由史官、司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法德英美等国早期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同样较为混乱。然而随着法律的发展和进步,法律解释权的主体越来越明确,如罗马最终由皇帝行使法律解释权,其他多数国家最终由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尽管不同国家法律解释的主体有很大的差异,但至少可以看到,法律解释权的主体逐渐从模糊走向明确。
法律解释权的称谓、法律解释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法律解释权的主体,都由模糊走向明确,表明法律解释权这一概念从模糊到明确的走向。经过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统治者、不同的法律制度都接受和认可了法律解释权这一基本概念。时至今日,法律解释权已经成为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
(二)从集权走向分权——法律解释权配置目的的演变
合理配置法律解释权在客观上有利于弥补法律的各种缺陷,促进法律充分发挥其作用。但是掌握法律解释权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法律实施的权力,统治者怎么会轻易放弃这种权力呢?各国统治者总是费尽心机,想尽各种办法配置法律解释权,努力使之既能为自己所掌控,又不至于妨碍法律的实施。于是,关于法律解释权的各种各样的配置就出现了。从总体上说,在古代社会里,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目的是集权,到了近现代社会,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目的逐渐走向分权。
古代社会法律解释权配置的集权目的显而易见。罗马建立帝制后,政治统治逐渐走向专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自然呈现出集权色彩。获得解答权的法学家显然不是一般的法学家,他们已经成为“御用”法学家。而且,这些法学家一般担任官职,因而他们必然丧失自由学者的身份和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很难想象他们的解答活动会有悖于皇帝的旨意。虽然罗马法学家内部出现过严重的对立,但在服从皇帝旨意方面,他们不会有差别。到了帝国后期,罗马皇帝逐步限制并最终剥夺了法学家的解答权,法律解释权由罗马皇帝独占。罗马法律解释权的这种配置,显然服务于皇帝的集权目的。在专制集权发展得尤为突出的中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更是基于集权的目的。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种赤裸裸的集权外,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无论法律解释权由哪些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始终处于王权或者皇权之下,其主要功能是服务于集权统治。即使在封建法律体系形成时期的英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给法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集权的目的,英王委派巡回法官和大法官解释法律并作出判决,是英王加强集权统治的手段之一。法国在革命前由王室最高法院巴利门行使法律解释权,也是当时权力集中的体现。
进入近现代社会后,法律解释集权的配置逐渐转向分权的目的。从法德英美等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看,法律解释权正在一步步地基于分权的目的而配置给法院和法官。法国在革命后剥夺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类似立法机关的“上诉法庭”,正是出于限制权力集中、实现权力制约的目的。而且,无论是德国《普鲁士邦法》对法官法律解释权的绝对禁止,还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对法官法律解释权的严格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了理性主义和分权思想的影响,只不过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理性主义和分权思想是僵化的,因而从总体上说反对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法官。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司法活动以及分权思想的进一步理解,法国和德国最终都认可了法院和法官的解释权。英国尽管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高层级法官的初衷是扩大和维护王权,但后来的发展显然走向了限制王权的道路。最终,英国的司法领域由职业法律家所垄断,法律解释权所呈现的分权目的不言而喻。在美国,行使法律解释权的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和国会的制约作用举世闻名。中国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把法律解释权赋予最高司法机关,显然是学习西方分权制衡的结果。总之,在近现代社会里,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以分权制衡为目的,只不过在有些国家这一目的实现了,在有些国家这一目的没有或者没有完全实现。
(三)从多元走向一元——法律解释权行使主体的演变
纵观历史上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物。罗马王政时期和共和国前期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是僧侣团,共和国后期和帝政前期变为法学家,帝政后期变为是皇帝,而且罗马的司法者也一度拥有法律解释权。中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神职人员和司法官、官府和私人都曾行使法律解释权,而法律解释权的最高行使者是君主。法德两国的法律解释权一度由立法者行使,最终演化为由法院和法官行使。英美两国在法律制度的形成时期就逐步确立法官的法律解释权,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显然,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在演变过程中从多元走向一元。
早期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必然是多元的。这是因为,法律解释权这一概念并不是法学家或者统治者提出来的,而是在法律实施活动中逐渐被人们认识到的。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才会产生解释的需要,但在法律实施中应当由哪个或者哪些主体来解释法律,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在法律发展的早期,不但不同国家的法律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也难以形成统一的体系,各种形式的法源都在调整着人们的生活。不同的法源在实施中必然产生不同的解释者,如在早期的罗马和中国,原始的宗教法的解释者只可能是神职人员。在早期的法国,由于习惯法、教会法和罗马法各自独立发展并在不同的地域发挥作用,当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必然是混乱的,不同的法律由不同的主体进行解释。德国、英国、美国在法律发展早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正是出现了如此混乱的状况,才引起了统治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律解释权这一概念才真正进入人们的头脑中,统治者在设立国家机关和分割国家权力时才会考虑如何配置法律解释权。
西欧诸国经过封建社会法律解释权配置方面的探索后,认识到法律解释权的重要性和法律解释活动的基本规律,在近现代社会里逐渐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司法主体。美国早期的法律家们由于深受英国法制的影响,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强调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并充分发挥其法律智慧创造性地确立司法审查权,使法律解释权更加牢固和强大地融入司法权中。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最高司法机关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因而它的配置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近现代社会里,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正在走向一元,即由司法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除此之外的其他主体均不再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大约有三点:(1)法律解释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经过历史上法律解释活动的蓬勃发展,法律解释权的行使给法律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各国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法律解释权的重要性,因而不少国家不得不在法律制度中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法律解释权越来越成为一种公开的权力。(2)国家的法制越来越统一。不少国家早期的不同法源往往各自为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权力的加强,法律越来越走向统一,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同一个法律体系内,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应当是一致的,因而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只会越来越单一。(3)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司法主体具有较大的合理性。法德英美等国最终都毫无例外地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司法主体,必然是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作出的慎重选择,而不是随意的安排或者偶然的巧合。司法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应当是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并且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证明。
(四)从神圣走向世俗——法律解释权行使方式的演变
与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从多元走向一元相对应,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也从神圣走向世俗。
早期法律解释权行使方式的神圣性,主要体现在神职人员的解释活动中。一般来说,带有神秘色彩的法律在解释中都需要通过神圣的方式进行,如西欧中世纪教会法的解释和中国商朝占卜官对法律的解释。通过神圣的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不仅限于宗教法,世俗的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神圣方式的影响。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进行重大政治、军事或者法律活动时常常举行神圣的仪式,打出“天意”、“天命”、“天机”等旗号为自己的活动进行注解;即使在民间案件的审理上,司法官也会用“乩仙批语”为法律的实施辩护。
在近现代社会里,法律越来越走向世俗,法官对法律的实施一般是公开的,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方式也越来越世俗,这可以从如下两点看出来:(1)法官对法律意义的解释越来越公开。法官不但要在判决书中表达他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不同法官在同一案件审理中对法律的不同理解也逐渐公开。(2)一些法官甚至通过行使法律解释权来表达司法对社会上某些重大事件的态度,用司法裁判引导社会的变革。而在司法权较为强大的国家如美国,法官甚至通过行使法律解释权来对抗政府和国会的改革措施。这两点说明,法官对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充满世俗味道。法律解释权行使的世俗性日益突出。
二、影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因素
历史上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及其演变所呈现的四个“走向”的规律,离不开某些因素的作用。政治体制、法律状况、解释原理和历史事件对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政治体制——左右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总体框架
有些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呈现出多阶段、多主体、跌宕起伏的特征,不同时期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变化很大。有些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比较平稳,虽然经历漫长的时代,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变化不大。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变化状况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但政治体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显著的原因,这可以用三个典型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
第一个国家是罗马,根据政治体制的不同,它的历史一般被分为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帝政时期,不同时期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第二个国家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它的政治体制可以分为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差别不大,都是在君权之下由某些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而第三个阶段中法律解释权在形式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与前两个阶段明显不同。第三个国家是美国,它的法律解释权在立国之初配置给法院后一直由法院行使,除了法院行使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之外,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三个国家在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方面产生如此大的不同,可以从它们政治体制的差异中找到答案。
罗马经历了多个政体,每一个政体在权力格局、执政理念、统治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不同政体下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必然不同。尤其是在帝政时期,罗马逐渐走向君主专制,只有代表君主意志的法律解释才能成为有效的解释,因而秉承君主意志的法学家自然会掌握法律解释权。而在帝政后期,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法学家的解释权逐渐被君主收回,由君主亲自行使。“没有多久,法学家的延续关系就断了。在半个世纪中,帝国一直处于生死攸关的时期,专制君主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在此时期没有个人解释(interpretatio)的余地,即使对于像帕比尼安、乌尔比安和保罗这样的供职于皇帝服务机构的法学家来说也同样如此。现在,法的唯一渊源是皇帝,法学家的位置已由皇帝文书处的无名民事勤杂吏所取代,生活脱离了罗马法。”[1]P31
中国的古代社会虽然可以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从政治体制上说,这两种社会的差别并不是很大。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都具有明显的集权色彩,各种权力大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相似性使它们的法律解释权始终掌控在君主手中,其他主体所拥有的法律解释权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整个中国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倒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冲击,国家政治体制在形式上发生巨大变化,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才发生显著变化。
美国自立国后,尽管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开国元勋们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内战、经济危机、对外战争等重大事件并未对政治体制带来冲击,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政体模式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某些事件的解决中进一步得到加强。因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得到高度发展,法官掌握法律解释权的做法除了得到加强以充分维护法官所坚信的民主和自由外,不会有什么改变。
从这三个国家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是左右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总体框架,法律解释权只能在这一框架内进行配置。
(二)法律状况——制约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具体条件
法律解释权是解释法律的权力,它既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受制于法律并作用于法律的权力,因而法律状况对它的影响不言而喻。法律状况的好坏可以从表现形式和完备程度等角度来衡量,而这些角度自然也成为考量法律解释权配置状况的一个切入点。
从表现形式来说,人类早期的法律无非是原始的宗教法和习惯法,这两种法律具有模糊性,在实施起来会发生很大的分歧,因而都会引发法律解释权问题。在早期的罗马和中国,法律的宗教色彩很明显,对法律的解释自然会落到神职人员手中。无论是罗马的僧侣团还是中国的史官,都必然会成为法律解释权的主体,这也是法律起源于原始宗教和习惯这一规律在法律解释领域的延伸。英国的历史一般被认为从公元五世纪开始,当时主宰英国的主要是从欧洲大陆侵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时期,人类早已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影响,而调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主要是习惯法,其宗教色彩并不强。即使该法后来受到宗教的影响,也只可能受基督教而不是原始宗教的影响。因而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法律解释权并没有像罗马和中国那样由神职人员掌握。
从完备程度来说,无论法律是否完备都会对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法律如果过于粗糙和简陋,必然需要大量的解释,法律解释权问题随即凸现出来。如英国即使在诺曼征服之后,也没有建立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对法律的解释势在必行。作为法律实施者的法官,特别是英王出于加强集权的目的而派出进行巡回审判的法官,自然会成为行使法律解释权的首要人选,否则其审判活动就无法进行。于是,法律解释权很自然地配置给了法官。而帝政时期的罗马和封建专制时期的中国,立法都非常发达,它们分别成为古代西方和东方创造的杰出法律文明的代表。一般来说,立法的发达也意味着需要解释的法律很多,因而法律解释应当是发达的。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立法在当时的社会中过于发达和完备,再加上维护君权的需要,统治者自然不能容忍对法律进行较大程度的解释。于是,罗马最后干脆不允许君主之外的主体解释法律,中国仅仅允许官方和民间在很小的空间里对法律进行注释。在这种环境下,法律解释权很难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力,而只能附属于君权。罗马曾一度由法学家行使法律解释权,也与当时法律的完备程度有关。法学家行使法律解释权时期,正是罗马法开始摆脱宗教的影响而向世俗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问题需要法学家予以解决。当法律逐渐完备时,法学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他们的法律解释权必然会被剥夺。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法律状况是制约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具体条件。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法律表现形式多样,形成不同的法律体系,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就会混杂,不同体系的法律由不同的主体解释。如果法律的表现形式单一,形成一个比较完备周全的体系,法律解释权就会集中到个别或者单一的主体上,法律解释活动也会受到诸多限制。
(三)解释原理——支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内在规律
从历史上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看,大约有三类主体掌握着法律解释权。第一类是法律的实施者,这类主体对法律的解释是站在实施法律的立场上进行的,他们的解释活动受立法者的影响不大,以致于出现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相抗衡的局面。第二类是立法或者立法参与者,这类主体对法律的解释一般是站在立法的立场上进行的,他们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立法的补充,因而他们行使的法律解释权实际上是立法权的一部分。第三类主体是介于立法者和法律实施者之间的主体,他们往往不是因为自己握有立法权或者法律实施权而进行法律解释活动,他们是靠自己所具有的某种权威而在名义上或者在事实上行使法律解释权。
这三类主体中,第一类主体的法律解释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巩固,并在有些国家中成为最终的法律解释权主体。如英美的法律解释权一直由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的这种配置不但没有受到质疑,反而日益加强。法德两国曾禁止或者严格限制法官解释法律,但最终承认了法官的法律解释权。第二类主体的法律解释权在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其最终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如法国和德国在遏制法官的解释权时,都尝试着建立一个类似立法机关的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然而法律实践宣布了这种尝试的失败。罗马和封建中国由于国家灭亡或者政治体制被推翻,它们实行的由立法者解释法律的做法也归于消灭。第三类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持续的更短,它们仅仅存在于人类法律发展的特定时期。
三类不同的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所得到的历史命运截然不同,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支配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最基本的原因应当是法律解释活动的规律。法律解释活动是一种解释活动,必然不能违背解释原理。从解释原理看,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三位一体的过程,没有理解和解释就没有应用,所有的应用过程都必然包含理解和解释活动。显然,法律解释与法律实施应当属于同一个过程,法律的解释者应当是法律的实施者,法律的实施者必然要解释法律,法律解释权只能配置给法律实施者。立法者或者立法参与者所掌握的法律解释权,实际上不过是立法权而已,他们对法律的解释更像是立法而不是解释,因而他们没有必要行使法律解释权。而介于法律实施者和立法者的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使他们作出的解释既不属于立法的延伸又不属于针对实施而对法律的说明,显得不伦不类,因此这类主体不能行使法律解释权,他们的法律解释权被剥夺是早晚的事。
尽管在人类法律发展的早期,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很多,但法律解释的发展趋势是法律解释权配置给法律实施者。这种配置结果不是哪个国家或者哪种法系的主观选择,而是法律解释活动的客观规律,是解释原理的必然要求。不同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结果,正是在这种原理和规律的支配下实现的。
(四)历史事件——改变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直接动力
事物的发展都按其自身的规律进行,但对事物发展的进程产生直接影响的往往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发展历程中,历史事件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改变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直接动力。历史事件的这种作用,在一些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出现较大变化的国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一个国家内部统治者的某些重大决定,会对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罗马法学家法律解释权的取得和丧失都是很好的例证。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法学家在法律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要归于帝政前期的罗马统治者奥古斯都的决策。此前罗马并无官方法律意见,任何以学识著名的人都可以发表咨询意见。但奥古斯都认为,法律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权威,于是规定某些意见具有如同其敕令一样的权威性。此后法学家们就开始追求获得这种特权。奥古斯都的措施使罗马法有可能成为一种科学,导致其不同于希腊法的命运,从而形成了法律发展史上一种新的法制类型。[2]P340在人类历史上,认为应当统一不同法律意见的君主不在少数,但建立把统一不同法律意见的权力交给某些法学家这一制度的只有奥古斯都,罗马法学家也因此而获得法律解释权。而罗马法学家法律解释权的丧失,则是查士丁尼编撰《国法大全》导致的直接结果。《国法大全》颁布后,查士丁尼立即禁止再行参阅其他任何法学家的著作。得到他承认的著作都被收录在《国法大全》中,因此只能参考《国法大全》。这样,同时又排除了其中收录的著述的原始权威。查士丁尼还禁止对其编撰的法典作任何评注。换言之,查士丁尼试图废除《国法大全》所未曾收录的一切先前法律。[3]P7可见,罗马法学家法律解释权的取得和丧失,都直接取决于当时罗马统治者做出的重大决定。正是这些历史事件,直接改变了罗马法学家在法律解释权配置历史上的命运。
革命对一个国家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改变影响更大,这可以从英法两国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对比中看出来。英国自立国以来,社会发展较为平稳,虽然发生过“光荣革命”,但革命最终以不同势力的妥协而收场,对旧制度的改变并不大。因此,英国早期由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做法一直沿用下来,历经千年而不衰。法国大革命是近代西方最为激烈、影响最大的革命,彻底颠覆了法国的旧制度,革命前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方式在革命后被彻底抛弃。肢解法院系统,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严格限制法官的法律解释权等做法,成为法国大革命在司法和法律解释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直到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在对一些案件的审判中,法国才逐渐纠正革命中的错误认识,开始承认法官的法律解释权。
三、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启示
对法律解释权的配置进行历史考察,探讨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的规律,分析影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各种因素,不仅是为了把历史事实弄清楚,把相关问题说明白,而且是为了寻找对当前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有益的借鉴。通过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中华法系代表性国家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可以感受到一些启示。
(一)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遵循法律解释原理和规律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不同主体都可以解释法律。然而真正的法律解释只能存在于法律适用领域。法律解释只有在法律的意义不明确时才能产生,但法律只有在同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时才会暴露其缺点。一方面,法律的僵化性决定了法律需要被解释。法律的僵化性首先表现为法律的不周延性,即法律作为抽象的行为规范,并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许多情形法律不可能作出规定,也不可能规定清楚。法律实施者不能因为某些案件法律没有规定就拒绝实施法律,他需要做的是进行解释,通过解释把模糊的法律意义说明白或者填补法律的空缺。法律的僵化性还表现为法律的滞后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对象会发生很大改变,但法律本身却不能随便修订。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对法律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由法律的实施者不断赋予法律中的文字以新的意义,使法律不断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法律之间的冲突决定了法律实施者需要解释法律。尽管法律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但其内部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无论是同一效力层级的法律还是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都可能发生冲突。法律实施者在冲突当中无论是对它们进行调和还是作出取舍,其实都是在对法律进行解释。因为这些法律都是有效的,当法律实施者拒绝适用某些法律或者对相互冲突的法律进行协调时,就意味着他已经对这个法律作出某些改变,尽管只是细微的改变,但他毕竟没有原封不动地适用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而是适用自己所理解的法律。由此看来,法律只有在适用过程中,在被应用于具体案件时才需要解释。
从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看,有权作出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最终是司法主体,也即是法院和法官。“法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把成文法实施到特定的案件中,通过审判对争议的问题作出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的判决。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它们必须在每一个案件中对成文法的意义作出可以运用到个案中的恰当的意见。这是清晰的意见,特别是当法院对成文法应当被怎样理解而公开表述意见时,应当认定法院的活动是一种解释。”[4]P11-12这番话道出了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关系。法律进入适用阶段后,抽象的法律同具体的案件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发现成文法的缺陷和漏洞的过程,也是司法机关对法律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原因在于,司法机关不可能把有缺陷的法律退回到立法机关那里,由立法机关再作出说明,而且即使立法机关再作出说明,这种说明也是抽象的,适用起来照样有缺陷。而且,司法机关也不能求助于其他机关对法律进行解释,因为该其他机关如果不是法律适用机关,它对法律的解释同样是抽象的,它的解释最后还要由司法机关来解释;该其他机关如果是法律适用机关,就等于司法机关背后还有一个最终的司法机关真正地掌握着司法权,它剥夺了现在正在审理案件的司法机关的司法权。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要适用法律都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否则它将无法处理案件。司法权被称为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不能以法律规定模糊或者有缺陷为由而拒绝审理案件,凡是需要司法权作出最终裁决的案件,它必须依法审判。只要司法机关掌握了法律解释权,法律上的模糊和矛盾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总之,尽管解释是任何主体都能做的事情,而且不同主体的不同解释在客观上有利于人们更为全面、客观地分析和探讨问题,但法律解释活动并不是任何主体都可以进行的,只有特定的主体才能作出法律解释。从法律解释的原理看,法律解释权只能配置给司法主体。
(二)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与法制状况相适应
法制的完备、统一状况不仅制约着法律解释活动,而且制约着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一些法治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往往比较规范、统一,而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就显得粗糙和混乱。认识到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与法制状况相适应,对于正在建设法制的国家和法制基本完备的国家来说显得更有意义,因为前者需要充分吸收已有的经验,避免可能的曲折,而后者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未必合理,结合法制状况对法律解释权的配置进行改进和优化,能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
正在进行法制建设的国家,在法制建设中既要充分发挥法律解释权主体的作用,又要避免出现法律解释主体杂乱的情况。法制建设在客观上要求加大法律解释的力度,通过法律解释不断完善和修正法律,促进法制的进步,推动法律的实施,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加大法律解释的力度,无非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不同的主体,使它们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相应的法律作出解释。第二种是先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各种不同的主体,等它们充分行使法律解释权推动法制进步后,再统一取缔它们的法律解释权,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应然的主体。第三种是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一种主体,扩大该主体解释法律的权限,使该主体在不同法律领域都可以充分解释法律。从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轨迹看,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正在走向一元,也即是只有司法主体才应当被授予法律解释权。采用第一种方案虽然可以调动不同主体解释法律的积极性,从不同领域推动法制的进步和完善,但最终会带来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混乱,各种法律解释相互冲突的局面不可避免。采用第二种方案同样会对法制建设带来破坏,因为法律追求的是连贯性和可预测性,突然取消一些主体的法律解释权将侵害法律的连贯性和可预测性。采用第三种方案既能充分实施法律,使法律不断适应社会的进步,又可以避免日后法律解释混杂的局面。显然,第三种方案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对于正在建设法制的国家来说,在其法律过于粗疏、各种具体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之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法律解释权直接配置给司法主体,充分发挥司法在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法制基本完备的国家,应当及时纠正法律解释权配置中的不合理的做法,改进和优化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实现法制的统一。当前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国家为了推动法制的进步,在法制不完备时就把法律解释权分别配置给不同主体,调动这些主体在法律解释方面的积极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制建设,法律解释活动获得长足的发展,除了带来法制基本完备统一的良好局面外,还出现各种法律解释相互冲突的不良局面,甚至出现法律解释的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法律本身的结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不利于法治建设,因为法律解释过多不但会导致法律本身的权威受到挑战,而且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相互矛盾也会加剧法制的混乱。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需要做的是尽快理顺不同法律解释权主体的关系,根据法律解释原理和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基本规律,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稳固、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取消一些主体的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权和法律解释回归其本位。
(三)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应当结合现代法治精神
法律解释权最终被配置给司法主体。法律解释权主体的演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法律解释权的配置逐渐走向合理的表现。因此,现代国家在借鉴历史上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时,应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历史,结合现代法治精神合理地配置法律解释权。具体来说,现代国家配置法律解释权应当做到如下三点:
首先,要摒弃多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做法,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单一的法律实施主体。当前有些国家存在多种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局面,尽管这种局面带来法律解释杂乱的结果,但取消一些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单一的主体却会带来其他一些不好的结果,既然如此,维持现有的局面或许被认为有利于法律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多个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情况下,是否取消多数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单一的主体,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应当看到,历史上多种主体行使过法律解释权,是当时的特定条件决定的。由于人类对法律的认识不深入,对法律解释活动的规律把握不准确,对君主集权的认可和接受,对司法活动的轻视,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推动等原因,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几经变迁。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人类在探索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程中不可避免会经历的曲折。当今一些法治国家的法律解释权最终配置给单一的司法主体,这种配置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但它明显比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多种主体更有优势,更能推动法律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因此,现代国家在建设法治的进程中,应当注重吸收最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和权力配置方式。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单一的司法主体,才是当前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最好选择。
其次,要摒弃集权观念下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方式,以分权观念指导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历史上无论是君主操纵法律解释权,还是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都带有明显的集权色彩。集权观念是古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的法治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约,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律解释权尽管常常被人所忽视,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大的权力,把它配置给哪个主体,哪个主体的权力就明显扩大了。如果把法律解释权配置给司法主体,则可增强司法主体的权力,更有利于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约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否则,司法权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其对法律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会小得多。因此,现代国家在配置法律解释权时,应当注重吸收分权观念指导下的配置方式。
再次,要摒弃法律解释权配置中意识形态的干扰,按照法律解释规律的要求配置法律解释权。通过考察不同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方式,对比它们的优势和不足,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英美法德等国当前采用的由法院和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这种结论并不是说,只有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方式才是科学的,比较恰当的说法可能是,英美两国数百年来一直沿用的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方式经过它们的法治实践,被证明符合法律解释活动的规律,比其他典型国家(如古代的罗马和中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更为合理,后来法国和德国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并且实践效果良好。英美法德等国当今的法治建设取得公认的成就,它们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方式自然也值得关注。对此,现代国家在法治建设中应当摒弃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待英美法德等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合理性。
注释:
① 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详见魏胜强的系列文章:《西方法学中的法律解释权》,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中国法律解释权主体的历史演变》,载《政法论丛》2011年第3期;《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探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德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演变》,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美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探析》,载《政法论丛》2012年第5期,《法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考察》,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 [英]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M].黄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 [美]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M].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 [美]梅里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 D. Neil MacCormick,Robert S. Summers.Interpret Sta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M].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Aldershot,1991.
TheHistoricalEvolutionoftheConfigurationofLegalInterpretationPower
WeiSheng-qiang
(Law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450001)
Investigat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of the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and Chinese legal system, we can discover the evolution regular pattern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as the follows: the basic concep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from fuzzy to clear,the purpose of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from centralization to decentralization, the exercise subjec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from multiple to single,the exercise wa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from the sacred to the secular. According to depth analysis on in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lloc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we can see,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overall framework which control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legal status is the actual conditions which restrict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is the internal rule which dominate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historical events is the direct motivation which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The inspi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are the follows: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should in conformity with legal status,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should combine with the spirit of modern rule of law.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 configuration; evolution
1002—6274(2013)03—113—09
DF03
A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研究”(项目编号:2012-JD-033)。
魏胜强(1976-),男,河南遂平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律方法、司法制度。
(责任编辑:孙培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