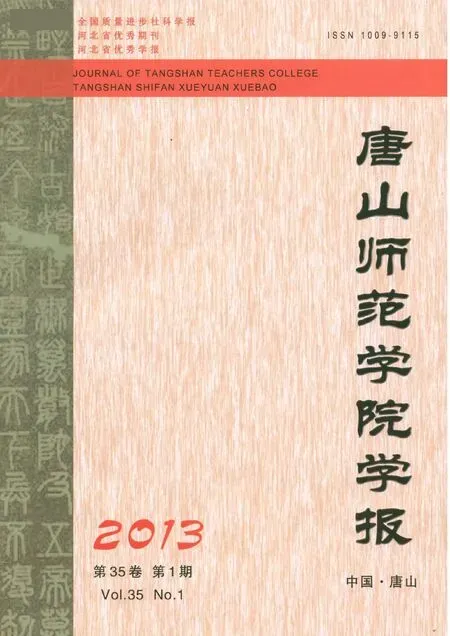“转注”综论
张素凤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一、转注异说述评
对于“六书”的认识,自唐代以来,各家说法不断出现,主要有“形转说”“音转说”“义转说”“形兼音说”“形兼义说”“音兼义说”“形音义兼及说”“首字转注说”“互训说”“声首说”“省形说”等等。这些说法有的名异实同,有的名同实异,可以说莫衷一是。这主要源于对许慎“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老考是也”定义的理解不同。笔者对各家说法进行了认真分析比较,并根据立足点的不同,对转注概念的诠释情况进行了简单分类,主要包括:从字际关系角度进行诠释,从造字角度进行诠释,从用字角度进行诠释。
(一)从字际关系角度对转注概念进行诠释
对于定义“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老考是也”,有的学者从字际关系角度进行诠释。由于例字“老”“考”之间意义、形体和读音三方面都有相近关系,因此同是从字际关系角度对转注概念进行诠释,各家侧重点不同,所揭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也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侧重字义关系
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尔雅·释诂》有多至四十字共一义,起六书转注之法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转注犹言互训,注者,灌也,数字辗转互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输互受也。”显然,戴震、段玉裁师徒对转注概念的理解侧重于具有相同或相近意义的字,也就是他们侧重于形音义三要素中的意义因素,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后人称为“义转说”“互训说”或“主义说”。
刘师培论转注,也以戴、段“互训”之说为据,但以为用《尔雅》来解释互训“泛滥而失厥归”,因此他在《转注说》里对戴、段说作了修正,以为只有《说文》里同部互训的字才算“转注”。
2. 侧重字形关系
有的以转变字形方向为转注,如“孙愐《切韵》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转’,戴仲达《六书故》、周伯琦《六书正讹》别举侧山为阜,反人为匕之类当之”[1]。从字形角度来解释互训,被后人称为“形转说”。
清曾国藩、钱大昭把表义构件省去部分笔画的字看作转注字。曾国藩在《与朱太学孔扬论转注书》里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凡形声之字,大抵以左体为母,以右体之得声者为子,而母字从无省画者。凡转注之字,大抵以会意之字为母,亦以得声者为子,而母字从无不省画者。省画则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来,惟好学深思,精心研究,则形虽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虽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耋等字之意从老而来;履字虽省去舟,而可知屦屐等字之意从老而来;……推之犛、爨、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类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画省而意存也。”这种观点可以用“省形”说概括。把转注字看作省形字的还有胡朋[2],他说转注“正在形声会意之间”。考从丂得声,而不称之为形声字,是因为“丂”虽是声符而“老”不是形符,“形声字,必有真形全形”;又以“孝”“昼”为例说明转注字与会意字的区别,即转注字的一个表义构件有所减省。总之,转注字与会意字、形声字的区别就是其表义构件有所减省,简言之,转注字就是省形字。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谓老之别名有耆、有耋、有寿、有耄,又孝,子养老,是也。一首者,谓此孝等诸字皆取类于老,则皆从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别名,皆同受意于木,故皆从木。”江声《六书说》:“立老字以为部首,即所谓建类一首。考与老同意,故受老字而老省;老字之外,如耆、耋、考之类,凡与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属于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数字,所谓同意相受。”南唐徐锴、清代江声对转注概念的理解侧重于具有相同部首的字,被称为“部首说”。此外,王筠认为“建类一首”是指同在一部,“同意相受”是指“其训互通”。
形转说、省形说、部首说侧重的都是汉字形音义三要素中的形体因素,因此,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主形说”。
3. 侧重字音关系
章太炎《小学略说·转注假借说》:“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迭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何谓建类一首,类谓声类……首者,今所谓语基。……考老同在幽类,其义相互容受,其音小变。按形体,成枝别;审语言,本同株。虽制殊文,其实公族也。”显然,章太炎对转注概念的理解侧重于语音相同相近的字,也就是他们侧重于形音义三要素中的语音因素,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后人称为“音转说”“主音说”。
黄侃[3]认为:“建类者,言其声音相类。一首者,言其本为一字。同意相受,又言别造之文,其受有所受也。”初文之转注,即同声同义而异字;又进一步推广为:转注为声义相联。
后来杨树达对章太炎“转音”说进行了修正和改造,他认为只有叠韵、双声两个部分属于转注范畴,而排除了同音部分,也就是说,只要具备音近义通条件,就能构成转注关系。张舜徽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声母通转说”,即在章太炎“同意相受、双声相转、叠韵相迤”的基础上扬弃了“叠韵”部分,认为只有声母相同相近的字之间才能形成转注。
显然,不管是侧重字形特点还是侧重字音特点的转注观,都有一个前提,即转注字之间要有一定的意义联系,或义同义近,或意义关联。因此,后世有的学者把侧重字形关系或侧重字音关系的转注观,称为“形兼义说”“音兼义说”等。
4. 形音义三者并重
梁东汉认为“建类一首”是指同一个部首,声音又相近,“同意相受”是指意义相同,可以相互训释。也就是说转注字与原字之间要形、音、义都有联系,转注字是对原字进行加注音符或者改换音符形成的,因此,所有的转注字都是形声字。周祖庠认为,“转注字是一种同源字,形旁相同、意义相同、语音相转的同源字”[4],也就是从字际关系方面来看,转注字之间,形音义三个角度都有联系。
(二)从造字角度对转注概念进行诠释
对于定义“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老考是也”,有的学者从汉字创造角度进行诠释。从汉字创造角度进行诠释,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从造字原因角度诠释和从造字方法角度诠释。
1. 从造字原因角度诠释转注
(1)语言变化是转注字产生的原因
孙中运认为,转注就是转语注声的缩语。转语,就是语言的变化,一个字或因古今音变,或因方言殊异,因此要按新的读音另造新字。另造新字的方法主要是“注声”,就是在原字上加注声旁。简言之,“因转语在原字上加注声旁的汉字是转注字”[5]。他认为“建类一首”的“类”即字类,“首”即部首。“同意相受”就是说部首即义旁和这个转注字的概念完全相同,即新字受意于部首。因此转注字不等同于形声字。持近似观点的还有周秉钧,他认为,转注是同义词的造字法则,强调因语言变化而转注,也就是语言变化是转注字产生的原因[6]。
同是把语言变化看作转注字产生的原因,陆宗达不赞同以上为同义词造字的转注观,他提出了“汉字构形、发展法则说”,认为转注是为从某一语源派生的新词制新字,即语词派生是创造新字的原因,显然,陆宗达用文字孳乳的规律来解释转注的概念内涵。
以上两种说法都把语言变化看作转注字产生的原因,其不同点在于,前一种说法认为转注是为因语言变化而产生的同义词造字,后一种观点认为转注是为同源派生的新词造字。毋庸赘述,同源词外延包含因语言变化产生的同义词,因此说,两种说法的区别主要是范围大小不同。
(2)因假借字多而造转注字
孙雍长认为,转注是造字方法,其产生原因源于当时假借字多,假借包含谐音假借和引申假借;转注字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减少假借字[7]。显然,这里的假借不仅包括借用没有意义关联的同音近音字,也包括用本字记录派生词的记词方法。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黎锦熙,他将六书合并为二书,认为转注就是在假借字基础上增加表义偏旁。
(3)因某字记录词义过多而造职能分化字
根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序》:“徐楚金(笔者按,即徐锴)则就考字傅会,谓祖考之考,古铭识通用丂,于丂之本训转其义,而加老注明之;犬走为猋,《尔雅》扶摇谓之猋,于猋其本训转其义,飚则加风注明之”[1],显然,徐锴认为,“丂”“猋”在用来记录本词的基础上又被借用记录同音他词,于是通过增加构件创造职能分化字,这是转注字产生的原因。
方有国认为,先民使用“转注”法造字,其着眼点主要不在假借现象上,而是在需要加以转注的字所记录的词义上。不仅转注造字法是针对词义的,“六书”中其他五书作为造字法,也都是针对语言中的词或词义而进行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含义是:给需要进行转注的“转注原体字”的意义建立一个事类范畴并为其确定一个类首,同时把不加改变的转注原体字的意义授给新造出来的转注字。“转注字”就是“回头加注(类首)”[8]。
表面看来,以上第二、三种说法从字的记录职能角度分析转注字产生的原因,与第一种说法角度不同。其实记录词义过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某字记录本词的同时又记录同源派生词,二是某字记录本词的同时又记录同音近音的他词。可见,第三种说法在外延上可以囊括第一、二两种说法。
2. 从造字方法角度诠释转注
孙诒让说:“盖仓沮制字之初,为数尚鲜,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则依其声义,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其后递相沿袭,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来也。”[9]郑珍也认为:“可知形声字以形旁为主,一形可造若干字,单各取声旁配之,转注大相别,字以声旁为主,一字分为若干用,但各以形旁注之。转注与形声事正相反,而实相成。”[10]显然,孙、郑认为转注是一种造字方法,即在原字基础上增加表义构件创造新字的方法。现代又有人提出,“转注”是通过在原有字的基础上添加一个意符或声符来创造新字的方法,即将部首之义(意)或声符之音转而注入新造字,从而产生在已有文字上加注意符或音符而造成繁体字或分化字的方法[11]。
汪荣宝也认为转注是一种造字方法,但他的观点又不同于孙、郑。他说:“故转注者,乃取一全体之字,削其一体而代之以他体,以为新字,而其义则仍与原字之义相通或相承也”;又说“转注者,以改字为造字者也”;并明确地说明了转注字就是“从×省”类省简了义符的合体字[2]。当代也有学者与汪荣宝观点类似,江胜利认为,转注是汉字的一种构成方式,即造字法则。“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中“建类”就是聚合形同义近的字,“首”即所建之类的部首字,“同意”指构字方式相同——首字省形为不成字偏旁,再注入义符或音符[12]。
(三)从用字角度对转注概念进行诠释
把“六书”分为“四体二用”,始于宋人,元明续有论述。明人吴元满《六书总要·六书总论》说:“象形,文之纯,指事,文之加也;会意,字之纯,谐声,字之变也;假借、转注,则字之用也。”又《谐声指南·引》:“六书形事意声,四者为体;假借转注,二者为用。”至清人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论述得更为详明。“四体二用”说是鉴于把“六书”看成同一性质的东西而无法自圆其说的重新解释,即认为“六书”具有“体”“用”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内容。
朱骏声对转注、假借的概念理解不同于戴震,他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凡一意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他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名者,曰假借。依形作字,睹其体而申其义者,转注也。连缀成文,读其音而知其意者,假借也。”[1]显然,朱骏声认为转注是用原字记录引申义的用字方法,假借是用原字记录音同音近他词的方法;但朱骏声与戴震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认为假借和转注都是用字方法。
后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也认为“转注”不是造字方法,而是用字方法,使这种说法目前在学术界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对转注性质问题的认识
(一)关于“六书”性质和分类标准问题
我们认为,汉字结构类型和造字方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结构类型是对已有汉字的结构进行分类研究的结果,是有据可循的;造字方法是创造汉字时所采用的方法,不难理解,造字时造字者如何考虑,具体某个汉字用什么方法创造出来,只能依靠汉字结构特点和类型进行推测,因此,严格意义上说,造字方法是不可确知的。同时,造字方法和结构类型又是密切相关的:造字方法是根据语词音义创造汉字形体的方法,结构类型是汉字形体与所记录语词音义的联系方式。造字方法和结构类型的共同点:都是汉字形体与所记录语词音义的联系,或者说,汉字形体与其记录职能的联系,简言之,就是字形与字用的联系。显然,结构类型和造字方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结构类型是造字方法的表现形式和结果;造字方法只能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和揭示。
正是由于汉字结构类型与造字方法这种一体两面的密切关系,因此,后世对“六书”的性质和分类依据有各种不同说法。那么,“六书”的性质和分类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从许慎写作《说文》的动机分析
许慎被称作“五经无双许叔重”,他写作说文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典籍解释混乱的时弊,从而准确地解经。因为当时经学界“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14]。而要正确解经,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每一个字的意义,因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13],因此,许慎花费二十二年的时间“探索文字的本源,推考文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及其由来”,从而“从古文经学派观点出发来发扬五经之道,为当时的政治政治服务”[14]。也就是说,探求字形与字用的联系正是《说文》的写作目的。
2. 从“六书”理论的起源与作用分析
“六书”一词,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作为“六艺”之一的“六书”,是“保氏养国子以道”的内容。这一点《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都提到了,而且许慎更明确地指出了儿童七八岁入学就开始学习“六书”。可以想象,七八岁的儿童不可能刚开蒙就学习造字,只能是学习识字,因此“六书”内容只能与识字相关,不可能是造字方法。而掌握字形与字用的联系,可以帮助识字,因此,“六书”的分类标准不可能是造字方法,而是字形与字用的联系方式。
3. 从许慎对“六书”概念的诠释分析
古人开始造字并不知道有所谓“六书”,更不可能根据“六书”理论指导造字。“六书”是后人根据字形结构总结出的理论。许慎给“六书”所下的定义,很能说明这一点。如“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视”“察”都是“看”义。显然,“看”的对象是字形,所以,字形应是先于“六书”理论而存在的。段玉裁将“察而可见”改为“察而见意”,则更明确地说明了“视”“察”字形的目的是为了见“意”,也就是看出字形构意,即字形与字用的联系。同样,“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是说象形字的形体与意义所指客观实物的外形相似,可以从字形看出意义;“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是说形声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表示意义类属,一部分与字音相关;“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是说会意字由两个以上构件组成,构件意义会合起来,就是会意字的意义。显然,这“四书”是根据字形与字用的联系方式划分出来的结构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字形与字用中的意义因素都有联系。
由于汉字结构类型与造字方法都是字形与字用的联系方式,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班固”把“六书”说成“造字之本”,此后很多学者延续班固的说法,但对于“假借”“转注”的诠释却意见不一。由于假借没有创造新字形,以及对转注概念的不同理解,有的学者还把“假借”“转注”看作用字方法,这就是“四体二用”说。
我们认为,“假借”“转注”作为“六书”之一,分类标准应该与前“四书”一致,也是根据字形与字用的联系方式划分出来的汉字结构类型。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是说假借字的形体与所记录语词的意义没有联系,但该字的读音与其所记录语词的读音相同相近,也就是说字形与字用的读音有联系。
可见,“六书”中的“五书”都是根据字形与字用联系方式划分出来的汉字结构类型,那么,“转注”是否也是从这个角度划分的汉字结构类型呢?下面我们将做专门讨论。
(二)对“转注”概念的理解
从字形与字用关系角度分析,“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是说转注字的某个构件与所记录语词的音、义都没法直接联系,只能通过“挹彼注兹”辗转注释的方式,把字形与字用联系起来。如:从“考”字小篆字形“”,看不出它和意义“老也”有什么联系,只是它和“老”的小篆字形“”具有相同的构件,而这相同的构件又不能独立成字,因此“考”的小篆字形不能和其记录职能直接联系,不能说明该字为什么具有“老”义。为了把小篆字形“”与其职能联系起来,《说文》把该构件说解为“从老省”,这样,借助与它具有相同构件且意义相近的“”来分析字形,使“考”的小篆字形与其记录职能辗转联系起来。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是说当一个字的某个构件不能与其职能联系起来时,通过把该构件说解为另一个构件的省略形式或反倒形式等,使该构件具有另一构件的构意,从而把该字形体与其记录职能辗转联系起来,使其字形能够解释其字用。
有的说法,与本文观点十分相似,如把省形字看作转注字。如:上文提到的清代曾国藩、钱大昭、胡朋等,从字形特点角度,把省形字看作转注字;汪荣宝、江胜利,从造字方法角度,把省形字看作转注字。这些说法的缺陷在于把转注字局限在省形字范围内。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首先是他们从“老”“考”的形体关系出发,或将关注点停留在字形结构层面,或将关注点放在造字方法角度,没有进一步探讨判断汉字结构和造字方法的依据——汉字形体与所记录语词音义的联系方式,没有进一步探讨“六书”的根本性质和分类标准;其次,他们把转注定义中“同意相受”的“意”误解为“义”。但是,根据“《说文后叙》中,许慎凡说经之义、字之义者,皆用‘谊’;凡说字形皆用‘意’”[12],“意”指的不是“意义”,而是“构意”“造意”;“同意”是《说文》用以解说字形构式的一个术语,是说不同字的构形用意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它可能指字形中的表义因素,也可能指字形中的示音因素。因此,转注字应包括所有需要辗转借助其他字形进行结构分析的字,不仅包括省形字,还应包括省声字、构件被分析为“倒某”“反某”“古文某”的字。
我们认为,“六书”是根据已有汉字形体与所记录语词音义联系方式所划分的汉字结构类型,即根据字形与字用联系方式划分的汉字结构类型。“转注”作为“六书”之一,其特点是,字形中某个构件不能与所记录语词的音义联系起来,但可以借助“某省形”“某省声”“倒某”“反某”“古文某”的形式与其他相关构件联系起来,从而与所记录语词的音义辗转联系起来,使其字形能够解释其字用。
[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序[M].武汉:武汉古籍书店,1983:3-12.
[2]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8:201-212.
[3]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0.
[4]周祖庠.我对“转注字”的理解[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5]孙中运.论“六书”之转注[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3-8.
[6]周秉钧.古汉语纲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57.
[7]孙雍长.转注论[M].长沙:岳麓书社,1991:51-52.
[8]方有国.六书“转注“补说.[J].汉字文化,2008(4).
[9]孙诒让.名原(下卷)[M].济南:齐鲁书社,1986:13.
[10]郑知同.说文浅说[A].清史稿·说文本经答问[C].北京:中华书局,1977:58-60.
[11]李海娟.浅谈“转注”与“类化”[J].齐齐哈尔示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70-71.
[12]江胜利.“转注”新论[J].黄山学院学报,2005(1):101-103.
[13]许慎.说文解字·叙[M].北京:中华书局,1963:319-320.
[14]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引言[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