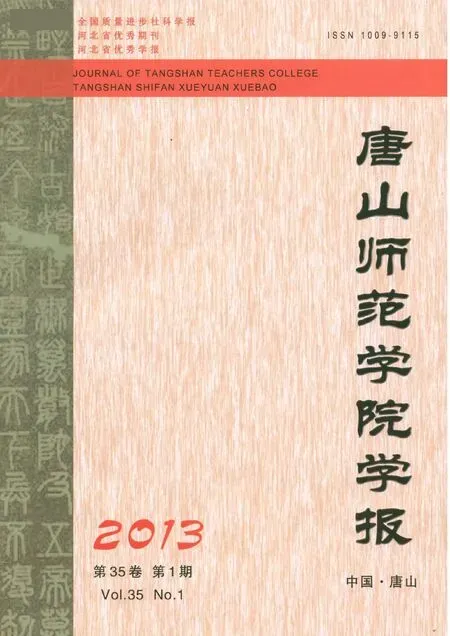印欧语言起源研究之旧石器连续范式
郑晓行
(淮南师范学院 外语系,安徽 淮南 232001)
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印欧语言起源问题研究动态的介绍尚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1-3]。本文试图介绍阿里内(M.Alinei)[4-5]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提出的印欧语言起源的旧石器连续范式(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以下简称PCP),通过梳理学术界对PCP的反应及其原因,探讨PCP的主要特点。
一、PCP介绍
(一)PCP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汤姆斯(H. L. Thomas)、比利时著名旧石器中晚期研究专家奥特(M. Otte)、德国中欧史前史研究专家霍思乐(A. Häusler)、语言学家阿里内、科斯塔(G. Costa)和波吉尔克(C. Poghirc)分别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种关于印欧起源的新观点[5],他们不谋而合,认为适用于世界上许多其他语言和民族的旧石器连续模式同样适用于印欧人和印欧语言,印欧语言应该产生于旧石器晚期现代智人(homo sapiens)迁徙到欧亚大陆的时候,而不是伦夫鲁的“小亚细亚起源说”[6]里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更不是吉布塔的“黑海—里海起源说”[7]里所说的红铜时代。这种观点的主要倡导者阿里内组织成立了国际研究团队(International PCP Workgroup),目前有27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术委员会由阿里内、巴利斯特(X. Ballester)、毕诺佐(F. Benozzo)三人组成,建立了专门网站(http://www.continuitas.org/)。到目前为止,该团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由当初几位学者的理论设想(theory)发展成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因此,该团队在 2010年把原来的 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Theory(PCT)更名为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PCP)。
(二)PCP基本理论假设
1. 连续性是PCP研究印欧语言起源的基本工作前提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5]表明,欧洲大多数红铜及青铜时代文化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大多数新石器时代文化延续了中石器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没有间断,没有任何大规模武力入侵并导致一种语言完全取代整个欧洲原有其它语言的证据。
同时,著名遗传学家斯福尔沙发现,人类基因的地域分布同语言的地域分布大体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及该语言所属的语系来辨别其基因归属;语言变异与人类迁徙同时发生[8-9]。牛津大学遗传基因学家赛克斯的最新成果表明,现代欧洲人80%的基因来自旧石器时代,只有20%来自新石器时代[10]。
因此,来自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表明,连续性是史前欧洲的基本发展模式,旨在研究印欧语言起源的PCP以连续性为基本工作前提。
2. 语言历史久远,语言发展具有稳定性特征,变化只是例外
根据古人类学最新发现,南非著名古人类学家托拜厄斯认为,在人属与南猿属直接人科祖先之前,语言中枢及言语的雏形就已经存在,这两个分支可能都通过遗传继承了言语的习性。罗百氏傍人和鲍氏傍人可以选择性地使用语言,但人属必须强制性地使用语言。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语言能力对于南猿属是否是选择性的,而作为人属的独特特征,却是强制性的[11]。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认知神经科学中心主任平克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2]。
因此,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时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1]。
阿里内认为,保持稳定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变化是例外。语言变化不是所谓的“语言的生物规律”导致的,而是受外部因素制约,可发生于语言接触和混合的过程中,也可与重大生态事件、社会经济文化事件等同时发生[5,13]。
3. 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对其进行历史分期
阿里内认为,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以印欧语系为例,可以通过比较所有印欧语言,找出存在于这些语言中相同的词汇,这就是原始印欧语词汇[5][13]。例如,假定现代印欧语言中表示“死亡”的词是原始印欧语词,都来自PIE*-mer,而表示“埋葬”的词却因语言而异,这表明埋葬仪式在旧石器晚期出现时印欧人已经分化。而印欧语言中用于指称中石器时代典型工具的词(如‘bow’、‘tar’、渔具、木工工具等)各不相同,这表明到中石器时代时印欧语言就已经分化了。又如,农业用词在不同的印欧语言中存在明显差异,这证明印欧语言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分化了。
4. 考古边界与语言边界重合
阿里内认为,不同时期史前文化之间的边界及其变迁在考古地层学中可以用地层图清晰显示,其中标注的不同分区具有自成性特征,并不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影响,受每一种文化发展的具体而独特的顺序制约,彼此区分开来。每一个文化序列对应一个特定分区,具有非常清晰而突出的文化个性特征。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可以把这些文化边界看成不同语系、同一语系不同语言及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之间的边界。例如,阿尔萨斯地区的法语与德语之间的边界就与考古学中区分凯尔特人区与现在说德语区域的新石器和红铜时代文化之间的边界一致[5,13]。
(三)PCP对印欧人及印欧语系的历史重构
同其它理论一样,PCP也试图对印欧人及印欧语系进行历史重构,阿里内认为,应把智人(约20万年)从非洲迁徙到欧亚两洲看成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而不应将之视为新近发生的事情,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原始印欧语已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首先,这与智人走出非洲的初始阶段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有关;其次,随着社会阶级分化与殖民战争的出现,分化节奏越来越快,新分化出来的群体居住于不同区域,而不同区域所处的文化、社会及政治阶段又各不相同[5,13]。
(四)PCP的理论目标
PCP是对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乌拉尔语系连续理论(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的发展[14],到目前为止,PCP已经对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虽然其基本理论目标是建立研究印欧语言起源的新范式,形成更有说服力的印欧语言起源的新理论,但该团队也希望PCP能够成为研究所有语系及其起源的通用范式。PCP如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获得成功,换言之,如果它能成为所有直接或间接与语言相关的研究领域的通用研究范式,它也将有助于更基础的哲学理论(如Gontier的“进化认识论”[15])的发展[13]。
二、学术界对PCP的反应及其原因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印欧语言起源的PCT经过2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研究印欧语言起源的新范式,但国际主流学术界并没有对该范式给予足够的关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一)PCP的工作语言是意大利语
尽管莫里斯认为,与印欧语言起源的其它理论观点相比较,PCP提出的关于印欧语言是中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语言延续的见解更易于理解,更有说服力[16],但遗憾的是,PCP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用意大利语而不是用英语出版的,因此,在英语界引证的人很少,可能要等到把这些意大利语论著翻译成其它语言之后,PCP才有可能赢得学术界的广泛接受与认可。
(二)基因连续性与语言连续性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
虽然来自基因科学的证据表明,现代欧洲人80%的基因来自旧石器时代,只有20%来自新石器时代[10],但这并不能证明印欧语言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也是连续发展的,基因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语言的连续性。
(三)对PCP确定的原始印欧语分化时间持异议
吉布塔认为,印欧人到达欧洲应该在公元前4000年,原始印欧语的分化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7]。主流学术界广泛接受她的观点,但也有与伦夫鲁结论一致的,认为印欧语言分化应该在距今7 800至9 800年之间,而且距今5 000至6 000年之间是印欧语言高速分化的时期,因此,伦夫鲁的理论与吉布塔的理论并不相互排斥[17-21]。因此,PCP确定的印欧语言分化的时间(旧石器时代晚期4.5-1.5万年前)远远超出了主流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时间。
(四)对“黑海—里海起源说”的强烈支持
吉布塔1956年提出的“黑海—里海起源说”是迄今为止关于印欧起源的最权威的理论,它在主流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其后任何一个关于印欧起源问题的假说都无法比拟的,就连伦夫鲁1987年提出的“小亚细亚起源说”也无法与之抗衡,关于印欧起源的其他理论观点就更难赢得主流学术界的支持。
(五)PCP对传统的挑战
PCP不能为主流学术界接受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它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摒弃了传统理论中的“突变论”(Catastrophism),支持“均变论”(Uniformitariamism),摒弃了传统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修正了传统理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解。(下文将具体讨论 PCP的这些特点。)如果 PCP的理论假设成立,语言变化速度远远没有传统观点认为的那么快,因此,历时语言学的年代框架将需要整体修改,同时也需要运用完全不同于传统比较语言学方法重新阐释人类语言语系的整体结构及语言间的谱系关系系统[22]。语言连续理论的倡导者对历时和比较语言学确立的方法已经提出了恰如其分的修正方案[23]。
三、PCP的特点
(一)跨学科性与学科依赖性
与其他研究语言起源的团队一样,PCP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cross disciplinary),非常注重运用其它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学科主要包括考古学、基因科学、普通语言学、古人类学和认知科学等等[24]。PCP的理论假设、历史重构、理论目标和研究方法都是建立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之上,但这也使得PCP具有很强的学科依赖性,也就是说,只要其它学科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PCP就可能受到质疑,其理论根基就有可能动摇,整个范式就有可能被推翻。
(二)摒弃“突变论”,支持“均变论”
阿里内认为,受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突变论者”和“均变论者”,前者占大多数。虽然绝大多数19世纪的语言学家支持后者,但这种支持只是表面现象(superficial),他们仍摆脱不了前达尔文时代“突变论”的影响,认为史前时代是无法穿越的迷雾,拒绝考虑任何与之有关的话题[13]。巴黎语言学学会成立之初就将语言起源问题设为研究禁区;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原始印欧语直到铁器时代才在欧亚两洲出现;吉布塔的“黑海—里海起源说”、甚至连伦夫鲁的“小亚细亚起源说”都没能走出“突变论”的阴霾,没能走进史前时代。
而阿里内通过分析来自不同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出结论,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规模如此之大由一种语言完全取代整个印欧大陆所有其他语言的突发事件。因此,PCP摒弃了“突变论”,极力支持“均变论”,并把“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13][25]作为指导原则,主张建立语言发展与人类史前进化之间的直接联系,并运用恰当的跨学科工具对其进行研究。
(三)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
研究表明,19世纪印欧问题研究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具体体现为雅利安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6]。这种思想把印欧人与其他地区野蛮人完全区分开来,认为原生史前欧洲人与其它地区的人一样,也是野蛮人,与现代欧洲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雅利安人讲印欧诸语言,宣称雅利安人优越于闪米特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将金发碧眼的北欧和日耳曼诸民族视为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种”,他们生活的土地就是所谓的“印欧人故乡”(Urheimat)。阿里内认为,19世纪大多数语言学研究受这种思想影响,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烙印,而后来的学者都完全照搬这些理论[13]。PCP摒弃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
(四)修正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解
阿里内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均变论对当时语言学研究影响最大,但同时也是最致命的,因为语言学家不仅误解了进化论,还把其中的均变论机械地运用于语言研究,把语言看成生命体,有生有死,与其它生命体一样按照类似的自然规律演变,时至今日,语言学家还在重复19世纪语言学家的致命错误[13]。
阿里内对这种误解进行了修正。在支持语言发展均变论的同时,修正了语言是生命体的观点,认为语言与自然之间的确存在接口(interface),但语言不是生命体,而是社会的产物,与货币、法律、工具、服装等社会产物没有本质差异,会受社会因素(而不是所谓的“生物规律”或自然规律)的影响在词汇和语法两个层次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与有机体变化无关。词汇变化具有文化依赖性(culture-dependent),一般不会引起语法变化,是语言使用者一生中可能经历的唯一的语言变化。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语法变化会在语言混合过程中与整个社会对新的语言模式进行心理语言调整的同时发生,从这个意义来说,语法变化具有历史依赖性(history-dependent),在通常情况下,社会处于稳定状态时,一个人一生中不会经历语法变化。语言的这种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少延续5代人:祖父—父亲—自己—子女—孙子(女),因此,语言发展的唯一规律就是保持稳定[13]。
(五)继承并发展了“乌拉尔连续理论”
乌拉尔连续理论是由专门研究欧洲乌拉尔地区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的关于乌拉尔人和乌拉尔语系诸语言起源的一种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乌拉尔人和乌拉尔语系诸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没有间断;乌拉尔人是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他们可能在旧石器时代的冰河时代占据了欧洲中东部地区,并在中石器时代北欧冰川消失的过程中随着冰盖消退而向北迁徙,最终定居此地[14]。
阿里内认为,乌拉尔连续理论取代了效仿传统IE理论而提出的乌拉尔“武力入侵说”,开创性地提出了乌拉尔语系诸语言是旧石器时代语言无间断延续的产物的观点,开辟了一条研究印欧语言起源的新路,并为印欧语言旧石器连续范式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参照[5]。
四、结语
与吉布塔的“黑海—里海起源说”和伦夫鲁的“小亚细亚起源说”相比,阿里内团队倡导的PCP作为研究印欧人及印欧语言起源的新范式尚处于劣势地位,但它是对传统理论的扬弃,在摒弃“突变论”、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修正传统理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解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语言变化的观点、词汇历史分期和语言边界的确定方法值得借鉴和推广。它将可能成为所有与语言相关的研究领域的通用研究范式,值得国际、国内学术界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支持。
[1]周流溪.印欧语言起源新说[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2):73-76.
[2]龚缨晏.关于印欧语系的起源问题[J].世界历史,2000(5):111-115.
[3]刘先宽.印欧语系的起源及特点[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81-83.
[4]Alinei Mario. Origini delle lingue d’Europa, vol. I: La teoria della continuità; vol. II: Continuità dal Mesolitico all’età del Ferro nelle principali aree etnolinguistiche, 2 vol[M]. Bologna: Il Mulino, 1996-2000.
[5]Alinei Mario. 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 An Introduction in Progress[EB/OL]. http://www.continuitas.org/index.Html,2011.
[6]Renfrew Colin.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M]. London: J. Cape, 1987.
[7]Gimbutas Marija. 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 the kurgan culture during the 5th to the 3rd millennia B. C[A]. G.Cardona; H. M. Koenigswald; A. Senn. 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155-198.
[8]Cavalli-Sforza L. L., Piazza A., Menozzi P. Mountain J.Reconstru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bringing together Genetic,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Data[A]. Proc.Natl. Acad. Sciences USA: 85[C]. 1988: 6002-6006.
[9]Cavalli-Sforza L. L., Menozzi P., Piazza A.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Sykes Brian. The Seven Daughters of Eve[M]. London:Corgi Books, 2001: 240-242.
[11]Tobias Phillip V. The evolution of the bra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A]. Facchini. Colloquium VIII: Lithic Industries, Language and Social Behaviour in the First Human Forms, The Colloquia of the 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s(Forlì [Italia]8-14/9/1996)[C], 1996: 87-94.
[12]Pinker Steven. The language Instinct, The New Science of Language and Mind[M]. London: Penguin Books,1994: 345.
[13]Alinei Mario. Darwinism,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New Palaeolithic Continuity Theory of Language Evolution[A]. Gontier Nathalie, Bendegem Jean Paul van, Aerts Diederik(Eds.).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Language and Culture. A non-adaptationist, systems theoretical approach[C].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New York, 2006: 121-147.
[14]Meinander Carl F.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inno-Ugrian Peoples[M].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Archaeology Institute, 1973: 3-14.
[15]Gontier Nathalie, Bendegem Jean Paul van, Aerts Diederik(Eds.).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Language and Culture. A non-adaptationist, systems theoretical approach[C].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2006.
[16]Morris Jonathan. Review: Mario Alinei - Origini delle Lingue d’Europa; Volume 1 - Teoria della Continuità,Volume 2 - Continuità dal Mesolítico all’età di ferro nelle principali aree etnolinguistiche (Il Mulino -Bologna, 1996 and 2000)[J]. Mother Tongue, 1996.
[17]Gray R. D., Atkinson Q. D. Language-tree divergence times support the Anatolian theory of Indo-European origin[J]. Nature, 2003(426): 435-439.
[18]Atkinson Q. D., et al. From words to dates: water into wine, mathemagic or phylogenetic inference?[J].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03, 2005: 193-219.
[19]Atkinson Q. D., Gray, R. D. Are accurate dates an intractable problem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A]. C.Lipo, M. O’Brien, S. Shennan, M. Collard(eds.). Mapping our Ancestry: Phylogenetic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and Prehistory[C]. Chicago: Aldine, 2006.
[20]Atkinson Q. D., Gray R. D. How old is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Illumination or more moths to the flame?[A]. in Peter Forster, Colin Renfrew and James Clackson(eds.), Phylogenetic methods and the prehistory of languages[C].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6: 91-109.
[21]Atkinson Q. D., et al. Languages Evolve in Punctuational Bursts[J]. Science, 2008(319): 588.
[22]Janhunen J. A. Some Old World Experience of Linguistic Dating[A]. In Bengtson, John D. (ed.), In Hot Pursuit of Language in Prehistory[C]. 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2008: 233-234.
[23]Pusztay János. Diskussionsbeiträge zur Grundsprachenforschung Beispiel: das Proto-Uralische[M].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 vol. 43. Wiesbaden: Har rassowitz verlag, 1995.
[24]Saukkonen Pauli. Suomalais-ugrilaisten kansojen ja kielten alkuperä ongelma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Finno-Ugric Peoples and Languages)[M].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Alinei Mario. Towards a Generalized Continuity Model for Uralic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A]. In K. Julku(ed.), The Roots of Peoples and Languages of Northern Eurasia. IV (Oulu: 18-20/8/2000)[C]. Oulu: Societas Historiae Fenno-Ugricae, 2002: 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