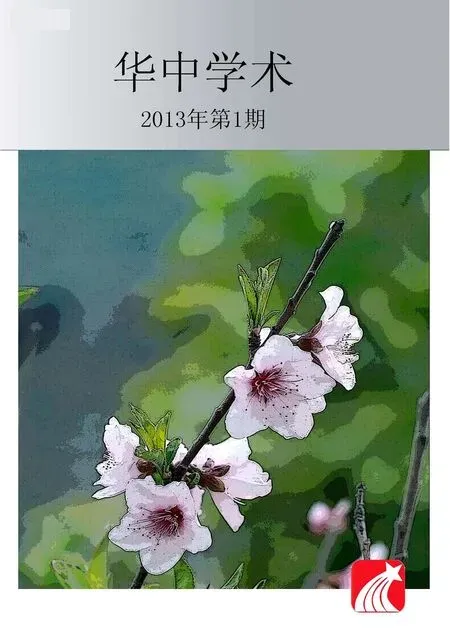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清代小说之比较
郑诗傧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关于《清史稿·艺文志》(简称《清史志》)的小说著录研究,目前学界尚未有相关论文发表,而以目录学的角度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简称《总目》)小说著录研究的文章,亦罕有涉及清代小说部分。本文就《清史志》与《总目》著录之清代小说作比勘,以了解乾隆以前清代小说著录之全貌。《清史志》共著录63部小说,其中成书于1778年(四库馆臣结束征书之年)以后的小说,共计23部;清人辑佚前人小说书目则有18部,将此两类不具可比性的排除在外,余下可考者22部。而《总目》共著录清代小说34部,除1部《山海经广注》在“正目”内,其余33部皆入《存目》。两相比勘,《清史志》之失录而《总目》存录的共计14部,《清史志》之著录而《总目》不录的有8部。《清史志》自谓“取则《明史》,断自清代,四部分类,多从《总目》,审例订讹,间有异撰。清儒著述,《总目》所载,捊采靡遗,《存目》稍芜,斠录从慎。乾隆以前,漏者补之;嘉庆以后,缺者续之。苟有纤疑,则从盖阙”[1]。既然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采录,则二者之间著录异同其背后的思想性,则有研究的必要。兹将二书著录情况列表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小说一览表

续表
一、《总目》著录之清代小说
根据《总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条说:“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2]又在《凡例》中指出“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寻常著述,未越群流”[3]的著作,一并列入存目,以备考核。如此,凡讹谬、俚浅、妄言、违经、平庸的著作,都被抑入存目,有的是“并斥而存目”,用以彰善瘅恶的。小说家向来被认为出自稗官,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其中被认为伪妄、平庸、俚浅等,自是不少,被归入《存目》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四库著录与存目所收数量差距之大,不得不作出如下之追问:清代小说真的都如此不堪,以至于仅有一部能被列入“正目”之内?为什么《总目》将余下33部(占清代小说著录总数的97.05%)全归入存目呢?归结原因有二:一是这33部小说抵触了官方编纂《总目》的主导思想;二是不符合纪昀等的小说观念。下面分别说明:
(一)有悖官方编纂《总目》之著录标准
1.限制规模与贵远贱近
杜泽逊先生在总结6791种图书之所以被列入《存目》的9条原因中,有“限制规模”、“贵远贱近”两条。据乾隆五十一年十六日刘墉奏折,谓乾隆四十三年至五十年春季,先后招募誊录人员,尚不包括省督抚学政下属采办人员,已达2712人[4]。可见,清政府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巨大。永瑢等《进〈四库全书〉表》有“汪洋无际,虑创始之为难”[5]之句。因此,《存目》中现在看来是宝贵的资料,如史部之杂史、传记、各省府州县志,子部之医家、杂家、小说家,集部之词曲、别集等,大部分被归入《存目》。且这些被摒弃在“正目”以外的图书,更多的是时代较近的著述。在《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中,就明确说明《总目》之著录标准是“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6]。的确,《总目》共计10251种图书,被收录的仅有3460种,其余的6791种都归入《存目》。而笔者统计《总目》中著录之清代著述,共有3493种,被收录在“正目”之内的只有766种,其余2727种全归入“存目”,足足占了78.07%。考察“正目”与“存目”图书,不难发现,“正目”中大部分是考据类、职官类或前冠有“钦定”、“御定”、“御纂”等字样的图书。从“限制规模”和“贵远贱近”来看,清代的著述必须从严删汰,“小说”的地位尽管在清代已有所提升,但在传统学术观念中,地位仍属低下,在选择标准上自然是严之又严了。
2.压制民族思想
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不仅是为了整理古代典籍,实际上更是为了全面检查传世的文献,借此全面泯灭民间所酝酿的反清复明思想。可以说,《四库全书》的存录与抽毁,都是依据乾隆皇帝的是非标准,除了把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列入违碍毁禁类外,其余的都区分为“正目”与“存目”两类。
康熙时的“通海案”和“明史案”,雍、乾两朝的“文字狱”,对汉族士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迫害。明清易代给社会造成了剧烈的震荡,生于明清之际的汉族士人,其生活及命运也备受挑战。异族统治带来的屈辱和压迫感,使清初的文字常笼罩在一片凄凉悲哀的氛围中[7]。对于明遗民,即“殆其生于明而拒仕于清”[8]者而言,他们的生活处境更是难堪。其挫折与失落感,比一般士人来得更强烈。仕与不仕,都是两难的境地。那些官仕前朝及清朝的,即便功勋卓著,忠于新主,亦被清廷列为贰臣;先仕清后悔恨失节而背清的,更是不折不扣的贰臣、反复者;至于那些未仕前朝,后来选择仕清的汉族士人,则被遗民群体所鄙弃,而清廷政府在有反复者事例的情况下,亦不可能对这批汉族士人的投诚全然放心,如此仕清者在生活中处处受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相反的,选择不仕的汉族士人,也摆脱不了清廷的屡屡召唤。顺治、康熙两朝,清廷屡颁征召“山林隐逸”令,又召“博学鸿儒”,此举除了是以富贵利达作为诱惑,借此分化遗民群体[9],也是从距离方面进一步缩小他们与朝廷的离心力,使之便于朝廷的管辖与监控,安皇帝之心。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当人们的自由受到了压制,取而代之的便是强制或迫害。”[10]倘若作家懂得在字里行间用隐晦的写作方式,那么他的著作不仅能够顺利出版、流传,且能使自己免于政治迫害。且只有少数细心的读者能从看似陈词滥调或显白的表述中推断出作者精心挑选的理据,即作者真实想表达的[11]。易代的创痛,使明遗民常处在压抑愤懑的情绪当中,他们选择发愤著书。因此,他们的作品常与传统的文学审美标准“温柔敦厚”相抵触。是否这33部清代小说都含有隐晦之意,难道都具有抗清思想吗?或许,我们可以避过这个问题,不做个别性的研究,而是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就算这些小说未必果真有反清、有不满清廷的隐晦之意,但作为深知上意的四库馆臣,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对整个清代,尤其是易代之际的著述,又尤其是小说创作的著录,抱着宁枉勿纵,慎之又慎的心态。
在这种心态下“审阅”图书,其心思必定更为敏感心细。施特劳斯对迫害下的写作与阅读交流进行过分析。他说:“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从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只要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真理就毫无例外地透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这种著述不是写给所有读者的,其针对范围仅限于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它具有私下交流的全部优点,同时免于私下交流最大的弊端:在私下交流中,惟有作者的书人才能读到它。它有具有公共交流的全部优点,同时免于公共交流最大的弊端:作者有可能被处以极刑。”[12]当然,也有人据此反驳说:“也许会有一些聪明人,一些细心的读者,他们并不值得信赖,一旦找出作者,就会向当局告发他。”[13]《存目》存录的小说作者如钮琇、王逋、王士祯、金维宁、吴肃公、王晫、余怀、陆圻、陈尚古、吴陈琬、傅燮詷、郑与侨、施闰章等,都是生于明清之际的汉族士人。他们的小说作品往往也被今人解读成具有反清意识,更别说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四库馆臣的总纂、编纂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既聪明,也够细心,但他们忠诚的对象不是作者,而是皇帝,一旦怀疑著述中有所“隐晦”,就必然归于《存目》,更别说那些显白而遭致禁毁的著作了。
限于篇幅,这里只以存目中的几部著作为例加以探讨。钮琇之《觚剩》,所记“仕宦名士,才子佳人之逸闻轶事,文艺科技及风土人情,间录遗诗佚文,兼及神怪诞说”[14],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十六亦评曰:“其文词皆哀艳奇恣,而记事多近游戏,故不免喜谈神怪,以征其诡幻,间有裨于考据者,亦百中之一二耳。”[15]此书曾因文多违悖,一度被列为禁书。钮琇后来为了躲避禁令,曾化名为《说铃》刊刻发行,但只是部分内容。实则是因为此书大量记载了“三藩之乱”、“康熙西征”、“庄氏明史案”等明清之际的历史事件,如正编卷七《粤孤》上“徙民条”记康熙十三年续迁五县沿海之民所造成的恶果,述当时清廷“先画一届而以绳直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迁者委居捐产,流离失所”[16]。吴肃公的《明语林》也被认为是“清初具有遗民倾向的志人小说之一,书中通过追念明代人物事迹,抑此扬彼,间接表达对清政府的消极态度”[17]。吴肃公乃明末诸生,入清后不事进取,曾云:“宋之天下亡于蒙古,而人心不与之俱亡。”[18]故其著述五种,全被《总目》退入存目。而郑与侨《客途偶记》所记述者,亦是明末所见所闻,多忠义节烈之事,其《义犬》、《义猫》、《义象》皆是虚构一些忠于主人,懂得知恩图报的动物寓言故事,向来被认为其借动物之忠诚以愧背主者,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及遗民意识[19]。
可见,易代之际的迫害严重,易代之际的写作艰难,易代之际的作品,在官方的控制下,能够著录于史志目录中,减少亡佚和失传的情况,更是举步维艰。纪昀作为总纂,对于著作之著录仍有其影响作用。
(二)不符合纪昀等人的小说观念
《总目》虽非个人之作,但后世研究者一般认为纪昀任总纂时,“每进一书,仿刘向、曾巩例,作提要,冠诸简首。又撰全书总目、存书存目,几至万余种,皆一手所定”[20]。另外,孙楷第先生也指出,纪昀常自称“余撰《四库提要》”云云,且仁宗亦谓“昀办理《四库全书》,始终其事,十有余年,甚为出力”,因此认为《四库提要》都是得到纪昀基本认可的,进而认为子部亦出纪昀手[21]。本文就《总目》的小说提要及《阅微草堂笔记》中关于小说观念的叙述进行研究,发现两者对于小说的观点是非常契合的,毫无矛盾。因此,可以说《总目》的小说观念,即是纪昀的小说观念。
首先,小说应具有“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的功能。《总目》子部小说家类提要论及小说有三派:一是叙述杂事;二是记录异闻;三是缀辑琐语。又说:“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固不必以冗杂废矣。”[22]纪昀在小说著作《阅微草堂笔记》中,亦多处表达了这一思想,如“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23],小说内容“大旨期不乖于风教”、不容“怀挟恩怨,颠倒是非”[24],以上诸条都说明了小说具有“劝惩”的功能,符合子部以“议”为宗,素有指导生活的责任。故凡是无益于世道人心,有惑人心之小说,皆被罢黜不载。《山海经广注》能够列入小说类“正目”内,正因其符合这项标准,《总目》将所有关于《山海经》的文献整理都一并同归小说类。到了《清史志》也一样,把《山海经笺疏》、《图赞》与《读山海经》等都一并列入小说类。
其次,小说虽非经史,但亦应重视体例。其门人盛时彦曰:“不明著书之理者,虽诂经评史,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先生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25]
其三,反对借小说相互标榜,相互攻击而有伤忠厚,描摹才子佳人而有失礼教。盛时彦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说:“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26]郑开禧之序则言:“今观公所著笔记,词意忠厚,体例严谨,而大旨悉归劝惩,殆所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与!虽小说,犹正史也。公自云:‘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纪》,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27]《总目》之所以拒收《聊斋志异》,也是因为其描写 “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28]。在纪昀的观念里,这都是“猥鄙荒诞,徒乱耳目”。
然而,若一部小说作品,虽猥杂、讹谬,却也不失教化,《总目》又是如何处置呢?综观其所著录,仍然是在“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的原则下操作。稍有不合纪昀小说观念的,即便符合小说的首要标准,即能“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亦退入《存目》中。其“小说家类存目提要”大抵包含三种:一是未加褒贬,只作简要的介绍,如《述异记》、《史异纂》、《豆区八友传》,此类大抵属平庸之作。二是有褒有贬,虽多处不符合纪昀小说观念,但仍具指导生活的意义,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如《玉堂荟记》、《蚓庵琐语》、《旷园杂志》、《簪云楼杂说》可“资考证”;《冥报录》、《雷谱》、《果报闻见录》能“寓劝诫”等。三是贬斥较多的。怀挟恩怨,言辞有伤忠厚,多鄙谑秽语,如《玉堂荟记》、《秋谷杂编》;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非,如《板桥杂记》;诬妄不实、俚浅讹谬,如《闻见集》、《明逸编》、《玉剑尊闻》;荒诞不经,如《信征录》;有失体例,如《庭闻州世说》、《明语林》、《砚北丛录》、《汉世说》、《有明异丛》等;标榜太甚,如王晫之《今世说》。
二、《清史志》之失录与《总目》之著录
《清史志》之失录与《总目》之著录,共计14部。目前,未有关于《清史志》的研究专著,论文方面则多是属于订误、辨证之类的内容。因此,本文尝试从可占有的文献进行比勘,作出合理的推论。
(一)采书限制
当然,《清史志》的失录,本来就是其书问世后被人所诟病的不足之处。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武作成及王绍曾之补志工作。《清史稿》纂修之时,处于动荡时局,众多图书遭商贾及列强买卖掠夺,经费也面临匮乏。因此,史馆一度陷入全局停顿,在采书方面也不太顺利。朱师辙曾忆述当时欲编《清史志》时,唯有京师大学堂及江浙图书馆将其所藏书目送清史馆,其余多未送,故在编修艺文志时未能利用到有利资源。相反,各种方略、内外大臣奏疏、天文地理诸志、各省方志、各种书簿、各种管制表方面,资料极为丰富。各省呈送省志、州县志等为数不少,京师图书馆所存乾隆前地志又多[29]。《清史稿》史部地理类一项著录便达816部。可见,著录的数量与著录的资料来源的多寡是成正比的。当然,由于材料的有限,因而无法断定《清史志》对于《总目》清代小说的失录,是不是全然与所占资源有限未能目验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必然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二)分类不一
小说徘徊在子、史之间,由来久矣。胡应麟作为小说理论家,就曾论及此:
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指郑樵)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30]
故个别史志目录中难免出现分类不一的情况。《总目》所录清代小说《鄢署杂抄》及《豆区八友传》,《清史志》将前者归入史部地理类杂志之属,后者归入子部谱录类食用之属。
对于《鄢署杂抄》,《四库提要》评曰:“国朝汪为熹撰,为熹字若木,桐乡人。康熙末官鄢陵知县,欲修县志而未果。因摭其地之遗闻琐事,缀为此书,自序称事涉鄢陵者十之六七,涉省郡别州县者十之三四,合以身之所历,目之所睹,得十四卷。大抵多采稗官说部一切神怪之言。盖本储地志之材,而翻阅既多,捃摭遂滥;又嗜奇爱博,不忍弃去,乃裒而成帙,别以‘杂钞’为名,是特说部之流。”[31]《总目》之所以将之归入小说,主要是一种退置的处理。汪为熹本来是欲修县志的,最后因为仅是摭拾当地的逸闻轶事,其中多有神怪之言。汪为熹自序亦云:“乍阅之似《鄢志》补注;细阅之,为祥为妖,可喜可愕。异时重修《鄢志》与省会郡邑志,不无数十条可备采择。”有鉴于此,四库馆臣认为其成书以前并未实践史学考证之精神,因“嗜奇爱博,不忍弃去”而导致“捃摭遂滥”,且又符合“资考证”之小说标准,因此退入小说家类。《清史志》归入史部地理类,则该是视其书名、体例,及其所记地理内容。本文从作者自序出发,认为《总目》之定位,更为恰当。
至于《豆区八友传》,本文则认为《清史志》之分类更正确。《总目》提要解释:“以制造菽乳,其名有八,因呼八友。各为寓名而传之,盖游戏之小品。”[32]形式上,虽然属于俳谐类,但书中所记实关乎豆腐的制作,因此归在谱录类食用之属,显然更为适宜。另外,虽然《清史志》未著录陈忱《读史随笔》,但即便著录,将之列入小说类的可能性极小,当在史部类。综观《清史志》中类似主题的著录,如《读史笔记》、《读史劄记》,都被列入史部史评类;《读〈战国策〉随笔》列入史部杂史类;《读诗随记》、《读诗或问》列入经部诗类;《读书笔记》、《读书随笔》、《读书杂记》则归入子部杂家类。显而易见,其著录标准取舍在于作者著述之内容,非以书写形式或类型而言。可以说,依据《清史志》编纂者的著录标准,这类的读书笔记都不隶属于小说家门下。《总目》则不同,类似著述唯有陈忱《读史随笔》被列入小说类杂事之属,其余如《读史管见》、《读史辨惑》列入史评类,《读书偶记》列入儒家类,《读书乐趣》列入杂家类等,看起来未有清晰且统一的标准,惟有兼及提要及文本的阅读研究,才能定论、判断《总目》关于此类著述的著录标准及其分类问题。
三、《清史志》之著录与《总目》之不录
《清史志》之著录而《总目》未著录的共计8部,即顾炎武《谲觚》、褚人获《坚瓠集》、张潮《虞初新志》、冒襄《影梅庵忆语》、李渔《古笑史》、汪琬《说铃》、史震林《西清散记》及汪绂《山海经存》。后2部小说,虽脱稿于乾隆征书以前,然由于前者刊刻在后,后者书板遭火毁,1778年作者去世前,亦是征书之年结束时才重新修订,故不予比较。
顾炎武之《谲觚》,《清史志》入小说家类,考《总目》之著录,原是将其归入史部地理类存目。《谲觚》乃顾炎武素日读经史所作的笔记,遂成卷帙。书中详考十事,如“淄川非薛”一事、辩“淮河”一事、考“泰山无字碑”一事等,皆有补于史部地理志。未知《清史志》及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入小说家类所持之理由。
至于其他,《总目》之未录,大抵原因有二:一是不录传奇小说;二是其书作者或书中所记人物为清廷禁忌。鲁迅曾指出自纪昀重新整理小说之分类时,不著录传奇[33]。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传奇小说被认为用以抒愤之作,致“以卑乱尊”且“败坏纲常”;又多描摹刻画男女之艳情、邪淫之事,被视为足以使人“心迷意乱”、“乱人情操”的淫书[34]。所以,纪昀认为“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35]。王利器所著《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从清人文集中所摘条目如“禁用传奇小说入文”、“传奇小说为孽”、“一切传奇小说不许私借”、“传奇小说最易惑人”[36]等都说明了清廷及士大夫对传奇小说的鄙视与偏见,也说明了《总目》不录传奇小说之根由。然而,传奇小说在清末至民国年间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张振国计算晚清以后各个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的数量,即道光后期11部,咸丰时期13部,同治时期19部,光绪前中期46部,清末民初41部[37]。晚清时期,新的革命运动兴起,西方文明入侵,为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带来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和传奇小说作家空前之多,作家身份遍及上下阶层文人以及编辑、记者、改良家、文学革命家等,许多小说家都是兼写传奇小说的[38]。传奇小说,不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明清之际的敏感之作,《四库》都是不如正录的。杜泽逊先生指出,《四库提要》中最受痛恨的两个人是王洙和李贽,李贽的罪过在“排挤孔子,别立褒贬”,指李贽是名教之罪人,故其著作全都入《存目》,焦竑因推崇李贽,大部分著作也仅得屈居《存目》[39]。《熙朝名臣实录》提要便云:“所附李贽评语,尤多妄诞,不足据为定论也。”[40]这些都是证明。而民国时期这些都不再是禁忌之列,《清史志》著录它们不足为奇。以下试做分析。
张潮之《虞初新志》是一部文言小说选集,书中所收包括传奇小说。《虞初新志》被收录在《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书目内[41]。观其封页上,盖有一个刻上“谨遵饬禁书目将钱谦益文三篇抽板送浙江书局销毁讫特白”之刻印。而书中所收作者如吴伟业、周亮工,与钱谦益一样,在乾隆皇帝敕命编纂的《清史列传·贰臣传》中皆榜上有名。且又收入李渔之作品。李渔著述之丰,《总目》却无一著录,倒是其《四六初徵》及《尺牍初徵》被列在四库禁毁书中[42],更遑论李渔之《古笑史》了。在“限制规模”与“贵远贱近”的前提下,四库馆臣自然更不会将这类滑稽小说存录在案。且当时以维持封建伦理道德自居的士大夫及清廷对李渔更是恨之入骨,这是因为李渔的白话小说与戏曲创作及小说戏曲理论著作都具有重大的影响[43]。且看董含《三冈识略》卷四“李笠翁”条:
李生渔者,自号笠翁,居西子湖。性龌龊,善逢迎,遨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及小说,备极淫亵。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中所不齿者。予曾一遇,后遂避之。夫古人绮语犹以为戒,今观《笠翁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当堕拔舌地狱无疑也。[44]
汪琬之《说铃》,作为《世说》的仿作,相对其他的仿作如《玉剑尊闻》、《今世说》、《汉世说》及《明语林》尚能被存其目,很可能因为汪琬作品中论及周亮工,或者在“限制规模”的前提下,《总目》作出选择性的删汰,将较为平庸之作罢黜。按今日之研究文言小说的史料看来,亦罕有论及《说铃》一书。
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亦是一本传奇小说,且冒襄作为明遗民,屡获清廷举荐,皆以“亲老”、“足疾”为由而坚拒不仕[45]。此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末清初社会动乱图景,揭发了明末社会上层的腐败、明末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更大胆地控诉了清朝统治集团进入江南之初下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执行命令时对汉族同胞展开的血腥暴行。且冒襄也如实记录了他的夫人董小宛如何恨透了满清贵族,并时时提醒夫君无论如何不应诏、不做官[46]。冒襄此书,字里行间毫无隐晦,自然是连《存目》亦不得而入。
褚人获之《坚瓠集》则主要记述明及清初见闻。来新夏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认为“是书虽辑前代掌故逸闻较多,然所涉及清初时事,多为亲历目睹,颇足征信”[47]。又说:“若有人进而排比全书目录,汇成一编,则旧闻掌故,更便一索而得。”[48]即符合“寓劝诫,资考证,广见闻”之标准,何以《总目》不录?可能之原因有二:一是述及时事,揭露黑暗政治,向往清平世界的内容[49];二是书中如《妇散重婚》、《姑嫂成婚别》等条中,揭露青年男女未能追求爱情自由,往往受制于社会动乱、封建纲常伦理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展现出民主精神的萌芽。纪昀认为小说有“议”,即指导生活的责任,并且反对描摹才子佳人的故事,况且《总目》著录标准之一就是不刊刻那些有违封建伦理道德的图书[50]。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特别重视君臣父子,封建礼教,那些歌颂爱情自由,对无奈遵循父母之命的情侣表示同情的故事,即是“离经叛道”之作,自然只能退入存目或不录。
《清史志》之小说著录还有重复著录的问题,如王士祯《陇蜀余闻》,既著录在史部地理类杂志之属,又著录在子部小说家类;施闰章《矩斋杂记》则同时著录在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及子部小说家类。类似失误,《清史志》亦见于其他部类。
四、结 论
本文对《总目》与《清史志》著录之清代小说进行比较,共发现了三个问题,并解决这三个问题:一是本文发现《总目》只将一部《山海经广注》列入“正目”,其余33部皆入“存目”。这与《总目》编纂的主导思想有关,在限制规模、贵远贱近及压制民族思想等主要因素的情况下进行选录,学术地位相对来说较为卑微的小说,又属于易代创作之际的近代小说,自然不可能位处“正目”。另外,由于清代小说的著述内容及创作体例、思想等,与纪昀等人的小说观念多有抵触与悖逆,因此被退入“存目”。二是《清史志》失录而《总目》著录的,共计14部。《清史志》著录的缺漏与其编纂背景有莫大关系,在动荡不安、经费不足、列强掠夺书籍等情况下,史馆面临采书的困难。后来的补志工作,如《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产生,便是例证。此外,小说观念的不同而导致分类不一,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三是《清史志》著录而《总目》之不录的共有8部。除了分类不一的因素导致差异,也因为《总目》不录传奇,并将含有离经叛道思想的小说或是记载了贰臣、悖逆之人等人物的小说一概摒除在外。而《清史志》编纂时,传奇小说的创作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被普遍认可,更没有明清易代之际的敏感问题存在,故著录情况有所不同。
注释:
[1]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页。
[3](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页。
[4]《档案》,第1928—1929页,转引自杜泽逊撰:《四库存目标注·序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页。
[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页。
[6](清)于敏中:《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第·十八函》(影印本),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
[7]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35页。
[8]谢正光:《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叙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9]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33页。
[10][美]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11][美]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12][美]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思政导师。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澄清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学生,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答疑解惑,消除思想政治疑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积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特点、方法的研究与探索,努力提高育人工作水平。
[13][美]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14]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1页。
[15](清)周中孚撰:《郑堂读书记》,《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16](清)钮琇:《觚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1页。
[17]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
[18](清)吴肃公撰,陆林校点:《明语林》,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251页。
[19]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5页。
[20]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2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页。
[2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
[2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9页。
[25](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2页。
[26](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67页。
[27](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58页。
[28](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2页。
[29]详见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30](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3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2页。
[3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5页。
[3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4]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6页。
[35](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68页。
[36]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7]张振国:《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绪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38]薛洪勣:《传奇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6—367页。
[39]杜泽逊撰:《四库存目标注·序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40](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59页。
[41]王钟翰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03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13—684页。
[42]王钟翰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34、15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17、499页。
[43]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9页。
[44](清)董含撰,致之校点:《三冈识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45]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410页。
[46]萧相恺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89—599页。
[47]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0页。
[48]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2页。
[49]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2页。
[50]杜泽逊撰:《四库存目标注·序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 华中学术的其它文章
- 上海中华书局法人治理结构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