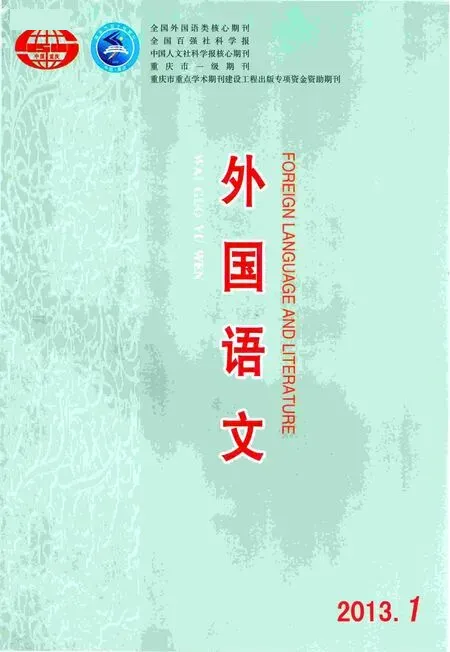布莱克早期诗歌中女性性意识的对立性
张 瑾 王 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是英国文学史上极具个性和独创性的一位诗人。对立性(contrariety)是布莱克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对立性观念超越传统的善与恶、肉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体现了对立力量间的积极的、动态的相互作用。M.H.艾布拉姆斯指出,“布莱克作品中所有的对立物都表现为男性和女性力量之间的相互对立与相互补充。这两种力量在强烈的爱—恨关系中成为所有形式的进步、组织、创造力或生殖力的必要组成部分。”(Abrams,1971:260)布莱克的诗作中女性形象丰富,从《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中细心的护士和慈爱的母亲到《塞尔书》(The Book of Thel)中的处女塞尔(Thel),从《阿尔比恩女儿们的梦幻》(Visions of the Daughters of Albion)中具有叛逆精神的奥松(Oothoon)到后期诗作中有邪恶的女性控制意志的女性,形象各异。布莱克早期诗歌①本文将布莱克的早期诗歌界定为从1783年发表的《诗的素描》(Poetical Sketches)起到1795年完成的“朗伯斯”系列寓言诗止。参见胡孝申,邓中杰.威廉·布莱克创作阶段划分刍议[J].外国文学研究,1998(1):103-107.中对女性性意识的处理上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他展现出来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的诗作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为他赢得女权主义预言者的声誉;另一方面,他笔下的女性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屈从于性压迫,一些评论家宣称他也是企图囚禁女性的父权制力量中的一份子。②关于布莱克妇女观的研究,参见D.Aers.William Blake and the Dialectics of Sex[J].ELH,1977(3):500 - 514;Rachel V.Billigheimer.“Conflict and Conquest:Creation,Emanation and the Female in William Blake’s Mythology[J].Modern Language Studies,2000(1):93-120;刘朝晖.“影”之谜:对布莱克的女性主义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0(1):81-86.而事实上,布莱克所关注的是女性性意识中存在的两种对立力量的冲突:解放与顺从,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抗争状态,而非相互否定。
一
性批评贯穿布莱克作品的始终,他认为性是“最直接、无所不含的一个问题”(Damon,1988:367),因为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以及宗教话语在这一领域均发挥强大的作用。性是他表达自己对人类社会、人类思想认识的一种途径,他对性意识的探索表现出他对社会强制规定的价值观念与人的欲望的对立以及人心中存在的对立力量的关注。布莱克相信性激情是最强烈的人类情感,性爱不仅意味着感官享受,还传递精神意义。布兰达·韦伯斯特(Brenda S.Webster,1987:205)认为:“被解放了的性意识对布莱克来说看似高尚价值的源泉——他将其与幻想和艺术连在一起。”布莱克颂扬人的性意识,认为它与想像力息息相关:“性爱……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们中的大多数可以进入想像的世界,对许多人来说,它是瞥见那个世界的惟一途径。”(Frye,2004:78)性欲望是神圣的,也是自由的。他甚至认为“随着感官享乐的改善”(《天国与地狱的婚姻》:194)①文中布莱克作品的译文凡只标出诗名和页码的均出自张炽恒译作《布莱克诗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其他译文为作者所译,标示英文作品集中的出处。诗歌均选自Alicia Ostriker(ed.).William Blake:The Complete Poem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81);其它作品均选自David V.Erdman(ed.).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M].New York:Doubleday,1988.,性爱是人接近永恒的途径。在一首手稿诗中,他写道:“谁在欢乐飞翔时吻它,/谁就将生活于永恒的黎明。”(《永恒》:116)人应该享受性爱的欢乐,如果他束缚自己,压抑性爱,他将毁掉“有翼的生命”(《永恒》:116),失掉通向永恒的机会。布莱克赞美人的性意识,尤其关注女性性意识,他认为性爱是男性和女性双方的需求:
男人在女人身上所需要的
是欲望得到满足的表达
女人在男人身上所需要的
是欲望得到满足的表达 (Ostriker,1981:158)
男女两性都迫切需要对方的身体,因此女性有权追求性爱。
布莱克笔下的女性努力将自身从性压抑中解放出来。《阿尔比恩女儿们的梦幻》一诗中纯真的女主人公奥松爱上塞欧托曼(Theotormon),但却在与所爱之人相见的路上被布罗明(Bromion)强奸了。布罗明抛弃了她,认为她是妓女;而塞欧托曼全然不顾奥松的祈求,认定她放荡、通奸。布莱克在这首诗中毫不隐讳地探讨了两性关系和女性性意识,“在父权社会的主导话语以更有力的方式压制女性性欲的声音的历史时刻,试图为女性性欲的自由表达寻找一片空间”(Bruder,1997:57),表达出女性解放性意识的必要性。
《阿尔比恩女儿们的梦幻》中,女性性意识的解放首先体现于追求性行为中女性的主体地位和积极作用。18世纪末,男性霸权主义几乎渗透在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两性关系与性爱也毫无例外地受其影响。女性要端庄、正派、有节制,否则便会被冠以放荡之名而遭到鄙视。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不可能要求被看作是性主体而非性客体”(Ankarsj,2004:61),她们只能是男性性欲望的对象,被动地等待男性的屈尊求爱。然而,奥松抛弃了扭曲女性情感的道德标准,在追求性爱中采取主动。她天真地相信每个人都有自由享受爱,所以公开宣布她的爱:“我爱塞欧托曼,/心中一片坦然。”(p.212)她采撷“柳萨的花朵”(Leutha’s flower)(p.212),从藏身的溪谷起身远行,“奔向整个灵魂想往的地方”(p.213)。奥松的行为体现了她性意识的萌发,因为在布莱克的诗歌中,柳萨象征着性(Damon,1988:238),采摘金玛丽花(Marygold)是“一种古老的性体验的象征”(Damon,1988:265)。摘下金玛丽花,奥松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性欲望,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出发去寻找塞欧托曼,表达她的渴求。传统求爱的模式在这里被颠覆了:尽管奥松最终陷入父权制的陷阱,她却成为有意识主动追求性爱的一方,而塞欧托曼则成为满足她性追求的对象。这显然是女性解放性意识的第一步。
奥松被强奸之后,布罗明与塞欧托曼对此的反应非常典型:前者要求女性“崇拜恐怖并且顺从暴力”(213),他代表了性暴力,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压迫;后者追求女性的贞洁,他认为奥松遭到玷污,不再纯洁,这代表了男性对女性思想的压迫。他们对奥松的态度体现了父权社会制定的女性标准和道德规范,这首诗成为“一曲爱的占有欲和道德立法者的虚伪性的哀歌”(Erdman,1954:211)。奥松在社会制度中找到了性压迫的根源,她直接控诉尤理生②尤理生(Urizen)在布莱克的宗教神话体系中代表理性,为能量(Energy)的限制者,律法的制定者。参见S.Foster Damon.A Blake Dictionary:The Ideas and Symbols of William Blake[M].(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8:419-426.,告诉他“你错了,天上的守护神”(p.217)。她挑战男性权威,质疑它对女性的公正性:
他用什么作罗网、圈套和陷阱?他怎样用抽象之冷水
围着自己,怎样用孤寂之林,为自己建造国王和神父
享用的城堡和高耸的塔尖;最后用律法的符咒
将燃烧着青春之火而不懂得既定命运的她,绑在
她所憎恶的人身上?难道她必须在令人厌倦的肉欲中
拖着生命的锁链?难道令人心寒的凶杀之念,定要
遮蔽她那永恒之春的明净天空……(p.218)
这是对社会剥削以及性别剥削的严厉控诉。男性权威,尤理生—上帝、国王和神父编织了“罗网”、“圈套”和“陷阱”来束缚女性的命运。婚姻似乎已经成了一张网,一种奴役的制度,它剥夺了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自由追求性爱的权利。奥松谴责无爱的婚姻,那只是法律名义下的灵车。她抗议男性勾结起来以贞操的道德律法控制、压迫女性,使其成为受害者、牺牲品。正统道德规范要求女性要羞怯,保持贞洁,这只是男性囚禁女性的一种阴谋。而在奥松看来,女性学会的只是一种“狡猾的羞怯(subtil modesty)”(219),因为她知道即使是那些已经接受了正统思想的女性依然渴望性爱:
你以羞怯的处女之名闻名于世来掩饰自己,
用你在夜之枕下找到的网来获取处女的欢乐,
并在上面打上“妓女”的烙印,在夜间把它
悄悄出卖,一声不出,仿佛在睡梦中一样。(p.219)
男性宣扬羞怯是虚伪的,而对女性来说遵从男性的说教违反了她们的意愿。奥松宣称她想成为妓女,只是因为她想自由地表达性爱,她认为“生命的一切纯洁的欢乐/都是妓女”(p.219-220)。对布莱克而言,妓女代表着得到满足的性欲望:“在妻子身上我会渴望/经常在妓女身上发现的/得到满足欲望的面貌”(Ostriker,1981:153)。妓女常被冠以放荡的恶名,然而她们和那些被虚伪的羞怯和贞洁所束缚的女性一样,同为男性统治的牺牲品。奥松抨击父权制所宣扬的压抑人性的羞怯,狂热地追求解放性意识。她崇尚个人喜悦的神圣性:“每一种欢乐都是一种爱”(p.218),尽管在性关系中处处受限,她仍然期待解放自己的性欲:
奥松是个充满了处女的幻想
向着美常在之处的欢乐开放的处女。
我多想在旭日中找到那处所,我在欢乐的交媾中
曾向那儿凝望;我多想在劳作之余,
在温暖的夜色中坐在岸边,汲取这生来自由的欢悦。(p.220)
很明显,奥松向往与所爱之人幸福地交融,只有在这自由的时刻,她所有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达到圆满。
二
奥松敢于同男性束缚抗争,体现出布莱克时代女性身上罕见的勇气、正义和力量。尽管塞欧托曼对她冷漠,她仍然向往“爱!幸福的爱!自由如同大风!”(220)。然而,这只是奥松乐观、理想化的幻想,因为这样的性解放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训诫。布莱克在对拉瓦特(Lavater)的《人的箴言》(Aphorisms on Man)①Reverend Johann Kaspar Lavatar(1741-1801)是瑞士哲学家和神学家,以观相术的著作而著称。他的作品《人的箴言》于1788年由布莱克的朋友亨利·福斯利(Henry Fuseli)翻译成英语。的注释中提到:
伟大的女人不专横,美丽的女人不虚荣,资质平平的女人不嫉妒,有成就的女人不夸耀——这是四个奇迹,伟大至极,足以分别占据地球的四个部分。
让男人履行他们的职责,女人就会成为这样的奇迹,女性的生命依赖于男性的光亮而存活,看一个男人的女性依附者,你了解这个男人。(Erdman,1988:596)
男性是“自我”,而女性则是“他者”,女人应该做的是依附于男性,甚至女性的性也只是男性的补充而已。强大的父权制力量规约了女性的身份和形象,不允许女性表达爱,女性满足性欲望的意愿总是被阻挠。女性要求性解放的欲望被置于与顺从力量的不断抗争中,两者构成了典型的布莱克式的对立性。
《塞尔书》写于1789年,展现了女性性意识中的对立力量。处女塞尔离开了她居住的哈尔溪谷(the vales of Har),“她神情黯淡地寻找那片神秘的天去了”(p.202)。塞尔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为“我要”或“我希望”,还意指“女性、女人们”(Swearingen,1989-1990:127)。既然欲望被定义为塞尔的特性,那么她的旅程和追寻可以被看作是从“原始的纯真之地”(Damon,1988:174)哈尔溪谷向成人性意识的未知世界的迈进。从这个意义上看,《塞尔书》讲述了女性的性历程。作为女性欲望的化身,塞尔探索感官体验,探寻性意识的表达。她同一朵百合、一片云、一只蚯蚓交谈,最后她在土块主妇的邀请下进到她的房屋:“别害怕,抬起你的处女秀足进去吧”(p.207)。土块的房子代表着有性行为的成人的世界,因为她已经被“结婚礼带”(p.206)绑住,成为孩子的母亲。然而,当塞尔进入这个她向往的世界后,只是发现了一幅凄凉的画面:
她看到了死者的卧榻,看到了每颗心的坚韧的根,
都把它不知足的卷须深深地嵌入土中:
那是个永远看不见微笑的、悲伤与眼泪的国度。(207)
性的世界充满了痛苦与死亡,这是一个由男性意志统治的世界,试图扼杀女性的性意识。很明显,进入性爱世界只能给塞尔带来死亡。在这个世界,塞尔看到了自己的墓地,听到哀鸣的声音:“为何一个脆弱的羁绊阻碍了热血少年?/为何一幅小小的肉的幕帘罩在我们的欲望之床前?”(208)。她的性意识已经觉醒,但不得不相信感官享受的毁灭性。在与正统思想的对抗中,塞尔被潜在的威胁吓倒了,她的性意识受挫,逃回到处女的溪谷。尽管心存渴望,她的寻求性意识表达之旅以失败而告终。
女性不仅屈从于外部力量,还内化男性要求她们顺从的力量。苏珊·福克斯(Susan Fox)(1977:513)认为:“布莱克在《阿尔比恩女儿们的梦幻》一诗中将主要人物设定为女性,不仅仅因为他崇拜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至少在潜能上和男性是平等的,也不仅仅因为他痛恨对女性的压迫,还因为他需要一个人物,她可以被强奸、被束缚、被压迫而没有任何援助,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唯一的救助是具备一种革命性的男性力量,以此来结束受虐境遇。”布莱克鄙视对女性的压迫,但是他的确看到了女性的无助和潜在的受压制并屈从于男性统治的倾向。曾经狂热地宣扬性解放的奥松没有达到彻底的女性性意识的解放,她所有的努力均无果而终。她依然不够强大,无法逃脱社会制度制定者的法网,这是一首“以描写最终被囚禁的爱而告终的自由之爱的宣言”(Cox,1992:127)。因此,奥松只能每天清晨在柳萨溪谷哭泣,叹息是阿尔比恩的女儿们能够听到的唯一的声音,也是她们能够回应的唯一的声音,溪谷弥漫着凄凉的气息。
某种程度上讲,奥松最终屈从于布罗明和塞欧托曼的父权压迫。奥松卑微地乞求塞欧托曼的爱:“她扭动着雪白柔软的身子,/呼唤塞欧托曼的鹰来啄食她肉体”,“鹰听从了她的呼唤,飞下来撕食血淋淋的食物”(p.214)。这一幕寓意深刻。奥松在塞欧托曼的鹰啄食了她的肉体后,“展露笑颜”(p.214)。鹰捕食象征着男性的性进攻,奥松呼唤鹰明显传递了她的受虐倾向。她落入了性压迫者的圈套,期待成为塞欧托曼性行为的被动客体。很明显,解放与顺从两种力量在奥松的内心交替出现,更为严重的是,她似乎已将男性的价值标准和准则内化为己有,按照男性制定的女性标准塑造自己的形象。奥松追求的自由之爱使她落入男性界定的欲望陷阱,即以男性为中心的自由之爱。她不再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是耗费精力为塞欧托曼编织捕获处女的网:
奥松我将布下丝织的罗网和刚玉的捕机,
为你捕捉柔亮如银或刚烈似金的姑娘;
我将在河岸上躺在你身旁,看她们这些荡妇
和你塞欧托曼一同游戏在爱的交媾中,狂喜无度。
奥松我将红艳如玫瑰色的黎明,贪欲似第一缕出生的光芒,
看着你的热切的欢乐,既不带着嫉妒的阴云
进入生育之爱的天空,也不会因自私而从事破坏。(221)
奥松接受了她曾经反抗的传统性观念,试图成为塞欧托曼控制其他女性的同谋。奥松的幻象体现了她的“施虐受虐狂和窥淫癖”(Damrosch,1980:198),她是这一幕的设计者,她观看塞欧托曼与其他女子放荡的嬉戏,以此获得乐趣。她带着一副宽容和满足的神情,好像她自己是性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就是说,即使是看上去最具革命性的女性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观念,倾向于服从男性,而这与她对自由之爱的向往是相背离的。奥松的幻象透射出她自己对性爱的渴望,然而,她却从对自由性爱的积极追求中退却了,自由结果只是男性的自由,她甚至与男性合谋诱使其他女性屈从于男性的性要求。“压迫不仅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内心”(Ostriker,1991:92)。也许无意识中,奥松将父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判断性解放的标准,她设计让塞欧托曼与其他女性交媾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强加给女性的只是充当男性性满足工具的角色”(Ackland,1982-1983:173)。顺从的力量扭曲了奥松的女性性意识,她自我克制,放弃了自己的性快乐。她从一个寻求性解放的女斗士变成了男性性压迫的同谋,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从这一角度看,《阿尔比恩女儿们的梦幻》成为精神战争的战场,性意识中的解放与压制两种精神力量相互对抗。
三
布莱克笔下极端的女性性顺从和性解放都蕴含着潜在的危机。极度的顺从使女性丧失了主体性,沦为“他者”,女性欲望“由于受到抑制,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动的东西,最终成为欲望的影子”(《天国与地狱的婚姻》:187),这对女性来说是毁灭性的结局。女性被剥夺了追求性爱的自由,顺从使她们成为性客体,男性欲望的对象。女性甚至被剥夺了享受性爱的权利,被迫放弃男女之爱,于是在《阿尔比恩女儿们的梦幻》中,她们所向往的“欲望的时刻”(p.220)就变成了自体性欲(autoeroticism)的一刻:
为了男子
而憔悴的处女,将在卧室的隐秘暗影中把子宫
唤醒,来享受巨大的快乐;禁戒肉欲之乐的青年
将把生殖后代置诸脑后,在窗帘的暗影中、
在静静的眠枕的褶痕里,臆造色情的影像。(p.220)
这是一种黑暗的、隐秘的爱,性意识被压抑、扭曲。当然,在布莱克看来,性压迫的牺牲品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但他更强调受压制的女性性意识。自体性行为①参见Eijun Senaha对《病玫瑰》一诗中自体性行为的研究:Sex,Drugs,and Madness in Poetry from William Blake to Christina Rossetti:Women’s Pain,Women’s Pleasure[M].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Mellen University Press,1996:11-28.尽管可以让女性得到片刻的欢愉,但它却意味着自我否定。看似自我享受的一刻实则更深刻地揭示出女性内心的痛苦,正是对正常性行为的否定而非性行为本身给女性带来了痛苦和毁灭。女性身体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她们被迫屈从,从而采取这种自我毁灭式的行为。艾琳·泰勒(Irene Taylor)认为:“父权制文化鼓励的女性性顺从导致残忍的冲突,毁掉了女性一切幸福的机会。”(Billigheimer,2000:109)
布莱克倡导女性性解放,但他也意识到了女性性意识中强大的女性力量的威胁。他在《月亮上的岛屿》中写道:“女性被称作是最软弱的化身,但我认为她们是最强大的”(Erdman,1988:457)。奥松追求自由之爱,但“每一次示爱都是力量的宣言,没有所谓的自私或自我牺牲,有的只是挖空心思的支配”(Paglia,1992:273-274)。女性性意识的过度解放会使其同样成为一种控制力量,唯一的区别在于女性的控制取代了男性的支配。《水晶柜》一诗体现了布莱克对女性控制欲的关注。一个年轻男子在田野里幸福地跳舞,但他被一个少女捉住了:“她把我放进她的水晶柜中/用一把金钥匙将我锁住”(p.88)。锁与钥匙的意象暗示了性行为,少女是主动的一方,而年轻男子是被捕获的对象。男子在柜子中产生了幻象,他看到从柜子的三面出现了三个少女的映像,若隐若现。男子的欲望被激发,他像火焰一样燃烧起来。他试图抓住少女,满足他对性爱的渴求,“可是那水晶柜烧了起来/变得像一个哭泣的婴孩”(p.89)。他的渴求被遏制,他的反抗被压制。这里,奥松的遭遇被完全逆转,女性的支配力量占了上风,结果它和男性的控制与支配一样具有破坏性。男子从一个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孤独无助、痛哭的婴孩。当女性的性意识解放走向极端,企图占据和男人一样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时,解放力量沦为一种压迫力量,解放本身也变得邪恶了。
在《欧罗巴:一个预言》一诗中,女性的控制欲望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展现了女性意志(Female Will)的野心。布莱克在这首诗中描写了一场持续了1800年之久的女性之梦,从耶稣的降生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艾尼萨蒙(Enitharmon)是天国的女王,她命令她的儿子向人类宣布下面的信息:
去!告诉人类女性的爱是罪恶!
永恒的生命等待着六十冬的幼虫
在一个从未有生命停留的寓言的住所:
禁止所有欢乐,从童年时代起,小女孩应该
在每一条秘密的道路上撒网。(Ostriker,1981:229)
通过宣称“女性的爱是罪恶”,艾尼萨蒙表达出父权社会对女性性意识的规定:从童年时起,女性应学会克制对感官享受的欲望,女性的自我克制将会使她获得“永恒的生命”。然而,艾尼萨蒙关于女性要克制、要顺从的宣言却隐含着要求解放的欲望,她在思考“女性,可爱的女性!可以有控制权么?”(Ostriker,1981:229)。这里,她使用了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说的狡猾的女性力量,这种力量通过“狡诈和置换的策略表现出来”(Williams,1998:78),即顺从是控制欲的伪装。“网”的意象在《阿尔比恩女儿们的梦幻》中代表对女性性意识的束缚,而这里它则暗示了伪装起来的女性对男性的挑战。这首诗的主题之一是“女性意志通过性是罪恶这一虚假信条战胜男性”(Damon,1988:132),女性意志是颇具毁灭性的女性支配欲望,艾尼萨蒙企图为男性编织一张网,控制男性,甚至毁灭男性。如果没有屈从力量与之抗衡,女性性意识的解放就会走向极端,构建起女性的性霸权。因此,女性性意识的解放和顺从两种力量应互相牵制,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而非互相否定。
布莱克在早期诗歌中对女性性意识的态度看似一种悖论,既有女权主义倾向,倡导女性性意识的解放,又有厌女情结,暗示女性性顺从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是布莱克有意为之。他的诗中女性性意识处于解放与顺从两种力量的对抗之中,这种矛盾性正是他诗歌的活力所在,因为他相信进步衍生于对立双方的斗争。同时,女性性解放与顺从这两个对立面应处于平等位置,否则一方战胜另一方,势必落入专制状态,对立性将被破坏。如吉恩·海格斯特鲁(Jean H.Hagstrum)所言,“理想的世界因物质的收缩和延展、对立力量之间的相互牵制而活力四射”(Hagstrum,1985:145)。布莱克对女性性意识的处理体现了他的对立性思想。
[1]Abrams,M.H.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71.
[2]Ackland,Michael.The Embattled Sexes:Blake’s Debt to Wollstonecraft in The Four Zoas[J].Blake:An Illustrated Quarterly 63,1982-1983,16(3):172-183.
[3]Ankarsj,Magnus.Bring Me My Arrows of Desire:Gender Utopia in Blake’s The Four Zoas[M].Gteborg,Sweden: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2004.
[4]Billigheimer,Rachel V.Conflict and Conquest:Creation,Emanation and the Female in William Blake’s Mythology[J].Modern Language Studies,2000,30(1):93 -120.
[5]Bruder,Helen.William Blake and the Daughters of Albion[M].Basingstoke and London:MacMillan,1997.
[6]Cox,Stephen.Love and Logic:The Evolution of Blake’s Thought[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
[7] Damon,S.Foster.A Blake Dictionary:The Ideas and Symbols of William Blake[M].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8.
[8] Damrosch,Leopold,Jr.Symbol and Truth in Blake’s Myth[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9]Erdman,David V.Blake:Prophet against Empire,A Poe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His Own Time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10]Erdman,David V.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C].New York:Doubleday,1988.
[11]Fox,Susan.The Female as Metaphor in William Blake’s Poetry[J].Critical Inquiry,1977,3(3):507-519.
[12] Frye,Northrop.Northrop Frye’s Fearful Symmetry:A Study of William Blake[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
[13]Hagstrum,Jean H.The Romantic Body:Love and Sexuality in Keats,Wordsworth,and Blake[M].Knoxville: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5.
[14]Ostriker,Alicia.Desired Gratified and Ungratified:William Blake and Sexuality[C]//Hazard Adams.Critical Essays on William Blake.Boston:G.K.Hall & Co.,1991:90-110.
[15] Ostriker,Alicia.William Blake:The Complete Poems[C].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81.
[16] Paglia,Camille.Sexual Personae: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M].London:Penguin,1992.
[17]Swearingen,James E.Will and Desire in Blake’s Thel[J].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1989 -1990,23(2):123-139.
[18]Webster,Brenda S.Blake,Women and Sexuality[C]//Dan Miller,Marker Bracher & Donald Ault.Critical Path:Blake and the Argument of Method.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
[19]Williams,Nicholas M.Ideology and Utopia in the Poetry of William Blak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0]张炽恒,译.布莱克诗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文中所标页码均出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