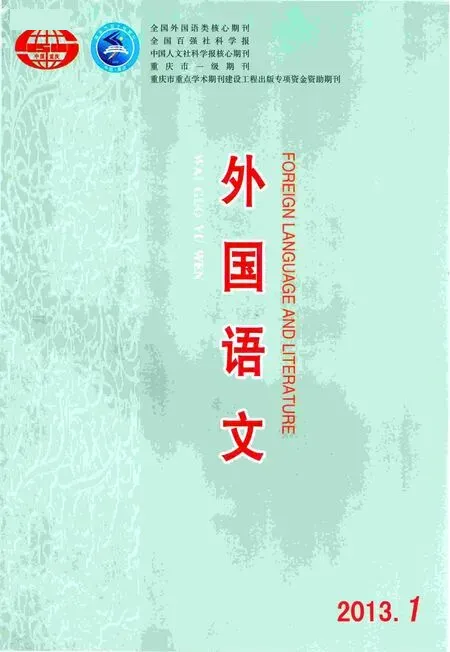浅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中世纪德意志民族工作观的影响
张 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
一、引言
马丁·路德作为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对德意志民族,包括其信仰、语言及其民族性格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当人们研究相关领域时完全不能排除马丁·路德的影响。人们研究德国人的工作观及其自中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他的神学观是不容忽视的。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中就曾探讨马丁·路德对新教徒“内在性”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韦伯尝试将新教伦理和一种作者命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联系了起来,并且最终作了结论。与之类似,人们自然也会猜想马丁·路德的新教神学教导与同“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德意志民族的工作观有某种联系。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原因也是因为马丁·路德神学思想的复杂性。马丁·路德既提出了一些新的神学观念同时也重新强调了一些已有的被忽视的神学教导。因此要细致地分析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对德意志民族的工作观的影响并非易事。本文要尝试分析的正是这一问题。
德意志民族较为成熟的工作观在中世纪已经形成,特别表现在中世纪城市里的行会文化中。因此对工作观的分析要从行会开始,这样才能清楚解释马丁·路德的每条神学思想对当时德意志民族的世界观,特别是本文所探讨的工作观或者说工作道德(Arbeitsethik)的影响。本文所强调的工作观更多的是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职业道德。
二、中世纪的工作观
“中世纪”(Mittelalte,Middle Ages)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界定。比如,与“中世纪”相对应的“新时代”(Neuzeit,modern age)描述的是“从1500年左右(1492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或者马丁1517年95条论纲的发表)到现在,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2]。中世纪的划分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等等。对于与宗教改革相关的研究我们最好把“新时代”的区间定于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发表95条论纲的1517年到现在,这样划分能够更好反映当时德国社会的现实。习惯上人们把中世纪划分为早期(5-10世纪)、中期(11-13世纪)、晚期(13-16世纪初)。考虑到德国行会的历史,我把本文所提到的中世纪限定在11世纪(中世纪中期)到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的1517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行会”的概念。在德语中行会有Amt、Einung、Gaffel、Gilde 等不同的称呼,但描述的都是中世纪产生的商人、手工业者的联盟。要研究德意志民族的工作观或者职业道德,行会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行会是由手工业者、商人和其他群体组成的一个组织联盟。建立行会的目的在于保护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并调整成员的经济关系。行会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行会的雏形,但是在德国直到11、12世纪成熟的行会形式才逐渐出现。基于这个原因,研究“工作道德”概念,研究的时间区间应限定在中世纪中期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此外还要强调的是工作观或者工作道德(Arbeitsethic)的概念。工作的价值在中世纪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为了保障自己已获得并处于上升时期的市民地位,市民阶层不仅开始创办一些社会组织,同时他们也需求获得心理层面的保障。基于这一原因,工作对于市民阶层来讲是一种首要的心里需求。工作的日常节奏、纪律、价值和工作中对自我责任和合作的理解适应于对领导的要求,即提供工作的雇主对其员工的领导要求。这一秩序要求维持了下来,并通过人最终在工作中培养的个人身份和性格。
另一方面,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在六日内创造了这个世界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可以说上帝本身也工作并将管理维护地球的工作托付给人类。然而,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作是上帝的委托,工作也同时被看作是劳苦重担,甚至是始祖亚当犯罪带来的罪的刑罚。例如创世纪3章17节至19节中上帝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3]3
当然,在行会出现前更早的古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就已经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算作“工人”,因此毫无疑问那时也存在一种封建形态下甚至原始形态的农民的工作道德。但在行会中形成的工作道德却是一种全新事物。原因在于行会作为城市商人、手工业者的联合组织,其从事商贸活动的成员除了进行买卖交易之外还要应对复杂城市生活的各样挑战,因此就需要有一种公共道德,其中一种不同以往的工作道德对于行会的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从中世纪起行会文化逐渐兴起与发达,同时也就伴随产生新的公共道德,包括工作道德。然而在中世纪,人们对工作的评价要比现代人低得多,当时的人们仅仅把工作当作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并且将其与劳苦受罚联系在一起。直到进入宗教改革后的“新时代”,对普通人而言工作才借着“新教伦理”被赋予更大的意义。
三、基督教与行会文化对中世纪工作观的影响
在古希腊古罗马自由常常意味着“不必工作的自由”。当时的“工作”的概念仅仅包含体力劳动的范畴,而精神劳动则被视为社会的特权。当时的体力劳动大多由奴隶承担,手工业劳动由社会的中间阶层承担,而富人、哲学家和政治家则享受悠闲且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体力劳动。到了中世纪,借着基督教的影响人们对工作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基督教教义对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对特定劳动形式的贬低提出了质疑,因为按照基督教教义上帝把工作托付给了每个人,因此工作是人的本分。圣经执笔者常常把上帝比作“牧羊人”、“窑匠”一类的工人,受此影响,中世纪人们虽然仍常常轻视工作的意义,但已不再把工作,特别是体力劳动看作是负面、否定的价值了:
列国阿,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3]772(耶利米书31:10)
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3]728(以赛亚书64:8)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理论上讲受基督教影响的欧洲中世纪对工作的看法是相对客观的。但是在事实上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工作常常被视为一种刑罚。尽管如此,基督教对于改善人们对工作的看法发挥了极正面的作用。这也为后来的基督教改革家通过宗教改革赋予工作更大的价值提供了机会。
城市行会对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精神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行会的意义也体现在对日耳曼民族行为方式及其“内在性”的巨大影响。历史学家埃里希·卡勒尔指出,行会文化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上对社会精神的首次表达,特别是城市行会对纪律和工作道德的强调,从此便衍生出了新的公共道德。在行会中,任何社会成员无论其背景、社会地位、信仰或族群都必须遵守一种共同的公共道德,这种公共道德与贵族文化有极大的区别。在农村贵族作为统治者享有许多特权,许多法律条文专门针对奴隶实施,而贵族则不必遵守。工作、勤勉、细致、纪律、效率等等都仅是奴隶的事。但在城市行会中则是另一种情形:人们无论什么出身信仰都遵守共同的市民道德,并将行会成员为群体作出的贡献作为评判一个人价值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城市行会公共道德成为了社会中间阶层的道德,并成为了市民道德体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四、马丁·路德的新学说及其影响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批判天主教会的95条论纲,自此宗教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马丁·路德对德国历史的重大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改变了德国的历史进程,引发了德国乃至欧洲的基督教大分裂),亦体现在他对圣经新约的翻译促进了德语语言的统一,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此外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对德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心态发挥了直接影响并参与塑造了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德国人对工作的态度、顺从性以及德国人的“内在性”很大程度上与马丁·路德有关。马丁·路德甚至被视为“新时代”最典型的德国人,因为他既是他所在的社会的反映,同时他又对后世影响巨大。诗人海涅写道,“路德不仅仅是我们历史中最伟大的人,也是最典型的德国人。在他身上德国人所有的美德和缺点绝佳地结合在了一起。他能够代表这个不可思议的德国。”路德的新学说集在神与人的关系神学探讨,其影响改变了德国和教会的面貌,也改变了欧洲甚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如上文所述,受基督教影响的中世纪工作观可以用“委托”和“刑罚”来概括,而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受基督教影响的的工作观的消极一面渐渐淡化。工作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使命(Berufung),一种职业(Beruf,或译为“志业”)或者上帝的托付而不再视为一种惩罚。有趣的是,德语中职业(Beruf)这个词与其它语言相比有着更深的意义。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Beruf“这个词具有双义性,即经济和宗教双重含义。“Beruf”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一种是上帝所赋予的角色。因此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勤奋负责的工作履行职责也是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正是由于德国人这种工作观具有宗教内涵,使其在与其它文化中的工作观相比时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1.马克斯·韦伯对马丁·路德天职观的分析
我们知道,基督教新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第一章韦伯观察到了在他的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拥有者、雇主、受过较高教育的熟练工人和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级培训的技术或者经营人员,少有例外地,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1]17通过详细的分析他得出结论“工作精神”和“进步精神”的苏醒要归功于新教,而旧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必须在新教的宗教发展中去寻找。在书中韦伯详细探究了路德的天职观,回到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他认为德语中的“职业”(Beruf)一词与英文的“calling”类似有宗教的含义,即上帝交给的任务。“Beruf”这个概念“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诸民族中,还是在古典时代的民族中,指谓‘天职’(在明确划定的终身坚守的工作领域这一意义上)这一意思的表述都不为人知”[1]47。然而这却存在与所有新教主导的民族中。韦伯认为德语中“Beruf”这个词的深层意义并不是圣经原文中就有的,而是通过马丁·路德的翻译所赋予的。新的词义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履行义务成为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于是职业概念的重要性增强了,并且履行世俗义务成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不再是中世纪时期僧侣的禁欲和苦修。在路德看来修道院内的静修不但缺乏“因信称义”(sola fide)的价值,反而是放弃现世义务的自私的利己主义,相反参与世俗劳动则是“同胞爱”的外在表现。与此同时,路德强调个人应当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因此路德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旨意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路德的教导也具有消极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路德教导的核心和他生活的重心都是使人灵魂得救,可以说宗教改革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和本文探讨的工作观的影响是应该是路德所始料未及的。
2.唯独信仰(Sola fide)
拉丁语“sola fide”意思是“唯独通过信仰”或者“因信称义”。借着这个论断宗教改革表达了跟经院哲学的恩典主张不同的观点,即罪人唯独通过对圣经的信仰(sola scriptura),唯独通过神的恩典(sola gratia),唯独通过基督对人类的救赎(solus Christus),而非通过自己的善行获得称义。“sola fide”指的是人对上帝恩典的完全的信赖,指出了人不是通过好行为赚取上帝的接纳,而是唯独通过信仰。这个教义的基础来源于圣经新约的保罗书信,即罗马书3:21-28,特别是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而在路德翻译的圣经中是“人称义是唯独因着信”,“唯独”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是没有的,更多是路德按着自己的解读添加的,因为路德认为人永远不能借着自己的好行为获得神的恩典。韦伯认为,通过对“因信称义”的不断强调,路德彻底否定了修道院生活组织以及修道士生活方式在上帝眼中的价值,同时赋予工作越来越大的意义,使世俗的工作成为了一种弟兄之爱的外在表达。天主教会教导上帝的恩典是通过“获得恩典的手段”得到的,例如圣餐、赎罪券和善行等等,而路德则完全否定除信仰以外的任何其它手段,反对教皇和神职人员管理和分配“获得恩典的手段”的权力。当时的天主教会认为信仰的来源是圣经和传统,但路德却坚持认为教皇和宗教会议也会犯错,信仰的唯一来源当是圣经。路德宣告了一种通向上帝的个人化的道路,即信徒不需要以天主教会为中介,上帝的恩典唯独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耶稣基督的救赎获得,而一个人了解多少圣经知识或者是否频繁参与教会事务就不再重要了。一个人即使从事低微的工作过着世俗的生活,他仍能获得上帝的恩典和眷顾,世俗的工作不再是没有价值的了。
3.马丁·路德与“两个王国“(Zwei-Reiche-Lehre)
根据马丁·路德“两个王国”的教义,一个人既属于上帝的王国又属于“世界的王国”。两个王国在上帝的权下被设立。“两个王国”是路德神学观对上帝统治世界方式的解释,它也构成路德宗神学的政治伦理基础。在路德看来,上帝统治世界采用了两个不同的方式:在属灵的王国通过属灵的方式(福音、经文、圣餐等),这其中仅存在一种“个体—上帝”的个人化关系,即隐形的教会;在包含整个具体的宇宙整体及其秩序的属世的世界则是通过属世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世界的法律与秩序)。他认为所有世界的秩序(家庭、等级、职业)都是上帝所设立的,因此也是不容随意更改和神圣的。也就是说,上帝的王国建基在对上帝的爱和弟兄之爱,而世界的王国则基于法律和秩序。路德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同时属于两个王国,被置于双重要求之下:作为属世的人服从法律和权威,作为基督徒则放弃自我。
在上帝的王国中信仰是个人的事,而在世界的王国里人必须服从世俗的当权者、国王和诸侯的统治,这也被认为是人的义务。世俗的政权由上帝设定,因此人不能破坏这一秩序。同样地,所有世俗的职业、工作、技能都能够被看作是上帝交给的任务来侍奉上帝。卡尔·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写道,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隶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从马克思对路德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看出路德对当时人们的人生态度的影响:出色完成工作任务是上帝所要求的,并且这也是与灵魂救赎相联系的服侍上帝的一种方式,因此努力热忱地工作对一个敬虔的新教徒来说也是理所当然了。
4.基督的身体(Leib Christi)
基督的身体(Leib Christi)这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意思:(1)在新约圣经中指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人中复活的身体,是基督徒救赎的方法和中心;(2)在新约主的晚餐中所用的饼被成为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教会赋予主的晚餐神圣意义的原因;(3)在天主教神学中指教会(Corpus Christi mysticum,基督奥体),而个体基督徒被认为是基督的肢体。第一个意义中讲的是历史中耶稣基督的身体,即(corpus Christi historicum),或者说拿撒勒耶稣的身体。第二个意义中饼和酒分别代表基督的身体和血。第三个意义讲的是教会,圣徒组成的会众或者作为个体单元的基督徒,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意义上的“基督的身体”的教义并不是天主教独有的,这一教义出自圣经被多数教会所接纳: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3](哥林多前书12:27)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3](以弗所书1:22,23)
“基督的身体”的三个意义都来源于圣经,都在圣经中清楚地出现过。但与马丁·路德神学思想更为相关的是第三个意义,也即“基督奥体”。“基督奥体”的神学思想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形成,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基督奥体”的教义并不新鲜,但却被天主教忽略。根据“基督奥体”的教义,所有受洗的基督徒都是“基督奥秘的身体”这一群体的一员,成员无论社会地位、世俗或宗派背景,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人必须维护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每一部分的健康,以此来保证整个身体的健康和教会的正常运转。借此马丁·路德提出,在“基督奥体”中每一个普通人的作用并不亚于一位牧师。任何工作都是重要的,因为每项工作都承担维护“基督奥体”健康的责任。就这样马丁·路德建立了工作和特定天职的一种联系,工作也不再仅仅被当作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了一项维护“基督奥体”健康的任务。人们必须顺服上帝的秩序并辛勤工作,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并获得灵魂的救赎。在路德影响下,当时深受路德影响的日耳曼民族在一定意义上就获得了殷勤严谨工作的动力。
五、马丁·路德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影响
当我们探讨马丁·路德对中世纪日耳曼人的工作观的影响时,我们会问“整个日耳曼民族都受到了马丁·路德新的神学思想的影响吗?”我们知道,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多年后,当时日耳曼民族居住的地区并非所有人都是新教徒,人口中很大比例仍是天主教徒,而宗教改革对他们信仰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此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这不仅在当时的德国,也在后来的美洲新大陆显示出来。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清教徒的“新教伦理”与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在近现代历史中现代企业制度与经济产业机制的产生都是与“新教伦理”密切相关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从基督教世界引入了这样的制度和机制,包括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韩国尽管近代以来出现了很大比例的基督徒人口,但并非传统意义的基督教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无一例外的对自身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西方化。概括地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工作观的影响第一阶段体现在对新教徒的工作观的影响,在随后的阶段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的运行中,即“新教伦理”影响下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与扩张中。马丁·路德的时代属于第一阶段,19世纪随着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整个过程中,打上新教烙印的工作道德始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
六、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德意志民族的工作观受到基督教极大的影响,其根基在行会发展的中世纪几百年里已经形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通过他的新的神学主张进一步影响和改变了德国人的工作观。尽管马丁·路德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士和神学家,他的宗教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革罗马天主教和人灵魂的拯救,但他引发宗教改革的神学主张不仅改变了教会,改变了德国人的信仰和精神世界,同时他也启动了一项社会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德国人的“内在性”和这里所分析的对工作的观念态度。在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工作观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勤奋、热忱、秩序、严谨等道德得到更大的强调。与此同时德国人的“安于现状”、对政治的冷淡和对权威的顺从也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切使得德国人能够凭借其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创造经济奇迹,但缺少了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则在历史上带给德意志民族极大的教训。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Neues Grosses Volkes Lexikon[Z].München:Taschenbuch Verlag,1979:403.
[3]圣经[Z].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