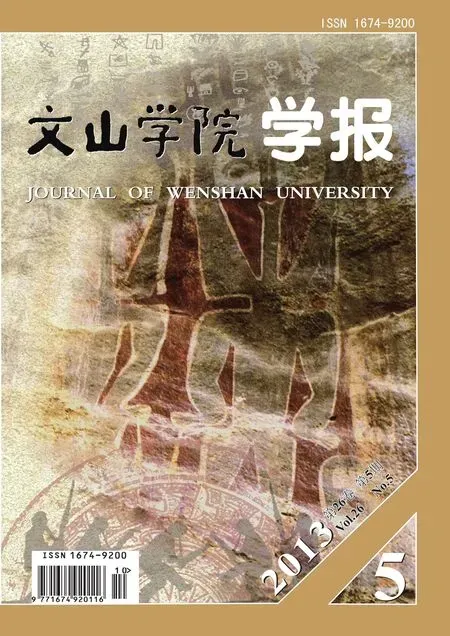论现代“童养媳”题材小说的文化意蕴
方华蓉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论现代“童养媳”题材小说的文化意蕴
方华蓉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在现代思想启蒙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中涉及童养媳题材的创作比较丰富,作家们从解剖这一大众习以为常的民俗入手,展开了对封建专制文化与国民劣根性的猛烈抨击,对挣扎在封建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群体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反省。
童养媳;国民劣根性;异化
20世纪初期,面对一蹶不振、内忧外患的民族形势,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精英掀起了一场旨在追求现代化,以期富国强民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将批判的笔锋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对准了阻碍民族前进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一些有着悠久历史,早已被纳入传统文化坚固堡垒中的民间陋习自然而然地进入许多现代作家的表现视野之中。诸如质子、典妻、冥婚、水葬等传统习俗,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千年,已经演变成一种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极具象征意义的全民盛典,沉积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模式。因此,发掘这些传统习俗的文化蕴涵,对反省历史传统中那些愚昧、落后、病态的文化因子,从而开启民智,解放国民精神,建立名副其实的现代民族国家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对“童养媳”生存状态的展示
童养媳是一种古老的婚姻模式,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它是指女孩在幼年时期即到夫家生活,等到适龄后再正式婚娶的婚姻形式。不同于质子、典妻这样一些确实有违传统礼教,当事人多少需要承担道德压力的乡野恶俗,童养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底层家庭经济困难,使得一些家庭不得不早一点将女儿嫁出以暂缓家庭危机,另一些家庭则好早点娶媳妇增加劳动力,将来也能传宗接代。这种表面上双赢的婚姻模式只是比正常的婚娶时间提前了,仪式简化了,既不违背礼教,又满足了许多群众的现实需求,因此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一代一代流传,以致习以为常。所以,童养媳不仅成为一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习俗,同时也成为一些封建官方政府实质认可的婚姻制度。正因为如此,童养媳的存在也一直被认为是自然而然,合乎礼法的。相反,这种婚姻制度的残酷性、愚昧性却被轻易地遮蔽,对这种婚姻制度中的悲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扭曲与病态反而为大众所遗忘。不仅如此,它在源远流长的传承中,已经成为一种深刻影响大众的传统文化模式。民众这种见怪不怪、麻木不仁的生命存在,正是现代思想启蒙者所深恶痛绝的民族病痛,它严重阻碍了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必须革除的国民劣根性。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启蒙的目的,现代文学中涉及到童养媳的作家作品,基本上都没有重在从阶级的、政治的视角展开社会批判,而是站在思想启蒙的立场,从文化解剖的角度,努力揭示这一传统习俗所隐含的大众灵魂与社会心理,从而展开对封建文化与国民劣根性的猛烈批判。
来自东北边陲的女作家萧红在她最为动情的回忆性小说《呼兰河传》中塑造了一个年仅12岁的童养媳小团圆媳妇的形象。她本来是一个健康、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可是一旦做了童养媳,就必须遵循所谓的封建妇道。她的一些本来属于小女孩的天性——诸如吃饭多、走路快、爱说爱笑等特点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严加管制,本着“为她好”的目的,家人与大众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折磨她,用以矫正一个小女孩的行为,力图把她改造成为一个循规蹈矩、刻板呆愚的小媳妇,以致这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在轮番的折磨下悲惨死去。
“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了,洗两次又该怎样呢?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热闹的人心里,都满怀奥秘。”
这是一种何等荒诞不堪的全民盛宴,以所谓的封建妇道去规范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继之以各种残忍病态的方式折磨她,然后心安理得地观赏这孩子的苦难,眼睁睁地看着她悲惨死去。这是怎样病入骨髓的大众灵魂和精神病苦,难怪鲁迅先生面对如此麻木不仁、扭曲病态的民众群体时,万分悲愤地疾呼——“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为了塑造一个所谓本分刻板、谨小慎微,一切符合传统妇道的童养媳,在大众与家人的合力改造下,这仅有12岁的孩子无辜死亡了。她的死是对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妇道、迷信、盲从扭曲的文化陋习最为猛烈的抨击。
来自南国多民族聚居地——湖南湘西的作家沈从文在他的短篇小说《萧萧》中也倾力塑造过童养媳萧萧的形象。萧萧父母全无,寄养在伯父家,12岁做了一个年仅3岁小男孩的媳妇。“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刀,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身体的发育与性的懵懂最终使萧萧与同龄的男性相好怀孕。她之所以没有被按照湘西习俗沉潭,全因伯父一时起了怜悯之心。最终她也逃脱了被发卖的厄运而被婆家收留,全在于她凑巧生了一个男孩,私生子意外拯救了母亲的性命。萧萧的生死悬于一线,何其可悲可叹。沈从文以平淡柔和的笔调,书写了一个令人心颤的童养媳故事,一种悲凉到极致的人生。封建专制时代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愚昧野蛮的民间陋习,人们精神世界的病态扭曲真正让人痛心疾首。
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孔厥的《受苦人》是一篇描写童养媳具有创新意义的小说,它不重在揭示童养媳所遭受的灵肉磨难,也不突出大众的精神病苦,而是从“性”的角度,痛陈了童养媳与身体残疾、年龄差距过大的丈夫结婚后令人颤栗的精神恐惧。“可想不到昨儿黑夜鸡叫三更他却又来缠我!我梦里惊跳起来,只听见他说‘能!能!’我一时吓怕了!他还说一句明明白白的话,天哪!怎么好呢?我一时实在吓慌了,我自己也不晓得怎的,我本来要说的话不由的一下子都脱出口了。”童养媳面对残疾的大龄丈夫那种左右为难、极度恐惧的人生困境,真正把这种古老的婚姻模式吃人的本质推向极致。从这一角度反省童养媳制度其实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童养媳与婚配对象的年龄差距太大,很多时候男方身体不好或者残疾,童养媳又缺乏婚姻自主权,由此所带来的精神与心理的折磨是可以想象的。千百年来,在这样的婚姻模式下,多少童养媳在无尽的凄楚中熬过了一生,何其惨烈而悲凉的生命悲剧。
童养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千年的流传中,它早已演变成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这一陋习的揭示与批判,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反省。童养媳制度下最为悲惨的无疑是那一代代命运凄惨的小女孩们,她们以弱小之躯承受了无数的非人折磨,她们的无尽苦难正是对这种文化陋习的强烈控诉。同情童养媳,表达对封建专制制度下女性命运的深深忧虑是现代作家们特别关注童养媳题材的原因,但是,揭示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依托与社会心理,发掘普遍的大众灵魂,从而开展必要的思想启蒙才是作家们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涉及到童养媳的现代文学作品,大多都会超逸出对童养媳个人苦难的控诉来展开社会阶级的批判,且较多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关注产生童养媳这种婚姻制度的文化渊源与现实中大众的精神面貌。“四个女儿是‘扁货’,前世讨债来的,就挂篮的挂篮,出卖的出卖,如今都变成人家的丫头或童养媳,拖着根黄毛辫子,在人家的打骂之下半冻半饿地过日子。儿子却是全部希望的化身,虽然家境贫穷,依旧把他看作宝物。”[1](P265)在父母的集体意识中,女儿是负担、累赘,家庭日子过不下去,把女儿当商品出卖,保全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家庭贫困是主因,但确实是父母亲手出卖了女儿,千百年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无疑更加强化了一代代小女孩亘古不变的生命悲剧。
那些以婆婆为首的肆意打骂、无情折磨童养媳的家族长者和乡里乡亲,她们也大多来自底层,生活艰难,克勤克俭,在封建男权专制下,她们遵循妇道,谨小慎微,完完全全是一群典型的贤妻良母。这些女人们大多确实是本着“为她好”的目的去改造一个孩子,正如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一再感叹的那样——“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规矩出一个好人来”,也就是培养出一个合乎封建妇道的传统小女人,她们因此而心安理得地虐待童养媳,制约她们的行为,也确实是因为千年的积习如此,千年里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模式与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定命使然。正如作家沈从文所感叹的那样——“大家全莫名其妙,只是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这样的艺术处理显然淡化了童养媳题材的社会政治批判意义,而有意强化了对这一习俗的文化解剖深度。越是这样的艺术安排,越是显示出这一陋习的大众性、民间性,就越是揭示了封建专制文化的流毒之深、之广、之顽固,也越是显示了思想启蒙的迫切性与艰巨性。
二、对“童养媳”心理状态的深度解剖
童养媳是女孩,又是儿童,在一个崇尚男权与“长者本位”的传统社会里,这一群体无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既承受着亘古不变的“性别罹难”,又遭受着长者对幼小者的权利欺压,她们的苦难无以复加。凝视着一代一代小女孩的千年悲剧,真是一种让人莫名伤痛的心灵磨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里,因为浸润着无数女童的血泪,埋葬着她们弱小的身躯而显得格外沉痛。童养媳的悲剧,是封建男权专制下女性的悲剧,一个一个的小女孩,无名无姓,卑微不堪,不仅沦为男权的牺牲品,也沦为所有长者的附属物,任意驱使,随意凌辱,承受了各种各样惨痛的非人折磨,如作家曹石清所言——“这是必然的,无论哪一个女孩子,一到别人家做小媳妇,在我们中国的贵国里面,是不免要吃一世苦的。”在这种境遇中苦苦挣扎的童养媳,只有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远离现代文明的启迪,缺乏主动思考的能力。长此以往,她们形成了一种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奴性与惰性,对自身命运始终处于一种不自知的蒙昧状态之中,代代相传,更是加深了这一女性群体的悲剧结局。
沈从文的小说《萧萧》是一部读来让人深深震颤的作品,他用平静柔和的笔调把童养媳原始蒙昧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病痛与苦难在他的表现中却产生了一种痛彻心扉的艺术效果,正如他的自述——“一种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12岁的萧萧做了一个3岁小男孩的童养媳,懵懵懂懂之中与同龄男子相好怀孕,她之所以没有被沉潭或者发卖,只是因为生了一个儿子,如此命悬一线而惊心动魄的人生悲剧却丝毫也没有震醒萧萧,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象。
这一天,萧萧刚做月子不久,孩子才满三月,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道理我要生气的……”
这是萧萧抱着她与小丈夫的儿子看自己的私生子娶大龄童养媳的情景,真是让人悲从中来,面对自己曾经的悲剧即将重演,当事人萧萧一无所知,竟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欣赏同类也是自己的苦难,她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一种彻底的原始蒙昧之中,这是怎样一种麻木不仁的苦难人生,真正让人感叹万分又黯然神伤。
冰心的小说《最后的安息》中的童养媳翠儿,在婆婆万般的折磨与虐待下,14岁死在了黑漆漆的小房间里。初次的安息,也是她最后的安息,短暂的一生在无尽的苦难、黑暗与蒙昧中熬过去了。“可怜翠儿生在世上十四年了,从来没有人用着怜悯的心肠,温柔的语言,来对待她。她脑中所充满的只有悲苦恐怖,躯壳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冻饿。她也不明白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快乐,只昏昏沉沉地过那凄苦黑暗的日子。要是偶然有人同她说了一句稍为和善的话,她都觉得很特别,却也不觉得喜欢,似乎不信世上有这样的好人。”她们,活得浑浑噩噩,死得悄无声息,这是一群不幸而可悲、可叹的女孩子。她们的这种生命存在,正是千百年来底层女性凝滞苦难却不自知的生命形式的缩影,一种女性群体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生命轮回。她们的悲剧人生,既是对千年的封建男权吃人本质的强烈控诉,也凝聚着作家对女性自身的深刻反省,他们在感叹底层女子逆来顺受、忍辱负重、驯顺善良的同时,又为她们精神世界的麻木、愚昧而深深忧虑。
童养媳的悲剧是封建男权专制下女性的双重悲剧,被折磨着的童养媳饱受身体与心灵的非人戕害,疯狂折磨她们的以婆婆为首的女人们同时也承受着灵魂变异与精神扭曲的恶果。在现代童养媳题材的创作中,作家们塑造了一群可憎可恨、扭曲病态的女人。她们是童养媳的女性长者,大多是婆婆,还有一些是女性群众,她们都是封建时代标准的贤妻良母,非常忠实地秉承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与制约,疯狂地折磨童养媳,力图将她们改造成符合封建妇道的小媳妇。男权社会为制约女性而制定的一整套礼仪与规范却借女性之手,再施加给她们中的弱者,最终却是为了维护大男子主义的中心地位和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习俗。
“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回去我还得打她。”
“我是你婆婆,我就是要打你,要管你。”
这是一个女人对自己同类的手段。居高临下,肆意凌辱,心安理得地充当了男权文化的刽子手,以“为她好”的目的疯狂地扼杀一个孩子。“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2](P345)其实女性最大的悲剧还不在于她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被形成与被消费的命运,而在于女性自身以男权文化的标准对同类的制约与戕害,自觉地扮演男权力量的同谋,扼杀同类弱者。在对童养媳的折磨中,婆婆无疑是胜利者,却又是彻底的失败者,她们秉承封建父权制的性别歧视,对童养媳进行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扼杀,自身心灵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化,她们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病态残忍,跟她们疯狂折磨着的童养媳一样,她们也处于一种精神世界更深的蒙昧之中。
在童养媳题材中,许多作家还塑造了一群麻木不仁、可憎可恨的女人,她们是童养媳的乡邻,是任劳任怨、谨小慎微、恪守本分的劳动妇女。在改造童养媳的过程中,她们充当帮凶与看客的角色。
“那才不怕羞呢!头一天来婆家,吃饭就吃三碗。”
“别说还是一个团圆媳妇,就说一进门就姓了人家的姓,也得头两天看看人家的脸色。”
“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在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
“看热闹的人,你望望他,他望望你。虽然不知道下文如何,这小团圆媳妇到底是死是活。但却没有白看一场热闹,到底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总算是不无所得的。”
这是一群女人怂恿婆婆殴打小团圆媳妇,并兴高采烈地观赏一个孩子苦难的过程,她们参与了对童养媳的扼杀。以封建男权的标准摧残自己的同类,这是何等愚昧而又病入膏肓的女性群体,在她们争先恐后地观赏童养媳的苦难中,又显示了人性的残忍与冷酷。“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2](P345)这类生活在封建父权制中的女人,无疑是男权统治下的弱者,却恪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自觉地以此为标准规范同类中的弱者,俨然异化成了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她们的变异、扭曲与病态,深刻地揭示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伤害与毒化,这是一种更令人痛心疾首的女性悲剧。
三、对民俗中国民固有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
童养媳,作为一种有着深刻社会与历史文化根源的古老婚姻模式,随着封建男权专制主义的瓦解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然而,童养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早已演变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观念和认知模式,这种制度的消失并不表示依附它而存在的思想观念的彻底改观,因此,对这种传统习俗所隐含的文化心理与民众精神状态的反省,应该是任重道远的。
[1]王西彦.王西彦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Modern “Little Daughter-in-Law” Novels
FANG Hua-rong
(College of Arts,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432000,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culture of the thinking enlightment, there were aboundant creations on“little daughter-in-law”. Through revealing the folk custom that people had get used to struggling under the feudal patriarchal culture, the writer attacks the feudal culture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expressing deep sympathy and re fl ection to Chinese female group.
Little daughter-in-law;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lienation
I207.42
:A
:1674-9200(2013)05-0047-04
(责任编辑 田景春)
2013-06-20
方华蓉(1975-),女,湖北汉川人,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从民间歌谣看中国历史上的童养媳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