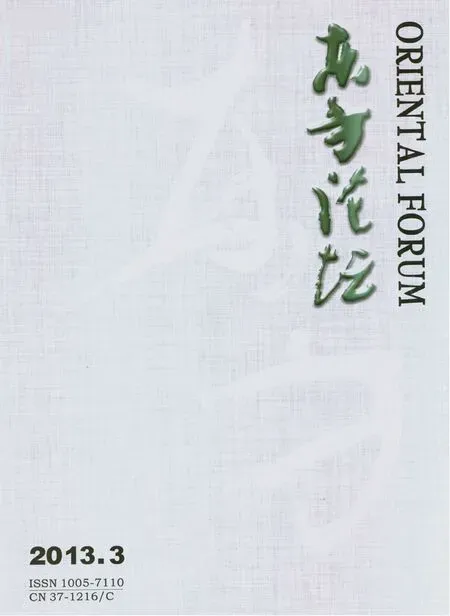《玉台新咏》所录《行路难》考述
——兼论《行路难》的流传演变情况
邓富华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玉台新咏》所录《行路难》考述
——兼论《行路难》的流传演变情况
邓富华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玉台新咏》收录南朝时文人拟《行路难》诗共九首,在题材上均与女性有关,主要反映了女性的生活遭遇和情感,在形式上以七言为主。作为最初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行路难》在产生之初顾名思义是感叹道路难行之意,并非挽歌,在经过袁山松的改造之后才作为挽歌在南朝广泛流传。鲍照是《行路难》发展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拟《行路难》组诗中既保留有挽歌的影子,又对《行路难》在题材与风格上进行了拓展,率先将女性题材融入《行路难》之中,用绮靡的笔调与华丽的词采来抒写女性的悲哀;此外,鲍照《行路难》中那些“发唱惊挺”的篇章则被唐代李白、骆宾王与王昌龄等人所继承。
《玉台新咏》;《行路难》;南朝;乐府;流传
《行路难》为乐府古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收有《行路难》歌辞五十九首,另有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二首及王昌龄《变行路难》一首。《行路难》古辞今不存,南朝宋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乐府诗集》与宋本《鲍明远集》题为十九首)是现存最早的作品。南朝时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录《行路难》共九首。本文主要分析《玉台新咏》所收《行路难》诗歌的特点以及《行路难》的产生流传演变情况。
一、《玉台新咏》收录《行路难》情况
《玉台新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据徐陵《玉台新咏集序》所云“选录艳歌,凡为十卷。”[1] (卷首)明胡应麟说:“《玉台》但辑闺房一体。”(《诗薮》外编卷二)清纪容舒则云:“盖此集所录,皆裙裾脂粉之词,可备艳体之用。”(《玉台新咏考异》卷九)事实大致如此,全书专收与女性题材有关的作品,而且大都风格艳丽绮靡,文辞华美。《玉台新咏》收录鲍照《行路难》共四首: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西家思妇见之惋,零泪沾衣抚心叹。初送我君出户时,何时淹留节回换。床席生尘明镜垢,纤腰瘦削发蓬乱。人生不得常称意,惆怅徙倚至夜半。
剉蘖染黄丝,黄丝历乱不可治。昔我与君始相值,尔时自谓可君意。结带与我言,死生好恶不相置。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还君玉钗玳瑁簪,不忍见此益愁思。
奉君金卮之旨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葡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折节行路吟。不见柏梁铜雀上,仍闻古时清吹音。
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绮幕。中有一人字金兰,被服纤罗蕴芳藿。春燕差池风散梅,开帏对影弄禽爵。含歌揽泪不能言,人生几时得为乐。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别翅鹤。[1](卷九)
“中庭五株桃”写阳春二三月时节,独居女子思念远方的丈夫。“剉蘖染黃丝”以年老色衰的弃妇口吻倾诉心中的愁怨。“璇闺玉墀上椒阁”则叙写一位年轻女子渴望爱情的苦闷。值得注意的是“奉君金卮之旨酒”,从内容上看,似乎是一首在宴会上的劝酒歌,但文辞绮丽,张荫嘉评此诗曰:“劝人勿扰,先进以解忧之物,平排而起,气达而辞丽。”[2](P226)特别是“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感慨红颜易逝,且对仗工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葡萄之锦衾”,铺陈女性室内之奢华,写得香艳绮靡。这四首诗均以女性为表现对象,要么写愁思,要么写被抛弃的悲伤,要么写红颜易逝,感情基调大都比较低沉。鲍照有拟《行路难》十八首,《玉台新咏》收录的只有上述四首,其余的篇章,有的抒发世路艰难,有的感慨生命短暂,希望及时行乐,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不再描写女性的生活与情感,基本无关思妇与闺怨。比如其五:“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山去,明朝复更出。今我何时当得然,一去永灭入黄泉。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委皇天。”[3](卷八)诗人认为河边的青草,冬去春来又会生长,而城上的落日,明朝也会复出,但人的生命却是一条不归路,即“一去永灭”,诗人借自然的永恒来反衬人生的短暂,在这种强烈对比中,表现出对生命流逝的无奈。“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既然人生苦短,就当趁着大好年华及时享乐。再如其十:“君不见蕣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词。”[3](卷八)诗人感慨生命如白驹过隙,盛年不永,繁华也最终归于虚无。其七“愁思忽而至”、十六“君不见柏梁台”、其十七“君不见水上霜”、其十九“诸君莫叹贫”也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由对生命有限的体认而发出对生命不永的惋叹。除此而外,还有部分诗作主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抒发内心的不平愁闷之气。如其四“泻水置平地”,王夫之评曰:“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言愁不及所事,正自古今凄断。”[4](P535)
《玉台新咏》所录吴均《行路难》两首:
君不见上林苑中客,冰罗雾縠象牙席。尽是得意忘言者,探肠见胆无所惜。白酒甜盐甘如乳,绿觞皎镜华如碧。少年持名不肯尝,安知白驹应过隟。博山炉中清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逶迤好气皆容貌,经过青琐历紫房。已入中山阴后帐,复上皇帝班姬床。班姬失宠颜不开,奉帚供养长信台。日暮耿耿不能寐,秋风切切四面来。玉阶行路生细草,金炉香炭变成灰。得意失意须臾间,非君方寸逆所裁。
洞庭水上一株桐,经霜触浪困严风。昔时留心耀白日,今且卧死黄沙中。洛阳名工见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白璧规心学明月,珊瑚映面作风花。帝王见赏不见忘,提携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张女弹,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月月对君子,遥遥夜夜宿未央。未央彩女弃明箎,争见拂拭生光仪。茱萸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树枝。不学御山南岭桂,至今千年犹未知。[1](卷九)
这两首诗都采用了较为整齐的七言句式,其中第一首写宫廷之中嫔妃失宠的悲伤;第二首写桐木“由枯到荣”的一段经历,很显然,诗人把桐木枯死后制成的“琵琶”作了拟人化的处理,从“帝王见赏不见忘,提携把握登建章”,“年年月月对君子,遥遥夜夜宿未央”来看,隐约一位受到帝王宠爱的妃子。这首诗名为咏物,实则咏人,形象地表达了一位女性受到帝王的宠爱之后所获得的一系列的殊荣以及心理变化。吴均另外两首《行路难》没有被《玉台新咏》收录,其中“青琐门外安石榴”诗,写游侠少年在长安不能得到重用的苦闷。另一首“君不见西陵田”则慨叹人生短暂与生命无常的意蕴。
此外,《玉台新咏》收录释宝月的《行路难》一首,写幽闺思妇;收录费昶《行路难》两首,第一首“君不见,长安客舍门”写名叫桃根的倡女,被选入宫侍奉皇帝,但宫廷生活寂寞凄凉,诗末有“薄命为女何必粗”的感叹;第二首“君不见,人生百年如流电”写宫怨,抒情女主人公最后唱出了“不如天渊水中鸟,双去双归长比翅”,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向往。王筠的《行路难》写闺中思妇的痴情,“情人逐情可恨伤,畏边路远乏衣裳”,情人虽已另结新欢,但她仍在担忧远方的他缺少衣裳,“愿君分明得此意,勿复流荡不如先”,还在希望对方能回心转意。不难看出,《玉台新咏》所选录的九首《行路难》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女性色彩,大都反映的是女性的生活和情感,揭示她们的不幸生活与遭遇。在形式上,这些作品采用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而且其中有三首是整齐的七言诗。从《玉台新咏》所收录的情况来看,虽然鲍照拟《行路难》最多,但那些与女性无关的作品则一概不录。有研究者认为“因为徐陵是从乐府的角度收录古代诗歌,所以,《文选》中许多遗漏的重要诗歌得以入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玉台新咏》实际上是一部歌辞总集。”[5](P97-98)
笔者以为,就《玉台新咏》收录《行路难》的情况而言,并非这一时期的每首歌辞都收,只有小部分收入,可见编选者的标准主要不是从歌辞的角度,而是重在题材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表现女性、反映女性的生活。谈蓓芳教授认为,《玉台新咏》选录标准体现的是女性特色,除个别作品之外的诗篇全都涉及女性,而且许多诗都写了女性的痛苦。[6](P21)从《玉台新咏》选录《行路难》 的情况来看,正可证实上述的观点。据统计,南朝文人乐府诗共1016首,其中女性乐府题材就有443首,占43%。[7](P13)而《玉台新咏》 在选录《行路难》时以女性题材为主,大致反映了当时乐府诗的创作情况,也显示了《行路难》在此时期的写作特点。章培恒先生认为,《玉台新咏》的编者选了一部完整的“艳歌”集,这表明了此人公然承认其对“艳歌”的喜爱超过其他类型的诗篇,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种大胆的行为。[8]需要说明的是,现存的《行路难》,鲍照创作最早,数量也最多,但其中的题材也较为多样,并非只有写幽闺思妇的一类,前面已经提到,他的《行路难》组诗中有不少是感慨人生的无常与世路的不平。但从他之后文人的拟作来看,至少在齐梁时代,文人关于《行路难》的拟作主要是以写闺怨思妇为主。
二、《行路难》早期流传情况
关于《行路难》的演变情况,王小盾认为《行路难》作为民间说唱之曲,经历了由乐府曲流入民间,演为琴歌和歌谣的传播过程。[9]而向回认为,《行路难》本是民间歌谣,在公元321年之前,《行路难》便已和《太山吟》、《梁父吟》、《幽州马客吟》等曲调在今河北南部一带以民间歌谣的形式流传了。[10](P242)也有研究者认为《行路难》原为北方牧歌,有慷慨激昂之风。[11](P223)针对学界这些不同的说法,有必要探其究竟。《世说新语·任诞》载:“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12](下卷)袁山松为东晋人,王小盾认为《世说新语》中的这段记载是抄自晋裴启的《语林》,而《语林》作于东晋隆和(362)之前,“可以说在公元361年以前,《行路难》已流入琅邪、金城(今江苏句容县北)等地,用挽歌的方式歌唱了。这是不同于陈武所学唱的‘歌谣’的方式,但它却是更早的音乐方式,因为它是汉代乐府风尚的遗存。”[9]《艺文类聚》引《陈武别传》云:“陈武字国,本休屠胡人。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十数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13](卷一九)可见在袁山松之前,《行路难》是流行于北方的民歌,作为在牧羊时歌唱的曲子,陈武所学唱的《行路难》是否为挽歌还存在疑问。王小盾认为用挽歌形式来歌唱的《行路难》是保持了其汉代乐府的最初状态,换言之,他认为袁山松之前的陈武所学唱的歌谣《行路难》已经失去了其本来面貌。但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一是现今已经无法确认陈武所学唱的《行路难》的文本内容与音乐形式,那么就不能说挽歌一定是《行路难》最早的音乐形式;二是据《续晋阳秋》所载,袁山松善音乐,而作为北人旧歌的《行路难》“辞颇疏质”,也就是歌辞缺乏文采,比较质朴,应该还是保留了其产生之初的特点。而袁山松在此基础上“文其章句,婉其节制”,可见他已经对民间流传的歌谣《行路难》在歌辞与曲调上进行了一番改造的。从现存的材料来看,袁山松在《行路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确实有很重要的作用,据《太平御览》所引《俗记》曰:“宋祎死后,葬在金城南山,对琅琊郡门。袁崧为琅琊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祎冢,作《行路难》歌。”[14](卷四九七)袁崧即袁山松,再结合《续晋阳秋》所载,袁山松根据北人旧歌已经将《行路难》改制为挽歌。
对挽歌之入乐府,《乐府诗集》引崔豹《古今注》云:
《薤露》 、《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为挽歌。[15](卷二七)
根据这段记载,田横门人为了寄托哀思,创作了挽歌《薤露》与《蒿里》,到汉武帝时,李延年对其进行加工改造,收入乐府。然而《乐府诗集》又引《乐府解题》 曰:“《左传》云:‘齐将与吴战于艾陵,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预云:‘送死。《薤露》歌即丧歌,不自田横始也。’”[15](卷二七)这又说明《薤露》作为丧歌产生的时代更早。挽歌始于何时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始于先秦,一种认为始于是汉代,吴承学认为:虽然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与证据,但它们的内涵是有差异的,所谓挽歌始于先秦是指作为送葬歌曲的挽歌,所谓挽歌始于汉代,则是指作为正式送葬礼仪的挽歌,两者没有矛盾,只是前者比较原始而随意,后者为官方所确认和规定,有比较正式的礼仪形态和音乐形式。到了汉代以后挽歌逐渐成风,并形成了有歌有辞的乐府挽歌形式。[16](P69-72)汉代挽歌盛行,已有很多相关文献记载,如《风俗通义》载:“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17](P568-569)《晋书·礼志中》也载:“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18](P626)《宋书》卷六九《范晔传》载:“晔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19](P1820)可见,挽歌的流传由来已久,《行路难》在产生之初是否即是挽歌呢?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还没有证据表明在《行路难》产生之初就是作为挽歌来歌唱的,且《行路难》究竟产生于何时也是一个未知数,但袁山松对《行路难》进行加工改造,使之为挽歌的事实确实不容忽视的。换言之,在袁山松之后,《行路难》作为挽歌流行开来,当然这种对曲辞的改造也是有依据的,那就是《行路难》本为低沉感伤的曲调,因此这种改制也就顺理成章了。《乐府古题要解》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20](P11)这个看法对后世影响太大,以为《行路难》最初即为表达“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王运熙先生在《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一文中就指出乐府诗曲名与歌辞内容吻合的作品大量存在,[21](P364-378)而乐府曲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经过演唱者及文人的加工而逐渐扩大其内涵,曲名与歌辞的联系也不再那么紧密。李慈铭在《〈行路难五首〉》序中说:“古乐府有《行路难》者,皆言行役之苦,山水险恶,习俗变诈,所以戒远游、重乡里也。”[22](卷戊)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很值得注意的,作为最初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行路难》在产生之初顾名思义是感叹道路难行之意,只可惜现在不能看到《行路难》的古辞,《乐府古题要解》的看法很可能是根据现存最早流传下来的鲍照的《行路难》而做出的结论。
三、鲍照对《行路难》题材的开拓及对后世的影响
本是北方民歌的《行路难》在经过袁山松的改造之后,在南方的文人阶层之中广泛流行开来。《行路难》在南朝有不少文人拟作,鲍照的《行路难》组诗是现存最早的作品,也很有名,但昭明太子编《文选》一首也没有收录。其原因,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引鲜于侁云:“子美忆谪仙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之句,又赠薛华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而萧统所集,独收五言,及观《行路难》之作,托兴幽远,遣言豪放,李杜往往摭其意而为词,则明远之才盖有过人者。”[23](卷三四)可见这与《文选》的选录标准有关,《文选》选诗以五言为主,至于晋宋以来的许多优秀七言诗,以其多为民歌风调,不符合昭明所主张之雅正要求,故《文选》多不录。相较于《文选》趋于雅正的选文标准,《玉台新咏》则多收乐府民歌。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中已有完整的七言诗句,比较成熟的七言乐府,最早的是曹王的《燕歌行》。但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乐府诗歌写作的诗人,他写了大量的七言乐府,其中的《行路难》就以七言为主,在他之后的《行路难》拟作,也是以七言为主,鲍照的《行路难》有七首均以“君不见”开头,形成了后世较为固定的模式;更应注意的是鲍照拟《行路难》在题材上的创新,《行路难》本为歌谣,其产生之初,顾名思义本是咏叹道路之艰难的,后改造为挽歌,慨叹人生的悲伤。但鲍照自出新意,将流行的挽歌《行路难》融入女性题材,重视对女性行为活动与心理的揣摩与描写,用绮靡的笔调与华丽的词采来抒写女性的悲哀。这是鲍照在《行路难》发展史上的新的创造,许学夷《诗源辩体》云:“吴均乐府七言及杂言有《行路难》,本于鲍明远,而调多不纯,语渐绮靡矣。此七言之四变也,下流至梁简文。”[24](卷九)可见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之大。
需要指出的是,经袁山松改造为挽歌的《行路难》,其歌辞已不能见到,但从鲍照的拟诗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行路难》作为挽歌的一些影子,尤其是那些表现个体生命消逝之后,叙写面对坟墓时的哀伤与凄凉的诗篇,如其七:“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这里渲染的是一种凄凉的情境:放眼望去,只见松柏荆棘,而杜鹃的哀鸣声萦绕耳边,个体生命最终的归宿都将是一个阴森的凄凉的世界。再如其十:“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词。孤魂茕茕空陇间,独魄徘徊绕坟墓。但闻风声野鸟吟,岂忆平生年少时。”同前一首类似,该诗也是以“冢头”为表现的场域,在叙写孤魂、独魄的同时,感慨生命的短暂与世事的无常。清代的宋长白谓:“鲍照年十八,赋《行路难》二十首,强半作墟墓中语。”[25](卷三)虽语涉夸张,但指出了鲍照的《行路难》中保留了此前作为挽歌的一些痕迹,结合《行路难》组诗的其它诗篇,我们不难发现鲍照在《行路难》题材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乐府古题要解》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20](P11)唐代文人拟作《行路难》,大多按照这个思路发挥,基本不再以描写女性为主。也可以说唐代文人笔下的《行路难》从南朝的“闺怨”主体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生感慨。这些篇章虽然长短不一,但大多有“君不见”一类的固定模式。鲍照对唐代文人拟作《行路难》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尤其是其中那些感情强烈、气势磅礴的篇章,如其六《对案不能食》等篇。萧子显论当时文章略有三体,其一“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南齐书·文学传论》)将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与鲍照的《对案不能食》相比较: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迭燮垂羽翼。弃檄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15](卷七十)
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6](卷三)
不难发现,李白的这首诗明显是继承了鲍照“对案不能食”的题材与风格,气势豪迈。而鲍照还在《行路难》中融入边塞题材,如第十四:“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急边气寒。听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远望得留颜。将死胡马迹,宁见妻子难。男儿生世轗轲欲何道?绵忧推抑起长叹。”[3](卷八)这类题材也在唐代得到继承与发展,其中骆宾王所作的两首长篇就以塞外行军为主题,诗中有“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改题为《从军中行路难》。王昌龄的一首为短篇,五言八句,也是以边塞为主题,题为《变行路难》。而这两种类型的诗歌成为唐代文人创作《行路难》的主流。可以说,《玉台新咏》在选录鲍照的《行路难》时,主要偏重于那些“雕藻淫艳”的诗歌,而在唐代,“发唱惊挺,操调险急”的一面被李白、骆宾王等人所继承,成为《行路难》的重要代表。也就是说,唐代文人关于《行路难》的拟作中,相较于南朝时以“闺怨”为主题的《行路难》,此时期的作品中“哀伤、悲伤”的意味逐渐减少,“激愤”“慷慨”的意味逐渐增强,也可见此期作家的主体情感在诗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与强烈。至此,《行路难》已经脱离了思妇与闺怨的狭义范畴,在更为宽泛的领域抒发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不平而产生的愤激以及自我宽慰与解脱。
[1] 徐陵.玉台新咏[M].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
[2] 鲍照.鲍参军集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鲍照.鲍明远集[M].四部丛刊影宋本.
[4] 王夫之.古诗评选[M].船山全书: 第14册[C].长沙: 岳麓书社,1996.
[5] 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M].北京: 中华书局,2000.
[6] 谈蓓芳.《玉台新咏》选录标准所体现的女性特色[A].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 黎艳.南朝文人乐府诗的新变[D].陕西师范大学,2004.
[8] 章培恒.《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9] 王小盾.《行路难》与魏晋南北朝的说唱艺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2002,(6).
[10] 向回.《行路难》演唱方式流变及其对后世文人创作的影响 [J].乐府学(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6.
[11] 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M].北京: 中华书局,2003.
[12]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M].四部丛刊影明袁氏嘉趣堂本.
[13] 欧阳询.艺文类聚[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李昉.太平御览[M].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15] 郭茂倩.乐府诗集[M].,四部丛刊影汲古阁本.
[16]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17]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8]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19] 沈约.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0]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四库存目丛书》影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
[21]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2] 李慈铭.白华绛柎阁诗集[M].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23] 陈仁子.文选补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许学夷.诗源辩体[M].明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刻本.
[25] 宋长白.柳亭诗话[M].清康熙天茁园刻本.
[26] 李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M].四部丛刊影明本.
责任编辑:潘文竹
An Examination of Difficult to Walk: Its Dissemination and Evolution
DENG Fu-hua
( Research Centr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Yutaixinyong (New Odes from the Jade Terrace) includes nine poems of Xinglunan (Difficult to Walk) composed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with its subjects related to females,and each line mostly consisting of seven characters.At the beginning,they were popular folk songs lamenting the difficult journey,as the name suggests.After Yuan Shansong's adaptation,they were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s elegies.Bao Zhao not only preserved the original meanings,but also extended the theme and style of the poems entitled Difficult to Walk,which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e subject of females had been adopted in these poems,with an ornate style and gorgeous words to express their grief.In addition,the heroic style was inherited by Li Bai of the Tang Dynasty.
Southern Dynasties;Difficult to Walk; yue fu; circulation
I207
A
1005-7110(2013)03-0070-06
2013-04-11
邓富华(1979-), 男,四川苍溪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以《登大雷岸与妹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