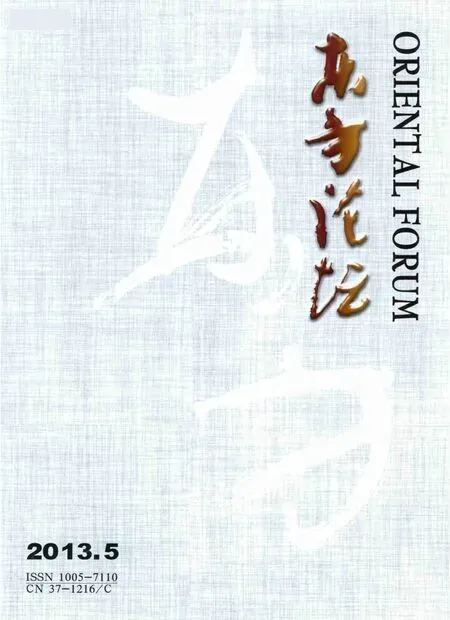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
王 勇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
王 勇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汉文学”为“汉文典籍之学”,尤其指中国典籍传播区域的域外汉文典籍。以阅读域外人士创作的汉文遗产,探寻其中国因素,考察其民族特色,并从中发掘裨益于国学研究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对域外汉文典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其二、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三、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
东亚文化圈;文化交流史;汉学;汉文学
一、中国的“汉文学”
(一)鲁迅与“汉文学”
鲁迅在国内学者中较早使用“汉文学”概念,《鲁迅全集》第九卷收入《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篇目如下: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书》与《诗》
第三篇 老庄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附 录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全集》在该书卷首附有编者说明:“本书系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1938年主持《鲁迅全集》编务的郑振铎、许广平等,将该书定名为“汉文学史纲要”,也并非完全无据。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油印讲义的第四至第十篇的中缝,写有“汉文学史纲要”。
归纳起来说,鲁迅将厦大的讲义正式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纲要”,将中大的讲义正式定名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而在厦大讲义中缝简称之为“汉文学史纲要”。
这部著作一书三名,已经让人纠结;而书名中的“汉”字,更招致多种猜测——“汉代”?“汉民族”?“中国”?“汉字”?
从该书正文10篇、附录1篇的名目来看,内容多涉及汉代文学。在此意义上看,鲁迅所说的“汉文学”,或等同于“汉代+文学”。
这种说法看似顺理成章,其实还存疑窦。约半个世纪后,这个书名终于引出一段公案。
(二)一段公案
20世纪80年代初,鲁歌多次撰文质疑《汉文学史纲要》书名,认定此书名系后人误解“鲁迅的原意”,鉴于“这一谬误己流传了四十五年之久,蔓延到全世界,问题相当严重”。故呼吁“亟须纠正”。作者如此判断的依据如下:
“古代”指从原始社会到汉,“汉”即汉代。该书《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共有十篇,《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第二篇 〈书〉与〈诗〉》,《第三篇 老庄》,《第四篇屈原及宋玉》,《第五篇 李斯》,内容是从“原始之民”到秦的李斯的文学史略,这些都是汉代以前的事,故鲁迅用“古代”二字概括之。从第六篇至第十篇(即从《汉宫之楚声》至《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才是汉代文学史内容,鲁迅用“汉”字来概括。因而鲁迅自定的题目《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切合这十篇的内容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去掉了鲁迅自写的“古代”二字,把题目改为《汉文学史纲要》,便不能包括前五篇的内容,造成了题不对文的谬误。现在应从速恢复鲁迅自定的题目,不应使谬误继续流传下去了![1]
作者强调“鲁迅原书名是《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古代’两字有特定含义,指从原始社会到汉代以前,……‘汉’即汉代”,即把“古代”理解为秦代以前,把“汉”解释为汉代。
这篇文章有点意气用事,事后冷静下来再做斟酌,作者发现了问题,尤其对“汉”的诠释有误,于是又撰文加以修正:
这里的“汉”,显然是汉民族之意,而不是汉代之意,因为屈原及宋玉不是汉朝人。所谓《汉文学史纲要》,即用汉民族的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纲要。[2]
鲁歌在《对1981年〈鲁迅全集〉的若干校勘之二》一文中,对此问题再次予以澄清:
我在《对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若干校勘》一文中曾指出《汉文学史纲要》书名有误,应改为由鲁迅亲定的《古代汉文学史纲要》。但我在该文中提出这里的“古代”二字指“从原始社会到汉代以前”,“汉”即汉代,是不够正确的。这里的“汉”不是汉代之意,而是汉民族之意。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有写《中国文学史略》的计划。此《中国文学史略》,实际上即《汉文学史纲要》,即中国作家用汉文所写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纲要。[3]
归纳鲁歌的3篇文章,最初将“汉文学”解读为“汉代+文学”,后两文对此做了重大修正,认为“汉”指汉民族,“汉文学”应该解释为“汉族+文学”。
鲁歌对《汉文学史纲要》的书名提出质疑,其勇气和慧眼值得尊重,但主要论点朝三暮四,论据也存在明显的瑕疵,如“古代”解释为“从原始社会到汉代以前”,又说“指的是从上古到汉末”(《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正名》),自相矛盾不说,这种“特殊”的诠释,既不符鲁迅的用词风格,也有违约定俗成的断代习惯。
顾农最先发难,他于1986年发表《〈汉文学史纲要〉书名辨》(《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1999年又发表《〈汉文学史纲要〉书名问题》(《出版广角》,1999年第11期),批驳鲁歌的观点,为《汉文学史纲要》正名,其根据是:
(1)书名经许广平审定;
(2)该书名已约定俗成;
(3)“古代”概念宽泛,包含“汉代”。
1987年,康文发表《〈汉文学史纲要〉书名应改正》(《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认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删去“古代”后,“书名令人迷惑不解”:
“汉文学”若作“汉代”讲,那么书中还讲到先秦、秦代了,若作“汉族”讲,也不能只讲到汉代啊?
康文指出误改书名之责或在主事《鲁迅全集》编务的郑振铎,证据是郑振铎1985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的下面一段话:
鲁迅先生编的《汉文学史》虽然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却是杰出的。首先,他是第一个在文学史上关怀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的。他没有象所有以前写中国文学史的人那样,把汉语文学的发展史称为“中国文学史”。在“汉文学史”这个名称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
郑振铎这段话的意思,说“汉”限定于汉民族,表示鲁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然而,我们知道鲁迅不谙少数民族语言,在他的著述中也从未表述过这层意思。
遗憾的是,康文虽然提供了郑振铎这条重要线索,也对郑振铎的观点做了批驳,但他主张恢复《古代汉文学史纲要》的书名,却对争议焦点的“古代”、“汉”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
(三)鲁迅的本意
这部书原是鲁迅的讲义,1926年下半年他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所编讲义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1927年在中山大学再次开设此课,讲义更名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纂《鲁迅全集》时,编者更名为《汉文学史纲要》,目前学界均沿袭这一名称。
如前所述,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略”,他于1926年9月14日致许广平信中说,自己在厦门大学担任的课程之一“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同年9月25日致许广平信中说:“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9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从昨天起,已开手编中国文学史讲义,今天编好了第一章。”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信中说:“《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
那么1927年赴中山大学任教时,情况又如何呢?据1927年3月印行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鲁迅所开的这一课程的名目是“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三时”,即课程名称是“中国文学史”,断代为“上古至隋”,课时为每周3小时。由此推断,“汉文学”之“汉”,等同于“中国”,绝没有“汉代”的意思,也不局限于“汉民族”。鲁迅在讲义上添加“古代”两字,意即限于“上古至隋”。
根据上面列举的各种资料,我们可以对鲁迅所用“汉文学”一词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梳理:
(1)这份讲义1926年最初起名《中国文学史略》,似有与《中国小说史略》匹配的意思(《鲁迅全集》第九卷为《中国小说史略》与《汉文学史纲要》合集),即从小说而推广至整个文学领域;
(2)1927年改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似乎大大缩小了范围,限定于“古代”,改名后的“汉文学”,应该理解为“中国文学”,不然既已明确“汉代”,再限定古代,岂非屋上架屋?作为证据,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讲义原稿,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则“中国”与“汉”同义甚明;
(3)鲁迅的原意似乎是讲授“中国文学通史”(或称“汉文学通史”),但第二次讲授时因故改变主意,聚焦于古代文学史,故称“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而绝非只讲“汉代文学史”,证据是正文10篇中的前5篇为秦以前部分,附录则延伸至魏晋时代;
1936年鲁迅去世后,1938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鲁迅全集》20卷,将书名擅改为“汉文学史纲要”有失稳妥,容易招致误解。
二是求解器求解过程:对内流体模型所划分的网格上所有含有单一变量的方程进行求解,直到获得该方程的解,另一个参数方程的求解需通过循环这一过程,该方程(相互耦合的非线性控制方程)可进行多次迭代求解,当所求解的方程组收敛,该求解过程结束。
这个“汉”字,近人、今人均不解,显然在中国语境中难理头绪。窃以为鲁迅以“汉文学”指称“中国文学”,有可能受到日本学界用词的影响。
(四)周作人与“汉文学”
中国语境中,“汉”大凡指汉代或汉族,“汉字”“汉诗”如是,“汉籍”“汉人”亦同。以“汉”指称中国,起自近代,源头则在海外。至于鲁迅所赋予“汉”的含义,疑来自留日经历,兹以周作人为佐证。
众所周知,周作人浸淫日本文化远比其兄周树人(鲁迅)要深,在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诸多日本因素的深刻痕迹。
周作人自编文集《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收录《汉文学的传统》一文,作者开篇即谈到“汉文学”的定义: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称。中国文学应该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人的著作不算在内。
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概念宽泛,而“汉文学”限定于汉文作品,但不包括域外人士的汉文著述。这里的“汉”,显然与“汉代”没有干系。他接着写道:
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
有关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周作人归纳为“汉文学里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种儒家的人文主义(Humanism)”,并进一步诠释说:
我说汉文学的传统中的思想,恐怕会被误会也是那赋得式的理论,所以岔开去讲了些闲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
除了《汉文学的传统》,周作人在《汉文学的前途》(《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首先指出:
我意想中的中国文学,无论用白话那一体,总都是用汉字所写,这就是汉文,所以这样说,假如不用汉字而用别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也好,反正那是别一件东西了,不在我所说的范围以内。因为我觉得用汉字所写的文字总多少接受着汉文学的传统,这也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字写下去,与这传统便有远离的可能了。
周作人把汉字与注音字母(参考日本假名创制)、罗马字区别开来,认为汉字负载着“汉文学的传统”:
我觉得用汉字所写的文字总多少接受着汉文学的传统……汉文字的传统是什么……这就是对于人生的特殊态度。中国思想向来很注重人事,连道家也如是,儒家尤为明显,世上所称中国人的实际主义即是从这里出来的。
周作人的观点,大抵可总结为,汉字承载的“汉文学”,其核心是儒家思想,还包括一些道家的成分。亦即,汉文学形式限于汉字,内涵则不限于文学。这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找不出根据,与现时流行的“汉文学”研究更是相去甚远。
于是我们就要思考,鲁迅与周作人的“汉文学”概念,究竟来自于何处?从这两人的经历来看,他们留学日本很可能是一个源头。
二、日本的“汉文学”
纵观中国学术界,在国学领域中很少有人使用“汉文学”的概念,而使用者往往具有域外(尤其是日本)学术背景。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个概念在日本语境中的内涵与外延。
(一)辞书的释义
在日本学术界,“汉文学”具有广义与狭义、内向与外向等多种解释。我们先看日本权威辞书《大辞泉》对“汉文学”的解释:
(1)中国传统文学。中国的古典文学。分经(经书)、史(历史)、子(诸子百家)、集(诗文集)4部。
(2)用汉文撰写的文学作品,以及对此进行研究的学问。
我们倒过来讲,第二种释义是凡汉文作品尽纳其中,并不限于中国,这是广义的;第一种释义是限于经史子集,一般不包括佛教、科技等作品,这是狭义的。或者说,第一种释义针对中国,属于“外向”的;第二种释义比较模糊,但囊括了日本人的汉文作品,含有“内向”的余味。
相比之下,《日本大百科全书》(小学馆)由大曾根章介执笔的“汉文学”条,则将其框定为“日本人的汉文作品”。即外延限定为“日本”,属于“内向”的;内涵限定为“文学”,属于“狭义”的。这在日本国文学领域是比较通行的观点,兹引录如下:
日本人创作的汉诗及文学性的汉文。所谓汉文学,无疑是日本人借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表达日本人思想感情的作品,但同时是在积极崇拜、努力摄取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学形态。因此,作者均关注中国文学的变迁,追随中国文学的潮流,并不断加以模仿,不能简单地判定为我国独自的文学。借用中国的形式而盛之于日本内容,这种双重性格便是其特色所在。
(二)冈田正之
在日本文学界,有一个具有中国学术背景的群体,他们熟谙中国文字、语言、文学乃至哲学思想、历史文化,其地位举足轻重,其影响不可小觑。代表人物有冈田正之、猪口笃志、山岸德平等,其中冈田正之的博士学位论文《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1929年由东洋文库出版,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汉文学断代史。
1964年,山岸德平、长泽规矩也在《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基础上,整理冈田正之遗著编为《日本汉文学史》(吉川弘文馆,1964年12月),此书堪称斯界扛鼎之作。该书卷末附有《日本汉文学史研究资料解说》,兹罗列几种:
(1)儒学方面,有《日本宋学史》、《日本程朱学之源流》、《南学史》、《海南朱子学发达之研究》、《南学读本》①[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国初孙徵君讲学苏门,号为北学;余姚黄梨洲宗羲,教授其乡,数往来明越间,开塾讲肄,为南学。”等;
(2)史学方面,有《善邻国宝记》、《异称日本传》、《邻交征书》、《日支交通史》、《日支文化之交流》、《上代日支交通史之研究》、《释日本纪》、《日本书纪集解》、《日本书纪古训考证》等;
(3)其他方面,有《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上代金石文之考证》、《皇典文汇》等。
很显然,日本语境中的“汉文学”,与中国语境中的概念不尽相同。赵苗在《日本汉文学史续论》(《经济研究导报》,2010年第16期)一文中,对《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评述如下:
全书共分五编,内容包括典籍的传来、归化民族和汉文学、推古朝的遗文、学校及贡举、圣学及人材、学术的风气、记纪和风土记、养老令、诗和诗集、汉文学和万叶集、宣命、祝词和汉文学等。此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引证的资料很多,遗憾的是将一些并非汉文学的内容也包括进去,使这部书的内容显得有些庞杂。
赵苗所言的“非汉文学的内容”,即历史、地理、经学、典章等文献,按现代中国人的概念,不能归入“汉文学”范畴,而这恰恰是日本“汉文学”的特征所在。
(三)和汉文学
从日本历史上看,所谓“汉文学”是对应“和文学”而萌生的概念。日本自古无文字,故早期的文学作品是用汉字记录的。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直接用汉文创作,取汉字之“义”,如《怀风藻》等;另一种用汉字来记录,取汉字之“音”,如《万叶集》等。第二种情况由于保持着汉字之“形”,视觉上与汉字无异,所以后世称之为“真名”,在此基础上通过省笔、草化而衍变成“片假名”、“平假名”,形成具有日本创意的表音文字“假名”,在视觉上与汉字已相去甚远。
使用汉字创作的作品归为“汉文学”,使用假名(包括“真名”)创作的作品划入“和文学”。虽然日本文学由汉和两条主线交织而成,但历代的国粹主义者轻“汉”重“和”的暗流一直涌动不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东渐及民族意识高涨,这股暗流逐渐浮出水面,在“国文学”的圈子里视“和文学”为正统、主流,通行的日本文学史往往摒弃“汉文学”,以彰显本民族文学的纯洁性。
这种观念显然有失偏颇,部分理性的学者早已有所觉察。譬如,加藤周一指出:“特别是向来的日本文学史,大多看作是用日本语书写的文学,而此书在这里所思考的是,日本人通过两种语言创造出来的文学。这两种语言之一是日本语,另一种是古汉语(在日本的所谓“汉诗汉文”)。”[4](P3)
加藤周一这部《日本文学史序说》的重要创新之处,即是把国文学者视之为“旁流枝叶”的汉文学,拨乱反正而回归于日本文学的流变中加以考察。因为他认为“从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日本文学至少存在两种语言:这就是日本语的文学和中国语的诗文”,至于两者的特征、功能及相互关系,他接着做了进一步阐述:
比如,《万叶集》与《怀风藻》、《古今和歌集》与《文华秀丽集》。不消说,在这里能够更丰富、更微妙地表现出日本人的感情生活的,不是用外国语写作的诗,而是用母语写作的歌。然而这个时候,散文方面情况已不尽相同。比如,用日本语书写的诗论《歌经标式》,其理路就比不上用汉文书写的《文镜秘府论》那样清晰。[4](P8)
也就是说,和文学富有感情色彩,而汉文学具有理论深度,两者既独具特色又相映成辉,在构建日本文学史不可偏废一端。正是因为上述特点,在日本文学中扮演“理性”角色的汉文学,往往超越狭义的“文学”框架,涉及到哲学思想、历史文化的宽泛领域。
如上所述,日本语境中的“汉文学”,大致有以下几种涵义,自大而小罗列之:
(1)汉文作品以及对此进行研究的学问(《大辞泉》);
(2)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经史子集(《大辞泉》);
(3)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文献,除诗文之外,还包括哲学思想、历史文化著作(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
(4)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文学作品,主要指诗歌、散文(《日本大百科全书》、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
归纳起来说,各种言说的分歧点在于:(1)专指中国,还是专指日本?(2)限于文学,还是广及思想文化?在日本语境中,中国的“汉文学”概念根深蒂固,最大限度可以涵盖经史子集;日本的“汉文学”涉世未深,一般拘囿于文学领域,即使如冈田正之等也仅旁及哲学思想、历史文化典籍而已,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因人而定,处于不确定之中。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构建“汉文学”学术体系的动向,传统观念受到极大挑战。
(四)日本学界走势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启动大学改革的程序,重头戏之一是次年开始实施“21世纪COE计划”(The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国家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每个学科重点扶持一个,以促其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有点类似中国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历史悠久而汉学积淀深厚的二松学舍大学,申请“日本漢文学研究の世界的拠点の構築(日本汉文学研究之世界基地的构筑)”获得成功,本人作为客座研究员参与其中,对其构建日本“汉文学”基地的过程比较熟悉。那么他们的“汉文学”是什么含义呢?
首先,该项目英文翻译为“Establishment of World Organization for Kanbun Studies”,与“汉文学”对应的英文是“Kanbun Studies”,其中“Kanbun”系“汉文”的日语读音,“Studies”不用说指“研究”或者“学问”。由此可见,这个日本国内唯一的“汉文学”基地,其意思是“汉文+学”。
我们再看二松学舍大学COE官方网站①网址为:http://www.nishogakusha-coe.net。对该项目主旨的陈述。先看第一段:
本项目所言“日本汉文学”,乃是以日本人用汉字汉文撰著的文献资料为对象的学问,对象范围不限于汉诗文等文学作品、记录类史学文献,涵盖佛典、佛书、天文历法、医 书、本草等所有分野之文献。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日本的COE计划一般按传统学科申报,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生命科学”等,但为传统学科分类所难以涵盖的交叉学科或新兴学科,特设“创新学术”的门类,二松学舍大学的“日本汉文学研究”基地便归属于此。那么,它的创新点在哪里呢?其独创之处即在于摆脱“经史子集”的藩篱,将研究对象扩展至“佛典、佛书、天文历法、医书、本草等所有分野”。一言以蔽之,凡用汉文撰写的文献,均列为研究对象。这从该校出版的学术期刊《日本汉文学研究》内容,亦可得到印证。
我们接着看第二段:
没有固有文字的日本人,通过学习中国的汉字汉文而摄取中国的学术文化。在此基础上,不久发明“训读”这种独特的解读方法,不仅使吸收中国学术文化的对象范围飞跃般地扩大,同时日本人自身用汉字汉文创作了大量的著述。
这里提到“日本人自身用汉字汉文创作了大量的著述”,数量究竟有多大呢?二松学舍大学COE团队已经做出两个书目,我们以后会具体涉及,仅现存的总数就不少于万种。
那么这些汉文书籍价值何在呢?我们接着看下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近代的日本,汉字汉文的文献构成日本学术文化的主干。因此,日本汉文知识不仅对日本文化研究是必不可缺的,同时也是日本研究的基础。有关此点,国内外的日本研究者强烈期待日本汉文学研究的充实与研究人员的培养。
日本学者的视野往往拘囿于国内,上述观点显得有些狭隘。现在国内盛行“域外汉籍”研究,大多数人不是冲着“日本”去的,功利一点的是为淘宝中国典籍的残篇断简,大度一点的也会去观摩其他民族的创意。
这篇文章的最后,感叹“随着明治以后急速的近代化,上述日本汉文学的研究倍遭冷遇,文献资料类的埋没、散逸触目惊心”,因而呼吁进行抢救性作业。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自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日本人的汉文水平日渐衰弱,要继承这份庞大的汉文学遗产,绝非易事。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大概要由中国文化传播者的后代来承担。
三、韩国的“汉文学”
虽然国内研究韩国古典文学或传统文化的学者,经常使用“汉文学”的术语,但这个概念在韩国如何形成、怎样流变,我们知之甚少。
在这一讲中,我们先概述韩国学界有关“汉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接着聚焦于该领域的开山之作——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探讨朝鲜汉文学的传统特征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史概述
韩国学者撰写的“汉文学”研究专著,已经译成中文且比较容易看到的有两种: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张琏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李家源的《韩国汉文学史》(赵季译,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初版于1931年(朝鲜语文学会),被公认为是“韩国第一部汉文学史专著”[5](P161),我们在下节对这部书再作介绍。
李家源的《韩国汉文学史》问世于1961年(民众书馆),这是一部通史,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韩国汉文学的发展历程。同一时期,还有崔海宗的《韩国汉文学史》(青丘大学出版部,1958年)、文璇奎的《韩国汉文学史》(正音社,1961年)、徐首生的《高丽朝汉文学研究》(萤雪出版性,1971年)等。
如果以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为“汉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那么20世纪50-70年代的几部著作可称为古典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学术界尚弥漫着“民族史观”的氛围,“汉文学”似乎是与“韩文学”脱节的、象征着古老落后、生硬古板的传统遗产。
李惠国主编的《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四章“文学研究”之第一节“古典文学与研究”,辟“汉文学研究”专项,对20世纪80年代后“汉文学”研究逐渐兴起的背景,做了如下的梳理与分析:
到了80-90年代,汉文学研究有了新的转机。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在韩国古典文学中汉文学所占的比重很大,要扩大研究范围、开拓研究之新途径,就应该对汉文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样就在韩国学界兴起汉文学热,后起的少壮学者们也纷纷投入到汉文学研究之中。这场汉文学研究热一改过去的沉寂局面,形成非常活跃创的研究局面。这时期的汉文学研究所涉及的范蜀很广,研究成果也多种多样,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包括韩国汉文学的形成、韩国中世纪各个时期汉文学发晨、汉文学作家和流派以及汉诗、汉语散文的创作及其特点等。在这时期的汉文学研究引人注目的是博士学位论文的日益增多,而且对汉诗的研究比重相对多一些。
代表性论著可举出如下几种:梁元锡的《韩国汉文学形成过程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李崇文的《高丽前期汉文学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2年)、金英的《朝鲜朝后期汉文学的社会意蕴》(集文堂,1993年)、尹在民的《朝鲜朝后期中人层汉文学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0年)、郑尧一的《汉文学批评论》(仁荷大学出版部,1990年)等。
与此前的古典式研究不同,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趋于细化,即集中研究每一时段、某个阶层、甚至某个人物;而且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涉及到社会学、文艺批评等领域;研究目的也从怀古到阐明“汉文学”的现代意义。
(二)《朝鲜汉文学史》
韩国语境中“汉文学(한문학)”,究竟是什么涵义呢?手头辞书的解释均太简略,我们还是来看看“汉文学”研究的开山作品——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是如何界定这个概念的。
1.作者简介
金台俊(1905—1950),朝鲜平安北道云山郡人,号天台山人。1928年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艺术系,1931年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法务系中国文学专业。他于1930年在《朝鲜日报》上连载《朝鲜小说史》,这是一部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的作品,可谓开近代文学研究之先风,在朝韩学术界享有盛誉。
1931年与李熙升、赵润济等创立朝鲜语文学会,同年出版单行本《朝鲜汉文学史》。1939年任京城帝国大学讲师,因从事反日活动,1941年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同年获假释后即赴中国参加朝鲜义勇军。1945年日本投降返回韩国,任朝鲜共产党文化部长、朝鲜文学家同盟执委等。1947年因参与“8.15暴动”(反抗美军当局、李承晚政权对左翼势力的镇压),被美李当局投入监狱,1949年11月在汉城水色被处死,时年仅44岁。
2.谋篇布局
全书由绪论、上代篇、高丽篇、李朝篇构成,绪论下分3章、上代篇厘为9章,高丽篇、李朝篇各7章。篇章结构如下:
绪论
第一章 传统文学观及今日之见解
第二章 朝鲜汉文学史之范围
第三章 朝鲜汉文学概观
第一编 上代篇
第一章 古代文学之鉴赏
第二章 三教之输入和三国文学
第三章 三国统一以前的文章家
第四章 强首先生
第五章 三国统一后的文学和学制
第六章 国言解经之先觉薛聪
第七章 金大问和禄真
第八章 罗未宾贡诸子
第九章 东方汉文学之鼻祖崔致远
第二编 高丽篇
第一章 高丽汉文学概观
第二章 高丽初叶之文艺
第三章 私学之勃兴与文运隆盛期
第四章 文人受难期
第五章 李奎报和较之晚出的诗人
第六章 李齐贤及其所处时代
第七章 高丽末叶的儒冠文人
第三编 朝鲜篇
第一章 李朝汉文学概观
第二章 草创期的文艺
第三章 成宗至明宗间的诗风
第四章 穆陵盛世之文运
第五章 月象溪泽四大家
第六章 仁肃间的巨星
第七章 近世之汉文学
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从上古时代开始叙述,但却于李氏朝鲜时代(1392—1910)戛然而止,这源于作者对朝鲜“汉文学”独特的视角,下面还会涉及。
3.学问分类
我们集中探讨《绪论》所含的3章。作者在第一章“传统文学观及今日之见解”中,指出“世间学问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即科学、文学、哲学,各自特征与目的如下:
一为科学,这是“知”的学间,其目的是求“真”;
一为文学,这是“情”的学间,其目的是求“美”;
一为哲学,这是“意”的学问,目的在于求“善”。
大意是说,人类做学问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真善美”的境界,而文学的功能在于抒发情感、美化生活。作者因而说:“所谓文学,是具有美的情感的文字,换言之,即将现实生活之利害进行艺术化之处理。”进而指出“朝鲜古代之汉文学,其体裁多求山水花月”的特征。
按照上述分类,作者划定东方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界限,即“博物学和天文学并不列属文学,同样,关于经术道德的所谓‘伦理哲学’亦不在文学范畴”。金台俊虽然认为“纵观文学进化之回程,寻其盛衰变迁之因果,推测今后文学之趋势,此乃士学史之使命”,但他的《朝鲜汉文学史》却“与此略有乖忤”,并在第二章予以铺叙。
(三)朝鲜汉文学的范畴
金台俊在撰写这部“汉文学”的拓荒之作时,首先面对如何框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他从学问分类的角度,指出“所谓汉文学理应指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但作者的意图却有所不同:
但我意在对汉文学作史学研究,专门考察汉文学,也就是说,我要抛开孔、孟、程、朱、老庄等哲学要素,单纯地对产生于朝鲜的、以汉文字写就的文学范围内的诗歌文章内容或形式之演变,进行史学研究。
传统意义上的“汉文学”,主要包括哲学思想与诗歌散文两个方面;而金台俊的创新之处,在于抛开“孔、孟、程、朱、老庄等哲学要素”,专注于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对之进行“史学研究”。
总而言之,金台俊在中国文学与韩国文学之间,开垦出一片“韩国汉文学”的园地。既然是一块独立的园地,必然具有排他性,即有必要与中国文学、韩国文学加以区别。与朝鲜文学的区分,作者这样叙述:
所谓朝鲜文学,是指完全以朝鲜文字“韩字”记录乡土固有思想感情的文学。用朝鲜语写成的小说、戏曲、歌谣等当属此范围。这便与汉文学区分开来。
上述区分非常清晰明快,即以韩文撰写的作品归入“韩文学”,用汉文创作的作品归为“汉文学”。然而,“出自朝鲜人的汉文学同中国人手制的汉文学有何差异呢”?作者继续论述:
中国人的中国文学,有先秦和两晋文章,有魏晋六朝以降直至明代之发达的小说,有六朝四六骈俪和唐诗、宋词及元曲,文学代代不辍。但是,自宋元以后,日渐发达的词曲小说文白(口语)混杂,且韵帘规则亦日趋繁杂,这对于语言习惯不同的外国人来说,欲模而仿之实在是件难事。因此,在我国对这类文学作品模仿之作几近于零。故此,朝鲜的汉文学全部是诗歌、四六和文章,并以此为止。
金台俊将中国文学以宋元为界分为两期,此前以文言作品为特征,此后以白话作品为特色;朝鲜对中国文学的摄取与模仿,不仅限于前者,而且多为传统的诗歌与散文。在本章的最后,作者特别加上“几句附言”:
一、本稿与拙作《朝鲜小说史》在许多方面重叠。每当此时我便简约带过,并力求用新的资料和实例加以说明。
二、佛家沙门的汉文学拟另觅机会阐述,故这里暂不论及。
三、朝鲜汉文学史不谈李朝以后部分。京畿三南诸家特别是西北各家均不置词。
拒佛教作品于门外、断代于近代以前,这与日本的“汉文学”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传统与走向
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的先驱意义及经典价值,不仅有后世的客观评价,作者自身在撰写过程中似也怀有一种继往开来的使命感。他在第二章中有如下述怀:
最令人悲哀的是,现在朝鲜的汉文学者一谈汉文学,文章必称先泰两汉唐宋八家,律诗必举鲍谢杜陆,于此止步。实际上这是虚言妄发。反映现代中国民族精神之发展跃动的文学,是中国现代口语即白话文学,古代文言体诗文已成为供人观赏的古董。我现在以此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即是兴盛一时的古典研究的终结。学习文言汉文、作汉文文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这项工作意味着对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这是汉文学史的使命,特别是朝鲜汉文学史的使命)。
《朝鲜汉文学史》付梓之际,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在哲为之作序,他首先肯定汉文学对朝鲜的巨大且深远影响:
自从汉字输入我国以来,我们的祖先一直用汉文编写历史、进行科举、吟哦诗歌、撰制文革。汉文固然有其弊缺,但绝对不是有害无益。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汉文筑就了我们的历史文化。无论你是把汉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在朝鲜的发展,还是将之视为朝鲜文学的一部分,但任何人也绝对无法把这个宽阔博大的领域排除在朝鲜文学范畴之外。
接着在感叹“汉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的同时,关注如何继承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如今有人制造汉字制限论。在汉字的宗主国中国也有人主张汉字撤废论。的确,汉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目前它正处于低谷受难期。在这个时期,如果无人对星散四方的古人诗文集进行搜集整理,对过去的汉文学进行整体研究,那么,用不了多久,一度盛行繁荣于半岛的汉文学将湮没无存,我们的后人将与之无缘见面。因此,我期望于研究者久矣。我不是企望复兴汉文学,我只是切实地感到这是整理民族历史上一段独特文学现象之迫切需要。
因此,《朝鲜汉文学史》的问世,正是作序者期盼已久之盛事,“对此我致以万斛之赞词”。对于该书“儒家著作全然被排除在汉文学史之外,纯粹从文学角度对文学进行历史研究”,金在哲也予以积极评价,最后总结道:
无论其内容还是其治学方法,乃至行文笔法,都会使传统式汉文学研究者瞠目于三舍之外。
关于此书在中国学界的评价,管见所及寥寥无几,兹引张琏瑰在《译者前言》中的一段话为例:
金台俊写于30年代的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行文简约,但内容丰富,结构严整。因此刚一问世,即被学界公认为是这个领域里开创性研究成果。这本书所厘定的朝鲜文学史范畴和主要见解,已被后学广泛继承,它已成为韩国治文学史者必读书目。
综上所述,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的主要学术创新点有三:将朝鲜汉文学从中国汉文学中剥离出来,强调其文言特点;将朝鲜汉文学与朝鲜文学链接起来,关注其民族创意;在重构“朝鲜汉文学”过程中,剔除了儒、道、佛等哲学思想成分。
不过,我们可以从这部著作中逆向印证,朝鲜半岛语境中,传统的“汉文学”恰恰包含了儒学、道教乃至佛教的诸多因素。这一方面与古汉语的“文学”意蕴相关,另一方面与流播东亚的“汉文”一词颇有渊源。
这里附带说一句,我曾经向多位韩国学者求证,在他们的意象中,“汉文学”应该断为“汉+文学”还是“汉文+学”?得到的答复均是后者,这一点与日本的“汉文学”极其相似。
四、东亚的“汉文学”
前面三节,我们分别讨论了中国、日本、韩国语境中,“汉文学”概念的形成与变迁、共性与个性等诸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鲁迅的“汉文学”等同于“中国文学”,内涵限于现今的文学作品;
(2)周作人的“汉文学”等同于“汉文文学”,内容主要指儒学,但作者限定为中国人;
(3)日本狭义的“汉文学”,指传自中国的经史子集,一般不包括日本人的著作;
(4)日本广义的“汉文学”,凡用汉文撰写的作品尽囊括其中,但不含佛教文献,有时特指日本人的汉文作品;
(5)韩国传统的“汉文学”,包括儒学、道家乃至佛教等哲学思想;
(6)韩国新兴的“汉文学”,排除哲学思想要素,限定为近代以前的文言作品。
显而易见,“汉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而且是一种跨越民族、超越时代的文化现象。既然如此,就有必要从东亚的视域,对其进行考究。
(一)东西方的“文学”
“汉文学”一词中的“文学”,既有蕴涵深厚的东方根基,又带有浓郁的西方色彩。
中国古汉语中的“文学”,据《汉语大词典》列出的主要义项有三:(1)文章博学;(2)儒家学说;(3)文章经籍。此外还有多种派出义项,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论语·先进》中说:“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家语》中又说子游“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而子夏“习于《诗》,能诵其义,以文学著名”。这里的“文学”,即“孔门四科”之一。据皇侃《论语义疏》“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一语可知,基本涵盖了《汉语大词典》的三项释义。
在西方语境中,英文的“literature”大约出现于14世纪,与法文中的“litérature”和拉丁文的“litteratura”同类,其共同词源为拉丁文的“littera”(字母)。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指“阅读的能力及博学的状态”,到后来也指“写作的工作与行业”或“高雅知识”的书本与著作。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西方的“literature”被译成“文学”导入到中国,于是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将东方传统的“文学”概念替换为西方式的“文学”,一是将西方舶来的“文学”视为新概念。
李春《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对上述两种倾向作了详尽剖析,兹摘 要介绍如下。
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揭开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他们将西方的“文学”概念强加于中国,认为中国文学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则提出打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的主张。胡适则引用《毛诗大序》中的名句来说明“文学”的本质:“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学改良刍议》)其实这段文字谈的是诗歌与乐舞,后者并不包括在文学中。
此外,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将中国“文学”的变迁描述成“言志”与“载道”互相消长,此起彼伏的过程。钱钟书为此撰写的书评,质疑将“文学”概念如此移用。
他指出,“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从西方引入“文学”这个概念后,人们开始把所有这些文体都归入“文学”这一概念下,而周作人又把“载道”和“言志”这两种不同文类的不同品质上升为“文学”的普遍性本质,从而做出了两者相互消长的判断。(《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新月》4卷第4号,1932年11月1日)
李春探讨的另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刘半农,他与胡、陈两人以进化论的逻辑来阐述文学变革的理由这一思路不同,明确指出新文学是作为西学之一种的“literature”:
欲定文学之界说,当取法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西文释Language一字曰“Any means of conveying or communicating ideas”。是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功夫也。……至如Literature则界说中既明明规定为“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res”。[6]
刘半农指出新文学运动使用的“文学”概念,乃“取法西文”,其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风格之美”(“beauty of style”),而且包含“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等体裁。至于“文字”与“文学”的差异,他做了进一步阐述:
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6]
综上所述,东西方的“文学”各有理路,但在近代却被混淆在一起,引发种种曲解。
就“汉文学”而言,原本滋生于东方传统的“文学”土壤之中,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为“孔门四科”,以儒学为主的知识体系及写作艺术,这与日本、韩国传统“汉文学”的意蕴大致相合;然而中国近代出现的“汉文学”概念,兼有东西方的“文学”背景,这种差异体现在鲁迅与周作人的言说中。
(二)东亚的“汉文”
“汉文学”概念,既可从“文学”的角度去诠释,也可从“汉文”的视角来考究。如同前述,在古汉语中,“文学”是个多义、宽泛的概念,并没有用作某个学问分野的统称,所以日本、朝鲜文脉中的“汉文学”,应该理解为“汉文之学”,因而有必要廓清“汉文”一词的脉络。
“汉文”一词自古有之,刘勰《文心雕龙·议对》“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是指其人刘恒,即“汉文帝”的省称,此第一义;僧佑《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或善梵义而不了汉音,或明汉文而不晓梵意”,乃汉字、汉语之意,此第二义;胡广等《性理大全书·论文》“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则谓汉代之文章,此第三义。
“汉文”用作“汉文帝”简称的第一义,为东亚各国所普遍接受。日本方面的例子,如《日本后纪》卷三十三,载天长二年(825)十一月三十日皇太子奏言,称天皇“行同尧舜,仁敦汉文”;朝鲜方面的例子,如《高丽史》卷二、世家二、太祖条云:“宰臣廉相王规、朴守文等侍坐,王曰:‘汉文遗诏曰: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前古哲王,秉心如此。”
“汉文”用作“汉字”或“汉语”的第二义,同样为东亚各国所广泛使用。如《高丽史》卷七十七、志三十一、百官二、诸司都监各色:“汉文都监。(恭让王三年改汉语都监爲汉文置敎授官。)”高丽朝廷原来设有“汉语都监”,恭让王(第34代)即位三年(1390)时,改之为“汉文都监”,其职能未有变化,故“汉语”与“汉文”同义甚明。
翻检日本历代史籍中,“汉文”出现频率甚高,而且经常与假名、国字对应使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文字,对此有系统叙述,文虽长,引录之:
日本中古时所著国史,概用汉文,惟诏策祝辞之类,间借汉文,读以土音,以为助语,旁注于句下。自假名作,则汉字、假名大小相问而成文,盖文字者所以代语言之用者也。而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韵,一切语言从此而生。其辞繁,音皆无义,必联属三四音或五六音而后成义。既不同泰西字母,有由音得义之法,又不如中国文字,有同音异义之法。仅此四十七音以统摄一切语言,不得不屡换其辞以避重复,故语多繁长,如称一“我”字,亦有四音,称一“尔”字,亦用三音,他可知矣。其语长而助辞多,日本语言全国皆同,而有上、下等二种之别。市井商贾之言,乐于简易,厌其语之长,每节损其辞以为便,而其语绝无伦理,多有不可晓者,故士大夫斥为鄙俗。凡士大夫文言皆语长,而助辞多,一言一句必有转声,必有辞,一语之助辞有多至十数字者。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如读书则曰书读,作字则曰字作之类。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译人之变易其辞,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
自传汉籍,通人学士喜口引经籍,于是有汉语。又以尊崇佛教,兼习梵语。地近辽疆,并杂辽人语。王、段博士所授远不可考,然其人来自济,或近北音。唐时音博士所授名为汉音,僧徒所习名为吴音,今士夫通汉学者往往操汉音。吴音大概近闽之漳、泉,浙之乍浦,而汉、吴参错,闽、浙纷纭,又复言人人殊,其称五为讹,称十为求,沿汉音而变者也。称一为希多子,二为夫带子,此土音也。市廛细民用方言十之九,用汉语亦十之一。此外称男子为檀那,则用梵语也。称妇人为奥姑,则用辽人语也。其他仿此。日本之语变而愈多,凡汉文中仁义道德、阴阳性命之类,职官法律、典章制度之类,皆日本古言之所无,专用假名,则辞不能达,凡汉文中同义而异文者,日本皆剧一训诂,刮一音读。买字如川、河之类,虚字如永、长之类皆然。故专用假名而不用汉文,则同训同音之字,如以水济水莫能分别矣。用假名贝不得不杂汉文,亦势也。汉文传习既久,有谬传而失其义者,有沿袭而踵其非者,又有通行之字如御、候、度、样之类,创造之字如辆、绘水作旋涡形,以禳大灾,名之目靳。拇地名.昌有北岛、昌田诸姓,读犹圃字。柠申木名,以之供神,故名。之类,于是侏侑参错,遂别成一种和文矣。自创此文体,习而称便,于是更移其法于读书。凡汉文书籍概副以和训,于实字则注和名,于虚字则填和语。而汉文助辞之在发声、在转语者,则强使就我,颠倒其句读以循环诵之。今刊行书籍,其行间假字多者皆训诂语,少者皆助语,其旁注一二三、及上中下、甲乙丙诸字者,如乐之有节,曲之有谱,则倒读、逆读先后之次序也。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
……
外史氏日: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日本之为国独立海中,其语言北至于虾夷,西至于隼人,仅囿于一隅之用。其国本无文字,强借言语不通之国之汉文而用之。凡一切事物之名,如谓虎为於菟,谓鱼为陬隅,变汉读而易以和音,义犹可通也。若文辞烦简、语句顺逆之间,勉强比附以求其合,而既觉苦其不便,至于虚辞助语,乃仓颉造字之所无,此在中国齐、秦、郑、卫之诗,已各就其方言,假借声音以为用,况于日本远隔海外,言语殊异之国。故日本之用汉文,至于虚辞助语而用之之法遂穷,穷则变,变则通。假名之作,借汉字以通和训,亦势之不容已者也。昔者物茂卿辈倡为古学,自愧日本文字之陋,谓必去和训而后能为汉文,必书华言而后能去和训。其于日本颠倒之读,错综之法,鄙夷不屑,谓此副墨之子,洛诵之孙,必不能肖其祖父。又谓句须丁尾,涂附字句以通华言,其祸甚于侏偶驮舌,意欲举一切和训废而弃之,可谓豪杰之士矣。然此为和人之习汉文者言,文章之道,未尝不可,苟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者无几。一国之大,文字之用无穷,即有一二通汉文者,其能进博士以书驴券,召鲰生而谈狗曲乎?虽工亦奚以为哉?
至于“汉文”用作“汉代文章”之第三义,则如同“汉字”之为“汉代文字”、“汉籍”之为“汉代典籍”一样,未被周边国家所接受。
然而,周边国家在受容“汉文”的过程中,却另外衍生出一些古汉语中所没有的新意蕴。在日本语境中衍生的新意蕴,首先指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学问,继指用汉字创作的作品,后特指日本人的汉文作品。
二松学舍大学“日本汉文学研究之世界基地的构筑”基地(COE),构建的“日本汉文文献目录数据库”的分类,可资我们参考。
大分类:日本汉文,和刻本汉籍,准汉籍,一般和书,洋书,论文;
四部分类:和刻本汉籍,准汉籍,汉籍;
日本十进位分类:日本汉文,一般和书。
如上所示,该基地将“汉文”与“汉籍”视为同类型的书籍载体,而且该基地的官方网站发布的主旨中声称:“前近代的日本,汉字汉文的文献构成日本学术文化的主干。因此,日本汉文知识不仅对日本文化研究是必不可缺的,同时也是日本研究的基础。”东亚区域中“汉文”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汉文”指用汉语撰写的文章和著作,这个义项是中国语境中所没有的,而其产生的契机似乎与“训读”密切相关。有关这一点,下面予以详述。
(三)汉文文化圈
“汉文”在古代东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构成东亚汉字文化的重要因素。
日本著名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曾撰《日本汉文学史资料及与此相关的图书学问题》①此文收录于山岸德平《日本漢文学史論考》,[日]岩波书店,1974年版。一文,专节梳理“日本汉文学”的概念。他首先指出:“通观明治、大正时代,汉诗、汉文之语,行于世间而义甚不明。诚然,此‘汉’非指汉代之王朝,而泛指古代之中国。”但这仅限于“文言文作品”,宋元以来科举考试时模式化的应策文、清朝上下通行的公文私牍——这些被称作“时文”的东西,“并不归入汉文之中”。长泽规矩也据此给“汉文”下定义:
如此,汉文的本义为“汉民族创作的文言体中国诗文”,然蒙古人所建之元朝,满洲人所创之清朝……(这些非汉族人)也不乏用文言体吟诗作文者,故定义为“中国人创作的文言体中国诗文”更为妥当。
在长泽规矩也所下的定义中,“汉文”完全等同于“汉文学”,即他打着“日本汉文学”的标题,却给“汉文”下定义——主体从“汉民族”扩大到“中国人”,然后又继续扩展至汉字文化圈内的其他民族:
还有,自古以来,汉字共荣圈内之人,不仅读汉文而且作汉文,他们的作品似也应对纳入其中。于是,此定义可扩充至“汉民族以外的民族,模仿汉民族的文言体中国诗文而创作的诗文”。
按照这个定义,所谓的“日本汉文学”,便成了“日本民族模仿汉民族的文言体中国诗文而创作的诗文”。
长泽规矩也把“日本汉文学”扩定在“诗文”的范围内,与二松学舍大学COE的定义——“本项目所言‘日本汉文学’,乃是以日本人用汉字汉文撰著的文献资料为对象的学问,对象范围不限于汉诗文等文学作品、记录类史学文献,涵盖佛典、佛书、天文历法、医书、本草等所有分野之文献”——相比,对象缩小了很多,显然无形中受到西方之“文学”概念的束缚。
然而,长泽规矩也的贡献也是伟大的,他把“汉文=汉文学”从“汉民族文学”的桎梏里解脱出来,置于东亚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汉字文化圈中加以关照,使我们看到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文化体,在历史迷雾中逐渐显露出骨架。
那么,与“汉族的汉文学”和而不同的“日本的汉文学”,究竟是如何架构起来的呢?二松学舍大学COE早在2001年就注意到“训读”的重要性:
没有固有文字的日本人,通过学习中国的汉字汉文而摄取中国的学术文化。在此基础上,不久发明“训读”这种独特的解读方法,不仅使吸收中国学术文化的对象范围飞跃般地扩大,同时日本人自身用汉字汉文创作了大量的著述。
近年,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出版《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岩波书店,2010年),对长泽规矩也的蓝图施以色彩,对二松学舍大学的构想予以细化,提出令学术界耳目一新的“汉文文化圈”概念。他指出,关于“汉文训读”,世人一直以为系日本人独创,但近年陆续发现朝鲜、维吾尔、契丹等中原周边民族的语言,甚至汉语本身也有“训读”现象;这种现象并非产生于儒教等中国文化内部,而是在汉译佛教的过程中,在外部文化刺激下萌发出来的;在东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借助“训读”而使汉文广为传播,因此以“汉文文化圈”概观东亚文化更为合理。
(四)扩大视域
从“汉族的文学”到“中国的文学”,再到“汉文的文学”——“汉文学”概念的外缘在次第延伸,而我们欣喜地看到,学者研究的对象也在不断拓展。
高文汉、韩梅合著的《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仅涉及到日本与朝韩,即上篇共5节专论日本,下篇4节聚焦朝韩。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即把东亚框定为中国、日本、朝韩,而在研究“汉文学”时习惯上剔除中国,于是就变成日韩与中国的文学关系史。
王晓平2001年出版《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作为“东方文化集成”之一种;200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修订本,该书在比较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多有发明。
作者对“亚洲汉文学”的提法有个说明:“不管这些文学在内容上有多么不同,在全部用汉字书写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需要把它们一并纳入研究视野,并且展开国际合作研究的时候,人们就希望找到一个公认的表述方式。迄今已有东方汉文学、东亚汉文学等说法,我这里采用的是亚洲汉文学。说法不同,所指大体相同。”
“说法不同,所指大体相同”,大概是作者比较谦虚的说法。我倒是认为,该书将视野从传统的“中日韩”三国,扩展至越南乃至历史上的渤海国、琉球国,是否意味着“汉族之文学”曾经波及之地,均可作为“汉文之文学”研究的对象?在这层意义上,冠以“亚洲”要比“东亚”留有更多的余地。
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开拓工作,如裴晓睿的《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认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中国的《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等古典小说传入泰国并激发当地作家的创作想象力,出现一系列译本和仿作,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小说文类的先河。此前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认为泰国的小说史始自19世纪末(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西方小说的介入。
泰国的《三国演义》等的模仿作品,虽然不是用汉文撰写的,但裴晓睿《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介绍,泰国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分别于1966、1985、1989年连续举办“汉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学术讨论,说明“汉文学”的概念在泰国是存在的。
如果把“汉文学”概念的内涵,丰富至中国文学对周边民族文学的影响,那么不仅泰国要纳入研究视野,印度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亦可成为研究对象。
不过我个人并不赞同无节制地扩大研究范畴,毕竟汉文文学的传播及影响,与汉文文本的模仿及创制,应该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五)理论建构
在“汉文学”理论建构方面,王晓平教授用力甚勤。他为《亚洲汉文学》修订版所写的代序《亚洲汉文学是亚洲文化的互读文本》,开宗明义提出:“在古代亚洲地区,不仅汉民族用汉字来书写,有些汉民族以外的民族,也曾经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还用汉字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用汉字作载体的文学,都称为汉文学。”
显然,这里的“汉”既不指王朝年代,也不意味国家民族,而是指书写符号的“汉字”(确切地说是“汉文”)。作者接着说:“域外汉文学虽是中国文学的亲戚,却是生在各方,不相往来,姓着各自的姓,过着各家的日子。”那么作者所说的“亚洲汉文学”,包括哪些国家或区域呢?
作者在修订版推出之前,撰写了《点击汉文学》一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13日)上。文中说:“盘点一下汉文学的家族,今天可以算成四大家:中国一家,日本一家,韩国朝鲜一家,越南一家,从历史上说,还有古琉球国一家,现在是算在了日本一家里了。”该书内容所涵盖的,除了中国、日本、朝韩、越南之外,还涉及到琉球、渤海等。
南京大学的张伯伟教授认为:“域外汉籍研究是本世纪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其价值和意义完全可以和上世纪的新学问──敦煌学作模拟,甚至有以过之。”(张伯伟《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
我很赞同这种说法,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两者在文化传承上具有本质区别,后者的价值和意义远大于前者。那么,这些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王晓平在《点击汉文学》中列出以下几点(序号为引者所加),可供参考:
(1)首先,在邻家汉文学中,保存着中国散佚的文学文献。近年来对各家汉文学中保存的敦煌文学文献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字学、历史学等的材料。来华的使节、留学生、僧侣撰写的汉文撰写的汉文游记、笔记,以别样的眼光,记录了中国历史的细节。其中朝鲜使节撰写的大量《燕行录》已在韩国整理出版,是为研究亚洲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同时,在这些记述的基础上,学士们还创作了很多以赴华使节经历为题材的汉文小说。
(2)其次,在邻国汉文学中,保存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域外传播和接受史的丰富材料。在朝鲜汉文小说中,不少作品以中国为舞台,而在日本汉文小说中则不乏根据中国故事“翻案”(即改写为发生在日本的故事),乃至假托中国人写作的作品,这些都直接或间接部分反映了汉文化在周边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而在其中的千变万化,则折射出彼此的文化差异。
(3)再次,在汉文学中,保存了各国民族语言文学的中国元素的来源资料,欲对各国文学原始察终,辨同析异,则舍此不免见木不见林。日本明治时代成书《谈丛》引依田学海的话说:“不熟汉文,则国文终不能妙也。顾世之学者,往往陷溺所习,是以笔失精神,文竟归死物。”依田学海的看法,很有见地,至于汉文与现代日文的关系,还颇有探讨的余地。各国情况又相距甚远,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有待于探求。
(4)最后,汉文学本身,就是各国的“国文学”。韩国古典文学名著《东文选》序曰:“是则我东方之文,亦非汉唐之文,乃我国之文,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同样,日本汉文学虽然充满了源于中国文化的用典、戏仿(parody)、拼贴、改写、引用以及其他涉及文化各方面内涵的“前知识”,构成互文性参照,然而也正如王三庆《日本汉文小说丛刊序》中所说:“如果追根究底,这些汉文学作品纵使以中国文学为肌肤,脉络中流动的却是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和血液,在文化和文学的传承转化当中,曾经以思想前卫,引领一代风骚的姿态,走向未来。”因而,深化汉文学研究,也就可能催生出对该地区文学、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王晓平先生对域外“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但从建构学科的角度来说,不避“蛇足”之嫌,再唠叨几句以作补充。
(1)首先,需要框定“汉文学”的范畴。如前所述,在日本及韩国语境中,“汉文学”的第一义指中国的哲学与文学,而现今国内学者大多只注目于域外人士的汉文作品,彼我之间可谓南辕北辙。
汉字文化圈(或“汉文文化圈”)本质上是一个视觉世界,因为沉默使互不相同的语言声音被掩盖起来,因而与经由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体系中恢复“听觉”,是大相径庭的。把“汉文学”定格于“视觉世界”,与通过译介展示的“听觉世界”区分开来,即可浑然自成一个体系,划界相对比较容易。
以近代国家为单位划界很不合理,曾是“汉文学圈”相对独立成员、现在已经消失的国家或民族应纳入视野;相反现在归属某个国家、但历史上某个时期未接受汉文学的地区,则应排除在外;南亚、中亚甚至西方人士创作的汉文作品,也当成为研究对象。
(2)其次,需要确定“汉文学”的内涵。虽然在前近代东亚语境中,无论“汉文”还是“文学”,均是人文知识体系的统称,除了诗赋散文之外,还囊括戏曲、小说、儒学、史籍等;但既然要面向未来重构“汉文学”,必须兼顾近代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分类,如果按照二松学舍大学COE的做法,“对象范围不限于汉诗文等文学作品、记录类史学文献,涵盖佛典、佛书、天文历法、医书、本草等所有分野之文献”,那么“汉文学”变成无所不括的大杂烩,不具有排他性就意味着核心意蕴的丧失。
考虑到古代东亚没有萌生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而西方“文学”概念所涵盖的对象,在东亚则散见于各类著述体裁中,例如史籍中的上古神话与民间传说、佛典中的偈颂与传记及譬喻、儒书中的典故与文论,乃至绘画上的题赞、碑刻中的行实等等,均具有“文学”色彩,应当纳入考察范围。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重构“汉文学”,意味着参照近代西方的“文学”概念,对东方传统的知识体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组,要在既不能死守东方的陈规,也不必照搬西方的套路。
(3)最后,需要建立“汉文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文化典籍,传统学者注重在中国历史中的时间传承历史,新近学者开始关注在东亚区域中的空间传播,除了“传承力”、“传播力”之外,我认为探究她的“创新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她能冲破语言的屏障,超越民族的藩篱,在异国他乡催生出万紫千红的奇葩,试想这是多么蔚为壮观的景象!所以说我们把“汉文学”置于“东亚”这个平台,然后必须兼顾两个源头——中国文化辐射的源头与域外文化发露的源头。
我曾经将域外汉文典籍的研究,分为以下三个层次:①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②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③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并指出:
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由衣裳而化为肌肤,再溶为骨骼与血肉,是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历程。因之,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第一层次,或踌躇于第二层次,应该深入至第三层次,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①王勇:《从“汉籍”到域外“汉籍”》,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3期转摘。
这大概就是我们研究“汉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动力与使命之所在。
[1] 鲁歌.对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的若干校勘[J].绍兴师专学报,1984,(1).
[2] 鲁歌.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正名[J].中山大学学报,1985,(3).
[3] 鲁歌.对1981年《鲁迅全集》的若干校勘之二[J].绍兴师专学报,1986,(1).
[4]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上卷[M].叶渭渠,唐月梅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5.
[5] 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3(3).
责任编辑:冯济平
"Sino-Literature" Disseminated to Southeast Asia
WANG Yong
( Research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Culture, Zhejia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
Sino-literature here refers to Chinese literature disseminated abroad.Foreigners study this literature to appreciate Chinese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Study on Sino-literature is carried out at three levels: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foreign culture;innovation brought about by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ircle in East Asia;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inology;Sino-literature
I109
A
1005-7110(2013)05-0058-14
2013-06-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批准号: 11&ZD082)阶段性成果。
王勇(1956-),男,浙江平湖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亚文化及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