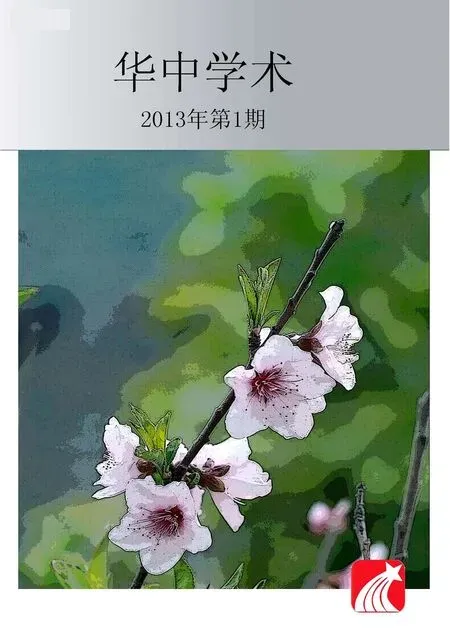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伦理学”不见了:寻找《天演论》的另一半
王松林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我们知道,19世纪科学在西方享有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证主义研究者坚信,世界万物皆是因果关系构成,通过精细的观察、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就能从特殊和多样的事物中归纳出某些普遍的真理。这种思想也深深地植根于19世纪的社会思想之中。社会哲学家和研究者相信,运用与科学研究相同的观察和实证方法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就可以归纳出适用于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譬如,孔德就认为存在着一个实证的世界,世界是一个有序的有机体,受到某些限定的规律的制约,而在这个有机体中最重要的力量乃是理性。在科学的实证主义精神备受推崇的背景下,一本巨著的出版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本著作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OriginofSpecies,1859)。
一
达尔文采用的正是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经过多年的环球考察,收集了动植物和地质方面的大量资料,经过归纳整理和分析,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对物种的可变性和适应性做了解说。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的起源》(TheDescentofMan)一书,从性选择、遗传和环境等方面解释了人类的演化过程。同三百年前哥白尼的著作对思想史的巨大影响一样,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对19世纪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他阐述的思想不仅影响了自然科学,而且也渗透到社会科学中。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就是这一时期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代表人物。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解释自然世界的因果关系的模式。斯宾塞将这一理论概括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推而广之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达尔文思想的曲解。
斯宾塞将达尔文有关生物进化的某些论点如“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life)等加以歪曲和夸大,用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从中演绎出所谓的“种族优劣论”,并借此鼓吹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优越性。他的观点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强权政治提供了依据。此外,斯宾塞还提出一整套所谓的“社会有机论”,认为人类社会也与动物有机体一样有三个系统:营养系统、分配系统和调节系统。与这三个系统对应的是社会的三个阶层——工人阶级、商人和资本家。其中,工人起着“营养功能”的作用;商人起着“分配和交换功能”的作用;资本家发挥“调节生产”的功能。在斯宾塞看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与生物世界运行的规律是一样的。他排斥合作,将集体主义贬低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原始的东西,并声称自己是个人主义的捍卫者。斯宾塞漠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竞争背后的道德责任问题。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将“进化”与“进步”等同起来。
达尔文也相信进化论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例如,他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就借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一说,认为土著文化由于无法与强大的西方文化相抗衡,最终将难逃厄运。这样看来,我们不能把19世纪人们对达尔文的误读或曲解,完全归咎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宾塞。达尔文受到误解或者曲解,跟他自己的观点不太鲜明有关。达尔文本人就曾隐约流露出一定的种族主义倾向。他将一些种族称为“野蛮人”(savages),将他们视作“亚种类人”(subspecies),他甚至认为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道德意义上的最高表现就是白人(高加索人)。达尔文本人曾表达过类似种族主义的看法,他说:“在不远的将来的某个时期……文明的种族将几乎消灭并取代世界上那些野蛮的种族。”[1]
达尔文的这种观点给19世纪后期盛行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有位名叫威斯特雷克(John Westlake)的人在他的《论国际法原则》(1894年)中公然宣称,世界上“未开化”的部分应该被先进的力量消灭[2]。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中的库尔兹曾受“国际禁止野蛮协会”之托撰写过一份关于非洲“野蛮人”的报告,库尔兹在里面“雄辩流畅,振振有词”地说,白人“必定会让他们(野蛮人)看成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我们是带着一种类乎神灵的威力去接近他们的”。报告在最后一页中写道:“消灭所有这些畜生!”[3]这句“动人心魄”的呼喊,堪称当时殖民主义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但是,达尔文从来没有否定过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拥有的道德责任。这里有必要澄清在19世纪两个重要的被人们混淆的概念:“进化”与“进步”。其实,在达尔文之前,进化论的思想就已经存在。不过,人们常把“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进化论将生命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提升、进步的过程。这种“进步”观使得后来人们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人类进化论产生了误解。赞同达尔文主义的人认为,“进化”与“进步”是并行不悖的,人类经过漫长的演变不仅在身体上向上站立了起来,而且在精神上和伦理道德上也摆脱了野蛮,走向进步和完善。这种思想正好迎合了大英帝国因工业进步而生的不可一世的民族自豪感。然而,我们知道,“进化”并不意味着“进步”;进化是变化,变化不一定就是“变好”,并不一定是向着“更高”或“更善”的阶段进步。哈佛大学进化论史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认为达尔文本人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严格区分“进化”和“进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解释了生命体适用环境的变化这一规律,但并未明确指出这一适用性的变化是朝哪个方向发展,即是为了进步还是提高。不过,达尔文似乎也意识到了人们可能将“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的危险。1872年,达尔文给美国古鸟类学家阿尔斐俄斯·海厄特(Alpheus Hyatt)写的一封信中说:“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认,不存在不断向前进步发展的内在趋势。”[4]但是,在达尔文生活的那个工业大跃进的时代,大英帝国弥漫着社会“进步”带来的喜悦与骄傲,“变化”即“变好”、“进化”即“进步”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达尔文的思想一经传播,他就无法左右、更无法澄清他思想中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被人曲解的成分。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人,往往从达尔文那里引经据典,由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盛极一时。
二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养料。许多欧洲人认为征服非洲或其他落后国家是他们的天赋使命,因为通过征服,他们可以给殖民地带来文明和进步。当时英帝国主义的倡导者萨里斯伯里(Lord Salisbury)就将国家分为两种,“存活着的国家”和“消亡中的国家”(living nations and dying nations),“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或是从慈善的角度来考虑——存活着的国家将逐渐蚕食消亡中的国家……但不要以为任何存活着的国家都有机会从治疗或消灭这些不幸的病人的垄断中获利……我们可不能让英国在任何重新瓜分中失利”[5]。由此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甚嚣尘上。
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达尔文主义的肆意曲解,特别是针对其漠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一位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此人便是赫胥黎。
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驳,反映在他1893年在牛津大学做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中[6]。赫胥黎反对将生物界的进化规律用于解释人类伦理的进化规律,他甚至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且根本对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靠“适者生存”的方法人类在伦理上可以趋于完善,宣称在人类进程中用“自然选择”的方式淘汰弱者是符合伦理道德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赫胥黎对这种无视伦理道德的残酷竞争予以痛斥。他甄别了“适者”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含义。在他看来,对自然界而言,“适者”指的是生物对气候和环境的适应;而对人类社会而言,“适者”即是最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高尚的人。他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不是像自然界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相反,社会文明的进步恰恰是通过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对宇宙过程进行抑制与战胜。赫胥黎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处于蒙昧、低级状态时,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确实会很大,但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特别是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缺乏伦理的“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life)将受到道德力量的有力遏制,在社会的发展中失去重要作用。
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胥黎把整个自然界称为“大宇宙”,人类社会称为“小宇宙”,两者的对立统一,成为其伦理观的基础。赫胥黎认为,“大宇宙”的生物的进化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但是“小宇宙”的人类活动是一个改造自然的过程,它是一种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人为状态,也即是他所谓的“园艺过程”。赫胥黎将处于自然状态的“大宇宙”与处于“人为状态”的园地(garden)“小宇宙”作了一番对比,指出了它们的本质区别:
不仅自然状态与园地的人为状态相对立,而且园艺过程的原理,即建立和维护园地的原理,也与宇宙过程的原理相对立。宇宙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剧烈的、永不停息的生存斗争;园艺过程的典型特征是通过铲除产生竞争的条件来消灭生存斗争。宇宙过程倾向于对植物生命形态的调整,使之适用眼下的生存条件。园艺过程则倾向于对生存条件进行调整,使之能够满足园丁期望培育的植物生命种类的生长需要。[7]
赫胥黎通俗地将人类活动比作在荒野中开垦、经营的“园地”,在“园地”生长的不再是“通过生存斗争进行选择的产物,而是根据有效用或美观的理想标准直接选择的产物”[8]。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适者不再是处于“最最顶端的最适合者,而是大量的适度的合适者”[9]。因此,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相比,“园地”里斗争的残酷性减弱了。在赫胥黎看来,要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不是靠人们逐渐去适应周围的环境,而是创造适应人类生存的人为环境;不是允许生存斗争自由进行,而是排除这种斗争;不是通过生存斗争去实现选择,而是按照行政长官的理想标准进行选择”[10]。显然,赫胥黎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对社会进步的调节、制约和促进作用,他提出要用伦理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伦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维持和不断改进一个有组织社会的人为状态,不断地排除残酷的无视伦理道德的生存斗争,以此与自然状态相对抗。人在这种可调节的社会中并通过这种社会发展培育出一种有价值的符合伦理规范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使人类社会维持和不断改进其自身的道德素养。这便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精髓,也是赫胥黎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发点。
三
严复留英期间就研读了大量对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文著作,尤醉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说。甲午海战之后,严复的“科举梦”破灭,他不禁为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担忧,出身海军的严复投书天津《直报》,连续发表四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在《原强》中,严复开篇就说:
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蓑,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11]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此后一百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物竞天择。严复发表的系列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阐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原则,鼓吹西学。
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以西学来唤醒民众,从1896年起到1908年,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严译《原富》)、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严译《名学》)和《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译《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译《法意》)等。这些译著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然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在严复的笔下成了《天演论》,也就是说,他只选择性地翻译了书中的部分内容,故意漏译了书中最重要的有关伦理学的论述。如前所述,赫胥黎在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旨在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后半部分 ——“伦理学”所讲述的,就是要表明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读者大都是通过严复对此书的翻译才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而《天演论》中介绍的进化论实质上是赫胥黎所批判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夸大和歪曲。严复的翻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创作”或曰“创造”,《天演论》名为翻译,实为著述。达尔文在中国被误读由此开始。
严复翻译《天演论》完全依据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现状之需以及个人的政治见解予以取舍,但凡原文与自己观点不同之处,均在译文中加以反驳或评注或干脆进行改写,目的在于以警醒当局,激励国民自强。因故,《天演论》一出,深得当时有识之士的青睐。康有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在《天演论》尚未出版时就借抄阅读,当即著文宣扬,认为“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梁启超在总结自己对达尔文的认识时这样说:“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贻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对《天演论》中宣扬的进化论大加赞赏:“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12]《天演论》影响到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仁人志士[13]。
学界多有误解,以为严复偏爱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排斥赫胥黎的伦理学主张,实则不然[14]。严复在《天演论》中认真地比较了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异同,从中可知严复确实赞赏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之“群学”思想(他因此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但是,他对赫胥黎的“善群”论(即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提出的“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或“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也推崇备至,认为赫氏著作倡导“人治”之精义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只不过,虽然意识到了赫胥黎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矫正意图,但是在甲午海战后的中国语境下,严复旨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危言警醒萎靡之中国,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是他侧重介绍书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淡化或故意“漏译”赫胥黎的伦理学思想的重要原因。正如严复本人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所言:“此书旨在自强保种。”显然,从译介学的角度来说,《天演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意义。
四
如前所述,达尔文本人其实没有将宇宙的自然法则与社会的伦理法则等同起来。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另一位探险家兼进化论学者(也是达尔文的好友)华莱士那里得到佐证。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对达尔文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华莱士在美洲亚马孙流域和马来群岛的探险和科学考察过程中,形成了与达尔文相同的进化论思想。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论文寄给达尔文,达尔文此前早就在酝酿进化论,华莱士的论文促使了《物种起源》的出版。华莱士还写过《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理论之说》(Darwinism,AnExpositionoftheTheory ofNaturalSelection,1889),表达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质疑。
华莱士坚信人的进化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的《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理论之说》一书中,他反对将达尔文的主张机械地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他特别指出人的艺术美感“不可能是在自然选择的法则下形成的”[15]。他强烈质疑“人的全部本质和所有能力,不管是道德的、智力的还是精神的,都如他的身体结构那般按照同样的法则和行为方式从低级动物的初级形态中获得”[16]。反对将自然进化论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当然不只是赫胥黎和华莱士,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当时一位哲学家凯尔德(E.Caird)的赞同,凯尔德在他给伦理学家格林(T.G.Green)的《伦理学导论》写的“序言”中说:“如果人,如同我们经验知识中的其他客体一样,仅仅是客观世界中的一个部分,按照固定的规则,作用与反作用于对方,那么,又何以证明他的道德自由呢?或者,又何以证明令他与别的动物区别开来的更高的使命呢?”[17]
英国小说家康拉德就曾深受华莱士的影响。康拉德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适者生存”的思想的讽刺,在他的短篇小说《福克》(Falk)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小说中的那位强壮的、相貌像原始人的主人公福克一次被人遗弃在一条搁浅的船上,船上的水手中只有两个人手中拥有武器,他是其中之一。这时,除了其他水手之外,已别无他物可以充饥了。两人吃完最后的一点食物后,为了生存开始了搏斗。强壮的福克赢了,他开始吃人肉。福克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可见康拉德对无视人类道德的残酷生存竞争的批评[18]。此外,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思想,也见诸康拉德早期小说的字里行间。譬如,在《奥迈耶的痴梦》中,尼娜(Nina)和戴恩(Dain)在相互信誓旦旦时的背景描写就颇具象征色彩,森林中植物的长势被形容为:“疯狂地往上爬,在可怕的宁静中残忍地相互纠缠,绝望地挣扎着,伸向上方给予生命的阳光。”[19]“生存斗争”的思想在此可见一斑。小说中的奥迈耶是个有强烈种族优越感的白人,同时又是个极为自私、道德堕落的人。作者在小说中刻意安排了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结局:奥迈耶最终落魄孤寂,沉湎于抽鸦片,他被他的宠物猴子领着到处转悠——奥迈耶的种族优越感在此彻底崩溃。康拉德在这里采用了戏剧反讽的手法,暗中影射了那些自以为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文明的进程中,欧洲人的道德没有进化而是“退化”——这就像奥迈耶,他从猴子的主人沦为猴子的仆人。
从赫胥黎、华莱士、凯尔德和康拉德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的“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有高度的警觉,并表现出或抵御或嘲讽的姿态。可惜,由于身处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的国人对此并未有足够的重视。
从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到今天,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历尽沉浮,现代语境下再读《天演论》,我们会发现,严复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另一半“伦理学”给“译掉了”。殊不知,这出于一时之需的“漏译”或“误译”所潜伏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危险,自《天演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之日起就埋下了隐患。一直以来,缺乏伦理关怀的无情斗争或是向大自然的残酷索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乃至心理层面上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状况延续至今,有越演越烈之势。今天看来,严复当年在《天演论》中“译掉”的伦理学亟待寻找回来——不仅仅是在书面上,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注释:
[1]参见 Knowles,Owen & Gene Moore,Eds.OxfordReader'sCompaniontoConrad,(Paperback)Oxford:OUP,2001,p.84.
[2]参见 Knowles,Owen & Gene Moore,Eds.OxfordReader'sCompaniontoConrad,(Paperback)Oxford:OUP,2001,p.84.
[3][英]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55—556页。
[4][美]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丁进锋、徐桂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4—65页。
[5]转引自 Cedric,Watts,APrefacetoConra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87.
[6]“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1893年5月18日在牛津大学Sheldonian Theater为罗马尼斯讲座(The Romanes Lectures)做的演讲,当年这一小册子就已经出版。1894年再版时改名为Evolutionand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篇幅也增加了许多,全书由五部分组成:一、进化论与伦理学:序言;二、进化论与伦理学;三、科学与道德;四、资本与劳动之母;五、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法。但严复只选择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来译介,且在翻译中根据本人政治观点肆意改译或评点。《天演论》与赫胥黎的原著相距甚远,因而不应该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译本。有关评论可参见翁美琪:《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否定 ——读〈进化论与伦理学〉》,《读书》1983年第6期,总第51期;纪坡民:《“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 ——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到严复的〈天演论〉》,人民网,理论版,百家争鸣,2005年1月10日。
[7][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宋启林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8][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宋启林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9]参见翁美琪:《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否定——读〈进化论与伦理学〉》,《读书》1983年第6期,总第51期。
[10][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宋启林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1]转引自钟岩苑:《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被误读一百年之一》,《南都周刊》2009年8月17日。
[12]以上康有为、梁启超和陈独秀所言皆转引自钟岩苑:《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被误读一百年之一》,《南都周刊》2009年8月17日。
[13]关于胡适对《天演论》的推崇,参见《四十自述 在上海(一)》,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关于鲁迅之受《天演论》影响,参见《朝花夕拾琐记》,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5—296页;关于《天演论》之于梁启超的影响,参见《梁启超致严复书》,收入王栻编:《严复集》第五册,第1570页。
[14]典型的代表是史华兹和李泽厚。参见欧阳哲生:《〈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读一:中国近代史上的〈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宋启林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15]A.R.Wllace,Darwinism,AnExpositionoftheTheoryofNationalSelection,London:Macmillan,1889,p.469.Quoted from Allen Hunter,JosephConradandtheEthicsof Darwinism,Beckenham:Croom Helm,1983p.12.
[16]A.R.Wllace,p.461.Quoted from Allen Hunter,pp.12~13.
[17]T.G.Green,ProlegomenatoEthics,1883;Oxford:OUP,1924,p.v.Caird's comments are signed and dated 1906.Quoted from Allen Hunter,JosephConradandtheEthicsof Darwinism,Beckenham:Croom Helm,1983,pp.11~12.
[18]哲学家罗素在论述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压力时曾引述了康拉德的这篇小说作为例证,指出现代社会人们将“生存斗争”引入生活,将成功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这是人的悲剧。参见罗素:《罗素道德哲学》,李国山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216—222页。
[19]Joseph Conrad,NotestoAlmayer'sFolly,Cambridge:CUP,1994,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