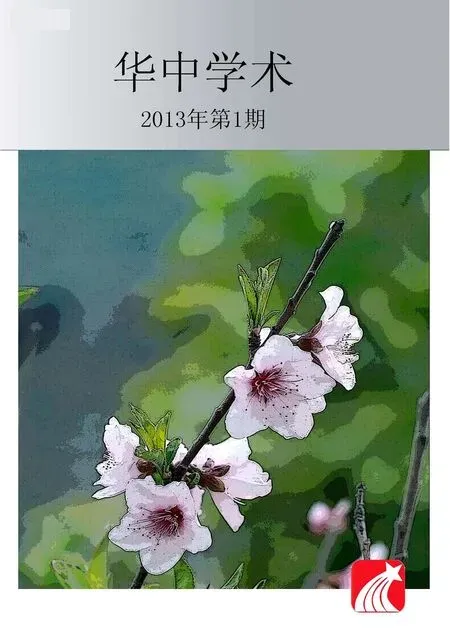科技、伦理与美的政治:霍桑《胎记》的伦理批评
毛凌滢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41)
霍桑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胎记》最初发表在1843年的《先驱者》上,后来收入《古屋青苔》短篇小说集,被认为是霍桑在“古屋时期最好的短篇之一”[1]。在当今美国一些大学的艺术与伦理课程中,该小说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库切的《耻》是必读的名篇和讨论的重点。从前的国外学者对于该小说的评论比较丰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胎记》代表人类的缺陷,包括原罪,暗示女性容易犯罪、悲伤、凋谢和死亡[2];有人认为故事暗示人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达到完美;还有人认为霍桑是在批评他那个时代所谓的改革,他认为改革是无效的,也是危险的[3]。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胎记》讲述的是一个失败而不是成功的故事,告诉人们怎样谋杀自己的妻子并成功脱身[4]。当然,也有评论者将这个故事解读为对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的批判,女性在这里被作为自然的象征,科学对女性/自然奥秘的入侵,导致了对自然界的极大破坏。也有评论强调其道德主题,主要聚焦在始终困扰人物的原罪问题[5];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讨论妇女是如何陷入男性思维的陷阱,最后沦为试验对象而被物化的[6]。中国国内关于短篇小说的评论,有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作品中的男权主义话语暴力和女性身体的反抗等[7],还有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讨论其中的环境伦理问题的[8]。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探讨该小说中所体现的两性间的爱情伦理与美的政治,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与道德伦理问题。
一、文学、审美与伦理批评
尽管康德认为审美无功利,法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也在其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并在1834年5月为其小说《模斑小姐》写的一篇长序中声称:“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那是某种实际需要的表现,而人的实际需要,正如人的可怜的畸形的天性一样,是卑污的、可厌的。”[9]深受其影响的英国作家王尔德,也积极提倡并实践“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认为艺术与社会道德无关。但是,文学作为人学,作为现实的第一世界在虚拟的第二世界的投射,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形式和文字之美,而不涉及二者所承载的文化,和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诸种道德、伦理与社会关系。古今中外,文学所承载的功能之一就是“寓教于乐”,无论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净化”、“升华”,还是中国“经夫妇,成孝敬,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学的教化作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作为作家个人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作品隐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并且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烙印。正因为如此,希瓦茨说“人的行为是文学文本的核心,它应该成为分析的重点。尽管人物塑造的模式不同,但人物的心理和道德必须被理解为现实人物的暗喻,因为理解别人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10]。他强调“新千年伊始,我们有必要承认英美人文主义传统的重要作用——从马修·阿洛德、亨利·詹姆斯到希利斯·米勒和雷蒙德·威廉斯,他们在英国和美国的写作和英文系的教学中仍然在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目前新批评、亚里斯多德学派、《党派评论》团体、语境主义论者和文学史家都认为:作家写作是为了表达其思想和感情;人们生存的方式和价值观对作者和读者都至关重要,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的洞察和人类处境的反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教授和思考文学的原因”[11]。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评论家伊哈布·哈桑认为,这个时代是该到了“文学教授们重视人类情感判断的时代了”[12]。苏瓦次更直接地指出“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表征就是伦理关系的表征”[13],而“文本要求读者做出伦理反映,是因为伦理就是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它从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片刻的缺席”[14]。作为亚里斯多德分子的布斯,认为“伦理”、“修辞”和“政治”密切相关。他指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伦理批评存在的前提。”“伦理批评描述的是故事的讲述者和读者或者听众之间的道义”[15],并且强调伦理批评作为一种理解文学叙事所折射的人类伦理和美学状况的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他在《为什么伦理批评从来都不简单》一文中,直截了当地对那些认为伦理批评与真正的文学和美学无关,以及伦理判断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判断两种思潮进行了批驳。在他看来,伦理批评跟所有的文学相关,不管是广义的文学还是狭义的文学。的确,它不像天气预报那样准确判断纽约明日是否下雨或者克林顿是否撒谎,但是当有责任感的读者对那些强有力的故事的伦理价值进行追问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产生被称为知识的东西。布斯强调:“如果说‘美德’含有一切真正的力量,如果一个人的气质是他诸种美德的集中体现,那么伦理批评对于揭示小说伦理跟个人和社会伦理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故事的情感是如何影响读者或者被读者以及伦理所影响的十分有用。”布斯在此相信伦理批评是必要的,不仅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那些竭力推动抽象的形式批评的批评家,最终心里也装着伦理问题,也认为好的阅读方式是那些能给我们带来益处的阅读方式,真正的文学是那些能给我们带来益处的文学”[16]。聂珍钊和邹建军两位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必须同文学的阅读和理解结合在一起,其次它又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等伦理价值”[17]。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它从人类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而来,其动力来自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短篇小说《胎记》就最好地诠释了美与道德伦理的问题,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纯粹形式和技术的问题,更是关乎人的道德伦理甚至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也必须以人为本,坚守伦理道德的底线。
二、《胎记》的爱情伦理与美的政治
在自然界,往往是雄性打扮以吸引雌性,但在人类社会,似乎自古以来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女性总是千方百计地打扮自己以获得男性的关注、青睐和爱情,美丽成为女性自豪的资本和追求的目标。从古代的各种化妆品的使用到现代的生物美容、整形技术,名目繁多,尤其在今天的视觉文化和眼球经济时代,对“看”的需求,无处不在的男性眼光对女性的“凝视”远远超过了霍桑的时代。女性总是不断地对自己不完美的形体或者面容,通过医学技术加以改变,大到削骨、隆胸、抽脂等轮廓的改变,小到拉皮、抗皱等细微局部面容的改变,十分常见。而女性在利用科学技术和生物技术美化自己、塑造更完美的自我,以满足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审美需求的过程中,不仅付出健康的代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当这种美的政治与两性情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当女性的这种以牺牲健康和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对身体的改造,无论是出于自愿迎合男性的目光还是出于屈从男性的逼迫,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是关涉爱情婚姻中的道德伦理甚至法律问题。像《胎记》中的阿尔默那样,以剥夺女性生命为代价的对容貌完美的追求,无异于谋财害命,也深刻地反映出在爱的名誉下掩饰的道德伦理的缺失及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胎记》中的女主人公乔治安娜的丈夫是“在各门自然科学中都享有盛名的科学家”阿尔默,阿尔默之所以娶她,主要是因为她漂亮。但美中不足的是,乔治安娜“左边脸颊上生着一块特殊的印记,与面部肌肉组织深深地长在一起”[18]。“当她脸色娇嫩、健康红润时,这印记便显得深红……她突然脸红时,这印记会渐渐变得模糊,最后消失……但是,只要情绪变化,面色苍白,那印记就会再现,犹如白雪之中一点红。”在丈夫阿尔默先生看来,大自然把他的妻子造得几乎尽善尽美,但妻子脸上的这一点点瑕疵,却令他震惊,并且认为它就是“人间遗憾的明显标记”。以致他愈来愈难以容忍,“他阴暗的想象力不久就将这块胎记视为不祥之物。它所造成的烦恼与恐惧,超过乔治安娜善良心灵与美丽容貌带来的欢乐”。晨光曦微,他睁眼看妻子的时候,“一下就认出那缺陷的标记”;夜晚炉火旁,夫妻相守,“他的目光会偷偷溜到她脸上,在木柴摇曳的火光中发现那鬼似的手形忽隐忽现”,于是这胎记在他眼里成为了妻子难逃罪孽、悲伤、腐朽与死亡的象征。为了彻底消除自己心头上的阴影,追求完美无缺的妻子的形象,他试图依靠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除去妻子脸上的胎记。结果手术失败,成为直接害死妻子的凶手。这一故事表明阿尔默在两性或者说爱情婚姻关系中的自私与浅薄,他对女性外在容貌之美的重视胜过女性内在的心灵之美,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念和对完美的追求,不惜冒险牺牲妻子的生命。其次,丈夫利用妻子的顺从和对自己的爱,是对对方爱情的亵渎,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表面上看,他是力图重塑妻子的完美,是对完美的极致追求,但实际上,这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欲念,并不代表妻子的真实意愿。因此,与妻子容貌的小小瑕疵相比,阿尔默的内心和道德却存在极大的缺陷,妻子的不完美是在脸上,但丈夫的人格缺陷是在内心,其带来的后果更加可怕。两性之爱更多的应该是包容,不仅需要接受对方完美的部分,也应当包容对方不那么完美的部分。难怪有人说:“霍桑还在小说中表现了男性对于女性的错误观点,正是他的行为导致了妻子的死亡”,大多数学者认为霍桑在此小说中主要是对男性而非女性进行控诉和谴责[19]。
悲剧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阿尔默对科学的热爱胜过了对妻子的爱,因为他“对年轻娇妻的爱,只有与他对科学的爱互相交织,并让科学的力量与他自己的力量相结合,才会如此强烈”,但是,根植于男性意识深处的男权文化对女性外表的重视与凝视,以及两性权力的不平等,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这证实了易思彤所言“男性往往试图通过改变女性身体,使其发生巨大变化来实现自己男性意义上的完美,并获得绝对的权力”[20]。在《胎记》中,乔治安娜的外表特征是书写的重点,但贯穿整个故事的是对丈夫智慧的描写,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性别角色特征:丈夫是家庭的决策者,妻子是无条件的服从者。乔治安娜同意成为丈夫的试验品,一半出于对丈夫的爱,一半是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对她而言,她从未觉得自己的容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并认为胎记是魅力迷人的标志,并且在乔治安娜的倾慕者们看来,这块胎记是她出生之时,仙女把玉手按在她的脸上留下的记号,正是这记号赋予了她令人倾倒的魅力。许多对她爱得发狂的青年,甚至愿冒生命危险,一吻这神秘的手印。但是,阿尔默先生坚持要摘除这个胎记,乔治安娜虽然倍感委屈,但在丈夫的“凝视下瑟瑟颤栗”。“他只要露出这种常挂在脸上的奇怪的表情看她一眼,她红润的脸蛋立刻就变得死一般苍白。那只绯红的小手就会明显地喷薄而出,恰似洁白大理石上的一颗红宝石浮雕。”而在其他男性观察者们那里,“若这块胎记不曾增添他们的艳羡,也但愿它能消失,好让这世界拥有一个完美的合乎理想的活标本”。虽然“阿尔默婚前极少或根本没想过这件事,但婚后发现自己的心愿正是如此”。尽管不那么情愿,但为了实现丈夫的心愿,乔治安娜让步了。她说:“也就是为了你,亲爱的阿尔默,否则我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意去掉这块胎记。”妥协之后的乔治安娜,最终表示可以喝下丈夫给予她的任何药水,哪怕是毒药,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成全丈夫对完美的追求。妻子的无私、善良和信任,与丈夫的自私和虚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是有着众多科学实验的失败记录和人格缺陷的阿尔默想去完美别人,不仅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寓言。正如霍桑在小说中所说,人的完美的确很难寻求,不顾伦理道德的对绝对完美的片面地、固执地追求,最终导致的是失败与毁灭。乔治安娜的美和瑕疵,正是她有别于他人的独特地方。同样,自然界正是充满了不完美和瑕疵,才显出了它的独特。
三、《胎记》的科技理性与道德伦理
起源于古希腊强调理性、拒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哲学思想,在欧洲启蒙时代达到了高峰。兴起于17世纪的英国并在18世纪的法国达到高潮的启蒙运动,在欧洲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并逐渐影响了美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它崇尚科学与理性,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强调凡事要以人的思维去判断,而不依赖天意或神的旨意,在对教会进行批判的同时,要求人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来改造社会,强调与自发的情感、主观的感受相对立的人的明智判断、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的能力,认为理性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启蒙运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不受束缚地使用理性,也常常等于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中心,文学与艺术的复兴相比,启蒙运动对理性和科学的过度强调难免造成了偏差,造成理性与感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的对抗与冲突。
霍桑在他的大多数小说中,对这种理性与感性、工具与人文的对立都有表述,比如《红字》中相信知识力量的齐林沃斯,幻想他知识的天赋可以掩饰肉体的缺陷从而获得少女的爱情,并且就像在书本中找到真理和通过炼金术找到黄金一样,运用其智慧找到了与海丝特通奸的牧师,并将对方逼向绝路,但他却没有因此获得快乐。但是,最能反映霍桑对于科学的质疑的作品,应数《胎记》。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当时人们对科学的痴迷:“那些年,电和其他大自然的奥秘刚被发现,仿佛打开了通往奇异世界的条条途径,人们热爱科学,那份神情与专注甚至胜过了对女人的爱。超群的智力,想象力,精神,甚至心灵,都能从各种科学探索中找到相宜的养料。这些探索,正如一些热诚献身者相信的那样,将把强有力的智慧步步向前推进,直到科学家找到创造力的秘密,并为自己开拓一片新天地。”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阿尔默也“毫无保留地致力于科学研究”。启蒙运动使封建神学式微,人对于自己有了巨大的自信,认为可以不依赖上帝,人也可以通过科学来认识世界,从而揭开宇宙的奥秘。终日痴迷于科学试验,认为科学可以创造一切的阿尔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其结果是:“阿尔默把科学当作他的宗教信仰,并且神化了科学的作用。”[21]
阿尔默对妻子的爱,是与科学的狂热和执着交织在一起的,这表明他并没有将妻子放在与自己同等的人的地位,而是将本该作为主体的人的妻子,与作为客体的认识对象的自然界或者科学并列在一起,无疑是将她等同于客体,等同于受试对象。试图通过去除妻子身上胎记的实验,证明科学具有改变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魔力,但是,妻子脸上胎记消失的同时,生命之花也随之凋谢。
对科学的过度迷恋和自信,使他失去了人性与理性。正如同人和自然都不完美一样,科学也不是万能与完美的,任何实验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事实上,乔治安娜也看到了丈夫笔记中的失败记录,阿尔默本人对成功也并无十分的把握,但是,他过度的执着害死了自己的妻子。
霍桑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科学与伦理的问题。诚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摆脱了盲从和愚昧,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相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认识未知的世界,并能运用科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的确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状况。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科学至上的唯科学主义,不但不能彻底根除人类社会的问题,使社会和自然变得更美,反而会因为对它的过度迷信给人类社会带来伤害,甚至灾难性的破坏。因为人类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智力和理性的问题,它还涉及复杂的人的情感、道德伦理等人文层面的东西。科学技术本身无善恶,但是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人,却必须具有道德善恶观和人文关怀。否则,对科技的滥用不但实现不了人类的理想,征服不了自然,反而会贻害社会,将社会和人伦道德引入混乱。科学是把双刃剑,带来的利益有多大,破坏就有多大。同时,科学对自然的征服,也常常以自然的报复为代价。
正如与霍桑同时代的作家赫曼·麦尔维尔所言:“这篇小说中的道德主题表现得尽善尽美。”[22]《胎记》虽然写于19世纪中期,说的是18世纪晚期的故事,却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即便今天读来,仍然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它仿佛就是一个现代的寓言,喻示了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人们所面临的美与伦理、爱情与伦理、科技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与18、19世纪相比,今天的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远远超过了霍桑生活的时代。但是,人们所面临的科技与伦理、科技与人文的冲突和难题,并没有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减少,相反,它们带来的冲突与危机在日益加重。当今的核扩散、生态危机、资源环境问题,已使现代人日渐陷入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之中。如果从事基因工程的生物学家完全不考虑伦理道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亦将混乱不堪。同时,对自我身体的人为的技术改造,如同不顾自然规律破坏自然一样,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对美的需求必须跟内在的心灵和道德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则,再美的形式也是空洞的。在视觉文化和注重“看”的眼球经济时代,在人们的欲望被外在的东西不断刺激膨胀并对道德形成挑战的时代,这一故事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注释:
[1]Elliott,Emory,Columbia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423.
[2]Youra,Steven,“‘The Fatal Hand’:A Sign of Confusion in Hawthorne's‘The Birth-Mark’”,AmericanTranscendentalQuarterly60,1986,pp.43~51.Rpt.inShortStory Criticism,Eds.Rachelle Mucha and Thomas J.,Schoenberg.Vol.89.Detroit:Gale,2006.
[3]Yellin,Jean Fagan,“Hawthorne and the Slavery Question”,AHistoricalGuideto NathanielHawthorne,Eds.Larry J.,Reynol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48.
[4]Fetterley,Judith,“Women Beware Science:‘The Birth-mark’”,Eds.Frank,Albert J.von.,CriticalEssaysonHawthorn'sShortStories,Boston:G.K.Hall & Co.,1991,pp.164~173.
[5]Elliott,Emory,Columbia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423.
[6]Meyer,Michael,TheBedfordIntroductiontoLiterature,Boston:St.Martin's,2002,p.376.
[7]陈榕:《驯顺的灵魂和叛逆的神态:对霍桑短篇小说〈胎记〉的女性主义解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8]朱丽田:《霍桑的环境伦理观生态批评视阈中的短篇小说〈胎记〉》,《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9]Gautier,Théophile,MademoiselledeMaupin,Trans.Helen Constantine.London:Penguin,2005.
[10]Daniel R.,Schwarz,“AHumanisticEthicsofReading”inMappingtheEthicalTurn,Eds.Todd F.Davis and Kenneth Womack,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1,p.4.
[11]Daniel R.,Schwarz,“AHumanisticEthicsofReading”inMappingtheEthicalTurn,Eds.Todd F.Davis and Kenneth Womack,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1,p.4.
[12]Hassan,Ihab Habib,RadicalInnocence:Studie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 Nov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13]Daniel R.,Schwarz,“AHumanisticEthicsofReading”inMappingtheEthical Turn,Eds.Todd F.Davis and Kenneth Womack,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1,p.3.
[14]Daniel R.,Schwarz,“AHumanisticEthicsofReading”inMappingtheEthicalTurn,Eds.Todd F.Davis and Kenneth Womack,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1,p.5.
[15]Booth,Wayne C.,TheCompanyWeKeep:AnEthicsofFi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8.
[16]Booth,Wayne C.,“WhyEthicalCriticismcanNeverbeSimple”inMappingthe EthicalTurn,Eds.Todd F.Davis and Kenneth Womack,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1,p.9.
[17]聂珍钊、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8]Hawthorne,Nathaniel,“TheBirthmark”inTheCompleteShortStoriesofNathaniel Hawthorne,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Company,1959,pp.227~237.
[19]Heilman,Robert B.,“Hawthorne's ‘The Birthmark’:Science as Religion”,Eds.James,McIntosh,NathanielHawthorne'sTales,New York:Norton & Company,1987,pp.421~427.
[20]Easton,Alison,“Hawthorne and the Question of Women”,TheCambridgeCompanion toNathanielHawthor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86.
[21]Millington,Richard H.,“The Meanings of Hawthorne's Women”,TheMeaningsof Hawthorne'sWomen,Hawthorne in Salem.http://www.hawthorneinsalem.org/Literature/Melville/LiteraryLinks/MMD1210.html.Retrieved 2/26/2012.
[22]Wagenknecht,Edward,NathanielHawthrone:TheMan,HisTales,andRomances,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1989,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