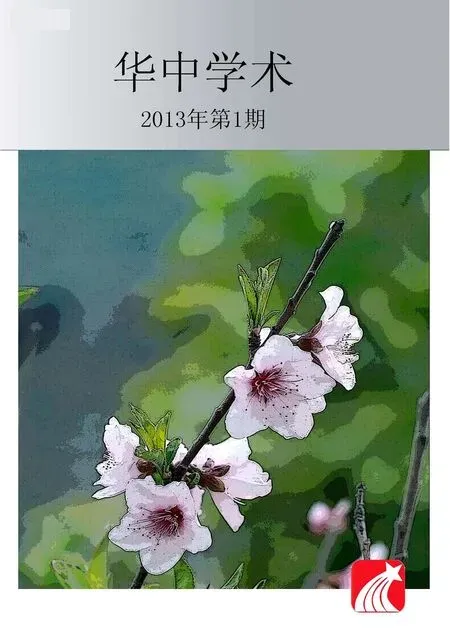知音传说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形态
王 源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知音传说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形态
王 源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汉阳江畔,琴声悠悠,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千古流传。2006年,这一独具魅力的民间传说被正式列入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知音传说是荆风楚韵的一种诗意表达,近年来,虽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关于传说本身的研究却稍显薄弱。本文立足前人研究的成果,结合新的研究材料,对知音传说的历史源流进行梳理,呈现它在不同阶段流变过程中的文化形态,勾勒出一条大致清晰的传承和发展的线路。
知音传说 知音 流变
汉水之畔,涛涛江水滚滚东逝,江城之上,悠悠琴声袅袅回荡。两千多年来,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巧遇知音的故事,在荆楚大地上广为流传,妇孺皆知。2006年,知音传说以其深厚的意蕴与独特的价值入选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受到人们的关注。从先秦典籍到明朝话本再到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音传说经过了长期的流传和演变,无论内容和形式在不同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
一、本事起源:先秦以来典籍中的知音传说
源远流长的知音传说,其本事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吕氏春秋》和《列子》,《说苑》、《风俗通义》、《韩诗外传》等书中也均有知音故事的完整记载。此外,《荀子》、《淮南子》、《新序》、《世说新语》等先秦以来的众多典籍也纷纷援引此事。
《吕氏春秋·本味》和《列子·汤问》一直是学者们较为认可的关于知音传说的最早记载。但是孰先孰后,大都较倾向于《吕氏春秋》早于《列子》。杨伯峻在《列子集释》中认为:“而吕氏春秋本味篇则大同于列子,列子袭本味文也。”[1]《吕氏春秋》为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而成,相比通常被认为是魏晋时代伪书的《列子》,其在文献上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后者。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第二本味)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如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列子卷第五汤问)
从文本上,《吕》和《列》都生动地描绘了“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二者因琴互通心灵情感的情景,但相较之下,《列》更加注重对二人由音乐相知相惜“知音”境界的艺术渲染,《吕》行文不似《列》生动,却更加偏重故事本身情节的完整性,最后交代了“钟子期死”,而伯牙“断琴绝弦”的结局。虽然这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知音故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吕》本中已经具备了后世故事发展流变中始终未曾改变的两个基本情节母题,即高山流水遇知音和破琴绝弦谢子期。因而,《吕氏春秋》应为知音传说的最古老和本真的形态,《风俗通义》、《韩诗外传》、《说苑》的叙述均与其差别不大。
此外,《吕氏春秋》与《风俗通义》二书的内容来源对于研究知音传说也有一定的启示。《吕》为吕氏门客所作,汇集了很多先秦时期的古史旧闻,而《风》亦为应劭“辨风正俗”之作,搜罗了很多汉代风俗,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音传说并非为文人杜撰而成,更可能来源于人们的口头传闻。
《吕氏春秋·精通》中还记载了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的故事,钟子期夜闻击磬声,心感悲凉,叫人唤来击磬者询问,才知其父死母离的坎坷境遇。这充分表明钟子期是一个善听、辨音的人,他能从别人的击磬声中听出悲伤之情,对音乐、对琴理有着独到的见解。而《荀子·劝学》载“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伯牙的琴技高超,不仅让马侧耳忘食,更让人怅然感动。《乐府解题》和《琴操》中也记载了一段“伯牙学琴”的故事,伯牙学琴,三年不成,其师成连先生将其送到蓬莱仙岛,让他在花草虫鸣的大自然中涤荡心灵,移情忘我,终成高超琴艺,创作名曲《水仙操》。这些散落在典籍中的故事,理应看成是知音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呈现出知音传说的早期面貌,同时也说明了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在当时已经深受人们喜爱,并广为流传了。
二、上下分流:两汉至隋唐时期的两种传承路径
从春秋战国开始流传,到两汉、三国、魏晋直至隋唐,知音传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它以怎样的故事面貌在人们的口耳之间广为流传,但是大量的文人作品和地下考古材料从侧面反映了知音传说在这一阶段的流变情况,并且开始形成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两种风格迥异的传承路径。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20世纪以来,地下宝藏的发掘为人们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文化之谜。在汉晋时期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带有伯牙弹琴、子期听琴图像的铜镜、壁画、画像石(砖)等,甚至在以祈祝内容为主的东汉神兽镜铭文中,明确有“伯(或白)牙弹琴”的字样。如:
“吾作明镜,幽湅宫商,周刻五帝天皇,伯牙弹琴,黄帝除凶……”(1975年鄂州市鄂钢工地墓中出土的东汉末期直行铭重列神兽镜)[2]
“吾作明镜,幽湅宫商,周刻容象,五帝天皇,伯牙弹琴,黄帝除凶,朱鸟玄武,白虎青龙,君(宜)高官,位之王孙,子孙番昌。”(1972年鄂州市鄂钢西山铁矿出土建安十年重列神兽镜)[3]
伯牙为何会和黄帝以及朱鸟玄武、白虎青龙等神鸟祥瑞一起出现在神兽铜镜的铭文中?与此同时,铜镜的纹饰中又为何将伯牙的形象和东王公、西王母、黄帝等神人形象铸在一起?有考古学者认为“汉朝中期铜镜就已经作为普通商品进入市场交易,铸镜的工匠将伯牙封成了神,在镜背塑造伯牙是一种自我宣传的手法,其意是我弹琴你欣赏,引申其意即为我铸镜你喜爱之意。为了寻找识货的知音”[4]。
在甘肃省敦煌佛爷庙湾墓西晋画像砖墓中的照墙上有多幅伯牙弹琴的画像,图像中,伯牙两袖飞扬,双手抚琴,对面的子期身体微微前倾,专注地听着伯牙的琴声。这样的画面如此频繁地出现在这一阶段的墓葬系统中,且多在湖北、四川、浙江等江南地区,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知音的传说在民间普遍流传,故事所表达的意义和情感深入人心。
以神兽镜、画像为载体的知音故事,传达了一种民间信仰层面上的文化形态,伯牙和子期被当成了一种神仙的形象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寻找背后的原因,有学者认为,音乐的五音宫商角徵羽是和五行阴阳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民众期望用伯牙的琴调和阴阳,驱邪祈福[5]。伯牙和子期的神仙化,还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东汉道教盛行,随着道教的传播,人们将琴艺高超的伯牙和知音善听的子期看成是和东王公、西王母、黄帝等寄托人们精神的神仙,也是极为可能的。因而,有观点认为“伯牙是汉至南北朝时高士神仙化的典型例证,其神仙化的过程完成于东汉”[6]。
知音的故事同样受到了文人墨客的喜爱,在这批上层精英阶层中,知音传说以另一种形态完成着传承和演变。它被作为一个典故频繁引用在汉赋、唐诗散文等各个体裁作品之中。“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司马迁《报任安书》);“伯牙之绝弦兮,无钟子期而听之”(东方朔《楚辞·七谏·谬谏》);“使师堂操《畅》,伯牙为之歌”(枚乘《七发》);“昔伯牙绝弦于钟子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曹丕《与吴质书》);“昔伯牙埋琴,而钟子期知其志;隶人击磬,而子期识其心哀”(嵇康《声无哀乐论》);“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子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勃《滕王阁序》)……
知音传说在文人的笔下幻化成一个能够表达他们内心渴求知音而又知音难觅的情感和文化符号。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后世的作品中,使得知音传说故事获得不断的流传和发展的动力,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共鸣。
三、节点交汇:明朝话本与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真正将知音传说推向巅峰的是明朝冯梦龙的话本小说《警世通言》中的首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首先,它不仅在内容上对典籍所载的故事进行了扩充,将原本百余字的记载改编成为七千余字的小说,极大地丰富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完整了情节结构。其次,冯梦龙在将知音传说经典化的同时,也完成了知音传说的地方化,将原本简单的故事落脚到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故事的开头明确为“春秋战国时期”,“湖广荆州府之地”,其中,汉阳江口、马鞍山、集贤村等地名都得以真实地体现。所以,冯本小说“是目前我们所知关于知音传说最生动完整的文本”[7]。然而,这些改编到底是冯梦龙创作虚构的偶然还是根据民间口头材料而来,究竟是纯粹的作家作品还是汉阳地区民间传说的真实呈现,对于知音传说本身的研究来说显得异常重要。
近来查阅到的一则新材料,为帮助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疑问,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线索。20世纪80年代,著名民俗文学家路工先生就在《访书见闻录》中附刊了他所收藏的残本明万历(约1610年)《小说传奇合刊》中的一篇话本《贵贱交情》。这是一个说话人记录的话本,记录的正是知音传说,与冯梦龙《警世通言》的小说极为相似。谭正璧先生在《三言二拍本事源流述考》一文中认为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先已有刻本”,即《贫贱交情》(应为《贵贱交情》),并认为此话本当为宋人之作[8]。尽管在《贵贱交情》的成文年代上,众多学者存在着一些分歧,聂付生在《冯梦龙研究》中将其列为“有争议的宋元作品”[9],但是与冯梦龙《警世通言》的成书年代天启四年(1624年)相比,《贵贱交情》确实在其之前。
话本是说话人敷演故事的底本,大多是对人们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采集和整理。《贵贱交情》的发现确实可以让我们大胆地做出这样的推断:在宋元明时期,知音传说是真实流传于人们的口耳之间的,且主要在汉阳地区传播,说话人将其写成底本,在瓦肆勾栏中传播给市民。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冯梦龙就是依据《贵贱交情》而写成话本小说的,但是至少对断定《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绝对不是其个人的文学虚构和创作。将二者进行仔细比较之后发现,《贵》与《俞》在字里行间存在着不少出入。冯梦龙将话本的开头“浪说曾分管鲍金,谁人辨得伯牙琴?而今交道如蜮鬼,空腹英雄一片心!常言道:‘一富一贫,乃见交情;一贫一贱,交情乃见。’”改为“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于今世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这样的删改,“文章虽然精炼些,但是说话人的俗语与语气可惜剪掉不少”[10]。
那么,冯梦龙是否可能直接受到了民间传说的浸润和影响呢?通过考察冯梦龙的生平资料,我们可以找到这样几种可能:第一,冯梦龙曾经在万历四十年到泰昌元年间(1612—1620),应楚黄友人的邀请数度赴湖北麻城一带讲学会友。第二,冯梦龙曾是湖广江夏人熊廷弼的门下之士,他曾在冯因《挂枝儿》遭遇封建正统攻击,落魄奔走之时伸出援手,为其解围,让冯梦龙大为感激,同时在与其交游的师友门生中,不乏大量的荆楚之人。在荆楚汉阳广为流传的知音传说直接为冯梦龙所听闻并深受影响的可能也并非为零。但是不管通过怎样的途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都是冯梦龙对民间流传的知音传说进行加工和润色而成的,并使之成为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在这一点上,它是俗文学和雅文学在交汇和碰撞之后产生的火花。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使得知音传说在民间的传播更加广泛,同时也造成了知音传说的形态基本固定,后世流传的内容也始终以此为基础,没有突破这种形态。
四、融合复兴:现代非遗背景下的多重互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5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式启动。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一时代契机,知音传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于2008年入选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非遗”的浪潮之下,知音的传说形成了口头与书面、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的多重互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让知音传说以崭新的形态呈现出新的活力。
从明朝之后,人们将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视为圭臬,关于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并没有太多的演绎。在对知音传说流传现状的田野调查中,通过采集蔡甸和汉阳地区民众活态的口头传说,我们发现,“非遗”背景下的知音故事是一种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互动。基层文化工作者从民间搜集活态材料,根据搜集而来的传说文本进行整理和保护。同时为了加强保护和传承,整理而来的文本又反过来成为更多民众了解和传播知音传说的来源。蔡甸区马鞍村、集贤村大多数村民是通过书本途径来了解知音传说的,却较少由老人和长辈讲述得知此传说。在蔡甸的马鞍村和集贤村存留有钟子期墓、知音亭、马鞍山、古集贤村等地名和遗迹,在汉阳江边有古琴台等纪念古迹,人们围绕这些古迹、传说和书面文本进行讲述和流传。在民间传说的流变过程中,这种口头和书面互动结合的现象是必然的,就知音传说而言,这种互动在“非遗”的背景下更为典型。
传统和现代的互动在知音传说的现代流变中也非常突出。传统的民间传说在人们的口耳之间相互流传,然而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知音传说以传统口头材料为内容,结合数字信息技术、现代建筑、商业旅游等现代手段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高山流水》影片,以琴台大剧院等为代表的现代建筑,“高山流水子期公园”等都成为承载和讲述知音传说的一种文化形态。
在知音传说的现代流变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官方和民间的互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和民间等社会力量都共同参与其中。国家文化部门积极倡导挖掘和保护民间故事、传说,制定积极的文化政策,以知音传说为基础发展知音文化;基层文化工作者深入传说流传地区搜集活态文本,编订《知音传说故事集》,进行知音文化研究等。在文化部门的组织下,本地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以知音传说为主题的诗歌、戏曲、歌舞创作等。在集贤村、马鞍村等知音传说的主要流传地,村委干部积极争取各项关于知音传说以及知音文化建设的项目,积极宣传本村与知音传说相关的地名和遗迹等。在田野调查中,当地一些有文化的村民,非常热心地参与知音传说的讲述和研究,将自己在本村中了解到的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文本提供给文化馆人员。
总之,知音传说经过数千年的流变和发展,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与时代紧密结合的文化形态,并将以中国文化的理想品格不断延续下去。
注释:
[1]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9页。
[2] 董亚巍、郭永和、李从明:《从一枚环状乳画纹带神兽镜中看东王公、西王母、黄帝和伯牙的形象》,《鄂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 鄂州市博物馆:《鄂州铜镜》,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4] 鄂州市博物馆:《鄂州铜镜》,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5] 王卉:《东汉镜铭中的“黄帝”与“伯牙”》,《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6] 王中旭:《敦煌佛爷庙湾伯牙弹琴画像之渊源与含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
[7] 刘守华:《千古风流论知音——我看伯牙、子期传说》,《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8]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
[9] 聂付生:《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10]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