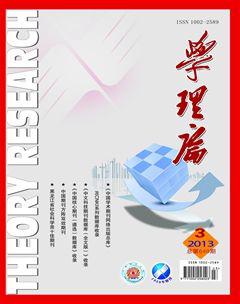公司累积投票制之法律经济学分析
胡强
摘要:2005年《公司法》第106条首次写入了累积投票的公司董事选举方式,虽仅是依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将之规定为任意性规则,但仍然博得了不少学者专家以及中小股东的热情追捧。然而,仔细观察之,累积投票制这一表决权规则违背了公司股东平等的原则,有背弃“一股一票”原则之嫌。并且,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累积投票制扭曲了股东剩余索取权和投票权重相匹配的原则,将引发不必要的代理成本。此外,该选举制下产生的董事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可能会导致公司原本最有效率的机构(董事会)成为“异议堂”,不利于股东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对于外部要约收购市场而言,由于累积投票制的引入,也会产生额外的不确定性和收购成本,从而弱化该市场的效率,导致资源的非优化配置。
关键词:剩余索取权;表决权;福利;激励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107-04
引言
为回应广大中小股东的诉求,我国新《公司法》审时度势,在第106条写入了意在强力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累积投票制。《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份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这一任意性规则可能令中小股东投票的权重呈倍数增长,使其在公司董事会选举中具有与其所拥有的股权数量不对等的表决权。对于中小股东拥有如此“盈余”的表决权重,学界普遍持盛赞的态度,认为这一规定符合中小股东的核心利益,是治理“一股独大”困境的良药。有学者认为我国不应将累积投票制设计为选入式(opt-in),而应当采取强制主义的态度[1]。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司法律应该引入表决权限制制度,应规定对控股股东等持股超过一定比例的部分没有表决权或对其表决权进行缩减[2]。此类相似的观点甚多,不一而足,其初衷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但显然已走向极端。
然而,学界对累积投票制的热衷与累积投票制的发起国的发展现状似乎背道而驰。累积投票制肇事于美国,最初用于政治选举,后引入公司表决权领域,一度相当盛行,有一些州法采取强制立法的姿态,如阿肯色、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等州。但这股热潮不久就转盛直衰,各州纷纷摒弃了强制主义的态度,转而采取许可主义;或为选入式(opt-in),即除非公司章程规定累积投票制,否则不予适用;或为选出式(opt-out),即除非公司章程做相反规定,否则适用之。就美国联邦层面而言,也经历着相仿的过程。1950年的《标准公司法》要求实行强制主义,但其后逐渐放松,至1984年,则明确采纳选入式,即除非公司自愿选择,否则不实行,至此未变[3]。就世界范围看,目前实行累积投票制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少之又少①。
基于此,累积投票制的优劣比较似乎颇有值得疑虑之处。而抛开“公平公正”的道德情谊,②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之,累积投票制似乎并非是一种有效率的选举制度,其并未增加股东的总福利,且极易破坏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
一、累积投票制违背一股一票权原则
新《公司法》引入累积投票制后,现实中,公司董事、监事的选举可以采取直接投票(straight voting)方式,也可以采取累积投票(cumulating voting)方式。在直接投票方式中,对公司管理人员的选举严格遵循了“一股一票”或“资本多数决”原则。资本是公司的基础,按照资本平等原则,公司必须以出资为依据在股东间分配权利,实行权利按资分配的平等[4]。
而累积投票制显然违背了“一股一票”的原则,其实质是“剥削”了大股东的表决权重。如果实行累积投票制,则小股东将拥有超过其剩余索取权的表决权重,但小股东本身没有与其所获得的表决权重相对等的剩余索取权,将引发道德风险并产生不必要的代理成本[3]。试举一例,假设某公司有A、B两位股东,A股东持股30%,B股东持股70%;现有3位待选董事,在累积投票制下,A股东将拥有90单位的表决权重,而B股东将拥有210单位的表决权重,A如果足够明智地将表决权集中使用,则可确保有一位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选为董事。如此,A股东在董事会层面的利益占据33%以上,高于其在公司拥有的剩余索取权(30%)。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累积投票制在赋予小股东“盈余”权益的时候将剥夺大股东与其身份相匹配的激励,原本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对公司全心全意的大股东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懈怠,因为勤勉的大股东需要将付出的边际努力所获得的边际收益部分地配置给小股东。而大股东的懈怠和偷懒对公司全体股东的福利而言无疑是一种折损。正如美国大法官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以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丹尼尔·费希尔所言:“如果投票者的表决权与其剩余索取权不成比例,则他们无法获得自己努力所带来的等同于其表决权比例的利益份额,也无须按其表决权比例承担可能造成的损失,这(利益和风险机制的匮乏)使得他们不可能做出理想的选择。”[5]
一股一票的选举制无疑更符合“经济人”的激励,这种按资本多寡的表决权制度尽管可能会带来“不道德”的结果,但经济福利的增长本身不是以道德基础作为发动引擎的。在累积投票制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所带来的代理成本和激励错配造成的资源不经济相比不能被佐证为拥有净产出时就强制规定公司董事等高管的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至少是欠缺考虑的。
二、累积投票制给公司带来决策“噪音”
公司采取累积投票制的另一个显见的弊端是,小股东所选举出的董事与大股东的代表基于对企业的政策和规划的不同偏好势必出现不同程度的意见相左,公司决策层的“噪音”可能会被放大。而代表小股东的董事为了维持在董事会的职位,有动机更加“勤勉”地为被代理人服务,因为一个富于“斗争”精神的小股东代表更容易被小股东解释为自身利益的捍卫者。然而,过于的“斗争”是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的,但董事会的“富余”决策成本又与“好斗”的董事的利益无涉,对小股东造成的边际成本也远远小于大股东。这种扭曲的激励所营造的罕见的股东与其代表的低代理成本却将使公司和大股东付出更多的交涉和协调成本。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意见相左造成的“噪音”成本并没有替代机制予以弥补。
此外,小股东因为在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小,其在公司的整体福利也远比不上大股东,因此其更有动机从事风险性大的经营活动。这种冒险主义行为极有可能并非出于理性的商业判断。一旦小股东的代表董事拥有相对于其他人更多的参与集体决策的便利时——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富余时间、出众的管理才能、特殊的信息渠道——这种政治程序的控制权就可能会落入一些没有代表性的少数派手中,他们因而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利用这种控制权,以此诓骗其他人共同做出一个对集体没有效率但满足其自身追求的决定[6]。
公司理论普遍认为,股东会的决策是充满“噪音”的,因为股东会就如同由一个个各怀私利的股东所组成的“聚众性”利益博弈竞技场,由于股东的利益趋同(股价上涨、盈余分红、规模经济等),因而这种“噪音”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但是将股东会的“噪音”不予隔绝地传染至董事会则无疑将束缚住公司具体的经营决策,使公司带着镣铐进行纷繁复杂的市场交易。如此这般,董事会高昂的决策成本将使其失去比较优势,并极易错失市场交易机会。因而,董事会成员过大的异质性就有可能成为公司经营失败的单个关键因素。
三、累积投票制可能导致要约收购市场失灵
在规模经济的背景下,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公司层面已产生极大的分离。伯利和米恩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为我们刻画了这一生动的历史图景。①基于此,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营者(董事会)与公司的名义所有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就相伴相随、悬而未决。如果把经营者和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其他利益集团和公司所签合同等量齐观,就会遇到一大难题,即:经营者被认为是能够控制公司的人;经营者之所以会用犀利的眼光盯着企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作为向股东负责的代理人[7]。
要约收购市场的有效性是对这一代理问题很好的回应。大量的研究文献证明,存在一个有效的要约收购市场能够部分遏制公司经营者的滥权,尤其对于公众公司而言,要约收购有益于增加股东的福利。对这一假说的最好解释是:同其他人一样,如果公司经营者能够得到自己努力工作的所有收益,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工作;但是在公司里,每个经营者的工作的很多收益都是有利于某些人,比如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管理者[8]。因此,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没有付出全部努力的激励,市场也找不到能够支付其全部努力的对价。这可以被称为公司股东的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②。这一剩余损失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以及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下可能会被放大。而有效的要约收购市场的存在本身,就因为其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慑力,从而可以适度填补损失的金额(尽管计算这种金额的方法也是充满困难的)。
然而,累积投票制的设计令公司管理者添加了自我防御的武器,他们原本就是“各自为政”的股东的代理人,且少数派股东基于累积投票制所积攒的既得利益和有限的收购溢价之间的差距使其很难做出同意被收购的决策。此外,失去参与权带来的失落感以及其对公司经营活动更多的话语权所赋予的原本乐在其中的旨趣也会随着收购而烟消云散。如此,由于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权方式所“生产”出的过大的异议权无形中极大地阻碍了多数股东整体福利的贴现,使其难以获得收购溢价带来的效用提升。另外,在收购谈判中,累积投票制所赋予的小股东额外表决权也会增加小股东的谈判能力,要约收购人谈判成本相对更高,且这种成本在发出收购要约前是隐性的。这一隐性成本足以阻■任何试图挑战公司控制权的潜在收购者。
四、累积投票制在公司治理中的选入问题
累积投票制固然有如上的缺点,且历史上也不乏证明其失范的事例。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在1883年Sharpsville铁路公司董事选举中,由于采取累积投票制,少数派股东不仅获得了董事会的席位,甚至还获得了(董事会)控制权。③但直选制本身也存有顽疾,因此,是否采用累积投票制依然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应该交由公司自主抉择,而不宜强制采用,从而作为公司的标准“菜单”。由此观之,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是较为理性的制度安排。
关于实践中公司选入累积投票制的具体方式,笔者认为,就闭锁公司(在我国公司法律语境下为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由于股东人数较少、规模较小,股东往往兼任公司高管,他们通过谈判达成合意的可能性较大,故应赋予该类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间。因此,是否将累积投票这一表决制度写入公司章程,作为赋权性规则授予公司股东将会是合理而明智的。就公众公司而言,如果累积投票制所发出的增进中小股东福利的信号有助于公司“招徕”潜在投资者(如公司募集设立时急需大量资金),公司大股东也有足够的激励将其写入公司章程[3]。
五、结论
基于“道德人”的禀赋,有不少评论人士表现出了对累积投票制这一公司表决权规则很高的热情,认为这一表决权规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有效改变我国公司治理中“一股独大”、控股股东操纵公司的现象,但这一论调至今未见有实证研究的支撑。况且,累积投票制自身就存在诸多令人质疑的劣势。此外,有学者还列举了多达六种减弱或者抵消累积投票制效果的方式[9]。因此,在公司治理,尤其是事关公司命运的表决权规则中强制做出带有明显偏向的制度安排的举措,无疑将引发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诘问;尤其是在错配激励的情况下,还会产生不必要的代理成本。
在公司治理中,实难苛求事事尽美,尤其是由《公司法》开出标准合同时,更应当慎之又慎。在商事立法中,借鉴国外的立法趋向并采取成本-收益的权衡分析,方能使立法经受得起市场的检验。在经济行为市场化的语境下,本着建构股东整体福利最大化的规则取向,就应当允许帕累托次优效果的普遍存在。①
参考文献:
[1]刘俊海.论股东累积投票权[J].环球法律评论,2003,(1).
[2]李勇军.解读公司累积投票制效用之假设——基于对我国《公司法》106条的分析[J].东方法学,2009,(6).
[3]罗培新,等.公司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范健,王建文.公司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M].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M].于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美]唐纳德·A.威特曼.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C].苏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9]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0]Michael C.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Vol. 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11]Amihai Glazer, Debra G. Glazer and Bernard Grofman, “Cumulative Voting in Corporate Elections: Introducing Strategy into the Equation,” 35 South Carolina Law Review,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