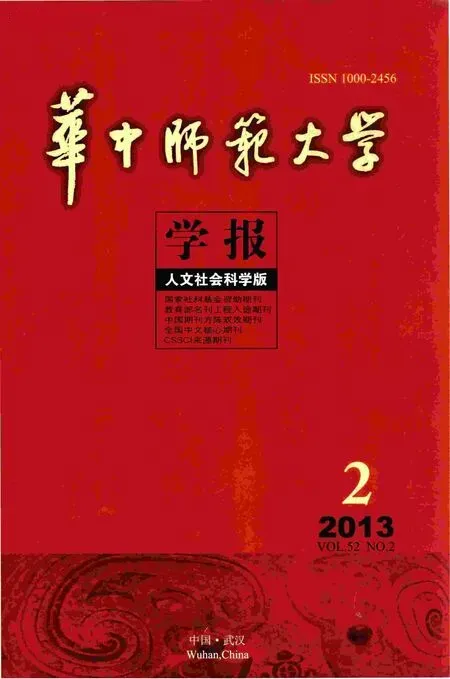中国农民工的信任结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
符 平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信任一般被视作个体的一种心理特质和性情倾向,①构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合作的前提。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走出农村、迈进城市,即意味着他们从一个以熟人信任维系秩序的生活世界进入了一个以陌生人为主体、信任维系机制更为复杂的新生活世界。一方面,他们来自于农村,受到传统乡土文化的深刻影响,“熟人社会”中的信任原则对他们的信任结构施加了重要影响;同时,他们也是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工人,其信任对象和信任来源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亦有可能遭遇信任危机。农民工的信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可理解为该群体对其他社会人群或制度机构会出于善意而行动的一种期待,即期望后者倾向于恪守承诺,并会尽可能避免伤害到他们。
不信任的群体心理是一种弥漫性的自我疏离机制,极易侵蚀、破坏特定群体对其他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也有导致群体产生越轨和失范行为的可能。虽然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有被城市接受、融入城市的渴望,但来自城市居民或制度的歧视和偏见使其难以获得较高程度的信任感,这反过来会导致他们对城市的疏离、敌视甚至报复。如此,农民工群体的信任问题绝不仅仅只关怀其自身福祉,同时也关涉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秩序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农民工信任结构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虽然迄今围绕农民工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关于农民工群体的信任问题还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更不用说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即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一、研究方法
关于群体的信任问题的经验研究可区分为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将群体信任当作一种自变量,探讨其之于群体整合、经济发展、政治实践和社会进步的角色、功能和意义。该路经是目前社会学研究信任问题的主流路经;二是将信任当作因变量,分析哪些具体的因素、通过怎样的机制和途径在影响特定群体的信任表现。虽然基于该路径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前一路径而言较少,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显现出日益严重的迹象,试图去解释这一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沿着这一路径前进的研究大体又可分为三种不同解释取向,分别是文化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和制度主义的。
文化主义的解释取向视信任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特殊文化或信仰的产物,侧重于探索特定信任模式的文化或心理情感基础。研究多认为中国人的特殊主义信任起源于浓厚的家族意识和由血缘、亲缘及地缘关系所带来的亲密认同心理。②结构主义的解释取向从社会结构(通常被操作化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交往状况)和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解释信任的现状及其原因,致力于阐明支撑某种特定信任类型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基础。研究多认为关系本身的亲疏和互动状况决定了信任的结果。③制度主义的解释取向主要从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环境角度解析信任的嬗变。研究多认为,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剧烈的社会变迁(尤其是陌生人社会的形成)逐渐瓦解了原有的信任基础,传统的信任维系机制所起到的作用日渐式微,但新的机制又尚未健全,社会的信任于是陷入了较大的危机之中。④以上三种解释取向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相对区分的研究手段,但又相互联系并有共通互补之处。
农民工的特殊属性在于,他们是一个跨越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流动群体,不仅体现出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双重特征,更重要的是流动过程给他们带来了社会关系和交往网络的重构。而这将直接影响该群体的信任表现。基于对农民工信任结构的基本现状描述,我们将沿着结构主义的解释路径,考察人口结构特征、社会交往和政府支持因素对农民工信任表现的具体影响。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2年1-2月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调查覆盖全国26个省市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本文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基本现状:农民工信任结构的差序格局
本次调查问卷中有专门针对农民工信任问题的信任量表。信任量表一共有14种置信对象,见表2。由于分值越低表示信任度越高,因此从信任的均值中可见,在农民工那里信任度最高的五类对象分别是家人、亲戚、老家朋友、老家邻居和中央政府,其均值都在2.5以下。信任度最低的五类对象分别是城市市民、领导干部、做生意的人、企业/公司的产品宣传广告和初次接触的陌生人,其均值都在3.0以上。家人居于所有置信对象的最核心,其次是亲戚和老家朋友,因此基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熟人群体属农民工最值得信任的对象。而之所以会是这样的结果,在于血缘和家族关系始终是农民工在生活、生产和心理方面获得最大支持的重要载体,同时在他们受到权益侵害、遭遇矛盾纠纷时,也是最有可能为其在第一时间提供保护和帮助的力量。基于市场关系或接触较少的对象在农民工那里是最缺乏信任感的。从置信对象的信任度排序中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农民工信任结构的特征与费孝通描绘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即大体上呈现出以“家”为核心往外推及的多层圈状特征。置信对象与其的关系越亲近密切,接触越多,越靠近信任的核心区域;关系越生疏,接触越少,越接近信任的外围。

表2 不同置信对象的信任度排序
尽管如此我们发现,虽然农民工的信任结构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特征,但政府信任却呈现出“逆差序格局”的特征。在现实中,农民工一般只有机会与家乡的乡/镇政府和务工创业所在城市的政府有所接触,但在政府信任范畴中,获得信任度最高的却是其与其几乎没有直接交往的中央政府,而最低的却是家乡政府。农民工对家乡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比务工所在地的政府更低。这一分析结果提醒我们,农村基层政权与外出务工农民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容乐观。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中央政府在农民工眼里是给予利益、对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的对象,是值得他们依靠的主体。而基层政府在他们眼中则有可能扮演截留他们应得利益、剥夺其合法权益的角色,因而是他们为了充分享受自身合法权益而需要与之博弈和斗争的对象。这样来看,在政治关系领域形成了信任的“逆差序格局”便不足为奇。此外,领导干部的信任度为3.111,是政府信任范畴中最不受农民工信任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府的信任度在所有置信对象中属于垫底行列,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与农民工的关系更好。政府的本质及其公共服务职责性质决定了,其应该比其他对象更值得农民工信任。不过从信任度均值来看,除中央政府外,两地基层政府与领导干部的信任度均接近或达到3,即还没有达到半数可信的程度,说明政府在农民工那里有着较严重的信任危机。
还需引起注意和重视的一个研究发现是,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生活在一个空间,在生活和工作的很多方面发生有交集,但市民在农民工那里的信任度却较低(均值是3.084)。这表明农民工对城市市民充满了戒备心理,两大群体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隔离感和不信任感。这种状况得以形成的原因更多的是以往研究所揭示的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抑或是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⑤值得今后的相关研究加以关注。
三、农民工信任结构的影响因素
1.变量处理
由于不同置信对象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采取因子分析方法对上述14个置信对象进行简化处理。为考察置信对象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我们需要首先进行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本文的KMO值为0.879,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比较理想。球形Bartlett检验的值为17162.440,并在0.001水平上双尾显著,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是可行的。通过使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varimax rotation)后,我们提取到3个因子,他们的累积解释贡献达到了62.015%,即3个公共因子可以反映原指标62.015%的信息量,见下表3。

表3 主成份法因子分析(旋转因子负荷)
通过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因子1包含的置信对象有领导干部、家乡的乡/镇政府、务工创业所在城市的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和务工创业所在城市的警察,上述对象在因子1上的因子载荷均超过0.6,我们将其定义为政府信任。因子2包含的置信对象有外地朋友、城市市民、初次接触的陌生人、做生意的人和宣传广告,其因子载荷也在0.5以上。不难看出因子2包含的是一种弱社会联系。此类置信对象与农民工之间的联系往往是藉由需求-满足的市场逻辑才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市场信任。因子3包含的置信对象有家人、亲戚、邻居和老家朋友,上述置信对象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将其界定为社会信任。
我们把上述三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作为因变量。通过对三个因子得分的正态分布检验,发现三个因子的分布均接近于正态分布,因此因子得分可以作为因变量直接进入回归分析。上述三大范畴的信任涉及不同置信对象。我们针对三种信任所引入的共同变量是农民工的人口结构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及在城市的工作年数和换工作频率。为便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在信任结构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我们将年龄处理为分类变量。其中1980年后出生的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虚拟变量取值为1。文化程度是测量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其作为连续变量处理。在调查时,我们将职业类别划分为10种不同类别(见表1),但在数据处理时,我们将其合并为8种类型,即自谋职业、产业工人、办公室人员、技术精英、服务行业人员、管理精英、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在对职业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后,其他职业作为参照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历经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具体形态的演变取决于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变化,取决于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但是,无论是党领导的哪个阶段、哪个形态的统一战线,都致力于构建保证中心任务实现的共同体。统一战线所构建共同体为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体现了阶段性和长期性、局部性和整体性的统一。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的纵向逻辑与统一战线的性质演变方向一致,经历从阶级联盟的共同体到政治联盟的共同体的发展。
由于三种信任的程度表现还有着不同的形成机制,因此除了上述共同的自变量外,我们还针对不同的信任范畴引入了不同的变量。对政府信任主要引入了政府支持程度的变量。政府是一个语义含糊的概念,涉及不同级别和不同部门,而在一般民众眼中则泛指一切公共管理和服务部门的权力机构。我们对政府进行了简化处理,主要考察了工作地政府帮助程度和老家政府帮助程度两个方面,而没有细分不同的政府部门。社会信任产生于社会交往,⑥因此社会交往的频率对其他人群在农民工那里获得的信任度显然会产生影响。而农民工从农村进城打工,不断的工作和空间流动是其重要的群体特征,⑦正因如此,他们社会交往的对象也总是在发生变化。流动过程显著地增加了他们与城市当地市民和其他外乡人的交往机会和概率,进而使他们的社会交往超越了传统的熟人社会圈子。与此同时,他们与熟人交往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因其流动经历而发生变化,如在传统社会关系的交往中注入市场关系的因子,而这种关系的改变显然会对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信任施加影响。为考察不同交往对象的影响,我们引入了城市老乡交往频率、城市外地人交往频率和城市当地人交往频率三个自变量。
2.模型及解释
表4给出了农民工信任结构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中回归系数越小表示信任度越高,反之则表示信任度越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引进了农民工的人口结构特征变量对三种不同范畴的信任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察了一些基础性的人口结构特征变量对信任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变量对三种类型的信任都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相对女性来说,男性农民工更倾向于市场信任和社会信任,相对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在年龄变量方面,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在社会信任范畴上没有差别,但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信任和市场信任的程度比第一代农民工显著地低。回归系数的大小也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最为明显。文化程度对信任有显著影响,表现为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市场信任和社会信任,而文化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政府信任。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所占比例超过了60%,而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要高于第一代,因此这里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获得的信任度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跨越城乡二元藩篱的理想和抱负,但其基本的权益诉求在城市世界却大多难以实现,体现为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较大落差。⑧他们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对社会更多地抱有某种怨恨感和不公平感,并更多地将诸多个人困境的成因归结于政府。这可能是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模型还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工的职业对不同范畴的信任的影响。我们将其他职业作为参照组,这样回归系数就是相对于参照组而言,各类职业对不同范畴的信任的影响。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获得总体的印象,即不同的职业类型对三种范畴的信任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从事自谋职业的农民工相对参照组而言,其社会信任的程度更高,而政府信任和市场信任则与参照组没有显著差异。产业工人是较大比例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产业工人的从业者相对参照组的其他职业人员而言,在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上都显著地高,但在市场信任上则与参照组没有显著差别。办公室人员属于城市的小白领阶层。该群体虽然在制度身份上仍然属于农民工,但在职业上已经实现了“去体力化”和“去蓝领化”的身份转变,不再是传统意象中的农民工。⑨研究发现,他们在市场信任和社会信任上比参照组显著地高,在政府信任上则与参照组没有显著差别。职业为技术人员的农民工则相对参照组而言,在上述三种不同信任领域都显著地高。从事服务行业的农民工相对参照组来说,在市场信任和社会信任方面的信任度更高。相对参照组而言,从事管理岗位和私营企业主两类职业的农民工在政府信任和市场信任上显著更高,而在社会信任上则没有显著差异。
以上研究发现揭示,在低端职业领域就业的农民工在社会信任上的程度更高,而属于技术精英、管理精英和经济精英(私营企业主)的农民工则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信任,即职业地位更高的农民工对政府和市场有着更高的信任度。上述结论表明,农民工对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与其职业的社会地位存在很大关系。具体而言,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越高,其市场信任和政府信任度就越高,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信任;相反,职业地位越低,则越倾向于以社会关系为载体的社会信任。对此的可能解释是,职业地位越高的农民工与市场和政府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也更多地受益于市场和政府提供的各种资源和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职业不仅标志着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也彰显了特定的社会交往对象和内容。譬如那些在车间工作的产业工人,其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是车间的工友和主管,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接触机会要少很多。职业地位较高的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关系,交往范围更广、更开放且交往对象更具有异质性,而职业地位较低的农民工的交往范围更小、更封闭且交往对象更具有同质性,因此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度会更低。

表4 影响农民工信任结构的多元回归模型
一般而言,外出时间越长,农民工的城市阅历越丰富,城市适应能力也会越强,因此理论上来说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对城市市民和陌生人的信任度。不过分析结果发现,外出时间长度对农民工的上述三种信任均无显著影响。但流动次数对政府信任和市场信任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农民工的流动次数越多,他们的政府信任度和市场信任度越低,而流动次数对社会信任则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频繁的流动和工作变换会导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在整体上显现出短期化和功利化的特点,因此流动频次更高的农民工与那些在流动过程中结识的对象之间的相互信任感更不容易建立,同时他们可能因对政府更失望而不大信任政府——流动越频繁恰恰是因为农民工的工作越不稳定和缺乏保障,他们可能借此对政府更加心存不满。
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对象和频率是不同的,而这会影响到他们在不同范畴的信任上的表现。模型5和模型6增加了社会交往变量以验证这一观点。结果发现,与同在城市打工的老乡的交往频率虽然对提高农民工的市场信任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提高社会信任具有显著的正面意义,即该类型关系的交往频率越高,则农民工在社会信任上的程度越高。与同在城市打工的外地人的交往频率对增进农民工的市场信任和社会信任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与城市当地市民的交往频率则会显著提升其市场信任程度,但对社会信任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对象与其信任的对象具有非常明显的叠合效应,即其与某个群体的社会交往越多,对该群体的信任度就越高。该结论的启示在于,如果说当下中国社会总体的社会信任度不高这一论点成立的话,可能主要是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疏离所导致。而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社会疏离则严重阻碍了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感的建立。不过就宏观层面上社会的整体信任度而言,我们却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的积极意义。由于他们在不断地拓展其社会交往的对象和范围,虽然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充满各种障碍,也存在一定的狭隘和局限性,但仍对促进城乡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提高城乡居民彼此的信任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农民工的信任结构从总体上体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对与自己有着血缘和地缘、接触较多的对象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同时他们又长期在城市就业,其生活和工作的诸多方面相对于农民来说更多地依赖于市场和政府的扶持与帮助,因而他们亟须超越基于社会关系为载体的社会信任,建立并提高对市场和政府的信任感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但研究发现,他们表现出很低程度的市场信任,而且除了中央政府以外,对政府信任范畴中的其他对象亦表现出较低的信任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不尽如人意,但结果同时又表明政府对他们的帮助程度与其信任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可感知的政府帮扶力度非常不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和举措帮扶当前属于农民工队伍主体力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提高农民工的信任水平的关键所在。当然,提高农民工对市场和政府的信任度还离不开工厂企业、其他社会群体和组织的积极配合与支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制度体系,扩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途径并增强其力度。此外,没有较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很难想象农民工对城市会形成较高的信任感。实证分析结果暗示,与城市当地市民的社会距离和隔阂是导致农民工缺乏市场信任的重要原因。就此而言,破除农民工与市民群体之间人为设置的藩篱、促进两大群体之间的互动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显然有助于提高他们对城市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
缺乏有效的促发和维系机制是造成农民工当前信任困境的根本原因。这既有来自农民工自身的主观原因,也与转型期社会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对城市社会和政府形成较高程度的信任度不仅对于农民工自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维持社会和经济活动有序运行、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是社会安全和秩序稳定的前提基础,因此多渠道重建农民工的信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Yamagishi,T.& M.Yamagishi.“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Motivation and Emotions 18(1994);Glanville,J.L.&P.Paxton.“How do We Learn to Trust?A Confirmatory Tetrad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Generalized Trust.”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70(2007).
②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域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③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高玉林、杨洲:《中西社会信任结构之比较》,《河北学刊》2006年第7期;邱建新:《信任文化的断裂:对崇川镇民间“标会”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④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翟学伟:《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郑也夫:《信任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⑤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⑥唐有财、符平:《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⑦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⑧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符平、黄莎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四个世界”关系的研究》,《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⑨符平等:《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