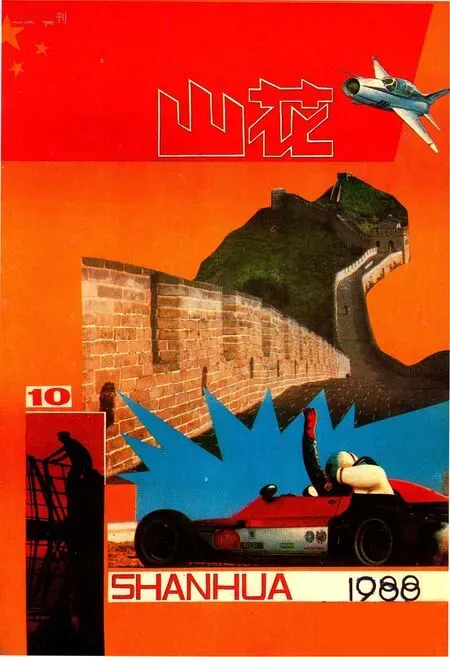自由而朴素的心性——吕德安访谈
吕德安 明 迪
第一部分
明 迪:儿童或少年时期有哪些事件或事情对您的成长有影响?并且怎样影响了您后来的写作?
明 迪:什么年代什么书对您影响很大?什么观点或什么内容影响了您?请具体谈宗教、哲学、文学等任何方面的书籍。
吕德安:在不同时期,我的书架中画册总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说到启蒙书,有一本书常常会在某个特殊时刻出现在脑海里,那就是童年时候在大人的棋牌桌下偶尔拾到的一本破烂的线装旧书,它的图画是白描,文字是老宋体。那时我对古体字可谓一字不识,但其中画着地狱情景的图画,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的震撼,可能是但丁《神曲》(包括它的插图)所不可相提并论的。可以说此书形成了我最初关于地狱的概念。也许那次深刻的印象(有声有色)也是我泛神主义倾向的基础之一。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学写自由诗,那时,一本《普希金诗选》,查良铮先生的翻译作品,对我有着启蒙意义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只是最基本层面上的文学教育,即我们抒发内心的感情可以用最日常的人性化词汇,比喻的美妙和智慧来源于生活。所以也可以说是普希金的诗,或者说查良铮的翻译语言,使“文革”时代那些政治口号诗及其诗歌观念在我眼里一夜间彻底失效,并使我隐约认识到当时的文学现状后面另有一个真正的文学。也许从那本书开始,我才开始关注起外国文学——只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少有翻译作品发表而变得如饥似渴。另外,也是这种偏爱,古典诗词那种表达方式也一下子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当时,和所有的年轻文学爱好者一样,我也在一知半解地学填律诗呢!
70年代末,我考入美术学校,读了法国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书中描写印象派画家高更逃离文明世界在土著岛生活,它对我的影响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但它启发了我对人生价值取向的思考。具体地说,毛姆笔下的画家高更,唤起了我对艺术人生的幻想,而要实现这个幻想,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殉道似的精神和勇气。这种精神和勇气至今一直激励着我的创作实践和生活态度。
当然还有《道德经》《圣经》《恶之花》等重要名著的影响,但这里,我更愿意提出《中国民谣》这本书,它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它也许从属于民俗研究,但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民谣,对我80年代的诗歌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歌里,我似乎对写诗和技巧的本质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就是一些东西通了,不好解释这是些什么,但它让我对《诗经》以及古律诗有了一种直接的洞见。我不会总结这些,我只是找到了根,并知道一棵树由此生长。就像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神之间总会发生什么,情况千变万化,但这些民谣告诉我:都在这里了,在语言发出声音的瞬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将它视为我的“创作秘笈籍”。
明 迪:为什么写诗?什么时候开始写诗?什么原因或什么事情引起写诗?是否持续在写?什么原因停顿?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代表作请总结一下。
吕德安:我写诗开始是我选择了诗,然后才是诗选择了我。我认识诗,先是中国古典诗然后才是所谓的自由诗。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认识它的外表,只知道诗作为一种文学载体,它是高级的言语方式,与现实一般写作永远保持着浪漫的落差,并似乎浓缩着可触摸的游戏规则,所以我写诗初期,选择这种载体多半是出于某种虚荣心。那时我喜欢上一个女孩,觉得光写信还不够表现我的品味,于是我模仿普希金,写起诗来了。所以说我写诗缘于一场自恋式的恋爱。那是1976年前后的事了。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意识到以后诗会缠上我。直到1979年,当我写出一些较像样的,结识了一些诗歌同道后我才立志要做一个诗人。也许这时诗才开始向我坦露自身的魔力,它是有所指向的,而我求近于它首先得保持敬畏。
我自认为80年代以后,自己的诗歌创作才开始进入逐渐自觉的阶段。这就是让诗歌回到生活,回到我们自身的现实。那时候我毕业分配到了福州一家书店工作,它离老家马尾镇很近,我几乎每星期都回去探望父母。我不太喜欢城市生活,似乎它对人性的生活(包括创作)怀着某种“古老的敌意”,那时我着迷于俄罗斯的叶赛宁和西班牙的洛尔迦的诗,还有民谣,也许这些也怂恿了我写乡土诗的倾向。当然,这个时候以《今天》为代表的“朦胧诗”已经风靡全国,我也喜欢那些诗人回归人性的写作,但是由于这些诗多数的灵感来源于对政治的敏感,从而削弱了诗性。而我要逃避这些,一心向往“田园诗”的境界。为此我将目光重新投向故乡和自然,将它视为灵感的源泉,要在那里找回属于自己的词汇和语调。这个时期我写歌唱式的抒情诗,所谓直抒胸臆,热烈而浪漫。同时我也写一些民谣式的抒情诗,并尝试着加入现代诗的叙事技巧。民谣对我的主要启发是,创作需要自由而朴素的心性。
通过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s)表示计量资料,t检验法进行比较,用(%)表示率,X2检验比较组间,有统计意义的P小于0.05。
我想那个时期我的心态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开放的,我也是一直在写不同形态的实验诗,只是那种直朴自然的抒情是我的主要趣向。事实上,那个时期我已经接触了弗罗斯特和叶芝的诗,并很快为之吸引,这才写出了《父亲与我》,诗中回忆了我和父亲在镇上的一次散步,诗中的音调介乎于歌唱与叙述之间。1992年,我旅居美国明尼苏达边上的一个小镇曼凯托,3个月后住到纽约去了。这次是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二年我那里写了长诗《曼凯托》,里面的情景半是曼凯托半是故乡海边的往事,诗句里透出田园式的恬静气息。我想说的是我的创作似乎总围绕着这些伟大的诗人,并致力于这些不同的音调之间为自己定个调;我的不同时期的创作,无论是持续或停滞都与这种可能的自我定位有关。最后我想说,也是这些伟大的声音让我重新体会中国传统诗歌。
1994年我回国,开始写长诗《适得其所》,此诗初稿只用了三个月,到完成断断续续有十五年,这期间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基本上过着游居两地的生活:纽约和家乡。这首诗以我回国后的山居生活为背景,写到了“回归”的主题。还是较为抒情风格。另外还写了一批短诗。我把这15年的创作归为最近的一个阶段。
第二部分
明 迪:近几年在读哪些书?得到什么启示,有什么收获?是否影响写作?
吕德安:近些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创作上了,读的书挺杂的,但主要是一批艺术类的。我很少专门有计划地去读书,但在创作前常常会读一点自己喜爱的东西。好像对投入创作能起启动作用。理论类的东西我向来读得少。
明 迪:您心目中的理想诗歌是什么样的?您的写作是否达到您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喜欢谁的诗(国内国外任何时期)?为什么喜欢?是否受影响?
吕德安:能带出一种自由感觉的诗,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诗的形态了。
我只能说不同时期我都有写出过自己比较满意的诗。
我只想说直到目前确定会一直喜欢下去的诗人,他们是李白、陶渊明、白居易、叶芝、弗洛期特、洛尔迦。在我人生不同时期真正喜欢并受到其诗影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四个四重奏》的作者艾略特,《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零档案》的作者于坚……不好一一细数。喜欢的理由是他们的诗不仅给我以巨大的写作幻想,还有他们的人格境界对我自己的人生具有种种启示。我想是大意如此罢。
明 迪:与哪些诗人交往?为什么?有无互相影响?如何排斥影响以形成自己的诗歌声音?
吕德安:早期由于各种原因与不少诗人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比较近的有舒婷、黑大春、于坚、韩东、西川等。他们一般首先是朋友关系,趣味相投吧,具体在诗歌上,大家基本各写各的,彼此影响似乎不大明显。
明 迪:怎样看待诗歌流派?有无参加过什么流派?诗歌流派有无意义?与前辈和同时代诗人相比,您自己有什么不同的诗学和显著风格?
吕德安:我一向不太注重诗歌流派之分,但我加入过个别诗歌团休。流派当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它强调了某种诗歌形态和诗人的价值观,使审美多元化。我没有什么诗学可标新立异,我只追从对我来说是诚实的句子。我曾一度追求民谣风格,这在当时首先是想追溯某种更为朴素和自由的歌唱方式,躲开流行的表达。我后来向弗洛斯特学习如何囿于自己的世界写身边的事物。现在还是如此。叶芝的后期诗也具有鲜明的朴素倾向和民谣里戏剧性的叙述方式,我所能做的只是借鉴他们的方式,去感知现实和语言的界限所在,并努力在诗中避免概念式的转述,而是将其转化为可触摸的诗意的语句。
明 迪:您如何评价汉语新诗起源?如何看待当下的汉语新诗?对您所亲历的(各个)诗歌发展阶段有哪些看法?您参与过什么论战?
吕德安:我从未系统研究过新诗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这个问题应该让给研究者。我一开始写诗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新诗的现实。对我来说新诗就是现成的或者说是现实的诗,是现实的正常言说和某种特殊的言说的内在的联系的结果。我很少去为新诗和古诗的不同形态而困惑,在此意义上,新诗对我来说只有“好诗”和“坏诗”之分。我尊重不同时期的所有优秀的新诗,因为它们向我们传达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作者在汉语传承上的新成就。古典汉语诗歌与当代汉语诗歌各有自身生长语境,而好的新诗我看来首先是它能够在当下的语境里既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又能灵活地发挥汉语的魅力。
第三部分
明 迪:如何看待诗歌翻译?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对您有何影响?您觉得选题和翻译质量如何?您翻译过谁的诗?或想翻译谁的诗?
吕德安:好的翻译诗在我看来就是好的汉语诗的一部分。阅读翻译诗一直伴随着我的写诗历程。翻译诗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具体文本意义上的。它还让我诗意地体验到不同的文化语境,从而启发我们对自身的语境的反省。弗洛斯特说诗是翻译丢掉的那部分,他指的更多是母语意义上的诗意的部分。对此我深有同感。但我同样相信,好的读者通过翻译,一样可以隔着一层语言去心领神会那丢失的部分。我不通任何外语,但我想高质量的翻译,是令读者想着用自己领会的方式再用汉语翻译一遍的那种。这种高质量的翻译在中国还是有的。
明 迪:如何看待中国诗向外译介?知道哪些被翻译出去的诗选和个人诗集?有什么反馈?对外译现状是否满意?希望在哪些方面会有所改进?
吕德安:以前读过资料,里面将外译出去的古汉诗再翻译回来,可谓面目全非,但似乎又是可理解的,用现代语法写就的新诗翻译出去也许不至于如此。我不太熟悉现代汉诗外译的具体情况,但我相信当下的诗歌外译还是滞后了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面貌及其成就,翻译人士应多从文化生态角度,而不仅仅从个人审美出发从事翻译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