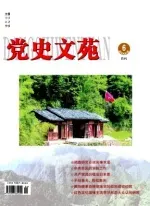试析社会变迁与苏维埃法的生成
肖子华 王 敏
(井冈山大学 江西吉安 343009)
不管是法律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强调法律与社会的关联性上都是基本一致的。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尤其强调,是社会本身,而不是作为独立自治的个人,才是法律的根源。[1]卢曼虽然宣称法律是自创生成的,但也强调法律与社会密不可分,法律的自我生成只有通过社会行动才能实现[2]P22。持续的社会变迁是现代化社会,尤其是20世纪的一个显著特征[3]P268。从清末变法修律,到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建立;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苏维埃法的创制,到抗日民主政府,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备,无不遵循一条由社会变迁引起法制变革的运行轨迹。作为社会主义法早期萌芽的苏维埃法的生成,则是在中国二元社会的形成、持续的制度变革和后来居上的革命文化背景下对法制现代化作出的局部的却是剧烈的反应。
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在没有遭到继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接二连三的冲击以前,是在一种几乎完全封闭和自足中不断重复着由乱而治、由治而乱的循环宿命和王朝更替的历史叙事的。19世纪中叶,当清王朝还沉浸在延续自汉唐气象以来的康乾盛世的繁荣当中时,以英、法、德等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已经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近代转变。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释放的不仅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理性之光,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以新航路开辟为契机,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以海外贸易为途径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向披靡,当东西方两个世界在19世纪中叶开始碰撞以后,各自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鸦片战争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一方面是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现代工商业在中国快速兴起,传统单一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并向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从军工、造船,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从一开始的官办,到1872年李鸿章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为中国企业的私有化打开了一扇门,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继官办和官督商办之后,纯粹私人商办的企业也陆续出现,著名的如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据统计,至1905年,全国举办的工商企业计有官办36家,官商合办16家,官督商办26家,商办384家,中外合办4家;而在此后的1906年至1927年间举办的企业更是高达2463家[4]。这些现代工商业的出现,对传统的自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现代工商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在中国悄然形成。
与二元经济相伴随,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日益明显。一方面,自洋务运动至清末新政,再到1926年以前的北洋政府时期,自上而下展开的现代工商业布局,特别是现代工业,基本在大中城市展开,小城镇和广袤的农村则几乎没有触及。另一方面,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与租界的设立逐渐增多,从1860年至1906年的几十年间,中国依据条约开放的口岸有60余处,自行开放的口岸有16处。这些原本就有商业基础的沿江沿海口岸城市,随着西方现代工商业的蜂拥而入,城市面貌发生巨变,从原来单一的或交通要冲,或行政中心,或商品集散地,向多功能的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现代城市转变。城市里由商人、手工业者、买办等阶层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性结构,与农村旧有的超稳定乡土社会结构并存,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
二、持续的制度变革
自清末以来的整个20世纪,在中国社会始终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就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现代化之所以始自西方,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蕴含了一种以特定的理性的经济形式、以自治和契约为特点的政治模式和理性的、普遍主义的法律构成的“现代性特质”。[5]法制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固有内容和重要评价指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中都有触及。罗荣渠提出两种现代化类型,其中内发型法制现代化似乎属于原创式变革的范畴,而外发型法制现代化大体归于传导式变革之列。[6]中国无疑属于后一种类型,但不管哪种类型,纵观欧美各国的法制现代化历程,又无一不是以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的变革为先导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士大夫阶层,包括清廷内部的有识之士,纷纷吁请“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启了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但运动并没有触及在中国已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帝制。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极大地触痛了国人,也改变了中国此后的政治走向,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改良派,疾呼通世界之知识,采万国之美法,提出设议院、开国会、行宪政,从制度层面进行变革。维新运动顺利进行了三四年,但1898年春突发的胶州湾危机使得平和的政治变革突然加速,最终在1898年秋戛然而止。“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由此不可逆转地在中国开启了制度变革的序幕。
1901年,在经过了庚子国变后的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并着手进行变法修律。清廷的新政宣示,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主行为,其内里则是1901年《辛丑条约》所表达的“辛丑共识”,即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观念上的差距。[7]P19—20受1904年日俄战争的刺激,清廷认识到,“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专制”。这时候在朝野内外取得的共识就是君主立宪,在五大臣宪政考察后,一度中断的政治改革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宕延至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打出了君主立宪的旗号,但距离以英国为代表的主权在民意义上的君主立宪相去甚远,更没有“王在议会,王在法下”的代议制精髓,立宪派在与共和派的赛跑中已被落在了后面,民主革命浪潮的来袭已不可避免。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匆忙公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备了西方议会政治的实质,但对于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已无济于事。中国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的法制现代化历程,第一次被革命打断。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应该说为在中国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随之而来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使得国人对中国制度建构的方向感到迷茫。北洋政府治下的军阀割据,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特别是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俄国政治变革的政党政治和平民路线模式,不但影响了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革命纲领和建国思想,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实行北伐推翻北洋军阀、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共同目标下,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基础。当以上目标基本实现时,两党在革命目标、策略和路线上的分歧则日益明朗,从此,国共两党代表的两种政体、两种制度之争,决定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革命法制的创建,成为延续了清末变法修律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立这幕法制现代化历史大剧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革命文化与法制现代化
自近代以来,在制度和法制变革的取向上,一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启的渐进的、经验主义的、改良主义文化观,后来的美国、日本遵循的是这条道路;一条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激进的、理想主义的、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文化观,俄国、中国遵循的就是这条道路。在谈到二者的差异时,柏克认为,法国革命以抽象的理性观念为基础,英国革命以传统的自由概念为基础;法国革命以破坏为目的,英国革命以发扬和维护传统中美好的价值为目的。[8]究竟走哪条道路,中国有过两次大的论争,一次是在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一次就是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之间。中共在1927年开启的革命道路和接下来的法制创建,无疑是法式和俄式革命的延续,在理论渊源上,从马克思到列宁,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的法制创建和苏维埃法的生成,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质。
1.法律工具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论中,阶级工具论和经济决定论被视为是看待马克思法律观点的两种主流的解释传统:法律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压迫地位较低的社会阶级的工具。[9]P266列宁也曾说,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10]P40—41在前苏联苏维埃法理论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科兹洛夫对法的工具性表述得更加生动,他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地球上首次出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创造着特殊的,前无古人的法,这不是其真正意义上的法(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制度),而是劳动者阶级镇压少数人反抗的手段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法。这毕竟还是法。”[11]P299—300从1928年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到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及其他大量的法律文件,都有这种思想的痕迹。
2.“国—社”本位思想
儒家文化强调“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皇权体制和中华法系的文化根基一直是建立在“国—家”本位基础之上的。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由、民主、法治的观念已深深溶入了西方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当中。当西方的宪政法治思想由洋务派、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陆续引入中国时,以自由为精髓的个人本位思想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国际上,进入20世纪后,个人本位思想逐渐在西方国家得到修正,国家主义逐渐抬头,像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幌子的纳粹主义,而在日本,则表现为以武士道精神为内核的军国主义。二是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导致国人对国家观念的更加强化,特别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人产生重大影响。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一文中强调“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获得完全自由”,“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这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不管是1927年至1934年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法制建设,还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六法体系”建立,国家至上的公法观和社会至上的私法观,都表露无遗。
3.政党治理的理念
政党政治发端于英国,至20世纪初已成为欧美国家政治运行的基本形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利用政党斗争夺取政权的成功范例,“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方略,从此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理念。党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管理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力量和系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法律上突出地表现为由党立法,司法党化。例如,井冈山根据地最早正式的发布法律文件《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就是由毛泽东指派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军队党组织——前委会议上通过后,便在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宣读颁布的。整个国民党时期,也是从党的主义产生法理,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立法,影响司法,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法制的基本特征。
[1]王宏选.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的法律—卢曼和托依布纳的法律概念[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5).
[2]卢曼.社会的法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李楯.法律社会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5]孙立平.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及其特征[J].社会学研究,1991(1).
[6]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J].中国社会科学,1990(5).
[7]马勇.清亡启示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8]柏克.法国革命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10]列宁.列宁全集(第2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杨心宇.[俄]谢尔盖·沙赫赖.[俄]阿利克·哈比布林.变动社会中的法与宪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