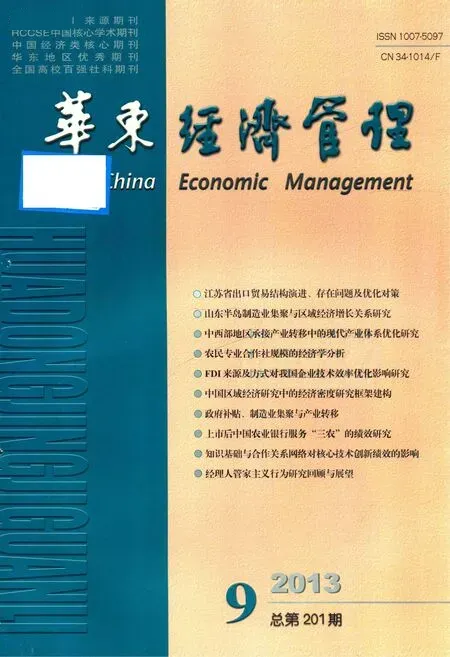经理人管家主义行为研究回顾与展望
刘 云,张文勤
(1.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2.南京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一、引言
企业经理人到底为谁谋幸福?多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领域讨论的主要话题。公司治理研究萌芽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主要探讨委托人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司治理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视角来研究委托人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即代理主义(agency)视角和管家主义(stewardship)视角。
基于“经济人”假设,代理主义视角把经理人视为代理人(agent),从而形成代理主义理论(agency theory)[1]。代理主义理论认为,经理人都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和自利的(self-serving),追求马斯洛所提出的低层次需要(生理、安全、经济)的满足,行为受到外在动机的驱使,组织认同感较低,与委托人之间的利益和目标是相互冲突的,是不可信任的。由于委托人与经理人利益追求不同、风险态度不同以及信息分布不对称,经理人行为是否符合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代理主义理论认为,为了处理委托人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委托人寻求通过监管(monitoring)和诱因安排(in⁃centive alignment)方式激励经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监管通过董事会来进行,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董事会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如报告、审计、规则等)来实现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趋同。诱因安排是指,通过把代理人的报酬与代理人的绩效联系起来的薪酬方案来实现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趋同。
与代理主义视角相反,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管家主义视角把经理人视为公司资产的管家(steward),从而形成管家主义理论(stewardship theory)[2]。管家主义理论认为,经理人是集体主义的(collectivistic)、利他的(others-serving)、追求马斯洛所提出的高层次需要(如自尊、自我实现等)的满足,行为主要受到内在动机的驱使,组织认同感较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是相容的,是可信任的。此外,该理论表明,代理主义理论所列举的控制机制可能会为生产效率带来负面作用,因为管家已经受到内在激励而产生有利于组织目标的行为,控制反而会削弱管家按照有助于股东的利益行事的动机,相反,公司应该设计出能产生高承诺和高投入导向的环境,如授权型组织结构。
自从Donaldson 和Davis 于1991年提出管家主义理论后,大量学者卷入到了经理人管家主义行为(managerial steward⁃ship behavior,下文简称管家主义行为)的研究浪潮中来,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20多年来管家主义行为研究的现状进行回顾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二、管家主义行为的概念内涵
关于荷兰小孩的传奇故事可以说是管家主义行为或者管家主义精神的生动例子。据说以前荷兰有个小男孩,路过一座堤坝,看到堤坝上有个小孔,他知道万一溃坝,海水就会涌进来,造成大灾难。于是,小男孩用手指塞入小孔,一动不动,直到大人发现他。这个勇敢而有毅力的小男孩故事流传甚广。
学者们关于管家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管家主义的概念内涵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以下是几家代表之言。
管家主义的早期定义主要强调决策者要超越自己的个人利益,采取行动和做出决策来为组织或股东的利益服务。例如,管家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针对社会群体或机构的人性关怀、慷慨、忠诚和奉献[3]。组织管家是指这样的人,他们表现出对组织最佳利益的承诺,他们与代理人不同,代理人的利益可能与组织及其委托人的利益相反[4]。管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最大化组织的潜能来追求长期的财富,同时通过追求集体目标来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的双赢[5]。基于代理主义理论和管家主义理论的思想,Martynov(2009)定义了类代理人行为和类管家行为,类代理人行为(agent-like behavior)是指经理人以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服务于自己的利益的行为;类管家行为(steward-like behavior)是指经理人关注组织整体的成功,当经理和委托人之间存在物质利益冲突时,经理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6]。
管家主义的定义后来有所发展,就是决策者除了考虑股东的利益,还要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考虑进来。管家主义的概念已经进化到既包括对机构利益的委托性义务,也包括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道德性义务。例如,管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是为了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行动,他们认同并承诺于组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7]。Caldwell 和Karri (2005)也扩展了管家主义的内涵,认为管家主义涵盖了针对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责任,承认组织治理与组织环境系统匹配的重要性[8]。Hernandez(2007)把管家主义定义为,把群体的长期最佳利益放到个人自我利益之前的态度和行为,它体现在领导运用组织权力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的程度[9]。
最近,有学者认为管家主义的概念不仅仅适用于企业经理人,同时也适用于组织员工,于是提出了适合任何组织成员的管家主义行为定义。例如,Hernandez(2012)在契约关系(covenantal relationship)理论的基础上定义了管家主义行为[10]。Hernandez 认为,个体与组织之间存在着隐性的契约关系,该契约关系代表了一种道德承诺,要求双方朝着共同目标而努力,而不是相互利用。这种契约关系隐含着双方的共同义务,个体通过牺牲短期的个人目标来追求长期的集体目标来体现他们对此契约关系的遵守。因此,Hernandez把管家主义行为定义为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从事保护他人长远利益的行为,管家主义反映了一种对他人的义务或责任感。
总之,关于管家主义的概念内涵,学者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管家是仅仅服务于股东还是服务于组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另外一方面是,管家主义概念是仅仅适用于经理人层面还是适用于包括员工的所有组织成员。
三、管家主义行为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Block(1996)认为,管家主义的本质就是“超越自我利益的服务”[11]。管家主义行为从理论上和概念上区别于利他主义(altruism)和组织公民行为(OCB)等其他亲社会行为概念。
利他主义是一个以增加他人福利为终极目标的动机状态[12]。研究表明,共情(empathy)导致了利他行为,当个体体验到了共情的时候,个体可能按照有助于他人的方式行事,而不顾自己的福利[13]。当个体有权在群体成员中分配福利的时候,有高度共情体验的个体将选择把资源分配给他或她所共情的成员[14]。然而,像利他主义这样的自我牺牲行为并没有考虑集体的利益,通过服务于单个受益人,由共情所引发的利他行为可能会侵蚀集体的利益[15]。相反,像管家主义行为这样的自我牺牲行为旨在有益于集体目标,管家主义行为服务于集体的利益。因此,管家主义是一个比利他主义更胸襟宽阔的概念,驱使决策者关注更为广泛的受益人。
组织公民行为是个体自主决定的,不被组织正式奖励系统所直接或间接认可,但会提升组织效能的行为[16]。帮助同事、建言、积极参与团队会议和在外维护公司形象等行为是组织公民行为的普遍例子。尽管组织公民行为有助于提高组织效能,最终能延长组织的寿命,但是从事组织公民行为的个体初衷未必在于确保那样的长期效应。相反,管家主义行为的出发点必须是关注集体的长远利益,从事管家主义行为的个体考虑自身行动给受益人利益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并做出牺牲来确保集体的长期利益[17]。因此,管家主义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考虑受益人利益所采用的时间跨度上,组织公民行为着眼于受益人的短期利益,而管家主义行为着眼于受益人的长期利益。
总之,管家主义行为与其他亲社会行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主要区别在于,管家主义行为拥有两个独特特征:集体导向,即关注利益相关者整体的利益;长期导向,即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同时,管家主义行为与其他亲社会行为的共同点在于这些概念都具有他人导向的性质,即关注他人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
四、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因素
从文献看来,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个人层面和环境层面来分别阐述。
(一)个人层面因素
在描述影响管家主义的心理因素时,Davis等(1997)指出,集体导向的管家主义行为通常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发生:第一个情形是,个体的行为受到内在动机的驱使,例如,管家行为会发生在自我实现(self-actualizing)需求或者自我领导需求较高的个体身上;第二个情形是,个体拥有高水平的组织认同感,因为认同一个组织并接受其价值观的经理不会体验到与组织之间的目标冲突[7]。Davis等(2007)通过100家公司的CEO 和董事进行调查,检验了Davis等在1997年提出的管家主义的前因变量,结论表明,投入(involvement)、文化(culture)和高层次需要(higher-order need)等三个变量能预测公司CEO的管家主义行为[18]。
Martynov(2009)认为,经理人的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和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可以预测经理人是按照自私自利的方式(像代理人)行事还是按照服务于组织利益的方式(像管家)行事[6]。个人的道德发展包括前习俗水平(pre-conventional level)、习俗水平(conventional lev⁃el)和后习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level)[19]。道德动机是指个体坚持行为的道德原则,把道德价值观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并为道德结果承担个人责任的程度(Rest,1986)[20]。Martynov 认为,代理主义行为包括利己的代理主义行为(self-serving agent-like behavior) 和利他的代理主义行为(others-serving agent-like behavior)。与处于其他道德发展水平的经理相比,处于前习俗水平的经理更可能表现出利己的代理主义行为;与处于前习俗水平的经理相比,处于习俗水平的经理更可能表现出管家主义行为;与处于其他道德发展水平的经理相比,处于后习俗水平的经理更可能表现出利他的代理主义行为;道德动机的强度将调节以上命题的关系,也就是说,经理人按照自己道德价值观行动的道德动机越强,以上命题关系就越强。
为了探索在家族企业中管家主义行为的形成条件,Da⁃vis,Allen,Hayes(2010)实证检验了员工的企业价值观承诺(value commitment)、员工对企业领导的信任(trust)、员工的代理主义知觉(perceptions of agency in leaders)对员工的管家主义知觉(perceived stewardship in leaders)的影响,同时就家族成员(family members)与非家族成员(non-fami⁃ly members)两个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结论表明,家族成员的价值观承诺与其管家主义知觉正相关,而非家族成员的价值观承诺与其管家主义知觉的相关性不显著;家族成员对企业领导的信任正向影响其管家主义知觉,非家族成员对企业领导的信任也正向影响其管家主义知觉;家族成员的代理主义知觉将负向影响其管家主义知觉,然而非家族成员的代理主义知觉对其管家主义知觉的影响不显著;与非家族成员相比,家族成员更加承诺于企业的价值观和更加信任企业的领导;非家族成员通常感知到企业领导具有更高水平的代理主义,然而家族成员通常感知到企业领导具有更高水平的管家主义[21]。
(二)环境层面因素
在描述影响管家主义的情境因素时,Davis等(1997)指出,国家文化是管家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他们分析了国家文化的两个维度,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对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在集体主义文化里面,经理可能表现出管家主义行为,在高权力距离文化里面,下属让渡权力给上级经理,经理们接受官僚层级结构赋予的角色,不太可能有与委托人冲突的方式行为[7]。另外,控制导向(control oriented)的管理哲学更可能产生代理主义,投入导向(involvement oriented)的管理哲学更可能产生管家主义[7]。
Putnam(2000)认为,管家主义最容易产生于关系稳定、存在显著相互依赖和互动的群体中,以及当人们享有一个类似的社会网络时候[22]。Corbetta &Salvato(2004)指出,在家族企业中出现管家主义的条件包括,家族对企业拥有高度的认同感和承诺感(超出外在动机)、家族和企业之间具有一致的价值观、公司具有长远发展导向等[23]。
Hernandez(2008)探讨了上司的领导行为对下属的管家主义的影响。Hernandez认为,下属的管家行为是上司领导行为的结果,上司的领导行为让下属产生了一种为了组织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服务的个人责任感。Hernandez阐述了上司通过关系支持型(relational supportive)、动机支持型(motivation⁃al supportive)和情境支持型(contextually supportive)等三种领导行为在下属身上培育了管家主义[17]。
Breton-Miller 和Miller(2009)探讨了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对家族企业领导管家主义的影响[24]。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是指决策者的经济行为和这种行为发生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决策者是嵌入在多重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系统对决策者的影响表现各异,系统成员会帮助决策者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因此,那些嵌入家族而不是公司的家族企业领导们将倾向于关注狭隘的、自私的家庭利益,体现出代理主义;然而那些更多地嵌入公司的家族企业领导们将更加关注公司的利益,体现出管家主义。
Miller等(2008)探讨了企业类型对经理人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25]。他们把家族企业分为家庭企业(family owned businesses)和非家庭企业(non-family owned businesses),家庭企业由家庭成员共同拥有和管理,非家庭企业仅仅被创始人拥有和管理着,没有其他亲属卷入到经营中。他们认为,家族企业的管家主义体现在公司领导们全神贯注于确保公司的持续经营(continuity)、培育员工社区(community)和紧密联系顾客(connections)三方面。通过对加拿大西部的中小家族企业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非家庭企业相比,家庭企业在产品开发、声誉开发和市场开发等方面进行更多的长远投资,从而在公司的持续经营方面展现了更多的管家主义;与非家庭企业相比,家庭企业在培育员工社区方面体现更多的管家主义,特别地,它们更可能进行员工培训、广泛使用员工的技能、更加弹性和包容、保留全员;与非家庭企业相比,家庭企业在顾客联系方面也体现了更多的管家主义,它们与顾客建立私人联系,同时缩小目标顾客群的范围。
总之,关于经理人管家主义的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个体层面因素集中在动机(内在动机)或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组织认同感、工作投入度、道德发展水平和道德动机、企业价值观承诺、对领导的信任、家族成员或非家族成员身份等方面。环境层面因素集中在国家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经营哲学(控制导向或投入导向)、群体成员相互依赖性和社会网络相似性、企业文化、上司的领导行为、社会嵌入和企业性质等方面。
五、管家主义行为产生的心理历程
有三项研究对管家主义行为产生的心理过程进行了阐述。
Hernandez(2007)描述了关系性支持(relational sup⁃port)、动机性支持(motivational support) 和情境性支持(contextual support)三个因素分别对下属管家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在这些影响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9]。具体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Hernandez 提出的模型
Hernandez认为,领导通过表现出对下属的需要和兴趣的关注、尊敬和公平,在下属与领导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从而创造了关系性支持。领导通过把组织远景沟通给下属,促进协调,形成凝聚感,在下属与组织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从而创造了一种情境支持。关系性支持(下属与领导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情境支持(下属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共同形成了动机性支持,从而激发下属的内在动机来为组织事业服务。
Hernandez假设,关系性支持、情境性支持和动机性支持分别直接正向地影响管家主义;关系性支持和情境性支持也分别直接正向地影响动机性支持;关系性支持、情境性支持和动机性支持对管家主义的影响分别受到道德勇气的完全中介。
Pearson 和Marler(2010)把管家主义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结合起来解释家族企业中员工管家主义发生的心理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Pearson和Marler 提出的模型
首先,在家族企业中,领导的管家行为或管家主义动机可以在整个公司中建立管家主义文化。作为公司的管家,领导更可能关注员工的利益,做出对员工有利的行为,例如雇佣的持续性,安排挑战性工作,学习新经验的机会,以及其他员工认为是支持性的和积极性的行为。当领导表现出管家主义以后,根据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和互惠规范,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就形成了,员工可能变得更加承诺于组织,同时也愿意按照组织和领导的利益做事(例如亲社会行为或公民行为),从而在员工身上也体现了管家主义。员工表现出的管家主义反过来也促进或强化了领导的管家行为动机。
其次,家族企业领导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企业中培育互惠性管家主义。家族企业领导与家族成员之间先前形成的良好人际关系、沟通方式、互动方式、行为规范以及共享目标等因素构成了家族社会资本。这个家族社会资本移植到公司就成了公司竞争优势的源泉,并有助于高质量领导—成员关系的快速形成,进而培育互惠性管家主义。
最后,家族企业领导的管家动机或管家行为能否换来员工的信任和对组织的承诺,取决于员工是否具有家族成员身份。与非家族成员相比,家族成员往往更容易知觉到公司领导身上的管家主义,也更容易对领导产生信任感和对公司产生承诺感。另外,家族企业领导的管家动机能否在整个公司建立互惠的管家主义文化取决于家族企业领导权力的集中程度。家族企业可以由创始人领导,也可以由家族成员共同领导,不过,互惠的管家主义文化在创始人领导的企业中更容易形成,因为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这种组织形式权力更为集中。
Hernandez(2012)描绘了个体管家主义行为的心理过程模型,如图3 所示。该模型中,组织层次的结构因素对个体的认知机制和情感机制产生跨层次影响,认知机制和情感机制共同导致个体的管家主义行为,心理所有权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时个体的管家主义行为又反向强化了组织层次的结构因素。

图3 Hernandez 提出的模型
首先,代理主义理论提出了通过规则和制度来限制员工行为的公司治理模式,代理主义理论勾画出组织如何通过诸如外在报酬(如薪水、红利、股票期权)、外部控制(如董事会、外部股东)和威胁(如收购、市场竞争)等手段把经理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协调起来;管家主义理论也提出了一套公司治理模式来促进员工为组织目标做出贡献,关注集体的利益。管家主义治理模式与一些结构因素相关,如管理实践、领导、政策、程序、系统和规则等,Hernandez把这些结构因素分为控制系统(Control Systems)和报酬系统(reward systems)。控制系统在组织中培育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员工的自治水平,强调员工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责任;报酬系统进一步点亮工作的内在价值,旨在培养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决定感,给员工带来内在报酬。
其次,在结构因素的影响下,个体按照如下的认知机制进行决策:①着眼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关注他人视角(other-regarding perspective);②着眼于他人的长期福利,即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也就是说,通过在权衡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决策过程中强调公共财富,个体的管家行为为受益者创造了长期福利。另外,结构因素强调员工的成长,显示了组织对成员的关心,从而强化了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由控制系统和报酬系统构成的管家主义治理结构促进了个体对组织的心理所有权,当个体感知到了这种心理所有权,他们就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证组织的长期福利,从而产生管家主义行为。最后,由于个体不能直接回报前任领导的决策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当他们成为领导后将采取同样的决策来对待未来的下属,以此来进行回报,这个现象叫代际互惠(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27]。因此,通过仁慈的代际互惠规范,个体的管家主义行为将反过来影响组织的控制系统和报酬系统。
总之,以上三位学者探讨了环境因素对个体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因素在这个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传导作用,这样有助于大家对个体管家主义行为形成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六、管家主义行为的测量
Davis等(2007)用实证的方法验证了Davis等在1997年提出的管家主义前因变量模型,让100 家公司的董事们填写问卷来测量他们各自公司的总经理所表现出的管家主义[18]。该研究初步开发了8 个条目的问卷来测量公司总经理的管家主义。因子分析结果表明,8个条目形成了2个维度,解释了56.4%的方差,第一个成分包括5个条目,反映了管家主义,第二个成分包括3 个条目,与管家主义无关。在接下来的统计分析中用到了第一个成分中的5 个条目。具体条目包括:我的战略举措为公司的利益服务;我的预算举措为公司的利益服务;我用职权为公司的利益服务;我用我的特权为公司的利益服务;我向董事会提供充分和及时的公司信息。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9。
Davis,Allen,Hayes(2010)调查了315 个家族企业中的366 个员工样本,测量员工对公司领导管家主义的知觉[21]。他们在Davis 等(1997)的管家主义理论模型和Davis 等(2007)开发的量表基础上,发展了3个条目的里克特量表来测量领导的管家主义。被调查者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到公司领导们表现出管家行为,量表的具体条目包括:我公司的领导们的举措更多地服务于公司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我相信我公司的领导们怀有具有公信力和吸引力的举措;我公司的领导们更多地采取长期导向而非短期导向的经营方针。该管家主义量表的信度系数是0.70。
Hernandez(2007)发展了一个管家主义行为量表,该量表包括3 个维度,即个人责任行为、内部平衡行为和内外部平衡行为[9]。个人责任行为强调领导者接受与领导岗位相关的监管责任,信度系数为0.83,具体条目包括:接受个人的监管责任;恰当使用领导角色解决重要问题;努力成为公司的好代表;按照好领导的行为标准来行动。内部平衡行为强调领导者要平衡自我与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信度系数为0.73,具体条目包括:平衡自己部门或单位与组织整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自己和组织之间的利益;愿意接受有益于组织长期利益的个人挑战。内外部平衡行为强调领导者要平衡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信度系数为0.76,具体条目包括:帮助他人明白平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重要性;寻求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平衡。整个量表包括9个条目,总的信度系数为0.87。
Martynov(2009)提出了管家主义行为的测量方式[6],这些条目包括:根据委托人的利益要求而行为,不必顾虑自己的物质后果;废寝忘食地工作,即使没有要求自己这样做;竭尽全力地工作,而不必考虑是否受到监督;把公司出售给最高价竞买人(这对股东来讲通常是好事),而不顾个人后果。不过,Aleksey Martynov只是提出了管家主义行为的测量工具,而没有利用该量表进行实证,因此其信度和效度无从考证。
Kuppelwieser(2011)探索了领导管家主义行为与下属创造力之间的关系[28]。在Hernandez 于2007年开发的量表基础上,Kuppelwieser形成了测量管家主义行为的工具,包括4个条目,具体为:愿意接受任何个人挑战,只要这些挑战服务于组织的长期利益;愿意接受任何个人挑战,只要这些挑战服务于团队的长期利益;帮助他人明白平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重要性;恰当使用领导角色来解决重要问题。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8。
总之,已有研究要么把管家主义行为视为3 个维度的构念,要么视为1 个维度的构念,不过大多数研究者接受1 个维度的观点。
七、管家主义行为研究展望
尽管管家主义概念在目前管理文献中出现较为频繁,但对管家主义的形成条件仍然保持贫乏地理解,而且,关于管家主义的结果变量也知之甚少。未来的研究可以朝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
(一)探讨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因素
个体特征会影响到经理人的管家主义行为倾向,尽管已有研究解释了部分心理因素对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但几乎没有研究者探讨人格特质(比如“大五”人格、控制源取向等)对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偏重。另外,经理人的行为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今天的“代理人”也许会成为明天的“管家”,或者相反。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探索决定经理人表现管家主义行为或者代理主义行为的环境因素。
(二)探讨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效果
关于经理人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结果,已有文献探讨得比较少,主要的结果变量涉及公司绩效和竞争优势。例如,Miller 和Le Breton-Miller(2006)认为,经理人管家主义导致公司不必花费更多成本来监督经理人的行为,把节省出来的资源投向公司创业,从而给家族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竞争优势[29]。经理人管家主义也被认为能对公司的战略弹性有贡献,进而增强了组织绩效[30]。Kuppelwieser(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领导管家主义有助于下属的创造力[29]。未来的研究可以在经理人管家主义的影响结果方面进行拓展。例如,由于公司管家的目标是追求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经理人行为的结果可能促进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反过来讲,由于外界要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经理人不得不做出满足社会呼吁的利他主义努力,从而促使经理人表现出更多的管家主义行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经理人管家主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另外,Martynov(2009)指出,并不是所有管家主义行为都会对组织有利,与一个高度合格的努力最大化自己物质利益的代理人相比,一个努力按照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行为的不胜任的管家可能给委托人带来更大的损害[6]。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管家主义行为与结果变量之间的调节因素。
(三)加强对员工管家主义行为的研究
管家主义行为不仅仅限制在管理层,每个员工都可以扮演一位管家并追求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管家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类型,旨在对他人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由于个体不必通过职位权力或权威来保持与组织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管家主义行为也能够在员工身上发生[10]。Davis等(1997)也指出,与来自组织正式职位的制度权力相比,超越正式角色而形成的持久性个人权力更能代表管家主义的特征[7]。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把经理人管家主义概念延伸到员工层次,探讨员工管家主义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
(四)加强集体层次的管家主义行为研究
不管是探讨经理人管家主义还是员工管家主义,这样的研究都是个体层次上进行的分析。其实,管家主义不仅能体现在个体层次,也能够体现在集体层次,即团队管家主义或组织管家主义。团队管家主义可以通过团队成员关于团队作为整体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管家主义的共享知觉来测量,组织管家主义可以通过组织成员关于组织作为整体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管家主义的共享知觉来测量。Schepers,Jong,Ruyter(2010)已经在集体管家主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研究,他们把团队管家主义定义为“为了组织和顾客的利益而监督和提升服务团队绩效的集体责任感”,并用西欧几家国际汽车制造企业的30个顾客服务团队样本实证了权变奖励(Contingent reward)、结构关联性(structural relatedness)、情感关联性(affective relatedness)、自主性(autonomy)等因素对团队管家主义的影响,以及团队管家主义对团队成员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的影响[31]。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就管家主义进行集体层次的分析或者进行集体层次与个体层次的跨层次分析。
(五)探讨管家主义气氛或管家主义文化
学者们已经分别从个人角度和环境角度探讨了经理人管家主义的影响因素,不过库尔特.勒温认为,为了理解和预测行为,就必须把人及其环境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因素的集合,并称之为个体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行为发生在这种生活空间之中,它既是人和环境的函数,也是生活空间的函数。在生活空间概念基础上,勒温提出了心理气氛(psycho⁃logical climate)和社会气氛(social climate)的概念[32]。未来的研究可以把个人和环境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在管家主义气氛的概念框架上研究经理人管家主义行为的动力机制。
另外,个别学者在管家主义文化方面做了开创性研究,例如Eddleston(2008)认为,与转换型领导具有鼓舞下属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顾自己的利益的作用相似,公司管家主义导向(stewardship orientation)也能激励员工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而行动。据此,Eddleston提出一个理论框架,转换性领导风格通过影响公司的管家主义导向,继而影响到公司的战略弹性(strategic flexibility),其中管家主义导向包括管家主义动机(stewardship motivation)和管家主义文化(steward⁃ship culture)两个方面[33]。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企业管家主义文化对个体管家主义行为的影响。
[1]Jensen M C,Meckling W Y.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2]Donaldson L,Davis J.Stewardship theory or agency theory:CEO governance and shareholder returns[J].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6:49-65.
[3]Donaldson L.The ethereal hand: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or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1990,15(3):369-381.
[4]Hill C W L,Jones T M.Stakeholder-agency theory[J].Th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2,29(2):131-155.
[5]Hosmer L T.The Ethics of Management[M].Chicago:Irwin,1996.
[6]Aleksey Martynov.Agents or stewards?Linking managerial be⁃havior and mor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9,90:239-249.
[7]Davis J H,Schoorman F D,Donaldson L.Toward a steward⁃ship theory of manage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20-47.
[8]Caldwell C,Karri R.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and ethical choices:A covenantal approach to building trust[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5,58(1):249-259.
[9]Hernandez M.Stewardship: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test of its determinants[D].Dissertation:Duke Univer⁃sity,2007.
[10]Hernandez M.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y of stewardship[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2,37(2):172-193.
[11]Block P.Stewardship:Choosing Service Over Self-interest[M].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1996.
[12]Batson C D.Prosocial motivation:Is it ever truly altruistic?[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87,20:65-122.
[13]Batson C D,Oleson K C.Current status of the 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J].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1,12:62-85.
[14]Batson C D,Klein T R,Highberger L,Immorality from empa⁃thy-induced altruism:When compassion and justice conflic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8:1042-1054.
[15]Batson C D,Batson J G,Todd R M,et al.Empathy and the collective good:Caring for one of the others in a social dilem⁃ma[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b),68:619-631.
[16]Organ D W.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It's con⁃struct cleanup time[J].Human Performance,1997(10):85-97.
[17]Hernandez M.Promoting stewardship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A leadership model[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80:121-128.
[18]Davis J,Frankforter S,Vollrath D,et al.An empirical test of stewardship theory[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Leadership:Research,Practice,and Teaching,2007,3(1):40-50.
[19]Kohlberg L.Stage and Sequence: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C]//D A Goslin.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Chicago:Rand McNally,1969.
[20]Rest J R.Moral Development: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M].New York:Praeger,1986.
[21]Davis J H,Allen M R,Hayes H D.Is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A study of stewardship perceptions in family busines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0(12):1093-1115.
[22]Putnam R.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New York:Simon &Schuster,2000.
[23]Corbetta G,Salvato C.Self-serving or self-actualizing?Mod⁃els of man and agency costs in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firm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4,28(4):355-362.
[24]Breton-Miller I L,Miller D.Agency vs.Stewardship in Pub⁃lic Family Firms:A Social Embeddedness Reconciliation[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9,11:1169-1191.
[25]Danny Miller,Isabelle Le Breton-Miller,Barry Scholnick.Stewardship vs.Stagnation: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Small Family and Non-Family Business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8,45(1):51-78.
[26]Pearson A W,Marler L E.A leadership perspective of recip⁃rocal stewardship in family firm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0(11):1117-1124.
[27]Wade-Benzoni K A.A golden rule over time: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decis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1011-1028.
[28]Kuppelwieser V G.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Creativity[J].Management Revue,2011,22(3),274-295.
[29]Miller D,Le Breton-Miller I.Priorities,practices and strate⁃gies in successful and failing family businesses:An elabora⁃tion and test of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J].Strategic Organization,2006,4(4):379-407.
[30]Zahra S A,Hayton J C,Neubaum D O,et al.Culture of fami⁃ly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ewardship[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8(12):1035-1054.
[31]Schepers J,Jong A D,Ruyter K D.Team stewardship in cus⁃tomer service teams: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AMA Winter Educators'Conference Proceedings,2010,21:109-110.
[32]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3]Eddleston K A.The Prequel to Family Firm Culture and Stewardship:The Leadership Perspective of the Founder[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8(11)1055-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