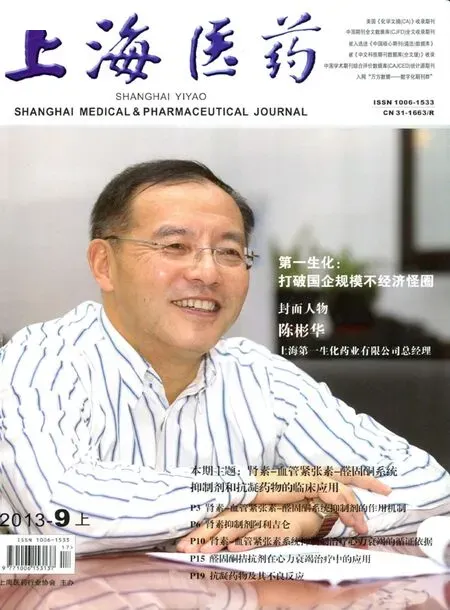醛固酮拮抗剂在心力衰竭治疗中的应用
高修仁 黄至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 广州 510080)
醛固酮拮抗剂已被有关治疗指南推荐治疗心力衰竭。本文概要介绍醛固酮拮抗剂的作用机制、循证医学证据和注意事项等。
1 对醛固酮致病的认识史
早在50年前,Luetscher和Johnson就观察到在患有心力衰竭的成年人和孩子的尿液中含有某种具有潴留钠离子特性的类固醇激素。随后,Davis等[1]通过选择性的静脉血采样和液相色谱法分析,确认此物质是心力衰竭时由肾上腺过度分泌的激素,命名为醛固酮。以后研究发现,在心力衰竭患者中,尽管最大限度地阻断了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但血清醛固酮水平仍然升高(这就是所谓的“醛固酮逃逸”现象),且其升高程度与疾病的严重性和预测的死亡率相关[2]。研究认为醛固酮是一个可促进心室和血管重塑以及心力衰竭进展的强有力的介质。
醛固酮是一种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其病理性增加与肾上腺分泌增多、组织器官自分泌和肝脏清除率下降等有关[3]。在心力衰竭患者中,促进醛固酮分泌的主要因素包括血管紧张素Ⅱ、血清钾浓度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等,而醛固酮对心脏具有促进心肌细胞肥大和间质纤维化的作用。新近进行的转基因小鼠模型实验证实,心脏特异性的11β-羟基固醇2型脱氢酶的过度表达和盐皮质激素受体的激活会导致心脏的向心性重塑、心肌纤维化并诱发动物早期死亡[4],但给予醛固酮拮抗剂治疗可使重塑得以改善、生存率亦得到提高。
2 醛固酮的致病机制
病理性醛固酮分泌增多对机体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在心力衰竭患者中,醛固酮主要通过对心脏、血管系统和肾脏的多效性作用促进重塑以及影响心力衰竭的发生和发展(表1)。

表1 醛固酮在心力衰竭发生和发展中的多效性
2.1 水-钠潴留与促进心肌重塑作用
心力衰竭时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激活,醛固酮合成和分泌增加且与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短期内可以增加心排量而起到代偿作用,但长期却会引起水-钠潴留、电解质紊乱和心力衰竭加重。醛固酮可增加钾、镁排泄,加重低钾、低镁血症,增加心力衰竭患者的室性心律失常和猝死的危险[5-6]。
2.2 醛固酮逃逸现象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ACE)抑制剂已成为慢性心力衰竭药物治疗的基石,短期使用ACE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Ⅱreceptor blocker, ARB)均可以降低循环中的醛固酮水平。不过,长期(3个月以上)使用ACE抑制剂后,循环醛固酮水平却不能保持持续的降低而反有所增高,出现醛固酮逃逸现象[7]。这种现象不能用糜酶旁路来解释,且联合使用ACE抑制剂和ARB也不能完全长期抑制醛固酮的产生。
2.3 致心肌缺血和心律失常作用
研究表明,醛固酮可致心肌纤维化而损伤大动脉顺应性,致心肌肥厚使冠状动脉储备能力下降;可阻断心肌对儿茶酚胺的摄取而增强交感神经活性,增加心率和心肌耗氧量。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基线血浆醛固酮水平与血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低镁血症会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而引起心肌缺血。此外,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内皮功能受损、心肌纤维化、交感神经活性增加、副交感神经活性降低以及钾、镁的丢失使组织传导的不均一性增加,这些均可诱发室性心律失常,从而增加心源性猝死危险。
3 醛固酮拮抗剂的药理学
醛固酮通过与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而产生作用。醛固酮拮抗剂现有两个药物,分别是螺内酯和伊普利酮。螺内酯是一个化学结构与孕酮相似的非选择性醛固酮拮抗剂,除有拮抗醛固酮的作用外,因还可在受体结合位点抑制双氢睾酮的作用以及可在外周血中促进睾酮向雌二醇转化[8],故存在会引起男性乳腺发育、性无能以及女性月经失调等副作用。伊普利酮是一个选择性醛固酮拮抗剂。与螺内酯相比,其对雄激素受体、糖皮质激素受体和孕酮受体的亲和力弱100~1 000倍[9]。因此,使用伊普利酮治疗不会出现螺内酯样的抗雄激素副作用。
4 醛固酮拮抗剂的循证医学证据
至今已有数个醛固酮拮抗剂进行过用于治疗心力衰竭和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下降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
4.1 治疗纽约心脏协会(New Yo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级Ⅲ~Ⅳ级患者的研究
1999年发表的“RALES”研究是历史上第一个考察在标准疗法的基础上加用醛固酮拮抗剂治疗严重心力衰竭患者疗效的临床研究,其共入选了1 663例NYHA心功能分级Ⅲ~Ⅳ级、LVEF≤35%的患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5±12)岁、平均LVEF为25.6%±6.7%、血肌酐水平<2.5 mg/dl,其中95%的患者在接受ACE抑制剂、11%的患者在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螺内酯的平均使用剂量为26 mg/d。平均随访24个月后发现,与单用标准疗法相比,加用螺内酯治疗能降低31%的全因死亡率(主要终点,RR=0.69, 95% CI为0.58~0.82,P<0.001)[10],同时降低因心力衰竭的住院率、因心血管事件的住院率和心脏相关死亡率,且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者仍可因加用螺内酯治疗而获益。以每年安慰剂组的死亡率27%计算,平均每9个坚持加用螺内酯治疗2年的患者中就有1人因此而获救。
4.2 治疗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患者的研究
“EMPHASIS-HF”研究是一项考察伊普利酮作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共入选2 737例年龄>55岁、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LVEF≤35%的患者,但排除了预测的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us filter rate,GFR)<30 ml/(min·1.73 m2)或血钾水平>5.0 mmol/L的患者。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8.7±7.7)岁,平均LVEF为26.2%±4.6%。绝大部分的患者正在使用ACE抑制剂或ARB(约94%)以及β-受体阻滞剂(87%)治疗。平均随访21个月后的结果显示,使用伊普利酮治疗可以减少27%的心血管死亡或因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主要终点,HR=0.63, 95% CI为0.54~0.74, P<0.001)以及24%的全因死亡率(校正后的HR=0.76, 95% CI为0.62~0.93, P<0.008)[11]。以每年安慰剂组的死亡率7.1%计算,每51(95% CI为32~180)个使用伊普利酮治疗患者中就有1人的死亡得以延迟。
另有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在轻度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考察了坎利酮(为螺内酯在体内的活性代谢物)的抗心脏重塑作用。该研究共入选了467例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并有心力衰竭症状、LVEF≤45%且正在接受最佳基础治疗的患者,他们分别再随机接受坎利酮或安慰剂治疗。坎利酮的平均使用剂量为44 mg/d。随访12个月后的结果显示,坎利酮组患者的LVEF增加值稍高于安慰剂组[分别为(39.9%±8.6%)~(45.1%±9.6%)和(39.7%±8.6%)~(42.9%±9.7%), P=0.04],但复合终点心脏性死亡或住院率较安慰剂组显著降低(分别为7.9%和15.1%, P=0.02)[12]。
4.3 治疗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患者的研究
在2003年发表的“EPHESUS”研究中,心肌梗死后3~14 d、LVEF≤40%并有心力衰竭症状的患者被随机分为伊普利酮和安慰剂治疗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4±11)岁,平均LVEF为33%±6%。大部分患者已在接受基础治疗,如ACE抑制剂或ARB(86%)和β-受体阻滞剂(75%)治疗。伊普利酮的平均使用剂量为43 mg/d。平均随访16个月后发现,伊普利酮治疗组的复合终点和全因死亡率都降低了15%(均RR=0.85,95% CI为0.75~0.96),同时心血管死亡或住院率也下降13%(RR=0.87, 95% CI为0.72~0.94),全因住院率(RR=0.92, 95% CI为0.86~0.98)和心血管死亡率(RR=0.83, 95% CI为0.72~0.94)亦降低[13]。以每年安慰剂组的死亡率13.6%计算,每年每50个坚持服用伊普利酮的患者中就有1人因此而获救。
5 相关指南对醛固酮拮抗剂的推荐
1999年“RALES”研究结果公布后,2003年各相关指南就推荐NYHA心功能分级III~IV级、LVEF<35%的重度心力衰竭患者使用醛固酮拮抗剂治疗(Ⅰ类推荐,证据水平A级)。201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公布了“EMPHASIS-HF”研究结果:对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的轻度心力衰竭患者,使用伊普利酮治疗可使复合终点心血管死亡或因心力衰竭的住院率降低27%、全因死亡率和因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分别降低24%和42%[11]。因此,2013年欧洲心脏病学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发表的新指南建议:醛固酮拮抗剂适用于所有虽已接受ACE抑制剂或ARB以及β-受体阻滞剂治疗、但仍持续存在症状(NYHA心功能分级Ⅱ~Ⅳ级)的LVEF≤35%的心力衰竭患者(Ⅰ类推荐,证据水平A级),起始剂量为螺内酯25 mg/d或伊普利酮25 mg/d、靶剂量为螺内酯25~50 mg/d或伊普利酮50 mg/d。
6 螺内酯与伊普利酮的换用
由于药理学上存在差异和缺乏有关效能数据,螺内酯与伊普利酮能否换用目前并未明确。但从售价上的巨大差异看(伊普利酮25 mg/片的售价为1.34~5.02美元,而螺内酯25 mg/片的售价仅为0.15~0.42美元),螺内酯可能较伊普利酮更适宜用于临床。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在尚未对螺内酯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下就使用其来替代伊普利酮治疗是否合适?鉴于“HAYASHI”研究与“AREA IN-CHF”研究结果[12],美国的专家共识认为,如果出现售价或保险偿付问题,可考虑使用螺内酯替代治疗。
7 醛固酮拮抗剂的安全性
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孕妇禁用、男性乳腺发育及与其他药物的互相作用是使用醛固酮拮抗剂时必须注意的安全性问题。
1)严重肾功能不全。GFR<30 ml/min的患者禁用醛固酮拮抗剂或需停药。在随机研究中,醛固酮拮抗剂和安慰剂两组的总肾衰竭发生率分别为8.9%和1.6%。但在“EMPHASIS-HF”研究中,伊普利酮和安慰剂两组的肾功能不全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分别为2.8%和3.0%)。
2)高钾血症。血钾水平>5.0 mmol/L的患者禁用醛固酮拮抗剂或需停药。一项对19项随机、对照研究的系统回顾性分析发现,醛固酮拮抗剂和安慰剂两组发生严重高钾血症的患者比例分别为5.9%和3%。后续的“EMPHASIS-HF”研究发现,伊普利酮和安慰剂两组血清钾水平>5.5 mmol/L的患者比例分别为11.8%和7.2%(P<0.001)。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患者的分析发现,提高对血钾和血肌酐水平的监测频率有助于减少严重高钾血症的发生[14]。
3)孕妇禁用醛固酮拮抗剂。
4)男性乳腺发育是使用螺内酯治疗的常见副作用。Ezekowitz等研究发现,螺内酯治疗可使4%的男性发生乳腺发育(对照组为0.6%);如将乳房压痛亦认定为是男性乳腺发育时,则其发生率更高。但伊普利酮治疗组的男性乳腺发育发生率与安慰剂组相当。
5)药物相互作用。伊普利酮是细胞色素P450酶3A4同功酶的底物[15],故当同时使用具有细胞色素P450酶3A4抑制或诱导活性的药物时,伊普利酮的血清浓度会受到影响。同时使用细胞色素P450酶3A4抑制性药物会抑制体内伊普利酮的代谢、增加血清中伊普利酮的浓度而提高高钾血症的发生风险。地高辛是P-糖蛋白转运的底物之一,而螺内酯是P-糖蛋白的强力抑制剂[16]。因此,螺内酯会降低地高辛的肾脏清除率,临床上应予注意。
8 知识空缺与研究的需要
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患者几乎占全部社区心力衰竭患者的半数[17],但到目前为止还无治疗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的理想方法。过去有关醛固酮拮抗剂的临床试验均以射血分数下降患者为对象,故现对醛固酮拮抗剂在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患者中的作用仍不清楚。
此外,“RALES”研究中的LVEF入选标准为<35%,“EMPHASIS-HF”研究中的LVEF入选标准为<30%,“EPHESUS”研究中的LVEF入选标准为<40%。目前对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没有统一的定义[18],同时也缺乏LVEF在35%~45%间的患者使用醛固酮拮抗剂的数据。在评估LVEF时,在观察者之间和之内亦存在一定的差异[19]。如果现正在进行的“TOPCAT”研究未来获得阳性结果的话,则醛固酮拮抗剂很有可能会用于所有心力衰竭患者或LVEF在35%~45%间的患者。
9 结语
现有临床数据显示,醛固酮拮抗剂不仅能显著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再住院率和生存率,而且也可作为经挑选后的心力衰竭或心肌梗死后左心室功能障碍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的组分(尽管仍未得到广泛应用)。“EMPHASIS-HF”研究结果不仅为我们填补了重要的知识空缺,而且还有力地支持了应将醛固酮拮抗剂加入到经挑选的伴有LVEF降低的轻度心力衰竭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中的观点。
[1] Davis JO, Pechet MM, Ball WC Jr, et al. Increased aldosterone secretion in dogs with right-sided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nd in dogs with thoracic inferior vena cava constriction [J]. J Clin Invest, 1957, 36(5): 689-694.
[2] Swedberg K, Eneroth P, Kjekshus J, et al. Effects of enalapril and neuroendocrine activation on prognosis in severe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follow-up of the CONSENSUS trial).CONSENSUS Trial Study Group [J]. Am J Cardiol, 1990,66(11): 40D-44D.
[3] Jessup M. aldosterone blockade and heart failure [J]. N Engl J Med, 2003, 348(14): 1380-1382.
[4] Qin W, Rudolph AE, Bond BR, et al. Transgenic model of aldosterone-driven cardiac hypertrophy and heart failure [J].Circ Res, 2003, 93(1): 69-76.
[5] Pitt B. Plasma aldostero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ithout heart failure or myocardial infarction:implications for pathophsiology, prognosis, and therapy [J].Eur Heart J, 2012, 33(2): 162-164.
[6] Guglin M, Kristof-Kuteyeva O, Novotorova I, et al.aldosterone antagonists in heart failure [J]. J Cardiovasc Pharmacol Ther, 2011, 16(2): 150-159.
[7] Vijayaraghavan K, Deedwania P. 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blockade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J]. Cardiol Clin, 2011, 29(1): 137-156.
[8] Rose LI, Underwood RH, Newmark SR, et al.Pathophysiology of spironolactone-induced gynecomastia [J].Ann Intern Med, 1977, 87(4): 398-403.
[9] Struthers A, Krum H, Williams GH. A comparison of the aldosterone-blocking agents eplerenone and spironolactone[J]. Clin Cardiol, 2008, 31(4): 153-158.
[10] Pitt B, Zannad F, Remme WJ, et al. The effect of spironolactone on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heart failure. Randomized aldactone Evaluation Study Investigators [J]. N Engl J Med, 1999, 341(10): 709-717.
[11] Zannad F, McMurray JJ, Krum H, et al. Eplerenone in patients with systolic heart failure and mild symptoms [J]. N Engl J Med, 2011, 364(1): 11-21.
[12] Boccanelli A, Mureddu GF, Cacciatore G, et al. Antiremodelling effect of canrenone in patients with mild chronic heart failure (AREA IN-CHF study): final results [J]. Eur J Heart Fail, 2009, 11(1): 68-76.
[13] Pitt B, Remme W, Zannad F, et al. Eplerenone, a selective aldosterone blocker, in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J]. N Engl J Med,2003, 348(14): 1309-1321.
[14] Wei L, Struthers AD, Fahey T, et al. Spironolactone use and renal toxicity: population based longitudinal analysis[EB/OL]. [2010-07-22]. http://www.bmj.com/highwire/fi lestream/353806/ fi eld_highwire_article_pdf/0/bmj.c1768.
[15] Cook CS, Berry LM, Burton E. Prediction of in vivo drug interactions with eplerenone in man from in vitro metabolic inhibition data [J]. Xenobiotica, 2004, 34(3): 215-228.
[16] Kim RB. Drugs as P-glycoprotein substrates, inhibitors, and inducers [J]. Drug Metab Rev, 2002, 34(1-2): 47-54.
[17] Bursi F, Weston SA, Redfield MM, et al. Systolic and diastolic heart failure in the community [J]. JAMA, 2006,296(18): 2209-2216.
[18] Massie BM, Carson PE, McMurray JJ, et al. Irbesartan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J].N Engl J Med, 2008, 359(23): 2456-2467.
[19] Kalogeropoulos AP, Martin RP. Visual assessment of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the era of high definition: the machine and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J]. J Am Soc Echocardiogr, 2010,23(3): 26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