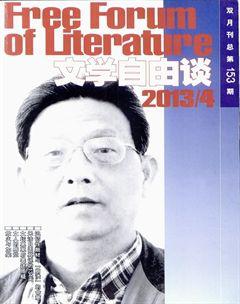茅盾的任职与解职
商昌宝
回顾历史可知,茅盾1949年后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和1965年被解职,同样充满着玄机。破解其中的文化密码,有助于我们走进和还原那段历史。
客观地说,茅盾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所谓意外者,如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就是其中一位。在《1949年赴会日记》中,他这样漫不经心地写道:“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直到张元济离京南下的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再次拜访茅盾,“复申前请”。张元济再三邀请茅盾回商务任职实出于工作需要,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正如同1920年代初年他不知道经常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的沈雁冰就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内的沈德鸿一样,在他离京两天后,这个昔日商务的练习生、前《小说月报》的主编、被自己选中的商务中层干部,已经一跃而成为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
对于茅盾任职文化部长,左翼阵营中的胡风,很不以为然,在1949年10月28日给梅志的家书中就曾不无鄙夷地说:“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子上,替茅部长象征一统,如此而已。”感到意外的党内人士也不少,特别是在香港期间曾多次批评过茅盾的乔冠华、杨刚等人,与茅盾一直有龃龉的上海文化局长夏衍恐怕心里也未必服气。至少名义上屈居副部长的周扬,心里也未必痛快。当然,作为党的干部,他们不能公开流露这样的不满。至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向毛泽东提出或暗示“想当文化部长的人”,自然就更怨气十足了。事实上,连茅盾自己也觉得有些突然,晚年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曾坦诚说:“当时实未料到全国解放的日子来得这样快,也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
另一方面,茅盾出任文化部长也是实至名归。其一,他有二十多年的革命经历和经验。他是1921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批党员,资历最老。而且他与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陈云、毛泽民诸多高官都有过密切接触。在整个革命的进程中,茅盾先后失去了三位亲人:1934年胞弟沈泽民病逝于鄂豫皖苏区,1945年爱女沈霞在延安因医疗事故意外离世,1949年女婿萧逸牺牲于争夺太原的前线阵地,于革命贡献来说,也算是功高盖世了。因此,作为“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由他出任文化部长,可谓两全其美。其二,茅盾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已被有意识地塑造起来。如早在1940年延安时,毛泽东就曾当面许诺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1945年,在周恩来授意下,战时的陪都重庆为茅盾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举行庆祝大会,虽然与毛泽东定性的鲁迅、周恩来定评的郭沫若地位不能比拟,但是作为第三位文化旗手,茅盾出任文化部长也算是名实相符、实至名归了。
不过,茅盾在多大程度上被重视,是个不可问也不好答的问题。因为按照党组负责制,周扬虽然是常务副部长,但同时还兼任党组书记。周扬后来另外还有一重要身份,那就是中宣部分管科学和文艺(包括中国作协)的副部长、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从部门的角色和地位来说,文化部与作协、文联都要受中宣传部监督和领导。这样,周扬在名义上是副手、下级,而在事实上又成了茅盾的领导者、监督者。当然,在胡乔木、陆定一面前,周扬这个文化部真正的一把手,也不过是个当差的。郭小川1967年写过一个交代材料,能够从侧面予以佐证:“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
不仅是文化部部长这一角色,从其它任职来看,也可以证明茅盾所处权力边缘的境遇。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这一位置可能为很多包括作家在内的文化人看重,但说到底,包括文联、作协这样一个本来属于民间的行业协会,因为前苏联首创而归为体制内并为1949年的新政府所沿承,虽然级别很高(现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均享受正部级待遇),但其拥有的权力、地位与真正被重视程度,是远远不能与中央其他各大部委以及各垂直管理机构相提并论,也就遑论其负责人了。当然,在中国官本位和人情社会中,为官之道在于充分使用权力,有时并不完全依靠权力本身,还要看权力者的谋略。事实表明,那些善于为官之人,哪怕名不见经传的权力,也会被放大至无限。反之,哪怕是官至高位,也会表现得捉襟见肘而被人看轻。
再如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姑且不论这个标榜和平的“会”是否真的要保卫世界和平,就是其“会”的工作内容,也无非是务虚性的发宣言、造声势。说到底,这种所谓与会交流,其实就是挂招牌、做姿态、走过场,至于是否能真正保卫了世界和平,以及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自家都有自家的小算盘,谁个也是清楚的。其实,世界和平如何保卫,原捷克总统哈维尔有过一番话值得思考:“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力……对自己的人民毫不犹豫撒谎的政府也将对其他政府毫不犹豫地撒谎。所有这些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人权是基本的条件,并且是真正和平惟一的保证。压抑公民和人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保证和平——相反,只有危及和平。”这话茅盾如果听到大概不会反对。
然而,当茅盾真正融入工作角色中,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意。不仅是文化部,作协也是如此。横在他面前的不仅有来自高层的“极左”思想、方针和路线,更现实的问题是他要面对周扬,而后还有钱俊瑞、夏衍、齐燕铭等,以及刘白羽、林默涵、郭小川、邵荃麟等所谓“周扬派”,这让他始终有种难见天日的感觉。所以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一贯审慎的茅盾终于找到可以发泄的机会。他抱怨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个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我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这些都是题外之言,不过,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由此可见,茅盾虽有过两次辞职的念头,却并非真正是因为要创作而无法保证时间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要遵守民主的规则——不能连任两届以上,而是他在工作极度压抑下的一种牢骚和不满。
这样的牢骚和不满在1958年写给作协办公室的信中再次爆发,在要求作协帮助解除自己文化部长、政协常委、《中国文学》和《译文》等“兼职”后,他不无委屈地写道:“几年来我对于文化部、政协常委、《中国文学》和《译文》主编,实在荒弃职守,挂名不办事,夜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我几次请求解除,尚未蒙批准。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席,外交宴会也不能不去,结果,人家看来我荒废职守,而我在三种‘会上花的时间,平均占每星期时间的五分之二。”显然,茅盾在信中不但陈述了自己出任文化部长是兼职,出任政协常委是兼职,主编《中国文学》和《译文》是兼职,同时也道出实情:他不过是应景的摆设,需要时出来露露脸,办实事时却又没什么权。
然而,这样的尴尬境遇又能怪谁呢?在理论上来说,作为革命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一个齿轮,不就该这样吗?革命需要你在哪里就在哪里,革命需要你怎样便怎样,即便是这样无聊的工作,甚至有伤自尊心,但不也是为革命做贡献么?又何苦常年失眠要靠药物来维持呢?
历史行进到1965年1月4日,也就是新政权建政十五周年之际,根据第二号国家主席令,茅盾被正式免职。同时,在1月5日的第四届政协会议上,茅盾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种人事安排,表面上是升职,而实际却等于宣布茅盾回家养老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
据韦韬、陈小曼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中讲,茅盾被免职之前,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后,周恩来已经与他约谈了去留问题。周恩来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在茅盾提出辞去作协主席之职时,周恩来又抚慰地说:“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呢?”尽管是关于免职的谈话,作为职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周恩来,也能够把话说得仁至义尽,让情绪低落的茅盾感激涕零,不但事后对儿子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总理是煞费苦心的”,还在周恩来去世后亲赴北京医院和人民大会堂为其送行,赋诗哀悼,并撰写了《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段回忆》等感情浓烈、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真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了。
其实,仔细咀嚼周恩来的这番话,话里话外充满了玄机。不妨以常理来分析:文化部工作没有做好,已经是钦定,但是追究职责,却没有指向部长,而是拿副部长们是问,这显然不符合官场的基本规则。而事实又确实如此,这也就进一步证实,茅盾的确是挂名的、象征性的文化部长,而文化部的“法人代表”是那个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人。即便是这样,茅盾此前提出辞职时,却未得到批准,理由竟然是“没有合适人选”,这其中又可见他的某种象征性的地位和价值,非一般人所能取代。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继续遵循联合政府的表面形式,纵览文艺界的非党人士,还真没有人比茅盾更合适。
其实,话说回来。即便是茅盾及其主管的文化部没有受到最高领袖的批评,他的部长之职也早该卸任了。因为在一个共和国里,对于任何一个部长来说,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已是世界民主国家的公例,违反此例即有违背民主共和而趋向极权专制。至1964年,茅盾已经连任三届,“执政”达十五年之久了。此时的茅盾于情于理都该交班退位了,大可不必如茅盾家人、一些研究者那样持惋惜的态度,虽然这期间存在着明显的非正常因素。
周恩来的话中还有一则信息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文化部的工作“不尽如人意”,是党员“助手”的问题,所以,“文革”开始后,无论是此前的周扬、钱俊瑞,还是后来的夏衍、齐燕铭,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点,也算是名副其实了。或者,再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茅盾继续履任文化部长,那么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之际,他是否能够得以善终,恐怕是难于预测的。而纵观茅盾在“文革”中的遭遇,虽然也被点名批判过,大字报贴到文化部大院,红卫兵也抄过一次家,儿子被审查过,儿媳被送往咸宁干校,但是相比于周扬、夏衍、刘芝明、陈荒煤、林默涵、石西民等身陷囹圄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副部长、党组书记们,茅盾真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也正应了那句俗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这样一个结果向前推衍的话,茅盾跟韦韬所说的那句关于总理的“煞费苦心”,还真是有些道理。也就是说,周恩来主观上未必提前想到要保护茅盾,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不过,周恩来对茅盾的保护,自然应该为人称道,但有个疑问,该保护谁又不该保护谁,这人选如何筛定?是根据亲疏远近还是官职大小,亦或是根据“罪行”大小?这其中的学问也该认真钻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