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在脚下,门在天边”
——读贾平凹《带灯》
○李忠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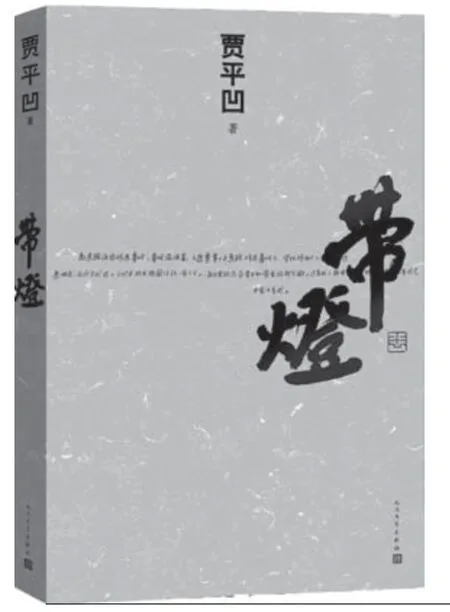
《带灯》,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贾平凹带来新作《带灯》以乡镇女干部“带灯”为主人公,从“维稳”与上访角度切入,反映乡村基层的问题与危机。小说贵在呈现矛盾的复杂性,打破单一的想象。“维稳者”带灯,善良可敬,不愿伤害农民,又不能渎职。她周旋于各种关系间,四处救急,斗智斗勇。上访者面目各异,各显神通。小说中的樱镇,与清风街(《秦腔》)、古炉村(《古炉》)命运相似,正在遭遇现代化的改造。它们构成同一个主题:乡土中国的现代裂变。
哪里能买到文字上的大力丸呢?
要辨识《带灯》的艺术特色,且从贾平凹的创作“转身”谈起。
《带灯》的后记写道:“我得有意学学西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可这稍微地转身就何等地艰难,写《带灯》时力不从心,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字上的大力丸呢?”这传递了如下信息:作者思变,属意西汉,并非别开生面,只是稍微一转,幅度有限,却何其艰难。新作部分保留了既往“密实流年式的写法”:繁密叙事,流水账式;巨量信息,无边细节,繁冗琐碎;日常生活原生态呈现。同时,他也略有“转身”。
小说的女主人公原名“萤”,却嫌恶“萤虫生腐草”之句,遂决意改名。因见萤火虫在草木间明灭,受到启发,她更名为“带灯”。这意思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其中寄意,不言可喻。她是樱镇综治办主任,负责“维稳”工作,处理乡村纠纷和上访事件。在整个樱镇,她是卓然不群、超然脱俗的。她是大学生,颇具才思,内心丰富,情感细腻。这就有了矛盾与分裂:她要应对农村无止的纠纷,深陷樱镇乱局;她又渴望精神超脱,构筑心灵空间。她在精神上爱慕着元天亮,并执著地给他写信。信笺内容不啻心灵诗篇,情感丰沛,譬喻丰富,联想环生,是小说的亮色。然而元天亮始终缺席,从未现身,好像缥缈的远方,不过是带灯个人的乌托邦。换言之,她将肉身存于浊世与当下,将精神寄于风景与远方。带灯说:“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缘此命运和境遇,作者备了两副笔墨:史传笔墨,以叙事语言全景式地模拟客观的经验世界;诗性笔墨,以抒情语言集中地表现主观的精神世界。这为读者打开了两扇门:一扇通往樱镇的生活世界,泼烦日子,鸡零狗碎;另一扇通往带灯的内心世界,诗情迸发,星空飞翔。前者是小说的主要构成,占大多数篇幅;后者是穿插其间的书信,宛如暗夜里的点点萤火。两者相映,形成诗与史的糅合。
这从《红楼梦》里看出端倪:叙写日常的生活世界,又穿插着抒情的诗词歌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说过:“抒情性渗透进了叙事结构,使叙事摆脱了灰暗单调的日常生活的重负和牵引,飞翔起来。”小说《带灯》本身也好像是佛案上的泪烛,光与泪的映衬,正是诗与史的糅合:灼灼生辉的心灵之诗,引领读者不断向上;问题丛生的乡村痛史,使读者忧心关切。
社会是陈年蜘蛛网,动哪都落灰尘
继“改革”(《秦腔》)、“文革”(《古炉》)之后,贾平凹从“维稳”的角度提出问题,铺排烟海细节,汇聚洋洋信息,遂成《带灯》一书。
“蛛网”是小说中屡现的意象,并多次形成蛛网之喻:“社会是陈年蜘蛛网,动哪都落灰尘。”这是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本质性概括,又是全书内容的总体性譬喻。动摇中的“陈年蛛网”,喻指处于现代剧变中的乡土中国;而“灰尘”则指变动中浮现的问题与危机。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又层出不穷,纠缠不清又混乱不明,所以“动哪都落灰尘”,按下葫芦浮起瓢。
负责“维稳”的带灯,骑着摩托,走村窜寨,解决矛盾,预防上访。其间目睹浮生百态,深感人世之艰辛,而又难以置身事外。鸡毛蒜皮如核桃树归属问题,人命关天如家族械斗事件,让她应接不暇,顾此失彼。
在作者看来,之所以问题丛生、危机四伏,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礼法崩解,宗庙祠堂失效,人们不再信守,而真正的法制观念与法制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人皆知维护权利,又抛弃仁义,所以上访意图迥异:有的诉求合理,关乎正义;有的别有用心,图谋私利。加之矛盾复杂、关系错综,当地政府调节不当,致使越来越多的人寄望于上访。国家以经济发展为要务,政府强调社会稳定,这就有了带灯所在的综治办。这就由“维稳”牵出了“变法”问题,而根底还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过程,常常是“变法”的过程。这不是在无序之域确立规则,而是要取代传统法律。传统社会并非无法无天,自有规范可依。为了追求现代性,对传统规范施以强制性变革,以现代法制取而代之,是为“变法”。而“变法”之际,矛盾丛生,以“普适主义”自诩的现代法制与民间的传统规范相冲突,而后者通常遭到压制与破坏。电影《秋菊打官司》反映了这种冲突。秋菊执意上访,最终在法律的干预下赢了官司,维护了“权利”,却在乡土社会输了“理”。当村长被送进“局子”,秋菊却无限困惑。如果说秋菊的上访与困惑,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与冲突;那么《带灯》中的上访与纷争,则反映出两者断裂之间的虚无与混乱。换言之,秋菊尚在冲突地带,无所适从;而樱镇的人已身陷断裂之隙,危机四起。樱镇上的男女比秋菊更激进、更现代、更知权利,横扫困惑,乡情撕破,伦理已抛。秋菊上访是讨个“说法”,而樱镇的村民上访多半是谋利。这是历史前行的必然代价吗?
旧制已经瘫痪,新制尚未健全。樱镇处于价值与意义的真空状态。透过纷纷扰扰的人事,樱镇确有重重苦难,却也是虚无之域。这里的男男女女,无所依附,只得各逐其利,争争吵吵,攘攘扰扰。小说里有两处怪诞的细节,着墨不多,颇有意味:一处是疯子捉鬼,另一处是和尚看鬼。疯子白天黑夜地跑,总说自己在捉鬼。和尚常坐在寺庙门口,看山下往来路人,分辨着人与鬼。在他的眼中,路上鬼影幢幢,唯独带灯是人。可以说,带灯是智慧而高贵的,是星空下的文化精灵。然而在文化失序的所在,她的挣扎只是徒劳。最终在重创之下,带灯精神失常,由文化的精灵变成文化的幽灵,夜游于镇街,与疯子相逢。这一疯一僧,小说里偶一闪现,却道出了这里的真相。
写作的仪式:谁在说
贾平凹的写作,总是伴随着个人的仪式,并由“后记”特别交代。创作《秦腔》时,他在书房置放巨大汉罐,日日焚香,祭奠、召唤故乡的亡魂活鬼。当汉罐冒出来的烟线被他的吁气吹散时,他就感到满屋幽灵漂浮。写作《古炉》中期,他请来一尊童子佛,供于书案,在铜佛的注视中写作。在他的意念里,是佛将神明赋予了主人公狗尿苔。与《带灯》直接相关的,是一块大石头,自然“凹”状,形近火山口。作者认为,创作就是火山口,平日沉寂,但内心汹涌,随时发生新的喷发。于是,贾平凹把凹形石摆在桌子上,当作火山口来敬供,以期给予自己力量。
这样的仪式,别有深意。作家主体的缺席,个人意志的消失及自我的无力。从创作空间书房看,作家并非独立主宰整个空间,而是与汉罐、佛像及怪石一同共治。这些物品并非书桌式的客体,反成为具有发言能力的主体。在贾平凹看来,它们蕴蓄神秘之力,甚至能参与他的创作。不论书房中还是作品里,贾平凹没有君临的姿态,反倒退守一旁,让出主位。汉罐所召唤的亡魂活鬼,一起向作家诉说身世命运。他耐烦地倾听,并将一切移于纸上,原生态呈现,就有了《秦腔》。如果说在倾听鬼魂时,他还能“盯着”汉罐,那么在童子佛前,他只能被“注视”。前者还略有主动,而后者就全然被动了。及至创作《带灯》,作者已感乏力,信心不再,只得乞灵于凹形石。这象征力量、活力的“火山口”是他的冀望,也投射出深深焦虑:“后记”处多次提及自己的衰老和创作的力不从心。童子佛像不过据有书案方寸,而凹形石却几乎占满了整个桌面。作家留给自己的空间愈发狭小。这里颇富象征意味,即作家的主体不断后撤,终至缺席;个人意志渐趋消失,自我已太无力。
早有识者指出:“贾平凹的《秦腔》在判断和反映‘真实’的同时,却泯灭了‘意愿’——那是主体意志虚无化的自我取消。”比之《秦腔》,新作《带灯》进一步“自我取消”,更为精神被动,彻底匍匐在社会现实层面,全然依附于失去总体性的无数细节。虽然带灯有所挣扎,但她执著地写信给缺席的元天亮,意味着她只能在语言的乌托邦中安身,寄望于个人的精神修炼,终归梦幻一场。
取消启蒙身份,瓦解宏大叙事,消解历史目的,回到乡土本身,呈现破碎当下,这些固然可以,也有其价值。但接二连三,一味消解、质疑和所谓“还原”,最终只是堕入虚无,无所适从,为读者留下历史破碎的图景。
作家需要突破
贾平凹颇有文学抱负,自称“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若真有意突破,我希望他莫再自我重复。《带灯》在技术上的半转身,并不能掩盖作者的故步自封。细节的重复,不算要害,暂不罗列。其主要症结至少有两处:
其一,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想象已经程式化。在他看来,现代性如大风劲吹,将乡村连根拔起,裹挟而去,不知方向。不论革命还是改革,莫不如此。这一总体性譬喻及认知,反复出现,自动化生产,已成定势。在《带灯》中,尘埃蛛网,动辄落灰,是这一思路的延续。总之,几部作品,一贯风吹人乱,未尝新变。这在根本上制约了作家的突破。
其二,塑造人物的思路过于单一。作者对带灯的塑造,明显在重复《古炉》的狗尿苔。两者貌似差异较大,却出自同一模板:“人境逼仄,所以导致想象的无涯。”这一具有张力的逻辑,先后在两部小说的“后记”中出现,反复陈说,恐人不知。带灯美丽又超然脱俗,狗尿苔丑陋却似天外来客,皆是乡村独异的存在。他们身处逼仄的现实,却生成无边想象:前者营构诗意空间,后者建立童话世界。还是民间老话: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如果作家不能克服上述顽疾,那么不论“转身”几轮,终是画地为牢。贾平凹以踢球比喻写作,我也借此修辞,作整体评估:《秦腔》进球了,《古炉》射偏了,而《带灯》已露疲态,仍卖力奔跑,满场转身盘带、传球倒脚,就是不见临门一脚。比赛告终,球在脚下,门在天边。
《带灯》让女主人公深入农村现实,绝望又坚韧地行进在当下:抱守记忆是枉然,瞩望未来又惘然。然而必须超越逼仄又破碎的现实,所以她自己携带精神的灯盏,在浊世暗夜撑起诗性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带灯是贾平凹的精神自喻:当历史失去目的,时代乱象纷呈,作家犹如踽踽夜行,只得紧贴沉厚大地,依附无边细节,自带明灯一盏,照出世路人心。但是,持灯之人把灯盏置于地上,转身藏于暗处,隐身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