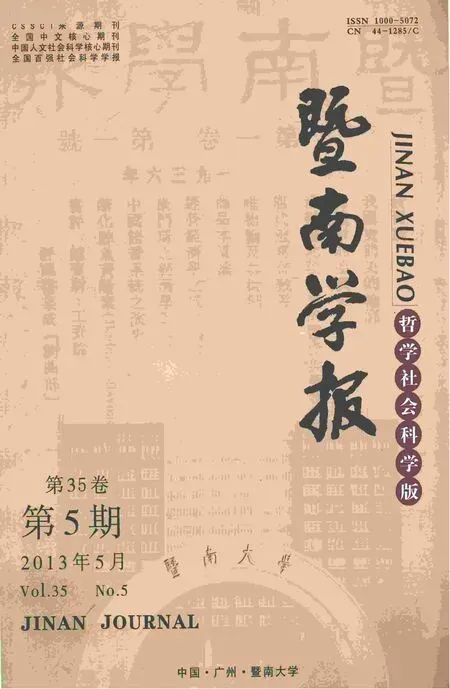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
赵静蓉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510632)
记忆是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研究的热门词汇,我们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可见到记忆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这充分证明记忆“具有一个观察被忽略了的和司空见惯了的东西的崭新的视角”,“具有融合力的、跨学科的潜力”。记忆开发了对不同学科中一系列现象的新的结合方式,涵括了众多不同意义的概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就对文化学中“记忆的繁荣”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这样说:“并不是在这么一个大概念之下,所有小概念的区别就消失了,只是强调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概念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正好是在‘记忆’这个大概念中才被发现的。有了这个大概念,才能进行命题类推法,才能研究它们的共同点,这是之前完全无法想象和做到的。”
记忆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三个问题。“谁在记忆”和“记忆什么”是一组互为因果的问题,“谁”是主体,“什么”是客体,记忆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被记忆对象的边界,而记忆客体又对建构和重建记忆主体的身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组概念关涉到记忆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是记忆的社会批判功能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基础。“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则指记忆的实施过程,它是基于记忆个体的神经系统和心理机制所完成的一系列意识活动,也是体现在民间神话、博物馆、地方志、纪念碑、礼仪风俗、档案材料、社会习惯等中的人类历史行为,它与记忆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与“如何记忆”这三者的循环构成了记忆研究的内部世界,而记忆的功能、记忆的价值与意义、记忆与文学或历史等学科的关系则构成了记忆研究的外部世界。
当然,记忆研究不仅仅指记忆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它还有一个根基性的领域亟待我们去开掘,即“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记忆”、“我(们)如何表述我(们)的记忆”或“我(们)的记忆如何被他人知晓”等问题。对此,我们常常有可能脱口而出“我记忆,并且我被记忆”,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尽管这一表述也部分地揭示了在理解记忆的过程中存在某种主客体间互文共生的关系,但它却无法透彻解释记忆被合法表达的实质,甚至令这个问题趋于神秘化。本文就是要对记忆表述的本质进行理论意义上的还原,并据此分析记忆的真实性问题。笔者认为,究其根本,这就是一个文化记忆和符号叙事的关系问题。
一、记忆的符号再现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过去总会被合法化”,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较为现实的方式回忆、想象并重新塑造过去,过去不仅取决于我们不断变化生长的记忆,而且取决于意识筛选、想象重构和媒介展现,因此,记忆的核心问题就是重现(representation),是表征,是语言和实在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审美联系。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符号才会发生。
记忆最基本的功能是存储功能,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未经过整理的、各种材料纷乱杂陈的潜意识世界,我们所有主动地、间接地经验过的生活都被包含其中。阿斯曼夫妇将其称为“未被居住的潜藏领域”,“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这类记忆的因素极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部分是受制约而难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因痛苦或丑闻而深深被埋藏的。……在集体层面,存储记忆包含了变得不可使用的、废弃的、陌生的东西以及中性的、身份抽象化的属于数据或资料类的知识,当然也包含了错过的可能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全部内容。”这一部分是没有边界的、无组织的、野性的、未被我们的意识所驯服的,我们要驯服它,本质上就是要对它进行符号化处理,基于某种现实情境的需要,有选择地征用、支配和占有那些材料,使其转化为与我们构建自身的主体身份相关联的、有意义的内容。
这一符号化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记忆从存储到重建,是一股潜流,它在我们的头脑和意识中悄然发生;其二,记忆从心理实在到经验活动,又是渐趋呈现和演示的,它只有借助“被言说”或者“被表述”才能成为一种确定的形式,从而才能为我们所认识。后者就是本文的立足点,也是笔者认为记忆研究中最具根本性的因素。显而易见,再现记忆或表述记忆最自觉、也最主动的一种方式就是语言行为。比如说“我记得……”、“回想当年……”、“那个时候我……”等等。对过去的记忆是被讲出来的,通过语言的叙述,记忆脱离昏暗繁杂的“未被居住的领域”,上升到确定的、明晰的“现在世界”,从意识的可能性脱胎换骨为语言的现实性,实现了在社会层面而非自然层面的“第二次诞生”,成为可供认知、交流和建构的文化现象。
从记忆主体的角度而言,记忆的二次诞生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建构和叙事过程。这与20世纪的史学理论革命(海登·怀特)和语言转向(R·罗蒂)有重大关系,也在更深的层面上关涉到我们对存在和实在的关系的理解。
前面我们已提到过,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受制于多重因素,不仅取决于过去本身,更重要的是,它还受到我们“言说”过去的方式的制约。在芬兰学者塔拉斯蒂那里,这显示为符号的逆向运动,也就是说,“符号的所在,是基本存在的结果”,“所有世界和命运都从无意识中凸显出来,凝结为一个符号,一种品味,一种嗅觉,一种香水,一种姿态”,符号的价值要靠记忆的功能来体现,记忆就意味着“将现在视为缺场的,超验的”。而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论里,这又意味着文化记忆的“视野”,即人类历史早于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文化记忆有其知识储备的外边界”,“文化记忆……是关于过去的一种独立形式。……不是某些可以发现的来源和痕迹,而是文化文本决定其视野的大小,并且通过其语义学的塑造世界的功能来给予文化记忆身份构成的简明性”。历史(实在)早于记忆(存在),而记忆又先于记忆的言说(语言),由此可见,记忆的符号化同样显示出反经验主义的含义。记忆基于事实,而符号叙事却可以与事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分析和推理来臻达真理,这既验证了美国哲学家奎因所说的“经验真理”和“分析真理”之间的差别,也证实了R.罗蒂所谈的“经验的强制”和“语言的强制”对我们形成真实信念的不同影响。荷兰史学家安克斯密特据此认为,语言转向说兴盛的原因是:“与经验论所相信的相反,我们相信为真的东西至少有时候是可以解释为是关于实在的陈述,以及关于语言意义的陈述,和关于我们在语言中所使用语词的意义的陈述。因此,和实在一样,语言也可以是真理的制造者。”
记忆的另一种形式是被记忆,即作为记忆的客体或载体,比如人、事或物象,如图片、档案、物件、博物馆、仪式等。事和物象本身是不会记忆的,但它们作为特殊的表意符号,却可以营造诱人回忆的氛围,充当激活或激发主体进行记忆的催化剂。经由主体的移情和投射,这些符号在记忆行为发生之前,就已变成了具有先验的情感结构的“形式”或“意象”,它“是从图式中捡出部分的一种手段,是在重建过去的刺激和情境中增加多样化机会的一种手段,也是克服按年月顺序的编排来呈现的一种手段”,它对记忆的最大帮助就是增强我们处理距离情境的能力。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将之称为“强迫记忆”,阿莱达·阿斯曼则命名其为“他我记忆”,在这种类型的记忆中,主体只是在等待,等待着“缄默的物品撞击”我们,主体同时也变成了媒介,用以传达和“翻译”出被事情或物象所触发的回忆。
二、记忆的文本化
正因为记忆是借助符号得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是关于记忆的陈述,因此记忆就绝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固定的,它必然要在过去和现实之间逡巡往返,部分可能被不断地重复,部分可能被打破重组,部分可能被消除抹去,也可能会有新的元素加入进来。“语言回忆的框架不是身体,而是社会交往。莫里斯·哈布瓦赫曾指出,回忆是在与他人及他们的回忆的语言交流中构建的。我们回忆许多我们能找到机会去讲述的东西。讲述是一种‘详尽的编码’,一种使经历变成故事的翻译。……记忆通过详尽和重复巩固自己,这也说明:没有被重复的就消失了。”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令记忆符号的意义不断增殖;同时,语言的建构本质也决定性地影响了记忆的想象性特征,使记忆与故事变得很接近。
因为语言的符号化建构,记忆变成了文本,或者说,记忆被文本化。表述一段记忆就像是讲一个故事,主体会因为记忆的现实情境和需求不同,而对过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修改、转换或补充,从而使之更倾向于“可被理解和可被接受的真实”。文本成了我们阐释记忆的媒介,并将记忆行为带入一个边界开放的记忆空间。这个空间的中心是“真实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和经历,是所谓不可撼动的、确然实存的历史;而与“真实的过去”拉开距离的则是一系列记忆文本,受不同主体、不同时代和不同世界的影响,这些记忆文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它们都是“真实的过去”的“痕迹”和“道路”,是对彼此的反思和证明,并共同组成了记忆共建的根本机制。
德国学者蕾娜特·拉赫曼在研究文学和记忆的关系问题时,借用后结构主义的概念“互文性”来指称这种文本记忆,她认为互文性就是“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记忆”,“它可以变化角度来观察、平衡并修改大文化文本中的各种单个文本”,而“每个文本都是对所有文本的记忆,这些文本都在这个文本中留下了痕迹”。互文性的魅力就在于文本间的互证和关联,但也正是因此,记忆变得不确切,并令人怀疑。假如“真实”变成了“关于真实的话语”,对过去的记忆可以被虚构、被塑造、被想象,那记忆的真实品质还坚不可摧吗?记忆的真实性或诚实性是否要被记忆的文学性或审美性取代?对记忆的表述是否因为语言和互文而变成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记忆的“真实性”?
我们不妨从本真性谈起。本真性是一个涵括非常广泛的概念,它与真实性、真理性、摹仿、仿真等概念都有非常接近的内涵,在艺术、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内也有不同的所指。笔者认为,真实性是最接近本真性的概念,两者的内涵和适用范围虽不相同,但真实性却是本真性的基本涵义。
人们对本真性的研究最初是在音乐领域里的,它是介于原作和表演实践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主要针对古典音乐、芭蕾和交响乐,而不适用于爵士乐和戏剧,指对作品的表演要符合作者的本意。用音乐符号来表现作者的本意,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讲,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单靠对乐器、演奏者等音乐资源的分析无法解释其他因素的渗透对音乐表现的作用。所以说,即使只限于音乐领域,对本真性的解释也有必要放在一个互文性的语境中来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真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或者可以对比不同情态下的符号表现,根据不同维度的比较得出更接近“本真”的解释。塔拉斯蒂就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分析出几种较有普遍性的本真性含义。首先,本真/非本真可与能指/所指或显在/内在等概念并置。“‘本真’指有意义、有内容、有所指的事物;而‘非本真’指没有内容、纯粹在现实表层移动的事物。”其次,遵循人的本质也是一种本真。第三,在学术话语领域里,词语和事物的对应体现出话语的本真性。第四,当时间(现在)、空间(这里)和行动者(我)这三个维度“普遍存在完整的连接时,就达到最大程度的本真性”。可以看出,塔拉斯蒂是把本真性放在一个行动过程中来看待的,他非常重视这一概念自身内部的“分离”和“超越”,并且承认打破彻底静止状态的“本真”以及遵从具有张力的“非本真”原则对艺术研究的有效性。
“本真性”、“真实性”或“真理性”重新成为一个问题,是20世纪理论界语言学转向的后果之一。从克罗齐的“美学与语言学的统一”到卡西尔的符号系统,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到罗兰·巴特的语言乌托邦,从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到伽达默尔的语言和真理,从巴赫金的对话论到福柯的话语和权力,众多学者都对语言和真理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在此语言学转向及其对真理问题产生复杂影响的大背景下,记忆的叙事特质也被反复论证,与记忆的真实性问题缠绕在一起,成为记忆研究的焦点问题。
当我们探讨记忆的真实性问题时,本真性和真实性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都指记忆的完整性、原生态性以及唯一性,与被遮蔽的、被表现的、被想象的、被主观理解的、片面的和派生的记忆有很大差异。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如此,与本真的或真实的记忆相对的,却不是虚假的记忆,而是对记忆的理解。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记忆是符号化的了记忆,是文本化的记忆,它已经表达了某种立场和理解,与原始真实的记忆拉开了距离。保罗·康纳顿强调要把社会记忆和历史重构区分开来,其意义就在于承认:第一,记忆文本不等于原始记忆;第二,记忆文本也不是对原始记忆的原封不动的复制;第三,记忆文本作为一种理解,已经构成对原始记忆的改变;第四,正是原始的本真记忆,记忆文本,以及对记忆的每一次表述或理解,一起构成了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历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虽然记忆和其他符号化行为一样,同样体现了一种互文性和运动性,但记忆不同于音乐、绘画或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在所有的符号化行为中,记忆是主客体之间距离最短、关系最密切的行为,是对人类的经验、情感、知识、精神和历史等的最直接记录。因此,虽然记忆再现的叙事本质关乎记忆的修辞学,但我们却不能只把记忆的修辞看作是纯粹客观的语符表意,我们还不得不同时考虑记忆的伦理特性,考虑记忆与主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记忆的真实性
按照塔拉斯蒂基于时间、空间和行动者三个维度的完整连接来考察本真性的理论,记忆显然是真实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境下,记忆行为都是主体(行动者)立足于现实(此时此地)对过往经验的回想(时间和空间),从此时的自我到彼时的自我,从此地的生活到异地的生活,记忆主体的返身性构建了无时不刻存在的记忆空间。从记忆的发生机制来看,这三者的关联从未中断过。显然,时间、空间和行动者之间的普遍连接并不能引起我们对记忆之真的质疑。但记忆的特殊性在于:记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记忆基于自身的“分离”是分别进行的。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和行动者既是普遍连接而自成一体的,它们各自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主体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心理状态下的回忆是不完全一致的,而任何一个细节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造成对整体的记忆世界的改写,从而导致我们对真实性的判断千差万别。
那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记忆的开放有限度吗?如果有,这一限度又会对记忆的真实性产生什么影响呢?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曾说:“记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分散的系统,总有一些框架在个体、代际、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将记忆和某些特别的时间视界与身份视界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联系不存在,那我们处理的与其说是记忆还不如说是知识。记忆是一种有着身份指向的知识,是一种关于其自身的知识。”显而易见,记忆的开放仍然有基本事实的边界限制,有“一些框架”令记忆无法越轨。简言之,这些“框架”主要有两个部分构成。其一,作为记忆主体之物质基础的身体。记忆最基本也最首要的是一种身体记忆,记忆的主体本质性地体现为有意识、有情感的身体。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曾说:“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受”建立在“知道”的基础上,借助语言“再现”历史,并对历史作出判断。作为记忆的物质基础,身体的体验是可感知的、可被认识的,它的支撑是客观真实的实体世界,因之记忆也是一种实在,是以身体体验为内核、以世界作为“他者”而构成的整体。其二,记忆是主体间的交互活动,单独的个体记忆不可能完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就像哈布瓦赫所认为的那样,任何个体的记忆都要被放置到群体的环境中考虑才有意义。与身份认同中“他者”对“自我”的建构相似,“自我记忆”也要借助于多种“他人记忆”才能完成,记忆心理学中所说的“闪光灯现象”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精辟形容。也就是说,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应以各自的闪光灯方式把自我的记忆联接到对一段历史的分享记忆中去,“即使他们的闪光灯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这是马各利特所说的‘共时记忆分工’(synchronic mnemonic division of labor)。它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努力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但这不等于每一个人有责任记住一切。保持记忆的存活也许要求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至少应该有一些记忆,但要求也仅此而已。’”
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同样的一段历史是公平开放的,这意味着它对每一个人所先在地创设的接受情境是相同的和一致的,这是谈论记忆真实性的根基,实际上也是当真实性失落之后,我们力图重新寻回的理想。尽管原汁原味的真实是不可复现也不可复得的,但上述两点,即记忆主体的肉身性(以及随之产生的实在性)和不同主体的、共时性的、闪光灯式的记忆分工则令记忆不可能无限开放,以致在追寻真实性的道路上完全迷失。这两点帮助我们搭建了一个记忆的藩篱,通过主体间性的力量完成记忆元素的叠置、补充、修正和整合,从而组建了有效的记忆空间。
有趣的是,正是在对记忆边界的思考和研究中,一个简单的事实昭然若揭。那就是:对记忆真实与否的判断是由记忆主体之外的“受众”来履行的,说出记忆或真或假的或者是在个体意义上与此记忆没有关联的历史学家、批评家,或者是记忆内容牵涉到的曾经的“当事人”,或者是对历史好奇的大众,总之,都不是真正发出记忆行为的主体本身。我们或许可以据此断言,记忆的真实性不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意义或效果机制,或者更激进一点说,它是一种价值论。这一点从当下学界对各种形式的记忆文本——如回忆录、传记、日记、书信等——的研究趋向上就可窥见一斑。
为什么因为叙事学和语言学对记忆研究的介入会造成记忆书写的合法性危机?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叙事学和语言学不仅要解决记忆再现的“可靠性”问题,还要试图辨析它的“有效性”问题。“可靠性”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关乎现实;而“有效性”则要求我们深化对历史的反思,增进我们对人类良知和社会道德的思考,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关乎对现实的建构。当研究重心越来越从“可靠性”转移到“有效性”上时,“受众”(记忆外空间)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判断就会强势“侵入”记忆的内部空间(主体、对象和记忆行为),并左右甚至改变被记忆对象的性质,令其有可能从真变假,由好变坏。记忆的伦理性因此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记忆之建构性的另一层含义。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也使记忆的书写成为一种“双重刻写”。记忆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记录历史,无论对个人生活还是集体历史它都能够充当最接近真实本貌的“见证者”,这一点不可能也不会因为记忆再现的符号化而被动摇。但是,也许记忆的伟大使命并不仅止于此。虽然记忆的真实性受到符号表现及文本表征的影响,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元化的、有生命的、有立场的记忆书写却又可以冲破一元论的、同质化的记忆乌托邦的迷雾,增进人类群体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错误的修正,也为人类构建更善更美的道德理想形成巨大的推动力量。记忆的真实性问题不能被神秘化,各种方式、各种立场的记忆言说都应当被允许,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现在为立足点,通过个体的记忆表述将众多的历史细节筛选、过滤,通过反复的“叙述”来修复历史和文化所受到的伤害。这也是记忆伦理的真义。
[1]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4]F·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6]Michael Kelly etc,eds.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
[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7]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Memory in a Global Age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
[C]∥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8]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