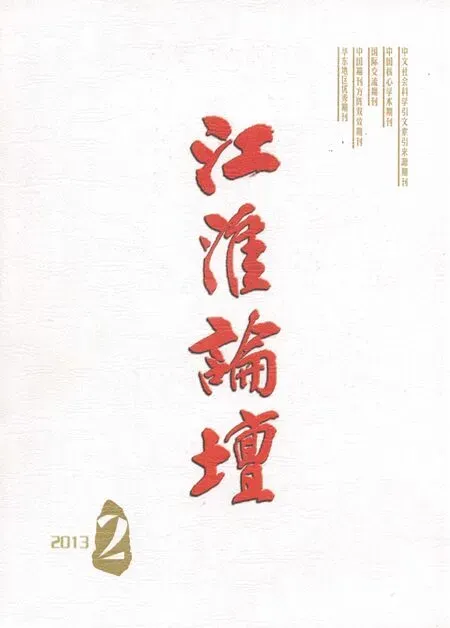文化断裂带上的足印﹡——论阿城的小说
王海燕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1)
经历过“五四”激进的以启蒙“现代性”为目的的“反传统”和“文革”更为激进的以“破旧立新”为号召的“反传统”,20 世纪80 年代,阿城这代作家无可选择地站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带上。 新生代的文化学者认为:“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被鲁迅看作‘铁屋子’, 并且对这种文化的认识本身也采取了一种寓言式的处理方式,那么,在80 年代特定历史语境当中发生的‘寻根文学’,却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再辨析工程,人们开始在这‘铁屋子’里挑挑拣拣, 试图发掘那些还值得传承下来的东西。在这里,不再简单是‘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两分结构,而是在此二元结构的基础上‘中国’、‘传统’ 本身的差异性也被提了出来。 而这种对‘中国性’自身的文化差异的追问,及其关于‘文化中国’的重构,使得一种不同于50—70 年代的‘民族性’叙事得以浮现,并成为80 至90 年代文化界的重要问题。 ”阿城是参与这场“关于中国文化再辨析工程”的作家。 他的“边缘化”的小说,深植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以包蕴、想象“中国文化”为手段,从而达到重构当代“文化中国”之目的。 他有着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极具个人化的方式。 他不算一个高产的作家,却用精品,在中国文化断裂带上, 留下了与传统文化筋骨相连的深深足印。 他再三说自己只是20 世纪80 年代创作的“个案”,“我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然而我们太需要对阿城式的“个案”给予剖析,由此看清“中国文化”传承/扬弃、延续/重构的合理性、可能性、路径方式、文学样貌,切不可因其不入多种版本文学史的主流而将其随意轻轻带过。
一、边缘化的人生启蒙,边缘化的人生经历,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成就了阿城小说的“边缘之相”。
阿城的父亲, 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因为《电影的锣鼓》等评论,在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全国知名右派。 家庭的政治变故,将共和国的同龄人阿城抛到了社会主流群体之外,因而成就了另一个被边缘的、特立独行也独思的阿城。
被边缘化和没有尊严的忧愤,在阿城童年、少年的记忆里刻骨铭心,尽管他后来的小说,包括其他文类的文字, 从来都对被视作异类的伤痛显得漫不经心,如同他在成名作《棋王》中,通过棋呆子王一生之口作出的声明:“‘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 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而正是被边缘化的政治遭遇, 导致阿城所受教育的边缘化,进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的边缘化。 北京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店、画店成了少年阿城的课堂和“免费博物馆”。 他声称“我的启蒙是那里。 你的知识是从这儿来的,而不是从课堂上,从那个每学期发的课本。 这样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了, 和你同班同学不一样,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样,最后是和正统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了。 知识结构会决定你”。 因此,阿城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有代沟,只有知识结构沟”。
青年和中年的阿城继续被边缘:赴山西、内蒙、云南插队十年有余(1968 年至1979 年);一作成名之后,他去了美国,又一个十年有余(1985年至1998 年)。 在国内外来来往往两年后,2000年他终于又回到出生地北京。 倘若说前半段的“边缘”是政治歧视,是人生无奈,那么后半段的“边缘”则是“习惯”,是“选择”,而不是“被”。 一路的人身历练使阿城的小说也成就了一副 “边缘之相”。
需要强调的是,成年之后阿城的“边缘化”似乎比少年时代更多了一份理性的成熟和思想的深刻:他从社会底层的、从乡村的、从少数民族地区的、从西方异质文化的诸多视角,看时代变迁的云卷云舒,看民族文化的变与不变。 阿城用他在“免费博物馆”里的获得,去确认民族文化深层那些积淀深厚、恒久不变的“常识”,去探究文化多元构成的历史根系,去思考文化的显性表达和隐性暗示,文化的规范性与非规范性的相互渗透参照,文化的普罗大众和中产阶级趣味,文化的“焦虑感”、另一种“焦虑感”和“不焦虑”,等等。
二、初始文本的“私密性”与不入文学主潮
因为被“边缘化”的自知之明,阿城成为一个没有强烈发表欲的作家。 请看他的几段自白:
我在公开发表文字之前,也写点儿东西给自己,极少,却没有谁来干涉,自由自在,连爱人都不大理会。 我想,任何人私下写点儿东西,恐怕不受干涉的程度都不会低于我
……自由写的东西若能满足自己这个世界,足够了。
《棋王》发表后,阿城1987 年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访问时这样回答《华侨日报》文艺副刊记者的提问:
我写好《棋王》后,一位朋友拿去看,他有一个在《上海文学》当编辑的朋友在他家里看到了手稿,就拿去发表了。 我都没来得及表态,手稿的标点符号还没写清楚就给人发了。 发了以后就热闹起来,我也被人吊起来了。
2004 年阿城接受査建英女士访谈时说:
我写的那些东西本来是私人交流的……这之前我寄过一些插队时写的东西给在纽约的丹青看过,也给美院的一些朋友看过。 八五年讲给李陀他们听的时候,李陀他们的鼓励让我明确知道,手抄的可以转成铅印的,可以给不认识的人看,这对我的心理有建设性,我永远感谢李陀他们在这方面给我的帮助。
画家陈丹青印证了阿城的如上所说:
从八三年夏天, 我记得此后一年多,阿城陆续寄了好多篇小说给我看,天哪,全是原稿啊!楞用圆珠笔写的那种,写在分行的、
有字格的纸上,一篇一篇寄过来。
阿城1991 年8 月18 日致法国评论家诺埃尔·迪特莱的信:
《遍地风流》 是我七十年代随手写下的一些文字,有关一些情绪,一些场景,一些人物和事物的印象。这些文字,通常很短,失散的也很多。 从乡下回到北京后,曾投给文学杂志,被退回来,大概是无法归类,小说? 散文? 笔记? 《棋王》发表后,各种杂志要稿很多,又很急,并且要求字数也多,于是两三篇合为一组拿去发表, 即你看到的<之一>、<之三>等等。当时给出去很多,后来都想不清楚谁拿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若干判断:第一,阿城小说的诸多文本, 包括他轰动一时的成名作 《棋王》,本是私密之作,原来并未打算发表。 创作心态“自由自在”。 第二,“手抄”转成“铅印”有较长的时间差。 作品写作的时间多在插队之时,即文革时期或改革开放初期;成名作《棋王》发表的时间为1984 年,《遍地风流》 系列短篇单独发表和结集出版更在其后,创作与发表的时间差十年左右乃至更长。 文稿一朝得见天日,彼时新时期文坛的主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已过月盈。 第三,没有《上海文学》的那位编辑慧眼识珠,阿城不入主流的作品破土而出,更不知会推迟至何时。 第四,阿城“抽屉文学”的部分佚失——阿城称“本来这类东西有上百篇的”, 而作家出版社结集阿城小说,1998 年《遍地风流》结集,计59 篇;2000 年《棋王》结集,计10 篇;两集无重复。 粗算即知:佚失数可观。
文学史家喜好归类。 不入文坛主潮的阿城,在多种版本的文学史中, 被归类至 “寻根派”作家,理由自然是因为他们的“同”:他是以韩少功“寻根宣言”《文学的“根”》为代表的若干篇著名“寻根论”的作者之一,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屡屡被研究者所引证。 他对新时期初期的中国文学“常常只包涵社会学的内容”颇感“悲观”:“社会学当然是小说应该关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 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他”。阿城从政治、经济的“问题小说”的新套中退却,也不再满足于对民俗民风的一般描摹,而是从文化视角对现象世界作审美的整体把握。 他不仅反对“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的“文革”,也对管窥蠡测的某类中国“主流小说史”疑窦重重,进而顽强地试图重建“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的关系,《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表达了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种种新论。 这些都是他与寻根群体同气相求的佐证。 他声明:“我是支持‘寻根派’的,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是要去找不同的知识构成,补齐文化结构,你看世界一定就不同了。 ”“排列组合多了,就不再是单薄的文化构成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阿城与寻根群体是有差异的, 他本人提到过这种 “差异”:“‘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 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 ”“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 韩少功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新东西。 原来整个在共和国的单一构成里,突然发现其实是熟视无睹的东西。 ”差异还表现在,另立新旗的群体急于形成有理论、 有实绩的潮流,从而获得文坛认可。1984 年底的“杭州会议”,便是寻根作家和评论家们的一次“文化合谋”。 而阿城始终宠辱不惊地玩着一个人的游戏——“抽屉” 里的东西早已形成——他习惯听从自己,听从“免费博物馆”的浸染,别无选择。 他对“寻根文学”有个人的基本判断:“寻根没有造成新的知识构成。 ”他本人也“造不成新的文体”。
三、阿城小说的“风度”
2006 年底, 王德威先生以 《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 在北大中文系演讲,他提出了其个人在小说史研究的论点:“我觉得在19、20 世纪漫长的小说现代化的过程里,早期作家学者的目标是‘祛魅’,无论是鲁迅个人或是他所代表的批判写实主义,都希望把小说作为针砭现实人生的利器,将传统中阴魂不散的鬼魅祛除。 但是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在小说界,可能是‘招魂’。 有心的作家希望借小说再次把我们曾经失去或者错过的各种斑驳的记忆,纷乱的生活体验,各样的理念情绪重新思考反省。 中国现代性在启蒙和革命之外,也许还有些别的?”无论如何,阿城都应算作“招魂”的作家,而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他的“别的”,究竟是何种模样?
评家大多偏爱阿城的“三王”,而对他个人化风格更为突出的《遍地风流》中的几十个短篇缺乏重视。 阿城这样解释他的《遍地风流》中“风流”一词:“‘风流’中的‘风’,是‘风度’,我此处结合了风俗、风度两层意思,每个短篇中亦是在捕捉风俗和风度,包括自然景物的风度。 ”“风度是指不自觉的时候,自觉了,就是摹仿出来的,也就不是风度了。 总之,《遍地风流》用直白的话说,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各种风度’。 ”评论阿城小说,我想“风度”实在是最贴切的词语。
下文我们探讨阿城别一样的“招魂”的“风度”:
第一,“不焦虑”的风度。
阿城以为: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五四那些人是有‘焦虑感’的”,“焦虑”的结果是五四以后的小说“文以载道”:“以前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是由文章来载的,小说不载。 小说若载道,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为闲书? 古典小说至多有个‘劝’,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道’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面对访谈主持人的插言:“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焦虑的人写出来的创作,争论也好,问题的提出也好,都是焦虑心态的产物。结果反而淹没了你说的这种人的声音。 ”阿城坚称:“我不焦虑。 ”他还进一步说明:“当你的知识结构扩展改变的时候,问题改变了。 这时你发现,还有东西。 ”于是,他别开生面地从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方面讨论这个“焦虑”。他批评“由于焦虑,我们现在对时间的承受力越来越脆弱,急得就像火烧猴屁股:一万年太久! 中国这才一百年,到五百年的时候,你再去看。 ”
“不焦虑”的阿城,写“不焦虑”的小说:他不是从显性的、单一的政治层面干预生活,而是从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层面展示生活;他以民间的价值立场,个体的价值恪守,外道内儒的文化倾向,不入主潮的小说样貌,对抗人文环境反人道、反科学的时风;他以“历史过程”拉长了睹物观世的焦距,以“边缘化”拓宽了“民族文化”的空间;他别有一种经历过大风暴之后的从容、淡定、敏锐、深邃。
《棋王》 一出, 不少评家狂评阿城与道家文化,对共和国的同龄人竟然衣钵老庄,颇感好奇和疑惑,也有读出儒家精神者,那似乎只是附加或至多是互补。 后来,我们读到阿城如下文字,才有些许醒悟:
我喜欢孔子的入世,入得很清晰,有智慧,含幽默,实实在在不标榜。道家则总有点标榜的味道,从古到今,不断地有人用道家来标榜自己,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 我曾在《棋王》里写过一个光头老者(本文作者注:车轮战中求平手言和者),满口道禅,捧起人来玄虚得不得了, 其实是为遮自己的面子。我在生活中碰到不少这种人,还常常要来拍你的肩膀。汪曾祺先生曾写过篇文章警惕我不要陷在道家里,拳拳之心,大概是被光头老者蒙蔽了。
细读起来, 阿城的小说实在都是入世的小说。 他推崇儒家文化所建立的社会基本规则、道德理想和伦理, 譬如 “信用”、“助人”、“尊重隐私”、做人“最起码的教养”等,把它看作文化传承中的“常识”,需要格外地看护和恪守。 这些也是他读杂书所形成的“知识结构”的价值核心,进而成为小说文本的价值核心。 看来“不载道”并非无“道”,只是不可以“腔”载罢了。 阿城讨厌小说的“学生腔”、“文艺腔”,甚至还有“寻根腔”。
第二,“人性之真”的风度。
阿城说:“丹青(本文作者注:画家陈丹青)要历史之真,我比较要人性之真。”诚哉斯言。阿城小说人物的最有魅力处,即是“人性之真”。 他以边缘人的视角,看边缘人的生活形态,书写人的纯粹的或不那么纯粹的动物性以及人的丰富的社会性,书写“文明社会”遭受的种种污染,拥抱乡土的、蛮荒的、原生形态的生命活力,眷恋历史纵深处多姿多彩的文化遗存。 阿城在《思乡与蛋白酶》、《爱情与化学》、《艺术与催眠》、《攻击与人性》等散文中解读人的动物性,当然那是科学而非文学,却能证明他对人的动物性有相当专深的研究。 而文学是需要赋予科学以梦幻、以想象、以浪漫、以复杂、以意义、以多义的,从这个角度说,“阿城的小说”比“阿城的科学”(人类学研究)更有滋味,只是在“冷峻客观”上,两者常常相通。
阿城以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形态彰显“人性之真”。 他既善写“衣食为本”,也善作“性的文学”。 于前者,一贯好评如潮;对后者,至今关注甚少。 评论夸赞阿城“民以食为天”的文本: 棋王王一生的吃相,知青们的蛇肉大餐,堪与任何中外文学经典相媲美。 更有好事者鼓动写《吃王》,不知作者是否曾经心动。 评家又普遍认为阿城不善写女人,不善写爱情,这是误读。 《遍地风流》短篇里,随处可见“性”的话题,只是写了性压抑的时代,性压抑的男女,性的非常之态,让人觉得荒谬和尴尬,却为当代“史传”平添了并非文人虚构的“传奇”:插队太行山的女知青,是在听粗俗的村妇不堪入耳的“天骂”中获得了人生的“性启蒙”,想象并幻想着自己人生的第一次 “天骂”。 (《天骂》)油灯摇曳的夜晚,知青们借着讲“同性恋”的故事壮胆,发展着“异性恋”的续篇,万般无奈间还得钻回“同性”的被窝。 (《兔子》)一对同班的少男少女,在懵懂交往中情窦初开,多少无法解释的美丽“春梦”,最终破灭在“文革”中——女孩被打致死,罪名是:勾引腐蚀红卫兵。 (《春梦》)在部队养鸭养猪的大兵,复员回乡找不到老婆,因与人打赌:女知青的裙子里是否穿了裤子,忍不住还想验证,被判流氓罪,死刑立即执行。 (《打赌》)爱情多么需要氛围,多么需要情调,多么需要诗歌,多么需要文学的助兴,知青们因为青春年少和教化,并不缺少这一切:《秋天》写秋的美景,秋的悠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时采菊? 而且悠然?秋天嘛”。知青由此快乐,由此冲动,由此野合,由此还想刻一枚“山气日夕佳”的闲章。 然而,“悠然”毁灭于现实残酷——村妇与人“耍流氓”,丈夫弄个狗皮睡在炕下,一个男人每次付给两分钱;于是知青揭发,吊打了那个女人;年底分红, 村里每个劳动力的全部所得是六分钱——“山气日夕佳”的闲章,从此没有刻完。 (《秋天》)或许——从此, 阿城笔下无正常意义的女人,无抒情想象的浪漫爱情。
阿城善写母性。 他说:“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为什么? 因为女子有母性。 因为要养育,母性极其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的第一等妩媚。 我亦是偶有颓丧,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 ”“韧”的母性是灾难的避风港,《棋王》中命途多舛的母亲,《会餐》中如老兽哺育幼仔的母亲们,无不令人动容。 这一定还因为,阿城本人也有一位伟大和敢于担当的母亲。
历史常常是由“大说”构成的。 阿城对所经历的历史重大事件敏感而又记忆深刻,而搬进小说里, 他不惜堂皇地拣拾历史学家遗落的饼屑,这倒回归了“小说”发生之时的本相。 读那些镌刻下时代印痕的情节、细节,体悟历史是如何从贴近平民而走向真实,如何从一斑而窥见全豹,如何完成宏大与卑微的链接,意义是如何产生或者被解构。 这一刻,“人性”在“小说”里扮演着书写者赋予的最为重要的角色。
1966 年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历史大事件,阿城小说的透视点却缩小至:“天安门广场遗留下近五万双被踩落的鞋子, 包括初中一年级学生王树林明年的新布鞋。 ”小说开篇为“布鞋”作了足够的铺叙,那是物质匮乏年代,贫民之家,姥姥千辛万苦,千针万线,为外孙备下的第二年必须穿满大半年的单鞋。 于是,宏大的、伟人的、有“革命意义”的历史一刻,与微小的、庶民的、初中生切身感受的历史事件, 产生了对话和张力(《布鞋》)。《小雀》、《纵火》等篇,也篇篇皆有“大说”与“小说”碰撞的力度,错位的惊悚,缠绕的魅力。 于是,历史因历史逻辑而宏大,小说因人性真实而鲜活。
第三,“笔记”体的风度。
“笔记” 体在当代中国小说作家眼中是陌生的、久违了的文体,但在文类革故鼎新的历史演进中却源远流长,枝叶繁茂。 陈平原先生的专著《中国散文小说史》,既定义了散文和小说作为文学的两大门类,各自的“独立性”——两者之间的“差异”,更别开一路地讨论了两者之“合”,两者某种程度的互补互动。 他对“中国小说”和“中国散文”发展过程中,两者互为“刺激”、互为“启迪”,“穿越文类边界的尝试”大加赞赏,他说:“在这方面,作为中介的‘笔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来,正是借助这座桥梁,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笔记’之庞杂,使得其几乎无所不包。 若作为独立的文类考察,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但任何文类都可自由出入,这一开放的空间促成文学类型的杂交以及变异。 对于散文与小说来说,借助笔记进行对话,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介入,都与之渊源甚深的‘中间地带’。 ”这无疑道出了“笔记”在中国文类演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阿城的肚里林林总总装了为数可观的 “笔记”,他向想要了解世俗变化的读者,推荐“不妨多看野史、笔记”。 仅《魂与魄与鬼及孔子》、《还是鬼与魂与魄,这回加上神》两篇,他便兴趣盎然、饶有趣味地转述过如下若干清人笔记: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刘炽昌《客窗闲话》、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袁枚《子不语》、李庆辰《醉茶志怪》,等等。 他还由“笔记”勾连出当代作家汪曾祺:“《阅微草堂笔记》 的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都有这个特征,所以汪先生的文字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字中仅有的没有文艺腔的文字。 ”“明清笔记中多是这样。 这就是一笔财富了。”其实,阿城与汪曾祺本是路径一致,他才会如此惺惺相惜。
阿城的小说,尤其是结集于《遍地风流》的短篇,彰显了文化断层中难得的“笔记”体风貌:随笔随记的叙述风格,截取或人或事或景,不求叙述的完整,却多有志奇志怪的跌宕;皮俗而骨雅,贴近俗世俗景,于朴野中透出文人情致、意趣、哲思;清俊摇曳、极简极净的文笔,在当代文坛能比肩者寥寥。
阿城的笔记体小说以俗为美。 他明白:“中国小说古来就是跟着世俗走的,包括现在认为地位最高的《红楼梦》,也是世俗小说。 中国小说在‘五四’以后被拔得很高,用来改造国民性,性质转成反世俗,变得太有为。 八十年代末,中国内地小说开始返回世俗。这大概是命运?‘性格即命运’,中国小说的性格是世俗。 ”王德威先生在北大的演讲特别强调了阿城《遍地风流》世界里的“风流人物”,是只有屁股眼是白的矿夫,站在纪念堂顶顺风撒尿的建筑工人, 穿着肥料袋做裤子的农民, 干校捣粪的学员……特别强调那些不文雅的、残暴的、惨烈的场面,他说:“这个是中国传统抒情诗学不会碰到的。 可是我认为阿城是有意为之。 而且他必须要写到这么粗俗,这么狂野,才能用来作为某一种抒情艺术形式的反省,以及对文类本身的批判,以及接之而来的超越。 ”王先生无疑点明了阿城小说最为重要的一面。 然而另一方面他或许还来不及细讲——阿城在不耻于言俗的同时, 骨子里推崇历代中产阶级的趣味、修养。 他有中产阶级崇拜症。 阿城毫不掩饰地表明:“其实后来想起来,我喜欢那个时期,就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不焦虑的人,他们在看莫奈、看梵高、看康定斯基,看左翼引进来的麦绥莱勒、柯勒惠支,表现主义的格罗兹,还有鲁迅喜欢的比亚兹莱。 ”阿城认为,艺术、文化是奢侈的事情,“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而“文化产生的那个土壤被清除了。 剩下的,其实叫文化知识”。阿城叹息文化的“根”被斩断,他凭吊“根”文化的审美旨趣。
阿城的《棋王》,从最底层的贫民到曾经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笔涉物质层面的生存到精神层面的需求——一面是知青的 “群体记忆”: 关于“吃”和“饿”的故事;另一面则由家世不凡的知青“脚卵”回顾别一样的传统:名人云集,高朋满座,吃蟹,下棋,品酒,作诗。 小说中的“我”会不合时宜地谈论杰克·伦敦、巴尔扎克,幼时曾见过的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名作《夜巡》,曹操的《短歌行》。会笔涉在河边画裸体写生的无名画家的人体审美论。 小说在更高的哲学层面,借神秘的“捡烂纸的老头儿”谈“道家阴阳”,“棋道”与“生道”;借未出场的“脚卵”父亲,传乱世生存之学。 这是阿城的另一种尝试和反省,他没有从“文革”流行的阶级对立的视角走进故事纵深——一副王一生母亲捡牙刷把磨制的让人潸然泪下的 “无字棋”和另一副“脚卵”家祖传的“明朝乌木棋”成为符号,前者指代人性母性,后者指代生存智慧和文化审美,它们的出场,完成了文化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汇合,即是小说篇末所言:“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象人。 ”
读《遍地风流》,看文明的碎片,边关景色中蕴含的文人审美理想:小河、草冈,草原青年男女间的打趣挑逗。情歌悠扬,爱情似火。(《洗澡》)峡谷、巨石、蓝天、大树、雄鹰、骏马、骑手,三五人家,一幢石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仿佛广袤苍穹,时间凝固,一派天高皇帝远的景象。 (《峡谷》)想想是作者随记于阶级斗争斗得鸡飞狗跳的年月,寄予的情感,既在文里,更在文外。
异族风情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首领、马帮、藏汉,气贯滇西的怒江,悬于万丈绝壁间的溜索,“命在天上”的过溜索的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搏自然的雄壮。 (《溜索》)
阿城小说落笔时选择刻意近俗而貌似避雅,除对传统小说与世俗的关系了然于胸之外,还源自他艺术品位很高的父亲。 阿城怀念父亲的指点:“八十年代我发表小说,我父亲从杂志上看到了,批评我在小说里提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知道而不显出,是一种修养。 就好像写诗,用典,不是好诗。 唐诗不太用典,并不表明他们不知道唐以前的典故。 你看李白、李贺,直出,有自我的元气。 ”阿城后来发表的《遍地风流》几十个短篇,“直出”居多,“元气”十足,避雅而不失雅,俗中藏雅——批评家是高人,小说家才受益良多。
小 结
阿城多少有些“偶然”地登上20 世纪80 年代文坛,他的小说“风度”却昭示了历史的必然:文化断裂带上, 文人们总会留下历史深深浅浅的印痕,即便焚书坑儒,即使经历激进变革,中华文化都将直面难以割断的血脉。 传承和变革缺一足便得跛行。 种子播撒于民间,根须伸展于街巷阡陌间,人为斩断,只能让显态文化即刻变脸,隐文或“手抄”于地下,或搁置于“抽屉”,正如棋王王一生所说,“棋谱” 毁了,“好在书已在我脑子里”。 春风又度, 自会再现星星点点的“绿”。 中国当代小说史上,阿城的那些边缘的、人性的、 久违了的笔记体的作品, 正是古老的“根”绽出的新鲜的“绿”。
[1]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8.
[2]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
[3]阿城.棋王[M]//吴亮,章平,宗仁发.民族文化派小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
[4]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N].文艺报,1985-07-06.
[5]阿城访谈.文学报,1987-03-19.
[6]阿城.阿城致诺埃尔·迪特莱的信[M]//阿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7]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M].北京:三联书店,2010.
[8]阿城.闲话闲说[M]//阿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9]阿城.魂与魄与鬼及孔子[M]//阿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10]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15.
[11]阿城.威尼斯日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