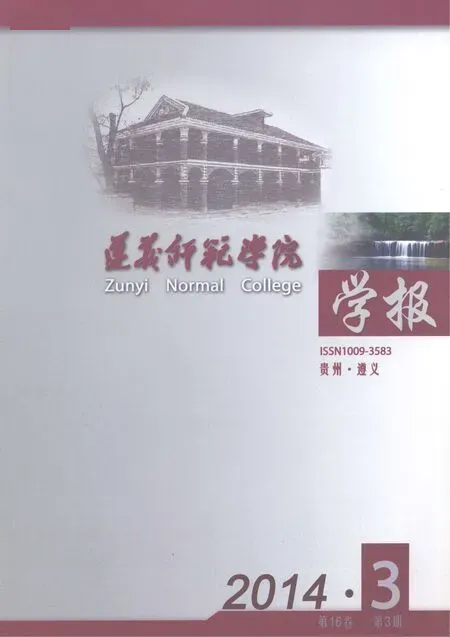播州土司研究现状及展望
党会先
(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播州土司是贵州土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袭七百余年,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素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美称,因此研究播州土司无疑是地方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司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播州土司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近三十年以来播州土司的研究状况予以梳理,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化播州土司问题乃至于西南土司问题的研究。
一、播州土司研究的成果和主要内容
(一)播州土司研究的成果
播州土司研究的成果较集中体现为史料整理和论文两个方面。
史料整理方面包括文献整理和碑刻整理。文献方面主要有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周大新、王燕玉、王正义整理辑录的《明实录·播州资料辑录》,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的郑珍、莫友芝的《遵义府志》,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重新点校出版的李化龙的《平播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宋濂全集·杨氏家传》,罗克彬整理编纂的《播州杨氏史籍编年》、《播州杨氏家谱——海龙囤直系》。关于碑刻的整理主要有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遵义地区文化局联合整理的《遵义地区文物志》,彭福荣、李良品、傅小彪整理的《乌江流域历代碑刻选辑》。
论文是播州土司研究最为丰硕的成果,包括论文集、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种。论文集主要是刘作会主编的《平播之役400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学位论文有陈对的《明代平播战争研究》、郝明的《元代播州土司研究》、余祥华的《播州土司与中央政权关系研究》、邓志祥的《遵义播州土司海龙囤遗址考察与保护》、邹淋巧的《略论杨应龙时期播州土司的内外关系》、沈治江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及成因透析》;期刊论文数量最多,据笔者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和超星数字资源等系统的查阅,统计出有关播州土司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0余篇。
(二)播州土司研究的内容
1.播州土司的发展演变和主要土司概况
这一研究内容在部分土司研究专著中有所体现,具有代表性的是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其中专门有一章节对“遵义府”的土司设置及主要土司作了介绍,包括治所、族属、承袭、事迹等,是至今专著研究中最为全面的;田玉隆、田泽、胡冬梅《贵州土司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也对遵义地区的主要土司及其制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如机构的设置、土司社会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播州杨氏家谱——海龙囤直系》一书是专门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的,它以家谱的形式对杨氏在播州的活动作了简单的梳理,并对海龙囤直系杨氏的族谱进行了考证。
着力于这一研究内容的论文也比较多,如罗宏梅、徐钰《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一)》、《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二)》。在《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一)》中,作者指出播州杨氏的统治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自第一世杨端至第十世杨惟聪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杨氏作为外来汉人,未采取任何汉化措施,相反注重与当地民族相融合的阶段;二是站稳脚跟势力渐强后,家族因权力之争内部矛盾凸显阶段;三是规范家族权位继承体制阶段。总的来看,这是杨氏巩固其在播州的存在地位并逐步完善家族团结的时期。在《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二)》中,作者对播州杨氏统治的第二个时期(即第十一世杨选至第十六世杨邦宪时期)作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这一时期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杨选、杨轸、杨轼时期,该阶段播州在经济、文化,甚至在政治形象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之后播州的飞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二阶段是杨粲、杨价、杨文、杨邦宪时期,该阶段播州杨氏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期,并且也是其历史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此外还有郝明的《元代播州土司研究》论述了播州土司的历史沿革、人文和地理环境,着重对元代播州土司制度进行了梳理,包括土司机构的设立、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执行情况,并阐明了元代杨氏统治下播州的社会发展情况;王兴骥《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考释》论述了自唐至元播州杨氏的统治范围随着其势力的增长不断扩大,元代达到顶峰;陈季君《播州土司制度的再认识》和《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阐明了播州土司制度的历史轨迹及其历史作用;张贵淮、雷昌蛟《播州杨氏兴亡与平播之役》,主要介绍的是播州杨氏从唐入播开始至明平播之役爆发这一历史时期的兴亡,并着重叙评了平播之役与杨氏的衰亡;张祥光《播州建置沿革与杨氏始末》阐述了播州建置概况与杨氏世袭情况以及杨应龙之乱。
2.平播战争
“平播之役”是万历三大征战之一,它的发生不仅引发了播州地区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变化,也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明王朝的兴衰,有观点就曾指出“平播之役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1],所以平播战争历来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对平播战争的研究,是目前学界关于播州土司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方面,主要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平播战争进行总体的研究、把握。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对的《平播战争研究》,文中第一部分叙述了平播战争的历史背景和播州土司概括,包括播州的地理和战略地位、海龙囤的军事防御体系、播州土司制度发展演变和杨氏与明政府的关系,第二部分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战争的起因;第三部分是对战争进程的介绍,这也是文章的重心所在;最后论述战争的影响。
(2)探讨平播战争的性质和起因。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李世模的《从杨应龙之乱的发展进程看其叛乱性质》,文中针对学界“明朝廷因图谋在播州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从而逼迫杨应龙,杨应龙并没有叛乱”这一观点,鲜明指出杨应龙之乱就是叛乱;禹明先的《杨应龙反明及其性质研究》则认为杨应龙反明是面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时的一种反抗行为。董桂花的《浅析平播战争发生的原因》、何伦的《明代川黔两省对播州管辖之争导致的平播因起》、翁仲康的《谈平播战争发生的原因》皆从明王朝对播州统治失当,如苛政、倾轧、民族歧视等角度找寻战争发生的原因。刘丽的《试论明朝民族政策与平播的关系》、庄广镇的《平播之役——流官制与土司制的大决战》、史继忠的《播州改流是历史必然》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层面分析,指出战争的发生是明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党会先的《从杨应龙个人性格探析播州之役的爆发和结果》是从杨应龙个人性格这一角度探析其对平播战争爆发的影响。
(3)探析平播战争中明政府取胜、播军失败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世模的《平播战争胜利原因初探》,该文论证了明军军纪严明、执法坚决是其最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张文的《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通过对比明军与播军武器的情况,指出火器的应用是明军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4)论述平播战争的意义、影响。如黎铎的《试论平播战役对遵义文化的影响》阐述了平播战役对遵义文化的影响,包括其经济形态的转变,文化教育的繁荣和佛教文化的勃兴。曾祥铣的《平播战争利于历史进步》认为战争对播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是播州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洪历伟的《平播之战对现代战争的启示》、郑继强的《试论“平播”对黔北仡佬族经济、文化的冲击及影响》则从军事、民族的角度探析这场战争的影响。
(5)对平播战争中重要人物的研究。主要的文章有黄万机的《郭子章与平播战役》、谭佛佑的《明季平播抗清巾帼英雄秦良玉》、姚香勤的《李化龙与播州之役》、杨隆昌的《浅谈刘綎在平播中的作用》、苏涟的《略论孙时泰其人》。
(6)海龙囤研究。海龙囤是播州杨氏修建的军事屯堡,对杨氏维护在播州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平播战争中杨应龙的最后据点,对战争的进程起着关键作用,此外,它还是国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中世纪军事屯堡,所以海龙囤自然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史继忠《遵义海龙囤》,这篇文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介绍海龙屯及其在平播战争中的作用;陈季君、徐国红《“海龙囤”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介绍了海龙囤险要、雄、奇的特征及其所蕴含的黔北土司文化深远内涵;何筑霞《触摸海龙囤》、吴秦业《疑惑海龙囤》等文章则是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介绍海龙囤。
3.播州杨氏族属
对播州杨氏族属的研究、考证是播州土司研究较早着力的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谭其骧《播州杨保考》,该文提出了杨保系罗(彝)族一支的说法;章光恺的《播州杨氏族属初探》则推断杨端带入播州的是僰人部队,而杨端本人是僰人中的大姓领袖;王兴骥《播州杨氏族属探研》以“杨保”一词指称播州土司杨氏,遂为族称;罗宏梅、徐钰的《杨端其人及其族别考》在分析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再次明确指出,杨端确有其人,祖籍就在山西太原,为汉族人。此外研究杨氏族属的还有周必素的《播州“杨保”名称含义再析》、禹明先的《杨端考》;罗荣泉的《南平僚非僰人辨——兼论播州杨保与南平军僰人为同一族类》。
4.杨氏墓葬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杨氏土司的墓葬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对杨氏墓葬的研究也成为播州土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谭用中的《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文中概述了杨粲墓调查发掘情况和该墓葬结构、石刻装饰、随葬器物及碑志等,同时考证了该墓主人及其生平事迹。周必素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通过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相关材料的分析研究,着重探讨其墓室结构、墓葬雕刻、出土器物和地面祭祀建筑等方面的特征和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播州社会当时的埋葬习俗与丧葬特点;倪艳阗的《杨氏墓群:见证一个土司王朝的兴亡》以杨氏墓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为实证,从考古的角度论述杨氏土司的兴亡。此外还有公犊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录》和曾春蓉的《杨粲墓中异于汉俗的雕像》。
5.播州土司的内外关系
播州土司的内外关系主要指的是播州土司内部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土司、乃至明政府之间的关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李良品的《论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该文概括了杨应龙时期的三种民族关系即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并指出杨应龙个人野心的膨胀,内外矛盾的恶化,特别是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直接导致平播战争的发生和播州土司的灭亡。王兴骥《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着重探析了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的关系;李正烈《明代播州杨氏七百余年土司政权》主要论证了杨氏土司与其属下何氏土司的关系,指出杨氏在播州的统治是“成也何氏、败也何氏”;余祥华《播州土司与中央政权关系研究》,详细论述了自播州土司制度形成后历代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6.播州土司文化
土司文化的研究是土司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陈季君的《播州土司教育探析》,这篇文章探析了播州土司统治下的教育状况,指出元代土司制度形成后,播州的学校教育随之兴起,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育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了播州以汉文化和古代儒家学说为主的文化教育;陈季君的《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阐述了播州土司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及其在南宋和明时期的兴衰发展;党会先《试论播州杨氏统治下的儒家文化传播》论证了儒家文化在播州传播的特点及促使其传播的原因;此外还有从旅游开发等角度来论述播州土司文化的保存、利用,如王家洪《遵义土司文化旅游开发探析》、钟金贵《播州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7.其它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禹明先《宋代播州杨氏军制考》;王兴骥《南宋抗蒙(元)战争中的播州少数民族》;周伟明《平播战争文献汇要及其史料价值》;纳春英《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
二、播州土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近三十年来学界在播州土司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内容也趋于多面化,然而与全国其它地区的土司研究相比,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研究人员
1.缺乏主攻播州土司研究的学者。这是播州土司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受到资料搜集困难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作播州土司方面的研究很难出成果,所以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浅尝辄止,几篇文章而已,不会将这个方面作为自己主要的科研方向,这就导致目前播州土司方面的文章虽不少,但缺乏深度,少有论著出现,其根源就在于缺少真正能够“钻”下去的主攻该方向的专门研究人员。
2.没有形成合理的研究梯队。在研究播州土司的学术队伍中,专攻且有成效的如王兴骥、陈季君等这样的学者为数较少,青年学者更为奇缺。不可否认,现在也有一些具有较为扎实理论功底的研究生成长起来,他们对播州土司也有研究,如陈对、郝明都是以播州土司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但更多研究生的研究仅是为了获取学位,在之后的研究中真正能够投身到这一领域的人还是少数,更多的是在获取学位后,就转入其它领域的研究,这就造成目前研究梯队不合理局面的出现。
(二)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出发的实证的逻辑推理的方法”[2],即文献研究法。作为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播州土司的研究自然不能脱离此研究方法,事实上在相当长时期内,学者们也主要是依靠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但这一方法在研究播州土司方面明显表现出其不足。播州的地方文献,尤其关于杨氏土司方面的文献资料,在“平播之役”后被平播明军销毁殆尽,现如今留存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见于《贵州通志》、《遵义府志》、《平播战争》、《宋濂文集·杨氏家传》、各地县志,《宋史》、《元史》、《明史》、《宋会要辑稿》、《元典章》、《元史类编》、《明史纪事本末》,但不多,只有零星记载。相对于其它地区土司研究所依据的大量文献来说,如此少的文献显然不能支撑该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向广、深处拓展,所以在播州土司研究中,除了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之外,必须引入更多理论与方法,如社会调查、田野调查、考古论证等等,否则研究成效将难以有大的突破。
(三)研究成果
通过以上播州土司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播州土司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成果形式上更多的是以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出现,论文集仅1部,即《平播之役400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介绍海龙囤的通俗性读物1部,即《海龙囤烟云录》,资料集没有,学术性专著没有,在研究上呈现出研究成果不平衡的态势,从中也可反映出该方面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
(四)研究内容
对播州土司的研究,在内容上也表现为研究不平衡的特点:
1.研究“偏”政治,忽视了经济和文化。和全国其它地区的土司研究类似,播州土司的研究在之前多是从政治层面进行研究,所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相对于此,社会经济和土司文化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特别是对经济的研究,目前所见成果几乎为零。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司墓群、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陈季君的《播州土司教育探析》、《播州教育考述》基本上理清了各个时期播州教育的发展概况,而近些年播州考古工作的推进,也大大促进了播州土司墓群的研究,但从总体上讲,对土司文化的研究仍较为单一,土司时期制度文化、物态文化、土司的行为文化等都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
2.研究“偏”于某一侧面,忽略了宏观整合。“土司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必须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开,才可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得到更加完整、更加本质的认识。”[3]但目前关于播州土司的研究则明显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具体来讲,有二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对杨氏土司的族属和发展、海龙囤、平播战争、杨氏墓葬等这些重要的人、事、物较为重视,但对于播州地区的土司制度、家族宗法制度、土司衙门系统、土司地方政务系统、社会经济形态、兵制这些更能揭示土司统治本质层面的研究则明显力度不够,从而使播州土司的研究流于表面化;其二,对于播州土司的研究多集中于杨氏土司,其它土司较少论及。事实上,杨氏土司之下,土司众多,所谓的“五司”、“七姓”皆是土司,仅桐梓县就有张氏、娄氏、梁氏等土司,但限于史料的缺乏,对其它土司的研究很薄弱,成果也较少。即使对杨氏土司的研究,也多集中与杨粲、杨应龙等几个人身上。上述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播州土司的研究。
三、播州土司研究展望
近20年来,土司学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几届“中国土司制度国际研讨会议”的召开对土司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极大地促进作用。这种背景,再加之遵义海龙囤“申遗”工作的开展,播州土司的研究必将也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首先,随着播州土司研究热的兴起,研究者不再单纯局限于历史学专业毕业的学者,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艺学等专业毕业的学者也大量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他们的加入不仅扩大了播州土司研究者的队伍,而且也必将为播州土司的研究带来新的方法,如人类学研究法,即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资料,有口述资料、图像资料、碑文、家谱、私人日记或笔记、民间传说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地辨别研究,去伪存真,这种方法事实上在当前其他地方的土司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再比如充分利用新的考古发现,将之与文献资料相互佐证,此方法在播州土司研究中颇具优势,杨氏土司墓葬的发掘、海龙屯新王宫的发掘,这些都为播州土司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文物佐证。其次,随着政府和学者的重视,播州土司的研究在内容深度和广度上也必将有所拓展,之前研究比较薄弱的经济问题、土司制度、土司的社会关系等也会有所突破,如目前遵义师范学院的李懋君教授就有一省级课题,专门研究播州土司的经济制度,此外,在贵州省“海龙囤申遗办”的主持下,将有几本专著问世,涉及到播州民族及其属性、播州民族文化、播州土司制度、海龙囤考古遗存研究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播州土司研究成果不平衡的缺陷。
[1]陈对.明代平播战争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2]毛佩琦.关于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2):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