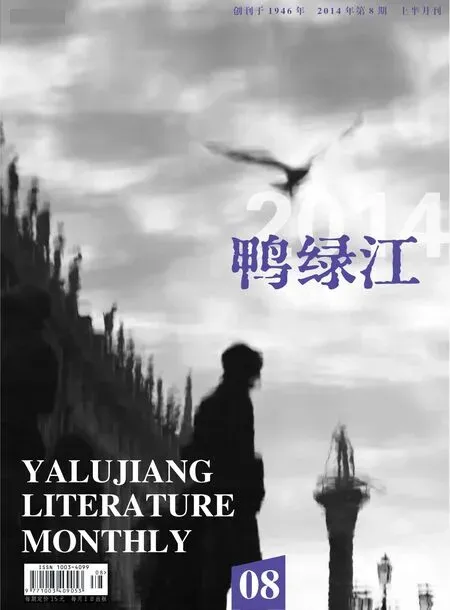『文学老头儿』张医生
王聚敏
『文学老头儿』张医生
WEN XUE LAO TOU R ZHANG YI SHENG
王聚敏

我这人向不喜攀官附贵,五行八作倒多有朋友。我也知道有个官员朋友是多么好,起码没有亏吃吧?但实践证明,我跟他们走不到一起,玩不到一块儿。即使在一起,心里也总有压抑感、不平等感,除非对方是屈尊纡贵主动跟我结交的朋友。可话又说回来,我算个老几,人家凭啥向你屈尊呢?我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很古怪的毛病,比如:假如我的朋友突然有一天成了官员,为避攀附之嫌,我会从此不登其门。前些年,领导要我为一位本地高官代写一篇某书的序言,我不干,拒绝了!领导说我傻。我卖力气他出名,又不给润笔,我才不傻呢。近些年来,又时有名人“拜托”我为其写点吹捧文字,我当然更不干,我觉得我不是受到了高抬而是受到了侮辱!相反,我愿意写的,要不就是那些与我的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平凡人,比如街头打烧饼的小伙儿、市场卖菜的老太太、换挂面的老头、修自行车的残疾人等等;要不就是那些富有生命激情、洋溢着生活情趣的奇人怪人。我下面要写的这位张医生,就属于后者。
说起张医生,现在邢台学院的老人无人不知、谁人不晓。邢台学院的前身是邢台师范学校,大名鼎鼎,名声在外,他还曾系邢师“四大名人”之一呢。这“四大名人”中,“白寿章的字画”之后就是“张医生的蛤蟆”了。所谓“张医生的蛤蟆”就是他根据中医“以毒攻毒”的原理,把蚧毒蛤蟆焙干擀为粉末,来为患者治病,此为张医生的一绝。而谁人不知,白寿章是书画大家,放在当今,也是国家一流,张医生能与其同提并列,可见他也并非是吃干饭的。

王聚敏,水瓶男,B型血,文学创作一级,《散文百家》执行主编,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作家协会特聘研究员,河北作家协会散文创作艺委会副主任;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第一、二、四届“河北文艺评论奖”、新世纪十年河北省散文创作成果奖(突出贡献奖)、首届《时代文学》优秀作品奖获得者。著有《散文情感论》。他的创作感言:写作,永远痛苦而美丽着!
说起来惭愧,我与张医生仅有一面之缘。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吧,有一天,我们编辑部突然敲门进来一位年龄五十大几的老头儿,自我介绍姓张,老家隆尧县,是邢师的校医,并称自幼酷爱文学,学过“三、百、千”,读过“三、水、游”,会背多少多少首唐诗宋词,而今想在小说上有所作为。我热情地请坐倒水,以为他是来送稿子的,问他带着稿子没有。谁知还没等我把话问完,他便神经质般滔滔不绝把我们办的文学杂志《百泉》“灭”了一番:“你们刊物怎么老弄些小诗歌小散文、小花小草呀?要振兴咱们地区的文艺,就要写‘史诗’、弄‘巨著’、搞‘大部头’呀。你看我,最近就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多卷章回体破除迷信的科普小说。”你看,又是“破除迷信”,又是“科普”,又是“长篇多卷章回体”,一下子把我逗笑了。
我问:“大作叫什么名字?”
他答:“《神考》。本小说填补了我国小说创作的空白,旨在考察世界上有无神仙鬼怪,以提高人们的科学意识。”
哈哈,“填补空白”?未免太傲气太牛了吧!我问:“你感觉大作写得怎么样?”
谁知我这一问,更激起他极大的谈兴:“我不是跟你吹,我这是一部汲取《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中的精华,去其糟粕而创作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算什么?”其情态、口气,颇似当年西南联大讲《庄子》的刘文典叔雅先生。
确实太傲了,不过我发现,张医生说这话的时候极其真诚、郑重和动情。我在一旁却笑得前仰后合。他见我笑,脸有愠色,为使我相信或服气,张口就跟我背起了几个章回的章目。这些章目,恕我现在已经记不全了,只记得第一回他是这样写的:“第一回:野狐仙大闹火神庙 张医生治病有奇方”。小说中的主人公“张医生”显然就是他,我问是吗?答曰是。
实事求是地说,从他的侃谈中,我发现张医生虽然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状况不甚了解甚至隔膜,但他旧文学的修养确实了得,尤其是古典诗词,他不但会背会吟,还能自铸新词,从容创作。那天他就当场给我背诵了他的《七律·登泰山》,他双目微合,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倏然间沉浸在一种节奏的快感和意蕴美的享受之中……说实话,张的诗词与其小说比,好得简直不是一个档次!但他却意属小说并只想搞“大部头”。
说话之间,将近中午,张医生告辞并言,《百泉》一定得支持他,使他的巨著《神考》变成铅字,说着他抓起我的手:“小王,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国文学而努力!”我说当然,并希望他早日完成这部巨著,我刊可以连载。他说:“好,我们一言为定!完成后我马上送来。”那是行外人之见,行外人是远不能走进这个“文学老头儿”的精神世界并会意欣赏其文学情趣

可是,自那次以后,我盼啊盼,想啊想,但张医生再也没有来过编辑部,连载之事遂告落空。是因其“巨著”没有完成,还是因“巨著”没有达到名著的水平?二十多年了,我仍不时想起他来。说来也怪,我与张仅有那一面之缘,岁数相差悬殊,但说实在,仅那一面,我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个热情洋溢、趣味横生、真诚而又满腹学问的文学老头儿!也许有人觉得他“妖道”“神经质”,的!
可悲的是,那些年,学校里许多人却把张医生的故事作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添油加醋,以增传奇。此不足怪,多数人是在赏其奇才,仰其特立独行。但有少数人意在调侃涮洗,比如有人调侃他的《神考》——张医生跟一个文学青年讲《神考》,说着说着就自己背念起来了:“第一章:野狐仙打闹火神庙,张医生治病有奇方。话说在河北省隆尧县境有三座大山,一曰唐山,二曰尧山,三曰宣务山。在宣务山之上,有一神庙,曰火神庙。有一天,母女二人徒步爬山,气喘吁吁,前来进香。进得庙门,母女先将馒头、豆包等供饷摆放在供桌之上,然后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待磕完抬头一看,供饷不见了。母女大惊进而大恐,以为闹鬼了,是神或鬼把供饷拿走吃了。母女惊恐万状,腿脚发抖。欲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张医生背到这里停下,那青年急问:“完了?”张答:“第一回完了。”青年疑惑:“怎么到关键时刻就停下了呀?”张急了,训那青年:“你怎么连这个常识也不懂啊?章回小说的特点,就是每到关键时刻,必戛然而止,以留悬念,使看官顿生再读下一章的兴致。”青年脸红,但又小心地问张:“那供桌上的供饷突然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这时候,张神秘地凑近青年,趴在他膀子上,小声耳语:“是一只小花猫把供饷叼走了。”
众人听了,无不笑得前仰后合,我则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位老头儿的文学趣味。
再比如,有人调侃张医生作诗,说他的诗只押韵没意境,像山东快书。其实不然,请看其中一首常被人调笑逗乐的《七律·登泰山》是这样写的:
串联大军志气豪,
步出摇篮跨东岳。
山高一五二四米,
不及珠峰膑骨高。
伸出左手捉玉兔,
伸出右手捉金鸟。
文科发达空间大,
理科发达空间小。
俯瞰东海一滴水,
地球是个土坷垃。
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后两句显然是调侃者为增强该诗的“可笑度”而加上去的。想一想,能写出如此好句子的张医生,诗中怎会出现“地球是个土坷垃”这样的俗句呢?而这样的好诗,恐调侃者也未必能够写得出呀!调侃者在此也许并无恶意,但调侃者若是行外人,犹可原谅;若调侃者恰也是文人、校园中人,则显得很可悲了。因为一个文人不能理解会意另一个文人的“怪”“妖道”甚或“神经”,并认可其才华天赋,反而取笑调侃之,以显示自己的杰出和高明,那么这个人是否真文人,就值得打问号了。在常人看来,张医生的言谈行状也许有点“怪”有点“妖道”,但那是一种文学家的怪,一种有文化的妖道呀!虽然张医生并不甚了然中外现当代文学,而只钟情于旧体诗和旧体小说。
关于张医生“怪”和“妖道”的故事,我听到的还有很多。比如1950年代时,他曾发明研制了“土飞机”一架:在自行车梁上焊接一螺旋桨,轮盘链接螺旋桨,脚蹬轮盘,以求带动螺旋桨,从而飞翔;比如除了用蚧毒蛤蟆治病外,还悉心研制治癌中药;再比如,学校有一对男女教师通奸,有一天上午他俩正在办公室做爱,被一个去交作业的学生撞上,那男的急中生智,迅速来了个“张飞大蹁马”,一下子侧身在女的身左,边揉女人肚子,边说是那女老师肚子疼,并忙嘱那学生快去叫校医张医生。张医生早就知道那对男女间的勾当,一听便拿了个最大的针管和针头,边走边说:“大针头伺候,大针头伺候!”令人忍俊不禁。还有他生活中那些阴差阳错的趣事儿……总之,张医生是一位富有生命激情、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且浑身洋溢着生活情调的文化人!在我眼里,他比那些校长书记甚至一线的教授,要有趣得多、有价值得多、伟大得多!虽然他的那部“巨著”《神考》至今尚未出版,变成铅字——这也成为我这个忘年交的一个牵挂。直到在前年的一次宴会上,我认识了他的女婿,才得知八十多岁的张医生近年已过世,心中一番唏嘘:唉,这位喜欢了一辈子文学,写了一辈子《神考》最终也未出版的“文学老头儿”张医生呀!
就像余杰所说的,随着北大那些有情趣有学问的老教授们的陆续去世、北大从此“无故事”一样,随着张医生的去世,邢台学院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无故事”的“务实”的新时期。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