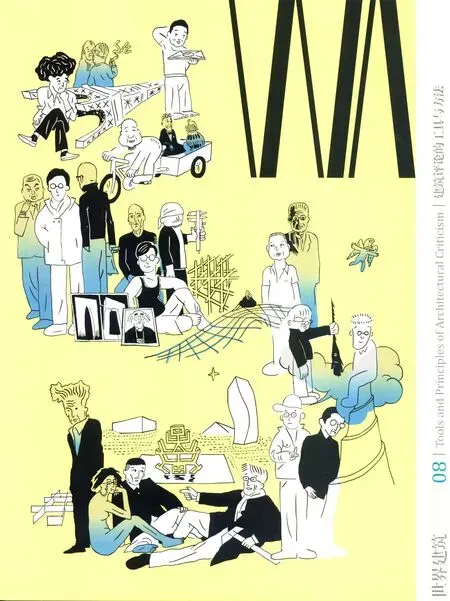具足的批判性建筑学
——主导知识再组织的当代建筑批评图式
周榕
具足的批判性建筑学
——主导知识再组织的当代建筑批评图式
周榕
作为现代建筑学的核心内容,现代建筑知识体系依据乌托邦原则而建构,分为陈述、解释与功能三大系统;而这三大知识系统分别导致了活力、意义、及创新性在现代建筑学体系框架内的丧失,令当代建筑知识体系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批判性建筑学试图通过在世型、交互型、前置型建筑批评对现代建筑知识进行再组织,从而发现活力、意义、与创新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并籍此将被乌托邦灭活的现代建筑知识体系,重新放回一个包容了批判性差异对立要素的具足世界。在这个具足世界中,批判性建筑学也在知识演进的整体背景下获得了一个更新的具足定义。
建筑批评,批判性建筑学,现代建筑知识体系,乌托邦,知识组织,具足世界,具足知识体系,具足批评
1 现代建筑学的乌托邦化知识组织体系
建筑学,诚如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所言,“既是行动也是知识”[1]15。与一切具有生命周期的学科一样,现代建筑学,也必将始于行动而终于知识。当现代建筑学的重心从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运动)暗自转移到知识世界的体系建构之后,现代建筑学就开始被知识组织所不断定义,而现代建筑学的发展也随着其知识范式的稳定完善而趋于减速乃至停滞。
作为现代建筑学的核心内容,现代建筑知识体系已经近乎完全支配了当代建筑的生产实践,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建筑学的格局与走向。由于当代建筑知识体系已发展为一个充分自足、自洽、自治的稳定而日趋封闭的结构,在当代建筑学体系内部,行动对于知识基本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既无法改变,亦难以增益;另一方面,愈益惯性化与惰性化的知识组织也无力为行动提供充足的驱动能量与创新想象,反之,却给行动设置了重重的观念禁区和思维捆缚。当代建筑学,亟待对其内部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为此,必须深入剖析当代建筑知识体系的存在状态,从其内容源流、建构逻辑与组织方式入手开展研究。
尽管建筑知识的源头是有关建筑行动的信息,但纯粹原生态的信息却不能成为知识。从建筑信息变成建筑知识,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处理、转化和组织程序:第一步是抽象组织——切断信息与周边环境的复杂关联并挤去感官经验的水分;第二步是归纳组织——通过特征提纯剪裁掉信息中多余的差异性枝蔓,以提高其认知效率;第三步是分类组织——令游离的信息根据关联原则纳入特定集合,这个分类筛选的过程将大量非典型、特殊化、难以归类的信息屏蔽在建筑知识体系之外;第四步是系统组织——将类型化知识进行关系定位,并将这种关系状态固化为一个定义明确、逻辑自洽、层级清晰、并易于认知、检索和传播的结构体系。这一组织过程,再度剔除掉大量与系统逻辑相异、相悖、及难以用系统原则进行一致性解释的加工信息。如是,只有经过大量加工而在知识体系内被锚固定位的信息,才能成为知识。这个过程,恰如食材进入菜谱的过程。
仔细检省建筑知识体系的构造流程,不难发现诸多匿名而隐形的“把关人”(Gate Keeper)存在的印迹,经由这些层层把关者的机制化作用,建筑知识体系已经不再是客观、中立、真实的实践信息,而是一种预设了价值态度与构造逻辑、具有强烈观念导向、价值好恶、并具有与真实世界无关的高度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文化建构。也就是说,现代建筑知识体系所呈现的,仅仅涉及建筑学“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把关人”想让外界看到的那一部分。换言之,现代建筑知识体系实质是一种“匿名的集体偏见”。这个集体人格的“把关人”,把一切不符合其“理念”的实践信息都阻挡在正统建构的建筑知识体系的大门之外,例如,曾经的弗里德里希·汉德瓦萨(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又如“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而在知识体系中心活跃的知识经典,构成了建筑界与建筑史的所谓“主流”。
对应建筑实践的“认知、思想、生产”这三大行动环节,依据工具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现代建筑知识体系,也由“陈述、阐释、功能”三大知识系统构成。凭借这三大知识系统的转换构造,丰饶、复杂、多样、微妙的现实世界,被脱水为仅仅解决了“5W+1H”这些低限问题的知识世界。具体而言,陈述系统贮藏了回答“When、Where、Who、What”等问题的广义历史知识;阐释系统罗列了诸多回答“Why”之疑问的理论知识;功能系统提供了与生产过程“How”相关的实用知识。相应的,以传承建筑知识为主要诉求的现代建筑教育,也以历史、理论、实践三大主干课程系统为基础,搭建起整体的体系框架。
作为人类现代文明体系的一个分形组织,现代建筑知识体系同样带有强烈的乌托邦特征——超越经验、理性至上、纯净抽象、剥离时空、统一自洽、完美高效……。这个乌托邦组织图式,完全背弃了古典建筑学以经验“典范”为核心进行特定而生动的知识组织的原则,转而以抽象“结构”为核心建构普适性与自治性的知识体系。和所有类似的乌托邦结构一样,以乌托邦范式组织起来的现代建筑知识体系,在极大地提升了建筑学的结构精密度与知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令当代建筑学与真实的经验世界渐行渐远;其结果,不仅使知识失去了介入现实的合法性和能动力,更让知识生态的繁衍失去了现实世界的给养源泉。
2 当代建筑知识体系的“内卷化”困境
乌托邦化的构造机制,决定了现代建筑知识体系只能作为完整而鲜活的当代建筑世界的“缩水版”与“脱水版”,它并不能覆盖当代建筑学的全部信息域和完整问题域,仅仅可以提供一份对建筑的现实与可能世界粗略描摹并大加扭曲的认知地
图。当知识世界从真实世界剥离出来以后,由于二者之间缺乏一种紧密互动的关联机制,两个世界开始分道扬镳,现代建筑知识体系逐渐步入一个独立发展轨道,成为一个与真实世界无关的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
现代建筑知识体系的自治化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知识再生产的效率在自治的早期阶段得到有效的提升,其生产效率迅速超过现实世界的建筑生产率。这个阶段的知识再生产,对于建筑实践起到过很好的启迪与引领作用;二是知识体系在经历了爆炸性的创新增长期之后,因缺乏外界信息的有效输入而过度依赖体系内部的自我繁殖,从而开始出现“内卷化”(Involution)倾向。
“内卷化”概念源自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被他用来描述诸如哥特建筑和毛利雕刻这样的文化模式——“当其确立了某种稳定的形态之后,尽管无法转化为更新的形态,但仍然通过内部更加复杂化的方式不断发展”[2]。而当代建筑知识长期在体系内部自我繁衍、知识构成日趋复杂,却始终无法跃迁到能量级更高的创新轨道,恰是研究“内卷化”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
“内卷化”现象,表现为当代建筑知识体系的三大系统性痼疾:活力丧失、意义消退、创新乏力。从发生机制上分析,这三大痼疾的病灶分别存在于“陈述、阐释、功能”这三个知识系统的内部。
(1)陈述性知识系统灭绝知识活力
现代建筑学术体系的基础,是知识的结构性定位,以及对知识呈现方式与再生产流程的范式化规定。对知识进行结构定位和范式规定的初衷,是提高知识体系的传播和生产效率,但由于知识体系内部产生了严格的知识固化关系,打破既定关系进行重组的成本随着知识的衍生性累积而不断提高,导致在体系内部构造知识新关系的可能性与能动性——亦即知识的“系统活性”严重降低。高度结构化的陈述性知识系统,在建立知识检索的“效率机制”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灭活机制”,其结果,是当代建筑学来自体系内部知识再生产的内驱型发展动力越来越弱。
(2)阐释性知识系统涤除意义空间
所谓阐释,就是用确定的逻辑关系来定义知识关系,以形成从知识的“能指”到“所指”之间清晰的理性认知结构。现代建筑学崇尚“阐释科学主义”(Interpretive Scientism),试图用阐释结构取代价值结构,用符号取代意义。因此,阐释系统的目的是通过对知识体系进行统一的格式化梳理,来建立一个没有理解死角、具有高度认知透明性、自我指涉、自洽自治、自圆其说、从而意义自明的知识乌托邦。但事实上,乌托邦结构的天然祛魅性导致其系统内很难容纳意义关系的滋生。因为意义,是人类对于价值的情感判断而非理性评价;意义关系,是基于经验的情感关系而非基于逻辑的符号关系。在阐释系统中,所谓的“能指”与“所指”其实都只是抽象的知识状态,和真实世界无关,和个体的真实情感无关,因此必然与个人性的意义建构无关。
(3)功能性知识系统压抑创新可能
现代建筑学内部最为吊诡的一个现象,就是其价值系统推崇创新,但其知识系统却既不能解释创新的机理,更无法建立起系统性可持续创新的机制。作为与建筑实践关联度最高的功能性知识系统,不仅难以有效区分建筑创新与建筑生产之间的本质差异,反而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系统内充塞了过多在既有范式下的建筑生产性知识,致使建筑创造活动日益被范式知识所引导的大规模建筑生产活动所取代。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创新要么依赖天才式灵感爆发的神秘几率,要么等待来自系统外部的不确定推动力;而建筑的功能性知识系统发展越完善,其对建筑创新的压抑程度也就越大,一旦发展成为成熟的范式化知识系统,其内部创新的空间便被挤压殆尽。
知识体系的内卷化倾向,表征当代建筑学的系统活性在持续衰退——当代建筑学日益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应答、以及从现实中发现新问题的能力。活力、意义及创新性在现代建筑学体系框架内的丧失,令乌托邦化的现代建筑知识体系日渐遭受其是否具备时代“正当性”(Legitimacy)的质疑。这种质疑更广泛地来自建筑教育领域——以知识传授为主要载体的建筑教育,既难以开启学生的建筑智慧,更无从激发学生的创新想象,也不能为学生提供价值导航,仅只教会了学生用熟练的知识组织流程替代真正建筑创造的障眼法。简言之,一个在实践中日益失效并因此失去学科合法性的现代建筑知识体系,亟待通过新的组织逻辑进行重新定义。
3 反乌托邦组织图式的“批判性建筑学”
乌托邦组织的单一站点、统一逻辑、一元化控制,是造成现代建筑知识体系被系统“灭活”的主要原因;乌托邦图式对经验世界的拒斥以及对纯粹自治状态的坚持,根除了意义滋生的土壤;乌托邦结构对纯净致密的高效构造的追求,扫荡了利于产生新异突变的杂多生态;一言以蔽之,乌托邦化的组织结构是当代建筑知识体系陷入内卷化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代建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当代建筑学欲进行革命性的重写,首先必须从知识组织层面打破乌托邦结构的禁锢,继而以知识再组织为主线,建立起对既有的乌托邦图式具有批判性的新型建筑学体系。
美国建筑理论家迈克尔·海斯在他198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批判性建筑——在文化和形式之间》[1]14-29中,展示了如何采用批判性的态度、站点和方法,去发掘被乌托邦知识体系锁闭的巨大可能空间:他首先总结了建筑学领域两个对立的阐释性知识系统——“建筑作为文化工具”与“建筑作为自治形式”,并指出这两种阐释模式都因其纯化的极性追求而令建筑实践变得消极而僵化。要对建筑进行更富活力的描述以及更加复杂精微的分析,就必须将阐释站点从知识的两个极性状态回退,进入真实的世界。这意味着将每个建筑放置回世间的特定情境之中,籍此限制知识阐释对其真实生命状态的可能干预,从而令建筑获得某种“在世性”(Worldliness)。“在世”的站位令建筑与前述两种极性的知识观念之间产生了“抵抗的”(Resistant)和“对立的”(Oppositional)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对文化与形式两分的建筑阐释构成了一种批判性,而密斯早期的若干作品是对这种“批判性建筑”的最佳诠释。
此文中,海斯对我们的思想启示在于:
(1)质疑了建筑知识组织的乌托邦图式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无论该种知识组织的核心是文化还是形式,这种知识组织状态本身以及对极性阐释的追求对建筑而言都是一种危险。
(2)建筑学需要重新发现并回归真实的“世界”,“在世性”是建筑不可抹煞的属性,建筑一旦被剥离“在世性”而进入纯粹知识领域,即意味着建筑生命活力的消逝。
(3)密斯在1922年发表的摩天楼方案,拒绝了与任何一类成熟的设计范式相关联的类型化意义模式,而试图将意义归结为对呈现于一个特定时空、一个具有语境特质的瞬间(a contextually qualified moment)的建筑表皮和体量的感知(Sense)状态。换句话说,密斯在此建构的意义并非知识系统所赋予的抽离的、理性的、恒常的“阐释性意义”,而是在世的、情感的、瞬变的“语境性意义”。
(4)唯有切断与乌托邦式具有内在秩序与统一逻辑的知识体系(the knowledge of an internal
order or a unifying logic)之间的联系,感知才得以将建筑从非时间性的、理想化的自治形式领域挽救出来,并使其向生活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开放。
(5)对经验的征引乃是作品意义的内在本质所在。经验塑造了作品的特质与个性,令作品成为一个兼具感官特殊性与时间持存的事件,这二者对于生产和传递意义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6)知识总是试图将自相矛盾和感觉化的切身经验组织为一个(非时间化的)理想瞬间,而密斯在巴塞罗那馆中成功构筑起一个经验的迷宫阻止了这种知识组织的企图,从而让这件作品保有为一个在时间中持存的事件,其实际的存在状态被连续而流变地制造出来。
(7)作者身份(Authorship)可以令建筑师通过偶然的、特殊的、另类的知识生产与组织来抵抗文化的权威性,而这些私属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可以让整体的建筑知识增长呈现多样生态而非统一的范式逻辑。
(8)建筑批评和建筑设计都是知识的某种形式,两者在行动与知识的层面上理应保持同构性——向异议和对立开放的状态。
作为建筑批判性研究的地标性文献, 海斯的这篇文章尽管只谈论了批判性建筑的若干特征和极少案例,但其展示的创造性思路却足以开启一扇崭新的“批判性建筑学”的大门。沿着海斯的思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如下推论:
(1)批判性建筑学意味着对当代建筑的行动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新组织。如果说,批判性建筑设计对建筑实践起到重新定义作用的话,那么建筑批评就需要负起建筑知识再组织的责任。批判性建筑设计与建筑批评共同承担当代建筑学领域“批判性行动”的使命。
(2)批判性建筑行动并不囿于特定的表现形式,其实质在于对乌托邦知识体系的抵抗性态度与对立性站位。如果把“对立”理解为批判的空间策略,那么可以把“抵抗”理解为批判的时间策略。由此引申,差异化的空间站位与交互性的时间持存成为批判性建筑行动的两大最重要的特征;而空间的“在”(Presence)与时间的“存”(Duration)书写了“在世性”的两个基本涵义——因“在”而“多”,因“存”而“变”,“多”与“变”令世界具足丰饶,也为建筑的批判性行动提供了广袤的时空基点。
(3)由此凸显了批判性建筑行动的方法论模型——“入世”——把被知识绑架的建筑以及缠绕建筑的知识重新放回“世界”,在知识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建构起一种相互批判的二元关系。这种新的批判性二元构造,超越了现代建筑学传统知识领域中文化与形式之间看似两极实则一元的纯知识分歧,从而将知识组织的视野拓展到复合多个世界的具足性问题域限。
在批判性建筑学框架内重新定义建筑批评,建筑批评就从建筑学体系内行动与知识之间的反馈地位,提升到在不同构造的虚拟与真实世界之间进行沟通与互动的关键地位,进而,上升到通过持续不断的批判性行动对当代建筑知识体系进行重组。
4 建筑批评与当代建筑知识的具足性再组织
建筑批评,尽管被视为现代建筑思想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但却始终没能在现代建筑学体系中占据组织性地位。在乌托邦化的知识组织架构中,建筑评论甚至没有被当作一个单独的门类,而仅被看作是建筑理论或建筑历史研究的附庸。这就意味着建筑评论要么被当作小规模、临时性、或欠成熟的阐释性知识的尝试建构,要么被看成是片断化、进行时、前历史状态的陈述性知识的搜检备案。被排斥在阐释性和陈述性两个知识系统核心之外的建筑评论,被误认为仅仅是在知识系统边缘进行的短暂消费性的活动,因而在主导知识组织和系统建构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面前不免相形见绌。
边缘化的地位,令建筑批评对当代建筑学处于一种无能状态。事实上,由于建筑批评的基本逻辑与乌托邦架构的基本逻辑全然相悖,因此建筑批评在乌托邦知识体系内部的确是失效的,无力担负知识组织的重任。要让批评介入当代建筑学的知识组织,首先必须跳出乌托邦知识体系的封闭象限,而令批评在更广阔的操作范围内进行知识再组织。笔者将建筑批评这一主动拓展知识组织象限的过程,定义为“具足”的过程。
动词意义上的所谓“具足”,包含三重含义:首先是回到“世界”,从而令知识象限最大化,并让经过脱水化处理的知识经过经验“补水”而重获“在世性”——重建与经验世界的信息关联;第二是最大程度地网罗和收纳“世界”的内容,不挑不拣、不弃不捐,以“增补”被乌托邦观念格网所屏蔽、筛除、裁剪、脱水的那部分最具生动性与活跃度的信息,让其与乌托邦知识充分杂交混血;第三是“生境”化的知识语境建构,确保组织对象处于一个丰饶(比“丰富”更为冗余过剩)、杂多(比“多样”更强调异质)、演化(系统性持存并变化)、纠缠(不确定关系)、而平衡(动态关系)的生态环境与群落状态。
具足思维是典型的反乌托邦思维,从思维特征上看,具足思维与乌托邦思维几乎完全对立。针对乌托邦思维的单一站点、统一逻辑、一元组织等特点,具足思维试图以“多”化“一”,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最大象限,具足诸相
与乌托邦单一站点的观察和思考角度不同,具足将对知识的观察视点与思考站点尽可能分布到“在世”的最大时空象限,以利于知识状态的多样性、变化性、可能性的多面“显相”。所谓显相,是对知识状态的呈现与唤醒,令知识进入一种自我观照的觉醒状态、以及一种自我激发的活跃状态。
(2)最大包容,具足万物
乌托邦是排异性结构,而具足是包容性结构,非但如此,具足还是最大程度的包容结构——具足万物。唯有在万物中,一物的特质才能浮现,这种情形,恰与乌托邦结构用集体的普适性抹煞个体的特殊性形成鲜明对比。包容矛盾、冲突、缺陷、错误等畸零而鲜活的内容要素,具足建构本身就已经是对乌托邦所谓完美组织的一种批判,因为从组织的角度看,排它性的纯净完美本身就已是一种组织机制预设的不完美。具足组织包容一切对立之物,甚至将自身的对立物——乌托邦组织,也包容进具足的结构框架之内。
(3)最大关联,具足生态
乌托邦体系内部呈现一种致密的结构关系,具体结构内部诸要素之间则是一种松散、放任、不确定、自组织的关系状态。如果说前者的关系是机械性的,那么后者的关系则是生态性的。生态关系较之机械关系是一种更为复杂和高级的关系组织,生态关系允许偶然性、特殊性、多样性、异质性与失控性在其中的滋长蔓延。
总体来看,批判性建筑学的知识组织由“结构性组织”和“行动性组织”两部分工作构成。首先通过“具足结构”建立起一个总体的、生态性的知识组织框架,并将价值建构同步融入知识建构的进程之中。反乌托邦的具足结构,为批判性建筑学的行动性组织提供了一个匹配的、可依托的生态环境与工作背景。
从认知角度分析,乌托邦结构是透明的,而具足结构是不透明的,丛林状态的具足结构是无法像晶体状态的乌托邦结构那样可被总体认知与全面把握的。在具足森林中,唯有批评的光柱暂时投射之处得以呈现短暂的清晰性。
英国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富于洞察力地指出:“大数据时代对我们的生活,以及与世界交流的方式都提出了挑战。最惊人的是,社会需要放弃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仅需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需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就推翻了自古以来的惯例,而我们做决定和理解现实的最基本方式也将受到挑战”[3]。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注重“因果关系”的统一逻辑,恰好是乌托邦知识组织的基本特征,而构建“相关关系”,则是批评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构建起批判性建筑学中“建筑知识的批判性重组”机制:以动态平衡的具足性知识生态结构为框架依托,展开具体而微的批判性行动,组织起不断生灭的具有相关关系的知识群落。这些分布式而非层级式组织的微小的临时结构,因植根于经验而充满活力,因交往相关而产生意义,因杂交迭代而新异多变。批评的组织触角,也因此进入了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三生世界”。
5 在世型批评与建筑知识的活化组织
“固化、虚化、简化、僵化、老化”这“五化”问题日益困扰当代建筑知识体系,令其对现实的能动作用日渐降低,由此也造成了当代建筑学体系内部知识与实践的日趋分裂。
究其原因,这“五化”问题其实都来自乌托邦知识结构的固有属性——“固化”,源自乌托邦纯净而致密的结构对内部关系的刚性束缚,造成知识体系既难以在内部也难以与外部进行知识关系的重组;“虚化”,源自乌托邦理性而抽象的组织对于感官经验的弃绝以及对经验环境的切断,造成知识无法汲取经验世界的养分;“简化”,源自乌托邦结构为追求内在一致性而剔除掉内部的差异元素并降低了自身的结构复杂度,造成简化而自洽的知识级配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僵化”源于乌托邦组织的自治性运行因臻于完美而趋向停滞,也因自身构造的完美性而无从发掘继续发展的线索与动力,同时,乌托邦的完美结构与现实的非完美存在之间也找不到相互之间的接口;“老化”源于乌托邦结构的非时间性(Atemporal)特征,因此乌托邦知识体系非但没有动力针对建筑的时代发展做出及时的适配性调整,反而以结构性的傲慢将时代变迁视为非理性的浮云。
无论是系统的纯净度、抽象度、复杂度、完美度还是演化度,乌托邦知识结构与真实经验世界之间都存在着霄壤之别。这种系统性的不匹配造成当代建筑知识相对于当代建筑实践处在一种尴尬的体系性失效状态,知识体系的无效性导致知识活力的大规模衰退。相应的,随着当代建筑知识的系统性失效,以知识传承为主要载体的当代建筑教育也欲振乏力、创新无门。
既然知识活力系统性衰退的症结在于其乌托邦化的组织构造,批判性建筑学欲对当代建筑知识体系进行活化处理,就必须将知识置放于乌托邦的对立象限进行另类组织。依据前述海斯的研究,这个乌托邦的对立象限正是真实的经验世界。笔者把这种通过“入世”而进行知识组织的方法称为“在世型”建筑批评。针对乌托邦建筑知识体系的“五化”问题,在世型建筑批评相应采取5个步骤:
(1)裂解结构
打破乌托邦知识体系的一元结构、知识与结构之间牢固的定位关系、知识与知识之间科层化的普适关系,将知识尽可能还原到一个前组织的关系状态。
(2)重联时空
“在世化”的精髓就是“在地化”与“在时化”,因此在世型批评要求把一切建筑知识都要从超越时空的乌托邦状态还原为“地方性知识”和“时间性知识”。在批判性建筑学框架中,任何无时无地的知识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知识。而批评的前在条件,就是要为批评范畴内的知识加上时空限定的边界条件。与特定时空相锚固之后,知识的抽象普适性后退,而具象的特殊性被初步释放出来。
(3)链接经验
知识的增加意味着世界的减少,而知识与世界之间被剔除的部分正是经验。知识唯有通过链接经验才能“复活”,才能依托不可重复的经验特殊性来放大知识的特殊性,从而让知识对世界的作用,从“Reduce”转化为“Produce”。
(4)制造失衡
乌托邦这样的完美之物由于达到了结构的最佳均衡状态,而放弃了其他的发展可能性,因此和所有的完美之物一样,乌托邦提供不了创造性的入口。事实上,在一切文明体内,创造的最大动力都来自从文明发展的非均衡向均衡状态演化的内驱机制。建筑批评,就是一种通过破坏批评对象的既存均衡态来刻意制造失衡的外部干预机制。建筑批评可以籍由变换站点的“移位法”、从错误开始的“试错法”、炮制缺陷的“挖坑法”、交叉往还的“投石法”等运动战方法使原本处于结构稳态的乌托邦知识进入多种敌对性(Oppositional)的失衡语境,从而令其跃迁到一个被失衡的危险所激发的高能量状态。
(5)保持同步
与时间的锚固,让知识从近乎恒定的长效知识,变成具有生命周期的短效知识,逼迫知识体系随时处在一个濒临失效的边缘,只有通过不断补给具有“时效性”的新知识并吐故纳新,才得以维持一个动态平衡。建筑批评的一大作用,就是不断用时效知识来批判短效知识体系,对知识体系的当下合法性永远处在一个质疑的站点。
在世型建筑批评,通过建筑知识的非乌托邦型再组织来达成知识的个体活化与系统活化。以对密斯的巴塞罗那德国馆的研究为例,堪可说明乌托邦型常规知识组织与在世型批评对知识的活化组织之间的差异:
通常的建筑史研究,倾向于以抽象的陈述(例如时间、地点、人物、主题等等)来组织建筑知识并加以评价阐释。在这种知识组织结构中,巴塞罗那馆作为一个天才创作的整体活性状态就被所谓“流动空间”这个统一、抽象的组织规定给彻底掩盖了;对于现代建筑史这个追求自身结构完备性的知识系统而言,“流动空间”这样脱水式的简明知识构造是恰切而足够的;但对于后续的建筑实践来说,这样的知识组织状态是毫无创造活力可言的。诸如此类的建筑史知识学了再多,也不可能让人领悟到建筑创造的真正秘密。而海斯在《批判性建筑》一文中,通过对巴塞罗那馆进行现实的情境还原,不断用其真实的感知状态来质疑、挑战用既定的统一观念秩序理想化组织起来的有关巴塞罗那馆的知识。在这个批判性阅读的过程中,有关巴塞罗那馆的抽象知识,被转换成一个个活跃的具有相关关系的信息群落,这些信息群落向着更广阔的创造可能性充分开放。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世型批评还可以触发知识体系向真实世界的再度吸纳,通过批评所强调的经验环境与差异站点,来搜检那些被排斥在乌托邦知识体系之外,但在建筑实践领域具有地方性活力与效能的信息,并把这些地方性与时效性信息整合进当代建筑知识体系的动态增益进程之中。如是,零散片断的地方性知识和统一系统的乌托邦知识之间可形成一种相互批判的态势,这种差异化的知识张力将给当代建筑学带来持续性的系统活力。
6 交往型批评与建筑知识的意义组织
罗兰·巴特认为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意指。这个抽象而清晰的简单阐释结构,被现代建筑界借以发展成符号学的狂欢,或者莫测高深的所指玄学。于是,原本对建筑丰富、差异、多变、精微的意义
蕴藏与探寻,变成模式化、粗鄙化的“能指—所指”解读。建筑评论的地位,也由此被贬低到从能指到所指这条单程旅途的导游。
然而,能指与所指之间所隐现的,不过是建筑的“意思”,而非“意义”。意思是创作者的意图或阅读者的想象,而意义则是体验者与在世建筑之间一段持续作用的情感关系。意思是知性的,意义是感性的;相应地,界定意思的阐释结构由理性主宰,生产意义的价值结构则被情感支配。通常情况下,由于阐释结构是一个致密的、自我指涉的封闭性自治结构,故而结构内没有情感栖居的冗余空间;另一方面,个体纯粹的情感寄托常常引发非理性判断,由此导致理性的意思系统与感性的意义系统之间经常互不兼容。

1 昆明某工地(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

2 上京故事(主图),数码影像作品,2006,作者:周榕,成婴。
本雅明用“化学家”和“炼金术士”的形象比喻区隔了分别指向“意思”和“意义”的两类批评:“打个比方来说,我们把成长着的作品比作火葬时的柴堆,它的评论者就像化学家,它的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留给前者的是木头和灰烬,作为他分析的唯一对象,后者则一心想着火焰之谜:生命之谜。这样,批评家追问的是生动的火焰在过去沉重的木头和已逝生命的青灰上继续燃烧的真理”[4]。这里,本雅明用“生命之谜”定义了意义的终极特质。
图1所示是笔者2012年在昆明某工地所拍摄的场景——左侧是易燃易爆的乙炔瓶存放处,右侧是各种消防器材,两者之间有清晰的“意思”联接,乙炔瓶和消防器材已经形成了逻辑完整的阐释结构。然而,这个阐释结构却由于画面中间一个微型土地庙的介入而被打破了——消防器材是科学的,但却无法使工人安心,因此它只有意思而不产生意义;土地庙非但不科学,更会因香烛产生失火的危险,但是可以让工人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信仰寄托,因此它富有深层的情感意义。同时,乙炔瓶、土地庙和消防器材这三者进一步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意义关联,指向了我们时代混杂着的现代与传统、希望与不安、演进与停滞。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普通的乙炔瓶与消防器材之间的阐释结构(意思系统),因土地庙的加入而变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复杂的价值结构(意义系统)。这一场景生动指示出从意思到意义的可能途径——“交往”——外来介入方对既存的惯性“能指—所指”关系的持续扰动、涂抹与篡改。由于惯常强大的抽象“能指—所指”结构驱离情感经验的依附,故因“能指—所指”关系暂时中断而形成的理性意思的空白,恰成为经验意义的滋生之地。
受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通过多元对话来协调“生活世界”与“系统”的模式启发,笔者提出“交往型批评”的概念:交往型批评,即调动真实世界的情感经验主动介入知识体系既定的“能指—所指”关系,并以此构建复合知识世界与真实世界差异诸元的时间性微型意义空间。交往型批评的目的,是为当代建筑学重新建构被乌托邦知识结构所屏蔽掉的人间意义。
图2为笔者与成婴在2006年创作的数码影像《上京故事》,可用来大致说明交往型批评的基本方法。这张作品呈现了一个盛宴开席前餐桌的俯视图,东南西北方位的4个主餐盘中托放了当时北京正在建设中的四大建筑——国家大剧院、CCTV总部、鸟巢、以及水立方。餐桌中间是一个形状模拟北京旧城中海和南海水系的景观水盆。这幅作品尝试用非语言方式,仅仅通过画面上形式与空间关系的组织建构进行交往式建筑批评。四大建筑被切断了与其现实环境及知识语境的联系,呈现形式也选择了普通人不熟悉的顶视图,希望能尽可能干扰当时已经成为公式化的对这四大建筑的“能指—所指”解读;而选择使用中式宴席这一国人熟谙的经验场景,同时又并置了刀叉、葡萄酒冰筒、烛台等西餐元素,是试图通过一种混杂的感官经验将四大建筑向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经验侧面还原。不为人注意的是,画面右上角一杯倾倒的葡萄酒和桌布上的酒渍,则暗示着某种潜伏在欢娱深处的暗中的危险。整张画面,意思不明但意义复杂而开放。参与画面的差异各方在不同组合的关系状态中供应着通向多种可能性的意义线索。
交往型批评有着3个鲜明的特征:
(1)主动介入关系组织
和外部反馈型的批评模式不同,交往型批评强调通过异质元素的主动介入来扰乱知识组织的既存关系,并积极把关系导向新的可能性组织状态。
(2)增加差异交往元
在关系组织中,内部诸元的数量越大,关系组织的新可能性就越多;而内部诸元的差异性越大,关系组织的张力与活力就越强。因此,可以通过主动增加交往元的数量、加大交往元之间的差异,来获得更多更强的意义型知识组织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在交往型批评结构中,交往元的数量必须多于两个,而在这些差异交往元中,至少必须有一元来自情感或经验领域。
(3)增加持续往还回合
交往应该是时间性的,是在时间中持续往还、重复回合、试探差异可能性的。海斯在 《批判性建筑》一文中强调重复回合的力量,认为可以籍此执拗的作者身份形成短暂的权威性,其实这种所谓的“权威性”更多地来自差异各方在历时的重复回合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认同。
交往型批评把乌托邦知识引入意义领域,而其所建构的意义并非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不是知识与某种既存的文化模式或理论框架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知识与受众个体之间短暂契合的情感微意义,这些微意义使社会和建筑存在(实体与知识)之间达成不同层面的同情,而同情,才是一切文明体建构中最微不足道却也是最至关重要的认同基础。
7 前置型批评与建筑知识的生产组织
当代建筑知识体系的“内卷化”现象,通过由
知识范式和知识组织引导的建筑生产而蔓延到建筑实践领域。和当代建筑知识体系一样,当代建筑的生产体系也失去了系统创新的能量,而只能通过内部复杂化来继续发展。不幸的是,消费社会的来临令建筑生产“内卷化”现象日趋加剧,在消费语境中,真正的革命性创新无法被大众接受,而消费性社会机制又要求被用看似繁荣的创新假象所喂养。在这样的双向逼压下,真正的建筑创造由于低效率而倾向灭绝,建筑设计被系统性、高效率的知识再组织所偷换。当代常规型建筑设计,已沦为通过快速检索和搜集相关信息再加以重新组合、调整的流水线工种。
以系统性知识再组织取代个体灵感型设计的当代建筑生产模式,给了建筑批评一个切入建筑生产突前位置并介入知识组织型建筑生产流程的机会。而批判性建筑学所倡导的对建筑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再组织,不仅提升了当代建筑知识再生产的效率和水平,更是为当代建筑实践生产提供了机制性系统创新的可能性。
建筑创新,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基因突变,因此借鉴生物学意义上基因突变的机制,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建筑创新的本质。生物基因突变,是建立在大量杂交和多次迭代基础上的偶然性性状改变。反观批判性建筑学对于建筑批评的定义可以发现:差异要素的反复杂交与持续往还的思想迭代,恰好是建筑批评的机制特征。
在现代建筑学体系内,建筑批评被固定于建筑生产的后置地位,其职能往往更偏重于对建筑产品的意见反馈;充其量可以通过这些反馈形成对后续生产的某种导航机制。对建筑批评的后置定位,忽视了批评作为思想的主动杂交实验,其产出的迭代思想大大提高了在实践中出现创造性突变的机率。要进一步提升这种思想突变的机率,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固定周期内增加思想迭代的次数。而批评在建筑生产流程中的后置定位,人为限制了思想迭代的频率,批评之于生产出来的建筑产品而言,只能有一个回合的思想往还,如此低的迭代频率很难造成创造性突变的可能。
要提高思想的迭代频率,实现高速迭代,就必须把建筑批评提置于建筑生产的前端,并让批评贯穿于建筑生产的全过程,直至后评估阶段。如是,在一个建筑生产的周期内,思想迭代的次数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而创造性突变的可能性也随之显著增加。
前置型批评,令建筑批评家的身份,从建筑知识的生产者,转变为建筑产品的生产者,这一角色定位的根本性转换,打通了批判性建筑学的内在通路——建筑批评与批判性建筑实践,不再是貌合神离的体系拼凑,而是融通无碍的血脉汇流。
历史上,通过前置型批评主导建筑生产的案例并不鲜见。远如格罗庇乌斯和莫伯治,都是终生不会画图的建筑大师,却通过与设计团队的互动协作机制生产出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建筑产品。近如库哈斯所率领的OMA设计团队的生产方式,就是通过贯穿设计全程的批判性互动来保证其作品始终保持前卫性。
当代建筑生产,早已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化的分工合作。而现代建筑学既无能力解决个人创造的机制问题,更无能力解决生产组织的体系性创新问题。为此,批判性建筑学应该建立一个团队生产的“批判性协同”机制,即强调批判性的集体协作——由差异化个体的相互批判所引导的思想迭代型团队协作。
8“具足世界”与具足的批判性建筑学
名词意义上的具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包容批判性差异对立要素的富集结构,向全部的自然和文明造物开放。与静态的乌托邦结构不同,具足结构由于内部差异对立要素的相互批判,而始终处于一种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具足,最符合“世界”这个佛家用语的本义特征。简言之,具足是“大千世界”的混成与缩微映射。具足表现为空间上的“集异性”、时间上的“存变性”、和结构上的“圆融性”。在此,圆融并不与自洽同义,甚至相反,圆融是包容不自洽要素的矛盾、冲突、错误、缺陷但仍能保持动态平衡的一种结构状态。圆融的具足结构因刻意营造的不自洽构造而充满活力。
因具足必须集纳相互构成批判关系的差异对立要素的特点,具足世界并不等同于海斯所反复强调的真实世界。具足世界是涵括了真实世界与知识世界、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实存世界与虚拟世界等一切对立世界体系的混编集合。
乌托邦拒绝已然世界和或然世界,而只醉心构筑应然世界。但具足并不站在乌托邦的反面,而是把乌托邦也网罗进具足世界之中。正如王尔德所言,“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瞥”,一个不包容乌托邦的世界也并非真正的具足世界。
具足世界是差异对立的世界体系的混合而不是总和,因此具足世界理论上可以是各种尺度的包容批判性诸元的混成环境。由于内部批判性诸元相互之间始终处于一种高能链接状态,具足世界有着很高的系统活性。
当批评在具足世界而非乌托邦结构中全领域展开,批评也因此成为具足批评。具足批评表现为在世型、交往型、前置型三种批评形态类型,覆盖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三大哲学范畴,兼领认知解放、价值导航、形式生产这三重建筑学使命。
在通过具足批评打通建筑批评与建筑实践之间的壁垒之后,批判性建筑学终于在具足的意义上达到圆融状态。具足的批判性建筑学是以具足世界的建构为终极目标的批判性建筑学——以具足批评为工具,通过知识体系和建筑实践的生态性重组,让当代建筑学所身处的世界逐步补足而臻具足。
知识体系只有通过具足批评与具足世界进行多样性生态关系链接,才能够转化为临时性的具足知识体系。具足知识体系在保有理性、抽象、统一、自洽、纯净、致密、完美等乌托邦结构特征的同时,也随时向充满活力、意义和变异性的在世关系保持开放。
当代建筑学,亟待从“内卷式发展”跃迁到“演进式发展”(leap from involution to evolution)。为此,需要借助具足性批评工具的能量和锐度,破除当代建筑知识体系的乌托邦结构对自由创造力的禁锢。在网络检索能力无比强大,从而给检索所依附的乌托邦知识体系注入了一剂超级强心针的今天,人类反而更需要寻找到“非检索”、甚至“反检索”的知识组织途径,来保证知识生态的多样构成与健康演进。具足的批判性建筑学以具足批评为核心,试图通过非乌托邦化的方式对当代建筑知识体系进行批判性重组,以使当代建筑学在具足世界的背景下自由演化。
[1] K. Michael Hays. Critical Architecture: Between Culture and Form. Perspecta, Vol.21, 1984
[2]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80-81
[3]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大数据时代[M]. 周涛 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20
[4] 瓦尔特·本雅明.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M]. 孙冰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9: 162
A Critical Architecture of Affluence: A Schema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Leading to Re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ZHOU Rong
Modern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system, as the core cont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s constituted according to Utopian principles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ub-systems, namely, the narrative, the interpretative, and the operative systems. These sub-systems, however, have respectively led to the decline of vitality, significance, and originality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modern architecture, hence the "involution" impasse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system. The critical architectu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ims to reorganize modern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through three approaches to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the worldly, the communicative, and the prepositional, so as to identify a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 characteristic of vitality, significance, and originality. In so doing, modern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system will be rescued from the Utopian debris and be placed back into a world of affluence that encompasses diversified and oppositional critical elements. In this world of affluence, critical architecture will also be redefined in the new sense of affluence within the overall evolutional process of knowledge.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critical architecture, modern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system, utopia, knowledge organization, world of affluence, knowledge system of affluence, criticism of affluence
清华大学副教授
2014-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