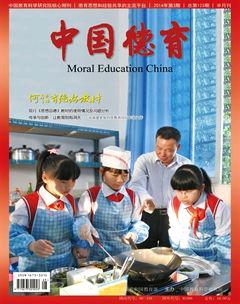“三位一体”的公民—西方公民概念的演变及述评
摘 要 在西方,公民概念的主体成员、权利内涵、地理外延随着历史不断地演变。在主体成员方面,公民由最初的少数特权阶层逐渐拓展为全体国家成员;在权利内涵方面,公民从单一的政治权利发展为多元权利;在地理外延方面,突破疆界限制出现了超国家的公民概念。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当代公民概念。
关 键 词公民;主体成员;权利内涵;地理外延
作者简介 李惠,香港教育学院管治与公民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公民”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汇[1],以致美国学者史坷拉感叹道:“再也没有哪个词汇比‘公民这个概念在政治上更为核心,在历史上更加多变,在理论上更具争议。”[2]公民一般被界定为作为一国成员的法律和政治身份,以及所被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在这一规定性概念下,西方公民的主体成员、权利内涵、地理外延随着时间、空间不断拓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民(公民身份)理论。本文试图从公民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探寻西方公民观念的演变,以便更清晰地认识“公民”的“三位一体”性。
一、公民的主体成员:
从特权阶层到普遍的个体身份
在古希腊时期,公民是一个特权阶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有资格成为公民。这部分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父母是城邦自由民的成年男性。如此限制把大量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外邦人、奴隶工匠排斥在公民范围之外[3]。其次,拥有一定的财产。拥有一定的财产既是成为公民的一个条件,也是参与公民生活的一种保障。梭伦在改革时提出按照财产的多少将雅典城邦的公民分为四个等级:500蒲式耳阶层、武士阶层、士兵阶层及劳动者阶层。第一、二、三阶层的人可以担任国家的主要官职,第四个阶层的人不能担任公职。不过,各等级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公民大会,成为陪审员,参与城邦政策的制定及法律审判。最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4]。参与政治生活是公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成为一个好公民的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的公民概念是以雅典这个小城邦为前提的,即在这个地理面积很小、人们彼此了解的小城邦中,具有公民资格的人虽然占总人口的大部分,但总体数目还是很少的。他们可以在规定时间里很快地聚集在广场上直接地参与政策的制定或一场审判。[5]这时的公民对城邦规模及总体公民数目有严格的限制,超过一定限制,公民这一身份甚至城邦民主将很难维持。
古罗马公民与古希腊公民有很大的不同。在罗马王政时期,居民分为两部分:贵族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享有政治权利,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平民、被保护人以及奴隶既不享有政治权利,也无需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后经改革,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均按财产多寡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改革虽然使平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平民仍不能享有与贵族同等的权利。到了共和国时期,平民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与贵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逐渐取得与贵族同等的公民资格。之后,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罗马公民不再局限于城邦内的居民,而是扩展到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但是,从公民的主体构成来看,公民依然是成年自由民男子,妇女和奴隶依然不享有或部分地享有公民资格。[6]
欧洲中世纪时,教会和封建君主是国家和人民的主宰,个体只是上帝的子民、封建君主的臣仆,而不是公民。直到十一世纪晚期,在新兴城市中,一部分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居民,主要包括城市商人、自由民、手工业者、律师和学徒,积聚了大量财富。他们渐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崛起,成为贵族、僧侣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市民阶层。经济上的优势使市民阶层追求更多的自由及政治权利。他们不断通过武装斗争或赎买等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市民阶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经济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要求源于其商业的原因。正是这些经济上的要求促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政治活动中来,成为国家政治的参与者。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正是在这种市民概念的基础上出现的。[7]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自由、独立的雇佣劳动力。而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只能产生具有依附人格的臣民,而不是公民。于是,西方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将体现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平等、独立等理念确立下来。李荣安和福特把这一阶段的公民称之为“liberal citizenship”,人民通过一系列的革命从而获得权利成为公民。[8]在这个阶段,公民范围和数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法律规定只要是国家的居民,不论等级、家庭出身和财产多寡,原则上都是公民。
到了现代,“公民”作为一种法律概念被确定下来。国家通过法律(一般是宪法)确定其成员的公民身份及其所享受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这是因为从18世纪开始,“国家”和“民族”这两个词语开始联系在一起,“公民”一词脱离了城邦的意味,附属于国家。公民是国家的公民,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国家保护公民的权利得以实现,而个体则要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从表面上看,如今公民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特权资格本质,实现了人人都是公民。但是这种实现仅仅是法律层面上的,在现实中是否每个拥有国籍的国家成员都平等地拥有权利和义务,这依然是一个问题。法律上的规定更多是一种形式,关键是其内涵能否真正实现。
二、公民的权利内涵:从单一到多元
在西方,公民的权利内涵是随着时间推进而拓展的。大体来说,公民的权利可分为三代[9]:
第一代,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民事权利是个体自由所必需的,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与信仰自由、个体财产权以及司法诉讼权。根据马歇尔的论述,这两大权利发展主要发展于十八、十九世纪。民事权利是自由主义公民传统所强调的中心,其核心是依法治理。一国之内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受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则可诉诸法庭寻求保护。政治权利就是个体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如作为政治权威团体的一名成员,或是作为这个团体成员的选举者。政治权利既是自由主义公民传统的核心,也为共和主义公民传统所强调。个体通过参与各种选举从而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决策当中,真正实现其权利。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互为依赖,民事权利保障了每个公民能够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个人事务,而民事权利的实现则依赖于公民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参与到与他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着的政治事务中去。[10]
第二代公民的权利包括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组成马歇尔所谓的公民身份的社会要素。社会权利指赋予个体的社会福利,包括教育、住房、健康方面的权利。经济权利则指个体在市场上的消费权、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参与劳动管理及获得社会经济福利的权利。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主要发展于二十世纪。二者是物质性的权利,是个体得以生存的基本保障,是公民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实现的前提条件。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教育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法律对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力的保护是有限的,但目前也缺乏一个非法律的保护体系来确保公民的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真正实现。大多数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的实现是与公民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即国家赋此权利于公民个体,但其具体实现却依赖个体自身。教育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受教育权,但具体到个体自身,他或她却依然可以自我决定是否去实现这一权利。在这过程中,国家的法律体系只能为其教育的权利的实现提供公平的机会与条件,在义务教育之外不能强迫个体去接受教育。
第三代公民的权利包括文化权利、环境权利等。马歇尔在1949年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公民的权利进行了经典而详尽论述,但在1949年之后的西方世界,新的移民浪潮、全球环境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不断挑战以往的公民权利内涵。如新移民对传统文化融合的反对,呼吁尊重民族、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性。而在面对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时,仅靠一国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为环境污染的影响范围往往超过国家界限,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些问题是马歇尔当时所没有预见到的,因而他未将这些问题纳入公民权利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到了二十一世纪,公民的文化权利和环境权利开始扩展。文化权利是针对不同的种族、文化、民族和语言的群体提出的,认为少数民族族群有权利保持特有的文化和语言特色,从而获得真正的平等。文化与族群权利的加入既拓展了马歇尔公民权利的内涵,也体现了公民是一个渐进性概念,它的拓展以促进社会平等为目的思想的体现。[11]此权利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国际性文件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环境权利则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个体因环境污染而受到伤害时,则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强调各国之间通力合作,保护地球环境,为了我们的邻国,也为了下一代。
三、公民的地理外延:从一国到全球
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开始探讨国籍是否为公民的标准。“公民”一词从此便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了一起,限定在一国的地理疆域之内。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伴随着全球化,跨国政治经济组织的出现,移民浪潮的兴起,公民身份不再受到国家地理疆界的限制,出现了“超国家区域性公民”与“全球公民”的概念。“超国家公民”概念的提出者Mary Rauner认为,这个概念不再将公民作为一国成员,而是把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12]
首先,在欧洲,随着欧盟的建立,欧洲公民这种全新的超国家区域性公民出现。这种公民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但却被欧共体和欧盟委员会所承认,并在1961年之后经常出现于欧盟的文件中。这种公民在欧盟通过四种形式得到发展:第一,欧洲人权法庭的建立和《欧洲人权公约》的通过,使保障欧洲公民人权成为现实。《欧洲人权公约》第25条明确规定:委员会可以受理由于缔约国一方破坏本公约规定而致受害的任何个人、非政府组织或是个人团体向欧洲理事会秘书长提出的申诉。第二,欧洲议会成立,欧洲公民可以参与议会选举。起初欧盟的公民是通过本国议会参与选举,但随着欧洲通讯委员会的建立,让欧盟公民直接参与欧洲议会的选举成为可能。第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欧洲公民这一形式制度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8条规定了作为一个欧洲公民所具有的权利:欧盟公民无论居住在欧共体的哪个成员国,在欧洲选举和市政选举中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承认任何公民有在欧洲议会请愿的权利。[13]
其次,世界公民这一观念由梦想变为现实。世界公民概念最早见于斯多葛学派的论述中,但此时这种公民仅仅是一种乌托邦梦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斯多葛学派论述学派再次提出世界公民的观念,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Justus Lipsiu,他宣称“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国家”[14]。在启蒙运动时期,世界公民这一梦想受到洛克与康德等大思想家钟爱。洛克在论自然法则时提出:“人类是属于一个共同体,他们组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社会。”[15]康德提出三种类型的法律,其中第三种就是全球法律。这种法律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之上:第一,随着人类的迁徙,所有的人类都有权利受到他所到达的任何国家的礼遇;第二,因为存在一个共同体,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滥用其权力都会被其他地方的人感受到。第二个原则所强调的全球公民责任在今天特别受到关注。到了十九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公民的对立面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受到过度的宣扬。国家之间的敌意冲突大增,世界公民的观念很难找到其发展的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受到全球利益驱使以及联合国这一全球性政治组织的作用,全球公民的观念再次被提出。到了二十世纪,世界公民真正从梦想变为现实。这是因为,一方面全球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共同的实现责任,让世界公民不再是一个口号。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大政治阵营对立的局面消失,更多全球性合作组织出现,让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个世界共同体“地球村”已经形成,这让世界公民有了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在当前世界公民的实践中,联合国这一全球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实际重要。特别是其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联合国人权组织积极在世界各国发动人权运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弱势群体作为世界公民的基本权利,这让“世界公民”一词真正走入平常人视野,也让世界公民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公民概念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公民主体成员方面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古希腊时期到十七、十八世纪,在这一漫长的历史中,公民的主体成员随着个体不断争取与斗争不断扩大增加,从最初少数的特权阶层、贵族,到大量自由民、城市市民的加入,再到所有国家成员都成为公民。到十八世纪,公民的主体成员已经基本上确定为所有的国家成员。在此之后,关于公民的争论与发展就开始转移到其权利的内涵及地理外延之上了。公民的权利从十八世纪追求个体自由民主的民事权利,到十九世纪拓展到政治权利。到了二十世纪,公民权利则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领域,把经济与社会这类物质权利也包括在内。到了二十一世纪,面对新的全球移民和环境问题,文化权利与环境权利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公民的地理外延方面,十八世纪开始确定以国籍、国界作为公民的地理外延,但到了十九、二十世纪,受全球化的影响,公民的这一地理外延逐渐被打破,超国家的区域性公民与全球性公民概念开始出现。
由此可见,在西方,公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但其发展却一直围绕主体成员、权利内涵、地理外延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公民概念。我们在理解公民这一概念、进行公民教育课程的设计及教学时,一定要全面地看待公民的这三个维度,同时必须认识到这三个维度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其必将出现新的发展延伸。
参考文献:
[1]Beck.Mor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Education[M].London: Cassell,1998:102-106.
[2]Shklar.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
[3]Aristotle.The Politics[M].London:Penguin Books,1962:39-42.
[4]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74.
[5]Heater.A Brief History of Citizenship[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18.
[6]张博颖,陈菊.西方公民观与公民道德观的历史演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至17、18 世纪[J].伦理学研究, 2004(6):88-94.
[7]张镇镇.公民概念的变迁与人的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65-67.
[8]Lee,Fouts.Education for Social Citizenship:Perception of Teachers in the USA, Australia,England,Russia and China[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45.
[9]Oliver,Heater.The Foundation of Citizenship[M].New York,London,Toronto,Sydney, and Tokyo,Singapore: Harvester Wheatsheraf,1994: 50-55.
[10]Marshall,Bottomore.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40.
[11]Banks.Diversity,Group Identity,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J].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8(37):3.
[12]Rauner.Citizenship in the Curriculum:The Globalization of Civics Education in Anglophone Africa:1955-1995[M].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1997:104-107.
[13]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1[EB/OL].[2013-01-01].http://baike.baidu.com/view/9909.htm.
[14]Lipsius.Two Books of Constancie[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39:96.
[15]Locke.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M].London:Dent,1965:80.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