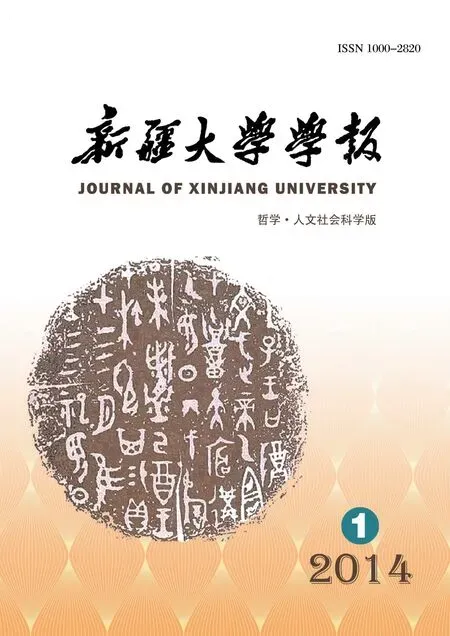古希腊与先秦文学比较散论∗
罗小如,郑晨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生期,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首页,也是后代文学尊崇取法的典范;而古希腊文学则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也是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马克思称之为“规范的、高不可及的范本”。古希腊文学与先秦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本文拟从细处入手,将古希腊文学与中国先秦文学进行某种微观上的比较解读。
一、萨福的诗与《诗经》的诗
萨福(约前612年~约前560年),是西方最早的有姓名记载的女诗人,柏拉图称她是“第十位文艺女神”,她现存的诗歌大多为零篇散简,却极具才情,各种外国文学作品选本皆有选介。本文以复旦大学版《外国文学作品选》所选的三首诗[1],与《诗经·国风》中的三首诗作一番有意味的比较。
先说第一首诗《一个少女》:
好比苹果蜜甜的,高高转红在树杪/向了天转红——奇怪,摘果的拿她忘掉——不,是没有摘,到今天才有人去拾到/
好比野生的风信子茂盛在山岭上/在牧人们往来的脚下她受损受伤/一直到紫色的花儿在泥土里灭亡(朱湘译)
这首诗以成熟的苹果、野生的风信子之坠落凋零为喻,表达了少女青春流逝而空候爱情的感伤。同样是以植物作喻,《诗经·国风·召南》中有《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要进行这两首诗的比较,首先要理解诗的字、句意义。《摽有梅》中“摽”是其中的关键词。历代学者大多把“摽”释为“落”或认为“摽”是“莩”的假借字,如毛传:“摽,落也。盛极则隋落者,梅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摽,婢小反。落也。”朱熹《诗集传》:“摽,落也。”释“摽”为落义,源于《尔雅·释诂上》:“摽,落也。”而认为“摽”是假借字的,来源于许慎《说文》。《说文·部》:“物落。上下相付也······,读若《诗》‘摽有梅’。”段注:“毛曰:‘摽,落也。······毛诗‘摽’字正之假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瑞辰按‘摽’或作‘蔈’······又作‘莩’,《韩诗》作‘莩’者,为正字,《毛诗》作‘摽’或作‘蔈’者,皆之假借。毛《传》训‘摽’为落,义与《韩诗》正同。”[2]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也与马瑞辰的看法相同。也有学者不同意“摽”训落,认为“摽”是抛掷义,如闻一多《诗经新义》:“摽,古抛字。《玉篇》曰‘摽,掷也’,《说文新附》曰‘抛,弃也’,重文作摽。······掷物以予人亦谓之摽。《诗》曰‘摽有梅’是也。”[3]闻一多先生用《诗经》中男女互抛信物以定情的民俗作为证据,以证“摽有梅”为女子向心仪的男子抛掷梅子以示所爱。其实“摽”训“落”或训“抛掷”是统一的,是从《说文》“摽,击也”的不同方面引申而已。徐铉校定《说文新附》:“抛,弃也。······《左氏传》通用‘摽’,《诗》‘摽有梅’,‘摽’落也,义亦同。”已明。
禹建华从语境、语法、异文三方面分析,认为“‘摽’可视为‘標’之俗写,意为树梢,而不训成坠落、打落。”[4]我们赞同这一观点。这里再从异文方面补充一些出土文献例证。出土文献中偏旁“木”、“扌”常相混,如《碑别字新编·魏元始和墓志》:“‘標’作‘摽’”[5]。石刻文献也有用例,如南朝宋《爨龙颜碑》:“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乡望摽于四姓,邈冠显于上亰。”[6]114北魏《元恪贵华王普贤墓志》:“祖镇北,以贞猷摽鲠,见免昏历。”[6]239北魏《王翊墓志》:“公膺积善之余烈,体钟美之粹灵,摽藂桂于八树,茂兹兰于九畹。”[6]259
“摽有梅”意即树上的梅子,“有”作动词。此类例子《诗经》中多见,如“墙有茨”、“野有死麇”、“山有扶苏”等。《摽有梅》以梅子变少、坠落象征青春消逝,梅子由存留树上的十分之七变为十分之三,再变为几乎全部坠落于地、需用筐来拾取,表达女子希望男子及时与之相会、不使青春虚度的心声。
对比以上二首诗,从句式上看,“摽有梅”和《一个少女》的“苹果在树杪”、“风信子在山岭上”均为存现句,二者不谋而合。从内容上看,萨福的诗全篇写物,但《一个少女》之名却已表明此诗是以物写人;《摽有梅》则以梅为题,但在托物起兴之后,则转入对爱情的呼唤。
再看看萨福的第二首诗《给所爱》:
他就像天神一样快乐逍遥/他能够一双眼睛盯着你瞧/他能够坐着听你絮语叨叨,好比音乐
听见你笑声,我的心儿就会跳/跳动得像恐怖在心里滋扰/只要看你一眼,我立刻失掉言语的能力/舌头变得不灵,噬人的热情/像火焰一样烧遍了我的全身/我眼前一片漆黑;耳朵里雷鸣/头脑轰轰
我周身淌着冷汗;一阵阵微颤/透过我的四肢;我的容颜/比冬天草儿还白;眼睛里只看见/死和发疯(周煦良译)
这首诗可与《国风·卫风·伯兮》作一番比较: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两首诗都是写给爱人的,都有着对爱人的由衷赞美,但爱人的形象一刚一柔,各有风姿。希腊神话中的神颇具人性,故萨福将爱人比作天神,侧重于其体贴温柔,而一个能倾听女子心声的男人更容易赢得爱情;《伯兮》则将爱人说成是国家的英雄,侧重其高大威猛的外貌(“朅”,毛传:“武貌。”即武壮高大),是一个以建功立业而为爱情增添荣耀的形象。
这两首诗都写到女子对爱的深切体验。吉尔伯托·默雷认为萨福的诗歌“以炽烈的火焰表达了丰富的内心活动、蕴藉的热情”[7],从《给所爱》一诗来看,确乎如此,诗中抒写的爱情之火灼烧下那种风驰电掣、从精神到肉体深度痉挛的特殊感受,应是每一个深爱过的人都能体认的,故貌似夸张而不觉夸张;而《伯兮》的“首疾”、“心痗”同样既是生理、也是心理反应,虽无《给所爱》的狂放热烈,却平实质朴得令人叹息,这自然与中西女子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有关。
二、普罗米修斯与鲧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大神,他创造了人类,又教给人类诸多生活本领,在他的众多功绩中,盗火的意义最为重大。火是智慧与力量的象征,本属天神所独有,而普罗米修斯将它盗来给人类。袁珂先生指出:“(鲧)和希腊神话里普洛米修斯因把天上火种盗去给人间被宙斯锁禁在奥林帕斯山上叫岩鹰终年啄食他的心肝的情节非常类似。”[8]据《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盗”与“窃”都是一种“不从”的行为。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认为:“希腊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表明了全部人类文明都建立在一种不从行为的基础之上。普罗米修斯从天国盗火给人类,奠定了人类进化的基础。”[9]如果说火是人类文明之光,那么土就是人类立身之本,是洪水没顶之际的最后希望,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障。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与中国神话中的鲧窃息壤正可等量齐观。
在这两个神话中,天的主宰者(天帝/宙斯)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在古希腊神话与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年∼前456年)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的专横被普罗米修斯一再指责,但他无法杀死普罗米修斯,只能折磨他,并且宙斯自身也逃脱不了被推翻的命运,这体现了古希腊人的命运观,而在中国神话中,天帝代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是他人命运的最终裁判者,鲧窃息壤本是为治水救民,却因“不待帝命”而被诛,《国语·晋语八》亦言:“昔者鲧违命令,殛之于羽山。”即使是他的后人禹作为合法的治水者出现,也须有“帝命”方能“布土定九州”。相比于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统治的怀疑,鲧禹治水却是为了恢复被洪水搅乱的秩序而不是要改变秩序,他的“不从”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一种更高范畴的“顺从”的基础上的。普罗米修斯最终被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而鲧则通过一种奇异的方式(复生禹)延续了自己的工作,实现了生前无法实现的愿望。这种委曲求全、隐忍述志的生存方式与普罗米修斯宁愿忍受种种痛苦也不愿向宙斯屈服、最终在几万年之后方得解放的人生理念实为不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另外,这两个神话中都隐含着“再生”这一神话母题。宙斯每天派一只鹫鹰来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但不论被它吃掉多少,随即又长了出来,这个神奇的构想与息壤这一神异事物颇具共性。“息”有滋生、生长义,《释名·释言语》:“息,塞也,言物滋息塞满也。”《集韵·职韵》:“息,生也。”《说文》“息,喘也”段注:“又引申为生长之称。”如《荀子·大略》:“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上引《山海经·海内经》“息壤”郭璞注曰:“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10]故息壤就是能自己生长的土壤。周延良先生认为它是“原始人类建立在生存祈向的物化、人化观念之上,而造就了这样一个超自然的意象。”[11]息壤寄托了人们抗御洪水的美好愿望。而普罗米修斯那能不断生长的肝脏固然代表了他的痛苦,却也是他健旺生命的写照。因此,能再生的息壤与肝脏都可以看作人类生命意识的意象化。另外,鲧腹生禹及因此而导致的洪水发而复平与普罗米修斯的最终获救(人马喀戎替他受难),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再生的模式,同样寄托了人们对先驱者的敬意和对生存的祈望。
相比于普罗米修斯,鲧的神话多了“变形”的功能,郭璞注引《开筮》(即《归藏·启筮篇》):“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命令,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三足鳖),以入于羽渊。”《天问》:“伯鲧腹禹(原作‘伯禹愎鲧’,从闻一多《天问疏证》改),夫何以变化?”鲧死后形体的变化与中国神话中盘古化生万物、女娲一日七十变、精卫化鸟、夸父死后杖化邓林等一样,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三、安提戈涅与聂嫈
安提戈涅与聂嫈,二人都是因为兄弟之死而殒身不恤的,二人的死都具有主动选择性,也就是说,她们本可不死,却双双自蹈而死。安提戈涅因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年∼前406年)的名作《安提戈涅》而名垂青史,聂嫈则于《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熠熠生辉。
安提戈涅的两个兄长为争王位而同归于尽,其舅克瑞昂继承王位,厚葬了哥哥埃特奥克勒斯而宣布弟弟波吕涅克斯为叛逆,并下禁葬令,违者处死。在古希腊,埋葬和祭祀死者是一种习俗,且被视为神律,未被埋葬的死者,其灵魂是不洁净的,是会得罪天神的。此时,对安提戈涅来说,王令与亲情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会选择苟全性命,像她的妹妹伊斯墨涅一样;但安提戈涅却毅然挺身安葬其弟,最终自缢于囚室。而聂政在刺杀韩相侠累后“自披面抉眼”,自尽之前毁容,本有保护其姐不受牵连之意。韩国为求购其名而将他暴尸于市,聂嫈明知弟弟“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12]999(张守节认为是为了保护严仲子,参见《史记正义》),但为了彰扬弟弟之英名,现身韩市,抚尸痛哭,心力交瘁而死于聂政之旁。若说安提戈涅是为了一个死去的灵魂不至飘泊,聂嫈则是为了一个死去的壮士不再寂寞。安提戈涅说:“我要埋葬哥哥,即使因此而死,也是件光荣的事;我遵守神圣的天条而犯罪。”[13]71聂嫈则说:“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12]999她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只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但推究起来却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西方人重死后的救赎与灵魂的安息,故后来基督教以天国为终极目标。中国人则重名,故以光宗耀祖为最高荣誉,如《孝经》所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开宗明谊章》)在母亲已去世、惟一的弟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毁容自杀后,替弟弟扬名、为聂家争光的责任被一个本应退居后台的女子自觉地担当起来。“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12]1000在扬名的背后,体现的是宗法制的文化积淀和以祖先崇拜为主要传统的民族宗教观念。后世的“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资治通鉴·晋纪》桓温语)只是这种传统的一种极端化表述。
如果把《战国策》、《史记》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人物的塑造方法和笔墨的浓淡上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有所不同。在《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是戏剧的主角,波吕涅克斯的死亡只是一个引子,由此引出安提戈涅的选择;而其妹伊斯墨涅则是安提戈涅的反衬。伊斯墨涅是识时务者:“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是女人,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13]71她的清醒与理智正与安提戈涅的坚毅与迷狂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聂嫈可以看作是聂政的正面衬托,笔墨不多却面目如生,令人扼腕,她的千里赴死为聂政的形象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聂政的隐名护姊与聂嫈的舍身认弟同样伟大,姐弟俩有如双子星座,为世人瞻仰,“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12]1000
中国古代文学滥觞于黄河文明,有着纯朴自然、艰忍务本的农业文明烙印;希腊文学则渊源于爱琴文明,追求自由、鼓吹个性是其底色;而在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双方亦有着不少共性。以上三则札记较为零散,涉及诗歌、神话、戏剧、散文等各文学体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见出古希腊文学与中国先秦文学在比较文学视域中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