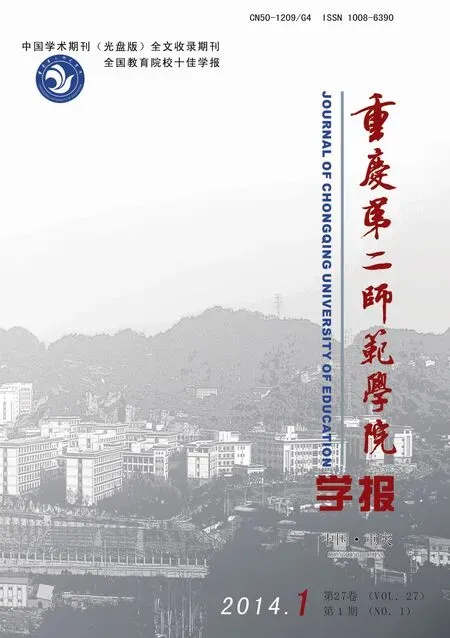刘勰与《文心雕龙》的乐府论
王 梅,王辉斌
(1.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2.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乐府诗批评史上的乐府论,据现有的材料可知,乃始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乐府》一文。刘勰(约公元465~约538年)之前,虽有从“论”的角度涉及乐府诗批评者,如释智匠《古今乐录》之某些题解与沈约《宋书·乐志》之“乐一”等,但因其大都以叙述的方式为主,而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论分析,故实不足以称之为“品第类批评”。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则不然。此文不仅为典型的“品第类批评”,而且也兼有“为批评的批评”(即“专论类批评”)之某些特点,①因之,其理论色彩之强烈,所持观点之鲜明,均非前此之各类乐府诗批评可以相比。刘勰“乐府论”的问世,标志着乐府诗批评的组织形式,由初始时期的“整理类批评”、“题解类批评”等,在齐、梁之际已上升到了一个颇为成熟的阶段,而其所代表的,则是乐府批评的一种跨越式进步。自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始,以“专论类批评”的形式进行乐府诗批评,即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潮流,且直至于清末民初时期。也正因此,各类与之相关的序跋、诗话等,即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从而使得乐府诗的批评,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一、“乐府”是一种文体
由乐府机关而乐府诗,是先秦乐府与汉魏(晋宋)乐府的一种共性存在,即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前乐府”,②抑或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后的各朝(如汉、魏、晋、宋等朝)乐府诗,时人对其之认识,无不是将其视之为一种文学品类的,这从徐陵中华书局1985年版《玉台新咏》即略可获知。以是书卷三为例,该卷共收有13位诗人的35首诗,其诗之类别,则依次为“拟古”、“赠妇”、“杂诗”、“合欢”、“七夕”、“乐府”、“连杂”等,③将“乐府”与“拟古”、“赠妇”、“合欢”等并列,表明“乐府”之于徐陵而言,乃为诗歌之一类已无疑。与《玉台新咏》同时而稍前的萧统《文选》,对于“诗”的部分之编排,也是如此。据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文选》可知,该书卷十九至卷三十三选诗凡15卷,萧统则将这15卷诗又细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等23类,而“乐府”则为其中之一,且选录“古”、“今”乐府诗整40首。这一实况表明,萧统编《文选》时,也是认为“乐府”乃诗歌之一类的。《文选》与《玉台新咏》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受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影响所致,因为其中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者,所表明的是“乐府”具有很强的审美属性。班固的这种认识,因是纯从乐府歌辞的角度而为,所以多为后人所遵从。
而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对于“乐府”的认识,则与上述诸家之所说与所作,乃迥异其趣。④正因此,其于《乐府》之开首,即开宗明义地写道:“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这10个字所强调的是,乐府诗具有独立的音乐特性,为“诗声合一”的产物。也即在刘勰看来,乐府是一种配乐而唱的文学样式,其乃由“乐”与“辞”共同构成。所以,刘勰又说:“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并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八音摛文,树辞为体。讴吟垌远,金石云陛。韶响维追,郑声易启。岂唯观乐,于焉识礼”。所有这些,均足以证明,刘勰对于“乐府”的认识,是建立在将音乐与歌辞互为关联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多维度的认识,自然要比纯歌辞的单维度认识更为具体、更为全面。
正因为刘勰认为乐府是一种可与诗歌并列的文体(诗体),所以在《文心雕龙》中,又特地安排了一篇《明诗》,且将其置于《乐府》之前,以表示“诗”与“乐府”是具有明显之区别的。《明诗》与《乐府》同时存在于《文心雕龙》的事实,所反映的是在刘勰的乐府认识观中,“诗”即徒诗;“乐府”则为声诗、乐歌,也即“乐辞曰诗,声诗曰歌”之谓。一言以蔽之,与音乐无关者为诗歌,与音乐有关者为乐府,这就是刘勰在《明诗》与《乐府》中对诗歌与乐府的界定。由此又可知,《明诗》所言之“诗”,与《乐府》所言之“诗”,乃是并不相同的。
“乐府”既然与音乐的关系密切,且其又是一种诗体,所以刘勰在《乐府》中,即着眼于音乐的角度,对其之生成与发展的脉络,首次进行了史的勾勒,认为:“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乃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这是说乐府起源于上古时期,但到了黄帝(《五英》)与帝喾(《咸池》)时期,就都难以考究了。之后,则据《吕氏春秋·音初》之所载,认为南、北、东、西四方之乐歌,主要诞生于夏、商时代,且各有其特点。“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锵锵,叔孙定其容与。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自从秦始皇焚烧了《乐经》后,汉初即有意恢复古乐,最终通过种种努力,虽然继承了秦代的旧乐,但中和平正的音乐,却是再也无法与之相见了。再之后,即为人们所熟悉的汉武帝“乃立乐府”之时。在刘勰看来,汉武帝的“乃立乐府”,就是在这种音乐文化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其功不可没。虽然如此,但刘勰又认为,汉代“乐府”与上古“乐府”相比,却是存在着许多方面之不同的,而这些不同,即成为了他在《乐府》中所批评的对象。
二、对汉魏乐府的批评
汉武帝“乃立乐府”的历史事实,对于当时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使古代的采诗制度得以恢复,为搜集、整理各地的民歌、民谣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流传于“代”、“赵”、“秦”、“楚”等地的民歌、民谣,即因此而成为了汉乐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为汉武帝所“乃立”之“乐府”,更多的则是组织文人作家进行新辞的创制,以备朝廷之所需。对此,《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二》乃有记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2]
其中的“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云云,即表明了当时参与创制新辞的文人作家之众,而“作十九章之歌”,所指则为《汉书·礼乐志二》所著录之《郊祀歌》十九章。由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制的“郊庙歌辞”,在当时是“五郊互奏”,⑤盛况空前。若就整个西汉的乐府诗而言,则还有问世于“乃立乐府”之前的《安世房中歌》等。在《乐府》中,刘勰虽然对这些“郊庙歌”进行了“品第”,但更多的则是对其批评。如云: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诗颂,诗效《鹿鸣》。⑥迩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郊庙,吟诗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3]
在这一大段文字中,刘勰采用“品第类批评”之方式,由汉初而曹魏,几乎将其间的文人乐府诗进行了逐一批评,这在自有乐府诗批评以来,实属罕见。而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则为“《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诸句,以及“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淫荡,辞不离哀思”之所云。前者为西汉乐府的代表,后者为曹魏乐府的代表,刘勰对此二者的批评,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汉魏(前206年~公元265年)470年的乐府诗进行了较全面之指责。这种情况的“品第类批评”,不仅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就是在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是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的。
据《汉书·礼乐志二》所载,《桂华》,为唐山夫人(一说为叔孙通)所作《安世房中歌》的第10首;《赤雁》,即《象载瑜》,为《郊庙歌》的第18首,刘勰将《桂华》、《赤雁》并举,其所代表者,即为《安世房中歌》(17首)与《郊庙歌》(19首)这两组大型“郊庙歌”,也即“郊庙乐府”。对于这两组“郊庙歌”,刘勰对其的批评,是“丽而不经”、“靡而非典”。所谓“丽而不经”,是指文辞华美违反了常规;而“靡而非典”,则是指语言华丽而不符合相关法度,综而言之,其实际上就是对《安世房中歌》、《郊庙歌》之“乐”与“辞”均不符合经典的一种指责。在刘勰的审美认识中,作品的“经典性”是十分重要的(参见《文心雕龙·宗经》),故其在对《安世房中歌》、《郊庙歌》进行评价时,即着眼于“乐”与“辞”两个方面,认为其既“不经”,又“非典”。其实,前人对这两组“郊庙歌”也是持有看法的,如班固《汉书》与沈约《宋书》即为其例。《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二》有云:“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又云:“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对此,《宋书》卷十九《乐一》亦有云:“周又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寿人》。其声,楚声也,汉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班固认为,这两组“郊庙歌”,既不曾歌颂“祖宗之事”,而“又不协于钟律”;沈约则指出,《房中之乐》本是古人用来颂扬先祖的,但唐山夫人却以之歌颂当代人(汉高祖)的功德,且又杂以“楚声”(班固亦作如是认为),即认为其“乐”不符合上古音乐的雅正传统。班固与沈约对“今汉郊庙诗歌”的这种不满,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特别是《乐府》之前,理应是早已了然于胸的,故而乃有“丽而不经”、“靡而非典”之批评。
在对曹魏乐府诗的品评中,刘勰则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魏之三祖”,也就是曹操(太祖)、曹丕(高祖)、曹睿(烈祖)三人。据拙著《先唐诗人考论》第三章第三节可知,曹操现存乐府诗21题27首,曹丕19题24首,[4]而曹睿则有9题10首(据《乐府诗集》),三者共计49题61首。对“三祖”乐府诗同时进行评价者,当首推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一书,其虽已佚亡,但《续修四库全书》本释智匠《古今乐录》引录其之所评,则有近十条之多。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亦引录了王僧虔之所评:“故王僧虔论三调歌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所以追馀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者矣。’”[5]郭茂倩所引,乃是据《南齐书·王僧虔传》而为,只是文字略有增删而已。其中的“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云云,即是对三人之乐府才华与成就的赞美。但刘勰却认为,“三祖”之乐府,“宰割辞调,音靡节平”,此之所言,实际上是说“三祖”的乐府“音调浮艳,节奏平庸”,[6]不符合上古音乐的规范。其后,即举出了曹操《苦寒行》、曹丕《燕歌行》等具体篇名,以为例说,认为《苦寒行》等“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然属于“三调之正声”的范畴,实则与《韶乐》、《大夏》等上古音乐迥异。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刘勰对于“三祖”乐府的评价,主要是认为其“辞”的悲伤成份过多,而“乐”则近似于“郑曲”,也即俗而不雅。既称“三祖”乐府诗“宰割辞调,音靡节平”,又认为其“实《韶》、《夏》之郑曲”,此则表明,刘勰之于“三祖”乐府的认识,虽然是“乐”、“辞”互关,实则是重在从音乐的角度对其予以贬斥的。而以“郑曲”喻指“三祖”之乐府诗者,这是曹魏乐府诗批评史上,也是甚为罕见的。
如上所述,刘勰所崇尚之音乐,主要为上古时期的“中和之响”,所以他说:“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认为西汉初期的音乐是“中和之响,阒其不还”,即中正平和的乐调,在这一时期的乐府诗中已难以见到了。以具有“中和之响”特点的上古音乐为标准,对汉魏470年的乐府诗进行“品第类批评”,所表明的是“宗经”在刘勰的乐府认识观中,乃占有很重要之地位,则其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也就不言而喻。
三、对齐梁艳歌的批评
刘勰在对汉魏乐府批评之后,接着即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诗声俱郑”的“艳歌”。在刘勰看来,“诗声俱郑”的“艳歌”在“乐”与“辞”两个方面,是较之“三祖”乐府“实《韶》、《夏》之郑曲”要严重许多的。所谓“诗声俱郑”,就是指乐府诗远离“《韶》、《夏》”的雅正传统,而向“郑曲”的发展。“郑曲”即“郑声”,语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因为“郑声淫”的缘故,所以后人多以之指淫乐、淫声、淫歌等,对此,《丛书集成初编》本杨慎《升庵经说·淫声》已言之甚详,此不具述。正因为“郑声”所代表的是“淫”,故其即遭到了儒家的种种排斥。虽然如此,但其所排斥的最终结果,却是“雅声浸微,溺声腾沸”,以致形成了一种“诗声俱郑”的格局。所以,刘勰在《乐府》中乃沉痛地写道:
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咏“来迟”;歌童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7]
这段文字对“艳歌”的批评,较之上述对《安世房中歌》、《郊庙歌》与“三祖”乐府诗的批评而言,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前者是“实《韶》、《夏》之郑曲”,这里则为“诗声俱郑,自此阶矣”。此则表明,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之前与之时,不仅对《安世房中歌》之类的“郊庙乐府”与“三祖”乐府诗进行了关注,而且于“艳歌”之类的乐府诗也是颇为关注的。对于此“艳歌”之所指,论者或语焉不详,或弃而不论,或认为是汉代的乐府民歌,等等。其实,“汉代乐府民歌”说是颇值怀疑的,原因则为这种说法,与汉代的乐府民歌之实况乃迥不相及。
据沈约《宋书·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可知,现所存见之汉代乐府民歌与“艳歌”相关者,实则只有《艳歌行》、《艳歌罗敷行》、《艳歌何尝行》等少许几篇,且其皆与“淫辞在曲”不相干,更与“诗声俱郑”了不相涉。就内容而言,这几首诗所写,与“淫”一点也不沾边;以音乐论,其所配皆为大曲,且为音乐家荀勖所“施用”(即整理配乐)者(参见《宋书·乐三》),因之与“郑”亦毫无关系(据现有资料可知,流传至齐、梁之《艳歌行》等,其音乐只有荀勖所“施用者”,而别无它种音乐,即刘勰当时所知、所见者,只能为荀勖所“施用者”)。所以,其绝非“淫辞在曲”的“艳歌”之属。而据现有资料又可知,在刘勰之前与乐府相关之著述,如班固《汉书》、蔡邕《礼乐志》、沈约《宋书》、释智匠《古今乐录》等,均没有称《艳歌行》等为“淫辞”或者“郑声”的;即如其后的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也无不如此。以常理论,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之前,是肯定熟读了沈约《宋书》中的四卷《乐志》的,也即其当时所见到、所知道的与“艳歌”相关的汉代乐府民歌,是决然不可能超出《宋书·乐志》四卷所记载之范畴的。既如是,则所谓“汉代乐府民歌”之说,也就值得重新考虑了,此为其一。其二,就现所存见的全部汉魏乐府言,其无论是文人乐府抑或乐府民歌,均无属于“淫辞在曲”与“诗声俱郑”者,所以,“艳歌”与“诗声俱郑”等之所指,也就绝非为汉魏乐府了。尽管刘勰认为“三祖”的乐府“实《韶》、《夏》之郑曲”,但其所批评者,也并非为“三祖”乐府之全部,而且即使是全部,“三祖”的乐府也是很难划归为“艳歌”一类的,这应该说是一种乐府诗事实。虽然,刘勰将曹操的“北上”篇(即《苦寒行》)、曹丕的“秋风”篇(即《燕歌行》)等,称之为为“《韶》、《夏》之郑曲”,但他也没有认为这些乐府诗就是“艳歌”,就是“淫辞”。此外,曹植集中虽然有多篇关于两性的情思之作,如《美女篇》、《妾薄命行》等,但这些篇什也是不能目之为“淫辞在曲”的“艳歌”的,这从刘勰在《乐府》中称赞“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云云,即略可获知。所以,“若夫艳歌”云云之所指,是既非为汉代之乐府民歌的,也不是汉魏之文人乐府的。
而应注意的是,在《乐府》一文中,上引“若夫艳歌婉娈”云云一段文字,是明显地放在“逮于晋世”之后的。以刘勰所述乐府流变之脉络言,“逮于晋世”之后的乐府,理应为刘宋乐府与齐、梁乐府,也即南朝乐府,但全篇却并未出现“宋”、“齐”、“梁”之朝代名,其中原因何在?这应该说是颇有考察之必要的。据《南齐书·王敬则传》、《南史·张贵妃传》、《梁书·简文帝纪》等之所载,齐、梁时期不仅骈文与宫体诗盛行,而且各种新声、新曲迭出,从而使得刘宋“歌词多淫哇”的“不典正”(《宋书·乐志》)之风,在这一时期更为炽烈。如《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即如是写道:“自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而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记载,则较此更为具体。其云:
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兢,去圣逾远,繁昔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声废矣。……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迫,少复近古。[8]
其中的“艳曲兴于南朝”、“新声炽而雅声废”、“大抵多溺于郑、卫”云云,即为刘勰《乐府》中之“艳歌婉娈”、“职竞新异”、“诗声俱郑,自此阶矣”的绝好注脚。由是而观,可知《乐府》中的“艳歌”之所指,为齐、梁乐府当无疑。出身低微而在当时又未步入仕途的刘勰,如果对这些“艳歌”进行类似于汉、魏乐府的批评,其无疑就是在自阻仕途、自断前程。虽然如此,但刘勰还是对其进行了批评,此即借汉乐府之名,以行对齐、梁“艳歌”的批评之实。即是说,刘勰在《乐府》之中,名义上是在对汉“艳歌”进行批评,实则其所批评者,乃为齐、梁“大抵多溺于郑、卫”的“新声”。换言之,刘勰《乐府》中的“艳歌”,所指实为齐、梁“艳歌”,而非为汉代的乐府民歌。这其实是一种“借代式批评”,后来唐人即多以此种方法进行诗歌创作,如杜甫《兵车行》中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之“汉家”,即属如此。这种“借代式批评”,尽管不如“点名式批评”来得直接,批得痛快,但却为作者免去了许多麻烦。在刘勰所生活的齐、梁时期,虽然并无“文字狱”之类的政治打击,但刘勰在撰著《文心雕龙》时,只是一个30多岁的未入仕青年,因之,无论是从理想抑或仕途言,其都是不允许他对本朝的“艳歌”进行公开批评的。更何况,梁武帝、梁简文帝等人还是这些“艳歌”的直接制造者。明乎此,则刘勰对齐、梁“艳歌”采用“借代式批评”者,也就极容易理解了。
四、刘勰乐府论的得失
《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为《序志》,其中写道:“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这是刘勰的夫子之道,意在向时人表明,其于孔子乃是相当尊崇的。正因此,他才认为:自有人类以来,还从没有出现过像孔子这样的圣人!据《南史·刘勰传》可知,刘勰虽然与佛教关系甚为密切,但以“征圣”与“宗经”为论文宗旨,却始终在《文龙雕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其于乐府诗的批评,亦与此大相关联。
以上的论述表明,刘勰的乐府观,基本上可用八个字进行概括,即:诗声合一,崇雅黜郑。在“诗声合一”方面,刘勰又侧重于“声”,故在一篇《乐府》之中,其之所论,实属“声”主而“诗”次,即使对某些具体作品进行品评时,也大都是着眼于音乐的角度以立论,因之,便有了“稍广淫乐”、“正音乖俗”、“音靡节平”、“三调之正声”、“《韶》、《夏》之郑曲”、“诗声俱郑”、“俗称乖调”等评语。而“崇雅黜郑”,则就更是属于“音乐论”的范畴了。所以,在刘勰的审美观照中,只有先秦的音乐才属雅正之乐,“中和之响”,而汉、魏乐府与齐、梁“艳歌”,要么是“淫乐”,要么是“郑曲”,更有甚者,则是“诗声俱郑”。总之,刘勰认为,在“秦燔《乐经》”之后的各种乐府所配之乐,都非雅正之乐,都不符合“中和之响”的审美要求。正因为刘勰所崇尚的是先秦雅乐,故而其对汉、魏乐府乃极为不满,甚至认为是“实《韶》、《夏》之郑曲也”。作为乐府的另一组成部分“诗”,刘勰亦是从先秦雅诗的角度予以品评的,如认为“宣帝雅诗,颇效《鹿鸣》”即为其例。在刘勰看来,只有“雅诗”与“雅乐”相配合,才能称得上是一首好的乐府诗,而汉初的《桂华》、《赤雁》诸篇,“魏之三祖”的《苦寒行》等作,则皆非如此,所以,他即将其以“丽而不经”、“靡而非典”、“实《韶》、《夏》之郑曲”等目之,认为其均与先秦雅诗相去甚远。
很明显,刘勰是以上古雅乐、雅诗作为品评的标准,以对汉、魏乐府与齐、梁“艳歌”进行审视与判定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乐府复古论”,其目的则是旨在从传统礼乐文化的角度,对当时繁荣发达的乐府创作进行“乐”与“辞”两个方面的规范,而“乐”则又为其之主要者。刘勰的这种批评论动机,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其在“崇雅”的同时又“黜郑”,人为地使二者绝对化,因而对汉、魏乐府的批评,不仅贬责过甚,而且还存在着某些认识方面的武断性,有的甚至为错误,如对“三祖”乐府的批评,即属如此。据沈约《宋书·乐三》所载,流传于刘勰所生活时代的《苦寒行》、《燕歌行》,所配乐分别为《悠悠》、《秋风》二曲,而此二曲不仅皆为平调,而且皆为荀勖所“施用者”,荀勖是西晋著名的音乐家,曾于宫中“既掌乐事,又修律吕”(《晋书·荀勖传》)多年,则为其所“施用”之《悠悠》、《秋风》非为“郑曲”者,也就甚明。所以,刘勰对于汉、魏乐府之“乐”的认识与判定,不可相信者,乃显而易见。此则表明,刘勰之于“魏之三祖”乐府的批评,或者说对曹操与曹丕乐府诗的批评,是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而且,其对“郑曲”与“楚声”不加分辨的排斥,也是有欠稳妥的。此外,刘勰在《乐府》一文中,由于未能从历史进化的角度就乐府诗的发展进行评价,而只是一味地尊古崇雅,特别是在对“乐”要求中正平和的同时,于“辞”也作如此要求,认为“三祖”的乐府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者,也是不可取的。至于其对俗曲、俗辞的不重视,就更是见出了其于“乐”与“辞”认识的不全面性。凡此,均表明了刘勰的乐府论是有失偏颇的。
但是,刘勰的《乐府》一文,作为乐府诗批评史上的第一篇“乐府论”,却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首先,《乐府》一文的问世,结束了乐府诗批评自先秦以来一直无“品第类批评”的历史,而成为后世对乐府诗“为批评而批评”之滥觞。此前的乐府诗批评,如“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等,虽各有特色,成绩斐然,但其却均不具备“论”的理性色彩,而《乐府》一文,则使之首次在这方面得以突破,并获得成功。其次,从批评的内容言,《乐府》一文具有明显的“史”的特点,其之勾勒与批评,由上古时期的“钧天九奏,既其上帝”,直至于齐、梁“艳歌”,其时间跨度之大,所论内容之丰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之深入,前所未有。其三,刘勰在《乐府》中首次将乐府诗作为一种文体的认识,不仅为其乐府观的一种具体反映,而且也丰富了文体学的内容,因而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后人无论是诗选家、诗人,抑或诗话作者等,皆将乐府诗作为一种诗体以待者,即无不是受刘勰《乐府》一文影响的结果。其四,刘勰在《乐府》一文中所力主之“乐府复古论”,对中唐元稹、晚唐皮日休、元末杨维桢等人的“古乐府论”,也是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的。⑦
注释:
①关于“品第类批评”与“为批评的批评”,可具体参见拙作《论“前乐府”的批评》一文,载《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48页-55页。
②关于先秦时期的乐府诗,即“前乐府”者,可具体参见拙著《商周逸诗辑考·自序》,第3页,黄山书社2012年出版。另可参见拙作《“前乐府”及其先秦的创作》一文,载《西华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29页—33页。
③在中华书局1985年版《玉台新咏》卷三所收13人35首诗中,另有李充《嘲友人》一首、曹毗《夜听捣衣》一首难以归类,特此说明。
④关于《文心雕龙》与《文选》、《玉台新咏》的关系,大体如下:据《梁书·刘勰传》,《文心雕龙》因沈约称道而为世人所重,同书《沈约传》载沈约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则其成书必在此之前;又据同书《昭明太子传》,萧统卒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享年31岁,则其编《文选》之时间,是必在梁武帝普通八年(公元527年)前后的;而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则明载《玉台新咏》乃成书于梁简文帝晚年(公元550年)。合勘此三者,可知《文心雕龙》成书最早,其后为《文选》,再后为《玉台新咏》,但《文选》与《玉台新咏》均未受《文心雕龙·乐府》之影响者,应与《文心雕龙》在当时不曾传入宫中相关联。若果尔,则知《文心雕龙》虽为沈约所“大重”,但其在当时的流传却甚为有限。
⑤据《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所载,《郊庙歌》十九章之末,依序分别有“建始元年”、“元狩三年”、“太初四年”、“元鼎五年”、“元狩元年”、“太始三年”之注,而其皆为汉武帝刘彻的年号,则《郊庙歌》十九章皆作于汉武帝时期乃甚明。其作者除司马相如外,另有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董仲舒、萧望之、邹阳等,具体参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张永鑫《汉乐府研究》,第164页。
⑥“宣帝雅颂,诗效《鹿鸣》”,唐写本作“宣帝雅诗,颇效《鹿鸣》”,甚是,以下所引,即据唐写本,不另注,特此说明。
⑦关于元稹、皮日休的“古乐府论”,可具体参见拙作《论唐代诗人的乐府观》一文,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1页—5页;关于杨维桢的“古乐府论”,可具体参见拙作《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一文,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4期,第55页—61页。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M].长沙:岳麓书社,1993.777.
[2]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3.484.
[3]陆侃如,弁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乐府第七)[M].济南:齐鲁书社,2009.154-155.
[4]王辉斌.先唐诗人考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95.
[5]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38.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9.
[7]陆侃如,弁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乐府第七)[M].济南:齐鲁书社,2009.158.
[8]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一,杂曲歌辞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