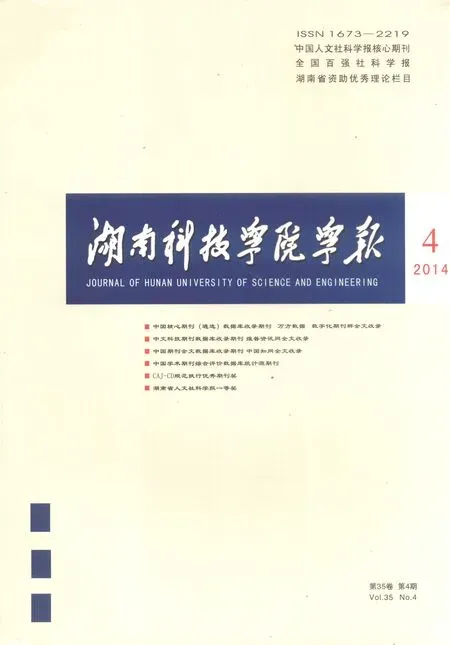谭嗣同早期佚著探隐
王 娟
(浏阳市文物管理局,湖南 浏阳 410300)
谭嗣同的早期著作,是研究谭嗣同早期思想和生活的重要资料来源,但其中一部分已经散失,这对于谭嗣同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拙文试图在分析谭氏现有著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佚作的内容作一番分析和探讨,并根据有关线索,对部分佚作手稿的下落作一些推测。
一
谭嗣同早年即好学深思,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在 30岁以前已有17种著作。谭氏《三十自纪》云:“今凡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一卷,《续编》一卷,《石菊影庐笔识》二卷,《仲叔四书义》一卷,《谥考前编》二卷,《浏阳谭氏谱》四卷,都十五卷。又《纬学》,翼经也;《史例》,书法也;《谥考正编今编》,名典也;《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天治也;《王志》,私淑船山也;《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欧阳、涂、刘也;《思纬氤氲台短书》,甄俗也;《剑经衍葛》,武事也;《楚天凉雨轩怀入录》,思旧也;《寸碧岑楼玩物小记》,耆古也,未成,无卷数。惟《史例》有叙。”[1]P55-56
上述17种著作,因《浏阳谭氏谱》有关内容已收入《寥天一阁文》卷二,故实际只有16种。除《寥天一阁文》、《莽苍苍二斋诗》、《远遗堂集外文》和《石菊影庐笔识》四种外,其他12种早巳散失,至今未有下落,但从书名和谭氏本人的简短说明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它们的内容。本文所称谭氏“早期佚著",即是指上述12种著作。《谭嗣同全集》编者方行先生在1980年为全集增订再版所作的《后记》中写道:“谭嗣同的佚著,据有关记载,尚有:《仲叔四书义》一卷,《谥考前编》二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至于未脱稿者有:《纬学》、《史例》、《谥考正编》、《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浏阳三先生弟子记(著录)》、《王志》、《寸碧岑楼玩物小记》、《楚天凉雨馆(轩)怀人录》等,惜均未发现。”[2]P553
方行先生文中所说《印录》值得略为说明一下。《印录》在谭氏《三十自纪》中未曾提及,全称应为《寥天一阁印录》,它辑录了谭嗣同本人所镌的部分印章,其后并附有谭氏所写跋文。最早提及《印录》的,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不久所写的《谭嗣同传》。民国元年(1912),谭嗣同的胞侄谭传赞在为刊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所写跋中,又再次提及此书。《印录》原件至今没有发现,但据谭嗣同的友人刘淞芙(名善涵)所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刘自金陵返湘,谭赠其《印录》以志别。次年戊戌政变,谭嗣同就义于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刘淞芙“家居无事,忽得之败纸堆中”,触动怀旧之情,特意写了《〈寥天一阁印录〉序》,以作纪念。[3]P142-143序言详细介绍了《印录》所辑印章的形式和文字内容,并转录了谭氏的跋文,从而为我们保留了这一珍贵佚著的主要内容。刘淞芙此文载《蛰云雷斋诗文集》,方行先生已将其收录于即将再版的《谭嗣同全集》中,故本文不再提及。
谭嗣同的12种佚著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已脱稿者,如《仲叔四书义》、《谥考前编》等。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方行先生将《剑经衍葛》列入已脱稿者,系根据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但据谭氏本人所述,此文在作者写《三十自纪》一文时仍未脱稿。可能此后逐步写成,所以粱氏有“《剑经衍葛》一卷”之说。如果确实如此,则《剑经衍葛》可以列入脱稿者一类。另一类是未脱稿者,共九种:《纬学》、《史例》、《谥考正编今编》、《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王志》、《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思纬氤氲台短书》、《楚天凉雨轩怀入录》、《寸碧岑楼玩物小记》。本文分析的重点是第二类佚著,即那些未脱稿者。这类佚著,多半为片断手稿,内容不会太多,过去因认为它们已经遗失,所以多在谭氏现有著作之外去寻找其下落。现在我们能否转变一下思路,试图在谭氏现有著作之中去发现它们的踪影和痕迹呢?根据这一思路进行尝试,笔者发现,上述谭氏佚著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并未完全散失,而是被保留在谭氏的笔记体学术著作《石菊影庐笔识》一书中。以下分别说明之。
二
《石菊影庐笔识》草成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其内容主要是谭嗣同随父移居武昌后,即光绪十六年(1890)至光绪二十年(1894)之间,所作的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它与上述谭氏佚著撰写于同一时期,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的方法,是根据已知谭氏佚著的主题,努力从《石菊影庐笔识》中去寻找与之有关或类似的内容,以此探索谭氏早期佚著的大致面貌。
一、《王志》,自注“私淑船山也”。王船山极其重视《周易》,认为它是“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4]P532。王船山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周易〉内传》和《〈周易〉外传》等《易》学哲学著作中。谭嗣同“为学专主《船山遗书》”[1]P138,其研究重点也是上述著作,并由此而“睹横渠之深思果力,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1]P9。《石菊影庐笔识》中与此有关的内容较多。《思篇》之一云;“理、数二也,而实一也。自其显而有定者言之曰理;自其隐而难知者言之曰数。……故知数者,知理而已,无数之可言也。”《思篇》之一云:“数者,器也,所以器者,道也。自邵子囿数为道,而数始为天下惑”[1]P123。象数和义理是《易》学中的基本问题,上述说法表明在《易》学基本问题上,谭嗣同继承了王船山义理学派的理性主义立场,并批评了以北宋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派的神秘主义。《思篇》之七论“衡阳王子(《易》卦六爻)十二位之说”,试图结合传统气本论和近代科学观念来解释卦爻的意义。由张载开其端的《易》学哲学中的气本论,到王夫之而集其大成,其特征是以阴阳二气的变化来解释卦爻象的形成和联系,并进而解释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谭嗣同继承了张载、王夫之的气本论思想,他在《思篇》之八提出“元气氤氲,以运为化生者也……中和所以济阴阳之穷也。”并得出了“变化错综,盈天地间,皆《易》也”的结论。[1]P127《思篇》之九谈“生物之气”和“天地往来之气”;《思篇》之十四批评“释氏之末流,灭裂天地”,提出“夫天地非幻,即声光亦至实,声光虽无体,而以所凭之气为体。”[1]P127-128《易·系辞传》提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思想,张载、王船山对此都详加阐述。《思篇》之十七、十九皆论“游魂”,并谓“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知生死,于以见万物一体,无容以在囿者自私也”[1]P132。另外,《思篇》之十三云“圣人之言,无可革也,而治历明时,《易》独许之以革。……革而当,圣人之所许也”[1]P129。亦为谭氏学《易》之重要体会。王船山不满于宋儒空谈“理”和“道”,而将所谓“道学”和“理学”改称为“精义之学”。)《笔识·学篇》之七十七对此表示赞成,认为“理之与道,虚悬无薄”,应当为之正名,改称为“义学”[1]P122,表明了谭嗣同对宋明理学所持的批评态度。如果我们由此推断说,上述有关思想是谭嗣同钻研船山哲学,特别是其《易》学哲学的重要成果,并很可能构成其所著《王志》一文的内容,大概不会是过于武断的说法。
二、《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自注“天治也”。北宋哲学家张载在其《正蒙、参两篇》中“尽破历家之说”,提出“地亦动而顺天以旋”。王船山对此则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地之不旋,明白易见”,“《正蒙》一书,唯此为可疑”。[5]P45,48谭嗣同不赞成船山的这一观点,认为张载的地动之说符合科学,具有远见卓识。《思篇》之三引张载地球绕日、月绕地球而运之说,指出“西人之说,张子皆已先之,今观其论,一一与西法合”,称赞“张子苦心极力之功深”,并谓“不知张子,又乌知天?”[1]P123-124此外《思篇》之四论“地圆而动”;其五论“地圆之说,非发于西人”;其六论“地动之说”,其十一论流星陨石,也都属于“天治”的范畴。
三、《纬学》,自注“翼经也”。谭嗣同治纬学,主要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北上赴癸巳顺天府乡试期间。他曾回忆说:“南昌沈小沂兆祉,吾瓣姜先生弟子也。……往与同学京师,渠治目录,嗣同治纬,相得欢甚。”[1]P265-266谶纬是两汉经学与图谶方术相结合的产物,但纬与谶有所不同。“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6]P47;其内容“纯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7]P109《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各有其纬。《思篇》之六谈地动之说,引用了《易、乾凿度》、《尚书、考灵曜》、《春秋、元命苞》等书,均为纬学的重要著作,其目的是以此证明“地之动,乃圣人之言”[1]P125。《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中有关“纬学”的内容虽然不多,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谭嗣同当时治纬学的一些情况。
四、《思纬氤氲台短书》,自注“甄俗也”。表明谭嗣同作《短书》的原意,是仿诸王充、王夫之驳斥五行八卦等迷信思想,批驳当时流行的风水、壬遁、星命诸说,“以与世俗相砥砺",其后则以《报贝元徵书》代之。谭嗣同在《〈思纬氤氲台短书〉叙》中说:“嗣同夙愤末世之诬妄,惑于神怪杂谶,使民弗乏乎事业,坐为异邦隶役,读衡阳王子辟五行卦气诸说,慨焉慕之。……尝分条讼辩,以与世俗砥砺,而仍恐自不出乎世俗,遂标日《短书》。奄积日月,得若干件,适有报欧阳瓣姜师书,足以隐括厥旨,间有未尽,复于《报贝元徵书》详焉。师以报书及拟为算学社章程,别刊《兴算学议》一卷,兹乃仅以报贝者代吾短书。”[1]P195
根据上述线索,可以发现《思篇》中有3条与原来《短书》相似的内容。其十六赞扬王充云:“《春秋》‘震夷伯之庙’夕,左氏谬言展氏有隐慝。……而百世之上,有王仲任者,独不信之。……汉人习闻谶纬五行之说,其诞至不可诘,王氏生于其时,乃能卓然不惑,指捕其失,持论虽时近偏矫,甚至非圣无法。然统观始末,弃短取长,亦可谓豪杰之士哉!”[1]Pl32其十八批评“好芝菌导引之说”,乞求不死之术。其三十四解释“兴必有祥,亡必有妖”,认为:“祥岜必谶纬书所纪之图册符瑞哉?君子是也。妖岂必五行志所陈之灾疴眚哉?小人是也。”[1]P133
五、《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自注“欧阳、涂、刘也”。《思篇》之四十论浏阳之学,谓“先迸如刘蔚庐师之纯粹精,涂大围师之直方大,欧阳瓣姜师之刚健文明”[1]Pl45其三十为《上刘蔚庐师书》。皆与此主题相符。
六、《楚天凉雨轩怀人录》,自注“思旧也”。《思篇》之四十一记“石菊影庐”、“远遗堂”;其四十二记“甘肃布政使署”;其四十三记“潮北公桑园”;其四十四记仲兄嗣裹;其四十五记赠贝元徵、唐黻丞、黄芳洲等楹联;其四十七记往年在灞桥、西安旅舍所见题壁诗;其四十八记甘肃友人李景豫、钱次郇、张松眉、曹悟生等诗文;其四十九记少年之诗;其五十记十八岁时所作《望海潮》词;其五十一记怀念仲兄之诗;其五十二记幼时之诗。皆为“思旧怀人”之作,很可能就是《楚天凉雨轩怀人录》的原有内容。
七、《寸碧岑楼玩物小记》,自注“耆古也”。《思篇》之五十三谈“孝堂山武梁石室”、嘉祥洪福院诸画像等古画;其五十四谈“以团扇浼人作两面画"。前者属于“耆古”,后者属于“玩物”,与《小记》内容相近。谭嗣同在同一时期给刘淞芙的信中曾谈过自己对书画的看法,可作为此文的注脚:“画虽小道,尤难语于今日。东国有好古之名,所辑皆峭倩入古。其称前古模样者,饕餮之象则出周鼎,鸡凫之形则本彝器。图雷之家推椎引鼓,若武士而不著翼,亦与王充《论衡》之说符合。彼国作者必考证今古,然后下笔,非若今之向壁虚造,苟然而已也。虫鱼草木尤足资博识。先儒亟尚图象,《尔雅》、《列女传》皆有圈。今摹覆流转,殆失真本。朱予据首某向之文,知《山海经》旧有图,当时服其特识。蒙不揣,辄欲补为之,得此足以自广。”[2]P475
谭嗣同所“玩”之物,不仅有石刻古画,而且还有古琴和古乐。《思篇》之二十二谈浏阳之乐“有声天下”,提到邱毂士和刘人熙的音乐著作《律音汇考》、《琴旨申邱》;其二十三谈音乐有关人心风俗;其二十四谈礼乐之分导致“声音之道微矣哉”;其二十五谈今之琴操“发音尖促凄厉”,“嗣同阗谱不下数十种,无不兼有此病。”等[1]P136,都是谭嗣同研习古乐的体会。如果此数篇不属于《寸碧岑楼玩物小记》,那么我们据此可以推测,谭氏很可能曾有撰述有关古琴古乐文字的打算。据刘人熙回忆,谭氏于光绪十五年(1889)赴北京求学时,“雅好音乐,善南北昆曲,能歌乐章”[8]P7,并“于鄙人所作,独有神契于《琴旨申邱》,他人所略而不道者,生独津津有味言之”[9]P2。谭嗣同致刘淞芙信中也曾谈及乐章,亦可作为参考:“乐章中复衬腔,与蔚庐先生言之,因援南北九官为证,衬腔凡乙字于昆山曲为南曲,和婉雍容,故应胜昔。后夫子著《琴旨申邱》一卷,遂采用鄙说”。[2]P48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谭嗣同12种早期佚作,除《谥考前编》、《谥考正编今编》、《仲叔四书义》、《剑经衍葛》和《史例》5种,其内容已经遗失外,其他7种,即《王志》、《张予正蒙参两篇补注》、《纬学》、原《思纬氤氲台短书》、《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楚天凉雨轩怀人录》、《寸碧岑楼玩物小纪》等,其部分内容仍然保留于《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之中,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谭嗣同早期生活和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共54条,据笔者粗略估计,与谭氏上述佚作内容有关者,约达38条,占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对于《笔识、思篇》与谭氏佚作之间的关系,要区分内容上的相似性和重复性两种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一、相似的内容。《笔识、思篇》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思篇》前半部分,即从第1条到第20条,大多属于科学和哲学的内容,与之对应的佚作应当是《王志》、《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纬学》和《短书》,而这四篇佚作的主题和内容则互相关联。笔者认为,《思篇》前半部与上述四篇佚作,在内容上是同源的。它们产生于同一时期,是谭氏同一学习和思考过程的产物,所以两者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和素材,只有形式和重点的区别。同样的思想和材料可以运用于《笔识、思篇》之中,稍作修改和加工之后,又可以使用于其他佚著之中。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这种密切关系,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前者,就可以了解后者的基本内容和大致面貌,同时又不致于将两者混为一谈。作这样一种区分,可以比较圆满地解释《笔识、思篇》与上述佚作既分别成书而又内容近似的情况。
二、重复的内容。《笔识、思篇》后半部分,内容比较杂驳。与之对应的佚作是《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楚天凉雨轩怀人录》和《寸碧岑楼玩物小纪》。特别是从第40条到第54条,很可能就是上述佚作的原来内容,谭嗣同未加改动,就将其分别编入了《笔识、思篇》之中,从其篇目相接、内容近似可以证明。根据这种解释,可以进一步推测《石菊影庐笔识》的成书过程。当谭嗣同作《三十自纪》一文时,《笔识、思篇》的内容可能仅限于现在《思篇》的前半部分。而当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谭氏在金陵刊行自己的著作“旧学四种”时,因见剩下的《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楚天凉雨轩怀人录》及《寸碧岑楼玩物小纪》等著作,无所归属,遂一并附之于《笔识、思篇》之后,由此形成了今天《笔识、思篇》内容驳杂,“思想”之“思”与“思念”之“思”兼而有之,不相类属的状况。
四
最后探讨一下谭氏早期著作手稿的下落。谭氏手稿大多散失于戊戌政变之际。谭嗣同在北京被捕时,部分手稿被抄没。据谭氏《狱中书筒》之二云:“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回会馆否?”[2]P533由此可见,被抄没的手稿,只有《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一种,并不包括上述谭氏早期著作。民国元年(1912),谭嗣同夫人李闰根据家存残稿,于长沙刊印《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补遗》,谭传赞为之作跋曰:“先叔所著书亦多矣,自《仁学》外,尚有《壮飞楼治事十篇》、《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要不仅所传四种已也。惟自京师被难至今,来尽珠还耳。稿多散佚,叔母李夫人因憾版之亡而谋重刊,并出所存《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一卷,《浏阳兴算学议》一卷夕先付手民,以寿梨枣,余稿寻获,再为续刊焉”[1]P288。可见,直至民国初年,谭氏遗失之手稿仍“未尽珠还”。
谭氏另一部分手稿则转送友人保存。据梁启超撰《谭嗣同传》云:政变之际,谭氏于被捕前“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又云:“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廖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札记》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恩纬氤氲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及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余将君之石交某某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2]P546-547。粱启超先生所述谭氏著作篇目卷数与事实略有出入,其所说《谭浏阳遗集》亦未见刊行,但这仍是目前所见关于谭氏著作手稿(包括早期手稿《剑经衍葛》、《印录》等)下落最明确的说法。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即在梁启超先生所留下的大量函件、手稿和书籍中间,可能还保存有若干谭嗣同早期著作手稿,如果仔细加以清理,或许会有所发现。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还有待今后的证明。
[1]谭嗣同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刘善涵.蛰云雷斋诗文集[Z].浏阳县政协文化工作组,1985.
[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
[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刘人熙.琴旨申邱[Z].光绪刻本.
[9]刘人熙.浏阳烈士传序[Z].民国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