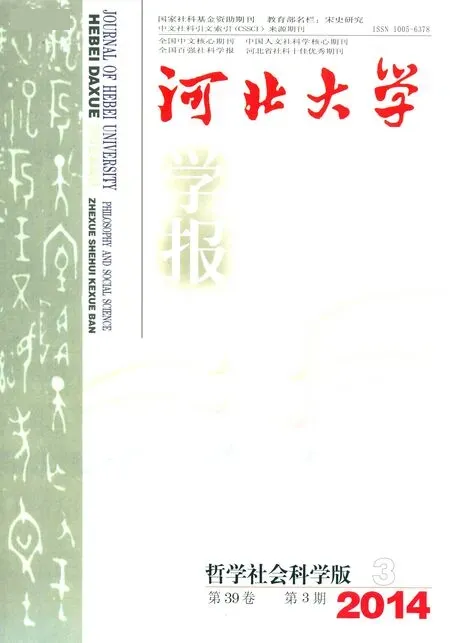“苏 有子 李峤无儿”小考
姜剑云,吴 萱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李峤与苏瓌皆为武后、中宗朝重臣,“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散见于各种杂史笔记,有三种不同说法,本文以新旧《唐书》、李峤长子李畅《唐正义大夫使持节相州诸军事守相州刺史上柱国赞皇县开国子李公墓志铭并序》等史料为依据,试逐一详加考证。
三说之一:中宗召李峤、苏瓌二丞相子问“所通书”,李峤之子应答未得其欢心。
此说最为多见,如《松窗杂录》载:“中宗尝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抚于赭袍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日忆所通书,可奏为吾者言之。’颋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失其名)亦进曰:‘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1]559此为最早也是最完整生动的版本。
完全引自《松窗杂录》的如《说郛》卷五十二下[2]774、《天 中 记 》卷 十 七[3]769、《何 氏 语 林 》卷 十八[4]705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三注明出自《松窗录》[5]4050,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李峤条:“皮日休《松窗录》云”后引此事[6]146,而《唐语林》卷三则说是二子“同年”[7]93。此外,内容基本与《松窗杂录》相同,文字稍简略,未提及“二子童年”的,有《类说》卷十六[8]272、《绀珠集》卷十一[9]489、《古今事文类 聚 》后 集 卷 六[10]91、《记 纂 渊 海 》卷 五 十八[11]643等。
此说涉及《松窗杂录》或皮日休《松窗录》等出处。经检索,《松窗录》一卷:《新唐书·艺文志》[12]1543、《通志》卷六十 八[13]798、《崇文总目》卷四[14]54以及《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15]433等史志书目均有著录,未注作者姓名;《郡斋读书志》卷二上[15]196、《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五著录为“唐韦濬撰”[16]1758;《千 顷 堂 书 目 》卷 十 五 著 录 为 李 濬撰[17]412;《宋史》卷二百六《艺文五》著录有“李濬《松窗小录》一卷[18]5222。检索皮日休所著,未见此书之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有《松窗杂录》一卷,提要云:
此书书名,撰人诸本互异。《唐志》作《松窗录》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窗小录》一卷,题李濬撰。《文献通考》作《松窗杂录》一卷,题韦濬撰。历代小史则书名与《通考》同,人名与《宋志》同。盖传刻舛讹,未详孰是。[19]1185
据此,《松窗录》与《松窗杂录》等当为同一书,韦濬或李濬撰。在其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书名、著者等多有讹舛。
我们再来探究一下这个记载的真实性。
首先,李峤长子李畅《墓志》云:“公讳畅,……以开元十八年岁次庚午六月甲寅朔十八日辛未,薨于东都宣风里第,春秋五十有二。”[20]519可知其卒于开元十八年(730年),享年五十二岁,那么,其生年应为高宗仪凤四年、调露元年(679年)。苏颋,其传见于两《唐书》其父苏瓌传之后,《旧唐书》本传云其:“(开元)十五年卒,年五十八。”[21]2881则颋应生于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颋比畅年长九岁,怎么可能“二子皆童年”?而那个“失其名”的李峤之子若不是李畅,更不可能是李峤其他的儿子,畅既为长子,余者会与苏颋在年龄上相差更多,“同年”之说,更无依据。所谓“同年”,一是指同年出生,由上述已知其为不可能;二是唐代同榜进士称“同年”,若果如此,“上近抚于赭袍前,赐与甚厚”,这种对待小孩子的方式显然滑稽可笑,而且,检索《登科记考》等相关资料,未发现苏颋与李峤哪个儿子同年及第的记载。
其次,由两《唐书》的《中宗本纪》可知,中宗曾两次在位,第一次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即永淳二年、弘道元年(683年)末,嗣位仅两月,即被其母武后废黜,圣历元年(699年)又被册立为太子,神龙元年(705年)复位。显然,召二丞相子之事不会在其册立为太子或者复政后,彼时无论哪个孩子都已成年,“二子皆童年”,显然谬甚!陈冠明先生所著《苏味道李峤年谱》就将此事系于永淳二年、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中宗即位,召李峤之子、苏瓌之子颋,使诵所通之书。”并在略加考证之后认为“凡此相比,甚是无谓,当是附会,故多异词,今不取。”[22]102此时,苏颋十四岁,早已不应算是“童年”,李畅只有五岁,虽可称“童年”,却当属年幼无知,这样的两个孩子,实在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理由。
其实,这样漏洞百出的记载,前人早有异议,《四库全书总目》在《松窗杂录》提要中就明确指出:
《松窗杂录》……惟谓中宗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颋于则天长安二年已为御史,瓌为相时,颋为中书舍人,父子同掌枢密,并非童年。故司马光深斥其说,颇不免于诬妄云。[19]1185
所引司马光之说,与上文略同,载《资治通鉴》卷二百七“考异”[23]6560-6561。
最后,我们不妨抛开对这个事件真实性的考证,再来分析二子对中宗问话的回应。“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见《尚书》卷九《说命上》“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24]295颋所言意在规劝君主接受劝谏,成为圣人。此语颇具温柔敦厚之风,既切中要点又相当得体。而那个“失其名”的李峤之子,似乎也并没有错,《尚书·泰誓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24]331“斮胫”“剖心”是典型的暴君所为。峤子是在提醒君王,不要“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此话无可厚非,充其量有些逆耳。只是中宗本就昏庸懦弱,我们只要读一读两《唐书》的《中宗本纪》就会找出大量实证。这次他也只拣顺耳的话听,可怜李峤之子,很有点对牛弹琴的悲哀,不仅当时没得到圣上的夸赞,千百年来更留下了“苏瓌有子,李峤无儿”的典故,看来,其真的是远不及苏颋深谙于君主面前应对自如的语言艺术。正如刘声木先生《苌楚斋随笔·五笔》卷一援引《松窗杂录》所载此事后的评论:“二子所言,皆不为无见,未易定其优劣。瓌子之言是规也,峤子之言是谏也,颇合‘规谏’二字之理。中宗既非有道之君,峤子直谏于祸乱未萌之先,其远识应在瓌子之上,未可以中宗一语,即为公是非。司马温公《通鉴考异》深斥其诬妄,然此书本体近小说家,各尊所闻,用资谈柄,固不必是丹非素也”[25]897可谓一语中的。
三说之二:苏颋因其父苏瓌去世,哀伤过度,固辞起复,时人有云“苏瓌有子,李峤无儿”。
此说见于《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四《孝下》:“《朝野佥载》曰:苏颋为中书舍人,父右仆射,卒。颋哀毁过礼,有勅起复,颋表固辞不起。上使黄门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终坐无言,乃奏曰:‘臣见瘠病羸痩,殆不胜哀,臣不忍言,恐其殒绝。’上恻然,不之逼也。故时人语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26]1910
而《旧唐书》苏颋传亦有记载:“瓌薨,诏颋起复为工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颋抗表固辞,辞理恳切,诏许其终制。服阕就职,袭父爵许国公。”[21]28802可见此事并非杜撰。
同样说法亦见于《记纂渊海》卷三十六《仕宦部》“起复”条[11]26。需要指出,“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在《记纂渊海》中两度出现,在卷五十八《论议部》“事物相形”下引了中宗问二子所通书之事,同一书,竟用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来证明“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么?盖其著者编纂之时亦未详加考订。
古人于父母去世后有守制的礼俗,不得应考,官员须解职,不得婚嫁或从事娱乐活动,谓之“丁忧”,这一点至唐代已形成了严格的规范。如果有因贪图功名利禄或其它原因匿父母之丧不报,或于丧制未终而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唐律疏议》卷十《职制部》就“匿父母及夫等丧”有明确的惩戒律令[27]204-206。白居易就曾因其母看花堕井而亡,却作《赏花》《新井》诗,被贬为江表刺史,由此可见官员丁忧之制度。
苏颋于丁忧期间“有勅起复”,却“固辞不起”,既是父亲离世过度悲伤所致,恐又与其出身世家,长期受儒家礼教思想濡染不无关系。他不仅未因守制影响自己的前程,“服阕就职,袭父爵许国公”,反而还因此赢得了时人“苏瓌有子,李峤无儿”的赞誉。那么李峤之子究竟有什么不孝之事留人话柄?
《旧唐书·苏瓌传》中记载,瓌“景云元年,以老疾转太子少傅。是岁十一月薨”[21]2879;《新唐书》苏瓌本传亦云:“景云元年,老病,罢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12]4399可知苏瓌卒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十一月,《唐律疏议》对“丧制未终”的解释为:“谓父母及夫丧二十七月内。”[27]204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苏颋为其父守制,即丁父忧至迟到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初,之后“服阕就职”。在这个过程中,李峤当一直健在,直到遭贬,“为庐州别驾而卒”。也就是说,其父尚在,其子怎会因不孝而落人口实?相反,李峤长子李畅《墓志》云:“妣燕国夫人,无禄未练而赵公薨,累丁艰罚,痛深创钜,杖而后起,殆不胜哀。君子以为难也。服阕,拜吉州刺史。”[20]519可知李畅父母盖相继离世,其当按制守丧且因接连遭遇失去亲人之故,十分悲痛,“服阕,拜吉州刺史”。
父亲过世,作为儿子,过度悲伤甚至放弃升迁机会,这确实令人感叹唏嘘,作为皇帝,表示理解并且“恻然,不之逼也”,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时人“苏瓌有子,李峤无儿”的感慨,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既然将二者相比较,就应以事实作为依据。然“李峤无儿”之说,惜无相关史料可考。
三说之三:苏瓌之子有才能,李峤之子不及也。
《册府元龟》卷七七七《名望第二》中记载:“苏瓌中宗朝历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子七人,颋、冰、诜、乂、颖、锐、颜,颋最知名,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诜,户部员外。瓌与李峤同居相位,峤有才华,其子不肖;瓌以干理而颋有文词,故代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29]9234,卷九四〇《不嗣》所载稍略。[29]11068综合分析有关文献可以看出,此当为“苏瓌有子,李峤无儿”最为合理的解释。理由如下:
首先,此说出自《册府元龟》。该书成于宋真宗年间,属于大型政书,所选内容均自正史,其编者也集中了当时精英。官修政书,可以凭借大量官方藏书资源,编书之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治国之道,可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毕竟不同于那些杂录笔记、稗官野史。
其次,苏瓌、李峤同为武后中宗朝台阁重臣,“瓌为相时,颋为中书舍人,父子同掌枢密”,成为当时美谈,苏颋又与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李峤在当时文坛享有盛誉,《旧传》云其:“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21]2993《新传》有 “而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12]4371。可谓权倾一时,文名卓著,但是,除前文提到的长子李畅之外,其余的儿子则显得默默无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峤有四子,畅、裕、粲、懿。据《世系表》及李畅《墓志》可知,畅终于相州刺史,“博览坟籍,尤工藻翰”,且“有集卅卷,传于后”;据《世系表》,李裕,终于海州刺史;李粲,终于濮州刺史;李懿为华阴郡太守[12]2546-2547。无论于文坛还是官场,李峤诸子远不能与许国公苏颋相提并论,或因本就属平庸之辈,或因其父获罪受到牵连,总之,“其子不肖”,也就难怪时人有“苏瓌有子,李峤无儿”的慨叹了。
尽管李峤在武后中宗朝曾位高权重,然因其先追随武后,依附二张,后又转而效力于韦氏一党,其为人多遭诟病,晚年又屡屡被贬,最终卒于庐州别驾。“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既见于杂史笔记之类,在未有更加确切的史料可资证明之前,本就未可确定其真实与否,有些子虚乌有之说,或确有以讹传讹之嫌,抑或“所谓失势之人,史家众恶归焉”[22]228。
[1]李濬.松窗杂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10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陶宗伟.说郛[M]//文渊阁四库全书:8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陈耀文.天中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9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何良俊.何氏语林[M]//文渊阁四库全书:10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王谠.唐语林[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曾慥.类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8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绀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8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祝穆.古今事文类聚[M]//文渊阁四库全书:92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潘自牧.记纂渊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9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王尧臣.崇文总目[M]//文渊阁四库全书: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翟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0]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陈冠明.苏味道李峤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4]孔安国.尚书正义[M].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5]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M].刘笃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26]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7]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8]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