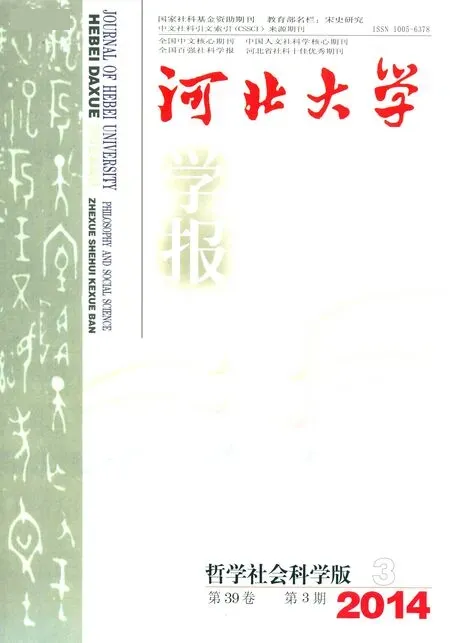《文心雕龙》三曹文体论与文学特性之揭橥
杨青芝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刘勰认为所有文体都源出于五经,并对五经的内容特征和形式要求作了区分,也是对所有文体、所有文章进行了大略的分类:1.源出于《易经》的学问类文章。“易惟谈天”,按《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论说辞序”也是如此,属于那种宏观、抽象的学问类文章,要求概念准确,逻辑严密,“旨远辞文”——推敲词句以表达抽象而深刻的义理。2.《尚书》记言,是思想和道理的传达,“诏策章奏”属于此类,《春秋》记事,“纪传盟檄”属于此类,二者相当于今天的公文及其他应用文,其中对内的公文要求意义明确,语言规范而平实;外交层面的公文,如盟檄这类各国约会的宣言或文稿,由于国家关系的微妙性,要求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某些微妙的意旨;其他社会交往中的应用文,也要求方式委婉而表意恰切。《尚书》中有说理的内容,属于学问类;《春秋》作为史书,是学问展开的基础,本身不是学问类。单就记事、记言而言,属于文学类。3.《礼经》内容是各种体制、法度,条款详细周密,在今天属于纯粹的公文。刘勰说“铭诔箴祝”属于此类,是因为这类文章涉及礼法,要求周到、严密,遵循一定规范。4.《诗经》和赋颂歌赞同属抒情言志类,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类。文学作品也有说理成分,不过是运用比兴等特殊手法。
刘勰的文体分类研究是一种方法,即《序志》中所谓“囿别区分”。五经分类法并不严密,全部文体按五经分类,也不能严格区分各自特性。进一步概括刘勰的五经分类法,实则是将全部文章、全部文体分成了学问文、应用文和文学作品三类。按这三类对“论文叙笔”部分进一步提炼,刘勰对学问文章、应用文章、文学作品的共性与特性认识就比较容易整合了。三曹文章涵盖了学问类、应用类、文学类,且都具有典范性,是刘勰文体论和形式论中经常出现的典型个案。《文心雕龙》中有30多处论及三曹诗文及其言论,不仅涉及到他们的诗、乐府、赋、诔等文学作品,也涉及到他们的诏策、论说、章表等应用文,还涉及到一些论学或者具有学问性质的文章。因此本文选择三曹论来整合刘勰对不同文类共性和特性的论述,总结他对文学文体特性的揭橥。
一、三曹文学作品
论文叙笔部分首先是论本源于《诗经》的诗体及赋颂歌赞。其中《乐府》相当于今天的歌曲艺术,只是乐谱不传,所以一般被当做乐府诗来看待。这类文体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文体。
在《明诗》篇中,刘勰说曹丕和曹植等“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不仅指出了这些诗作的特色,而且肯定了这些特色:内容方面有自然景物的描绘、人生遭际的叙述、各种场景的记载,都是为了抒发情怀,表现心志;形式上,不追求精细严密,写景只求鲜明动人而不追求真实。他由文学内容和形式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其特殊效果:“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雅”即“正”,是“持情性”,让人的情性保持或者回归正轨,让不平静或者不平衡的心理得以平复;“润”是浸润、感染的意思,是文学持情性的特殊方式,也是文学影响人心的特殊效果;“清”按有的学者解释,“作为一种风格,就是轻灵飘逸,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就是不落言筌,意在言外”[1]35;“丽”是文辞美。刘勰说曹植兼有这些优点,显然,他对于“偏美”是认同的,但最高标准则是情志正,或能够正情性,具有感染力,意蕴丰富而文辞优美。刘勰称赞三曹作品质朴——“魏之遗直”、刚健有风骨——“力柔于建安”,与它们能够“持情性”是一致的。
在《乐府》中,刘勰指出乐对于人心影响很大,因此“务塞淫滥”,不能放任情感,更不能让情感走向歧途。他对曹操等人的乐歌有异议:“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征人苦情,羁旅愁怀,从审美角度来说,是非常感人的,但是从持情性角度来说,则不能过度描写。比如说当代文艺作品中涉及到战争的题材,如果一味描写战士与远方亲人的思念之苦,过多反映战争的残酷,而忘却了保家卫国的大义,自然是不应该的。既然必须战斗,不可避免牺牲,当然应该以豪情壮志为主。文学作品抒发自然情志是合理的和必然的,理论家们提出持情性的要求更显得必要。作者应该自觉地追求崇高,不能是一味哀怨。三曹乐府之作心志迷乱,哀思过度,是感人至深的佳作,但不是最理想的文艺作品,刘勰这种评价并无问题。
诗持情性对于乐歌来说,主要是就歌词而言。“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从歌曲艺术的特点来看,歌词以简约为贵,这是《诗经》传统,《诗经》常常是配乐演唱的,很多篇目歌词简单,反复咏叹。三曹时代,诗和歌已经分开,词句重复的情况不再常见,那么刘勰由曹植所言“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得出“明贵约”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诗本身是否还成立呢?《明诗》篇中,刘勰对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现象,并无明显贬意,由此可见他并不会认为“贵约”是诗以及整个文学作品的必然要求。他经常提到简约,主要是就应用文和学问文章而言的。
刘勰将“诗”与“歌”分开,也是将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作了区分。他说:“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诗不一定要演唱,其“佳”不在于以声动人,而在于以意义触动人心,或者说,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在于理性,而非感性。这更见出其持情性的可能与必要。
曹植赋作很多,以日常生活描写和个体情志表现见长,《洛神赋》堪称古代文学经典名作,但是他不在刘勰所评魏晋第一流赋家之列。由刘勰赞赏王粲赋的细密、徐幹赋的博学、左思和潘岳赋的规模、陆机《文赋》的学识、郭璞赋的富含道理、袁宏赋的慷慨激昂之气来看,曹植的闲情逸致似乎小气了些,而《洛神赋》中那种沿袭屈原、宋玉虚构奇遇、艳遇以自慰的情志,刘勰在《辨骚》篇中已经表示了异议。这不是对文学特性的否定,相反,正是因为认识到文学作品有可能是放任个体情志,所以才强调“持情性”。刘勰指出赋的特征是“写物图貌”以兴发情感与志意,将持情性的要求转化为“风归丽则”。“文虽新而有质”,不能“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他不认为曹植是一流赋家的原因正在于此。为很多人喜爱的文学作品不等于值得推崇的理想作品。刘勰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对文学的一般要求,或者说对理想文学作品的要求,是没有矛盾的。
“颂赞”属于应景性的文章,文学性较强,后来常常附属于其他著述,或者成为文章中的一种表述方式,而非一直传承的独立文体。刘勰说曹植的《皇太子生颂》“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是要求颂赞要有明确的态度。《诗经》具有美刺传统,作者是赞颂还是批评,倾向性应该明确。有明确倾向,与文章如何表现这种倾向不是一回事。文学婉曲表现倾向的方式,在应用文中也是适用的。另外,倾向性建立在作者对人和事物的看法要全面的基础上。
综上所述,刘勰对于文学作品特性的认识是情志为主,也推崇思想性,并要求有倾向性。对于叙事性文章,可能由于当时叙事文学不发达的缘故,刘勰没有特别关注,不过,刘勰所谓“物”并非仅指景物,而是包括一切人事物,写物图貌不限于景物描写,也涵盖了叙事。文学作品要贯彻持情性的原则,通过文学作品来影响人的心灵,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满足于自我宣泄和自我表现。
二、三曹学问文章
《杂文》《谐隐》《史传》《论说》等属于说理性的或思想学问性的文章。
杂文包括问答体、七体和连珠,三曹这方面作品不多。刘勰指出,问答体本来是一种抒泄内心愁闷的方式,优秀作品是以深刻的思想和巧妙的文辞来表现作者不顺利时的高尚品德或泰然心情。这种说理的目的是达观看待人生遭际,具有文学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问文章。不过毕竟问答体主要指向的是宇宙人生之理,调整情志、持正情性属于写作动机和客观效果,所以还是应该归于学问类。刘勰说曹植的《客问》“辞高而理疏”,与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相对,可见其要求是既要包含深刻、通达的道理,也要有相应的辞采。“七体”也是如此。刘勰说曹植的《七启》“取美于宏壮”,与王粲的《七释》“致辨于事理”相对。《七启》的道理,不外乎是说出仕对于自己和对于时代更有意义,这个道理孔子早就说过,曹植举各种例子,反复阐申,显得文辞华美,很有说服力。刘勰显然更认同王粲能够将事理细密地阐说清楚。当然,兼二者之长更好。
谐隐是以戏谑或隐喻方式来说理。刘勰说这种方式在曹丕、曹植那里运用得比较好,“约而密之”,既简明又周密。
史传如同《春秋》,寓褒贬于记事中,发展到后来,会直接展开人物和事件评论,具有说理文或学问文章性质。刘勰对《史传》的要求是“文质辨洽”,兼有宏壮形式和优美文辞。三曹没有史著,论道说理则是少不了的。这方面曹植最弱。在《论说》中,刘勰批评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的《孝廉》“但谈嘲戏”,曹植的《辨道》“体同书抄”。说理文、史论都要有思想家的深刻和学者的严谨,这是普遍的高要求。刘勰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由此而来的说理文和学问文章,要有圣人的襟怀、气势、高度、深度和广度。“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学问文章是为了寻求真理的。“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思想家应该深刻、全面而周密,思想的表达上也需要严谨、周密。“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心与理合”“辞共心密”,不能够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由此可见,刘勰对于说理文和学问文章的形式要求非常高。
学术文章以明道经世为根本。刘勰对于一切文章都强调明道经世,不同文类在明道、说理上也有区别:文学作品以情志为主,以明道经世为更高价值追求,但不一定要包含道,刘勰在这方面体现出他的通达;应用文是体现道或运用道,侧重经世;而学问文章则是以道为主。刘勰要求文章有“风骨”,主要是就学问文章而言,对于文学作品则是高要求,不是必然要求。“风”是影响力或效果。“骨”是指充实的内容,也是指很强的思想性。风骨取决于主体的“气质”。《风骨》篇中,刘勰引用了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齐气”,刘桢“有逸气”。曹丕是说文人不同的气质,决定了文章的多姿多彩风貌,决定了不同文人擅长不同文体,有的人更擅长文学创作,或者所写应用文和学问文章文学性比较强,有的人则擅长应用文,或学问文章。刘勰最为推崇明道经世之文,将“风骨”由文章风格提升到文章的思想性和影响力层面,因此强调“养气”,要求作家培养德行、学识,增长阅历,深入思考。
三、三曹的应用文和公文
祝盟、铭箴、诔碑、哀吊、封禅较之颂赞同样具有文学性强,而应用性更强。这类文章或涉外交,或关乎政治人物评价,所以要求事信、理正,严肃、严谨。这也是《礼经》的特点。
刘勰说有些作者将祝文写成骂文,指责过失,“唯陈思《诘咎》,裁以正义矣”。他不是说祝文不可以诘问、指斥,而是要求作者本人立场公正,思想正确,评价公允、客观。铭文有褒有贬,箴文以警戒为主,都要求事实可靠,文辞简明深刻。曹丕的《剑铭》,单纯记载造剑之事,比较平实,只有“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一句提升了剑器的意义,因此刘勰不大满意,说此文“器利辞钝”,可见他要求这类文章辞藻上更有感染力,要求有更深刻的思想。
诔文和碑文多是为大人物而作,是史传的模式,不注重史的客观性,偏于颂美。刘勰要求这类文章记人记事“暧乎若可觌”,表达亲情要真挚感人,和文学作品很相似。他批评曹植的《文帝诔》“体实繁缓”,那是因为《文帝诔》多少有些不得不为的应景性质,感情空洞,辞藻重复。篇末一百多字抒发作者本人的怨情,刘勰认为不合文体要求,今人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那才是出彩之处。单就一篇诔文而言,确实是体制不合。后世诔文受此影响,也常常是借悼怀故人抒泄己意,使诔文由应用文演变为文学作品。
《封禅》就记载帝王事迹而言,源出于《尚书》,有史传性质。帝王事迹关乎天命或历史规律,因此封禅文是“一代之典章”,应该“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效仿《伊训》《尧典》的内容,辞藻宏伟富丽,合于古道而不深奥,用今天的表达形式而不流于浮浅。刘勰说曹植的《魏德论》假托主客问答方式,冗长而意义不明确,缺乏光彩,这种批评比较客气。曹植赞美曹丕的文治武功,未必出于真心,这一方面是曹丕达不到古圣先王那种“运天枢,毓黎献”“经道纬德”的高度,另一方面是曹植作为文人缺乏良史的骨气。也可能是他与曹丕毕竟是亲人而非敌人,不能像陈琳的檄文那样“壮有骨鲠”“敢矣撄曹公之锋”。不管怎样说,刘勰对于涉及政治的文章有着气势、骨力的要求。
诏策和章表是纯粹的公文,刘勰当然也要求有气势和骨力。前者属于上对下,自然不缺气势。因此刘勰更强调指事明确,如曹操时期的法令,令行禁止,不得违背。当然,上对下的公文,也要注意合理合法,如曹丕下诏给夏侯尚说“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就被蒋济责为亡国之语[2]273。刘勰举此例,是为了说明诏策的关键不在辞藻,而在内容。刘勰赞同曹操所说“为表不必三让”“勿得浮华”,对于曹丕时期的表章追求靡丽则有所不满。他非常推崇曹植的表章,“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结构和语气雍容大度,文辞简练,意旨明了。章表如果过激或过于谦卑,效果自然不佳。即便心态从容,如果没有好的表达,也不能体现这种心态。
通过从文体分类角度对刘勰三曹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应用文、学问文章和以诗体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对照,总结刘勰对文学特性的揭橥[3]。从内容方面看,学问文章以载道明理为主,应用文是在明于事理基础上对道理的运用,作者应该博见多闻,掌握可靠事实或材料,“精研一理”,体现某方面的思想价值或指导实践的作用;诗以抒情言志为主,侧重审美价值,博学明理可以提升其价值。刘勰强调诗“持人情性”和“思无邪”,体现了文学艺术实现思想价值、政教价值的特殊有效性,并不影响其审美价值。刘勰以“事信”衡量屈骚,指出其异乎经典的新变,并未见明显的否定,恰恰是揭示了文学作品的特征。“事信”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或者是合乎生活逻辑,或者是合乎作品自身逻辑,或者是合乎接受心理。
从形式方面看,学问文章和应用文要求文字简明扼要,结构严谨,思路清晰,概念准确,这些要求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是必然要求。《神思》篇中说到神与物游,主要是针对文学创作而言;科学或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物象,主要还是以概念和逻辑分析为基础。《通变》篇对于学问文章来说,是要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日新其业”,是思想内容上的创新;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则主要是指形式创新,因为主体的情感和意欲常常是“怀旧”的,审美心理结构不容易改变,也不一定非要改变。《情采》篇论理和辞的关系,应用文不能“辞巧理拙”“理不胜辞”,文学作品则不一定求“理”,主要考虑情和辞的关系。《夸饰》篇适用于文学作品,对于学问文章和应用文来说不仅多余而且有害。
[1]胡海,秦秋咀.中国美学通史3·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 陈寿撰.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张燕.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体”与“变”[J].晋阳学刊,2013(3):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