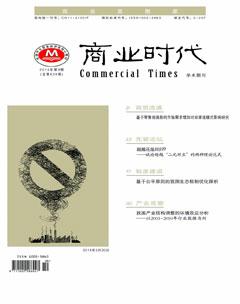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社会资本的重构
李宇征
内容摘要:传统中国,国家政权无力深入乡村,农民以家庭、宗族为合作单位的乡族式社会资本占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手段对传统乡村社会资本进行改造,以期达到农民与国家协同行动、互惠合作的目的。然而,在打破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的同时,政权并没有代之以行之有效的现代社会资本。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 乡村 社会资本 重构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深刻改变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1949-1976),被学界称之为“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始终把农村当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着力点。概览毛泽东时代乡村社会资本的嬗变,分析其利弊得失,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会资本
相比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概念,社会资本的概念兴起较晚,而且争议颇多。简单来讲,社会资本就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群体或政府组织利用这种模式达成一致性行动,增进相互期待和信任的途径以克服其面对的不正当的短期诱惑。其中,网络、规范和信任构成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其中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规范是社会资本的手段,信任则是社会资本的目标。
传统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语出《诗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秦宰相李斯语)。封建王朝更迭频繁,但是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的剥夺却无实质上的变化。乡村的人力、物资仍然是封建统治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基础。作为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权力网络及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乡村。只不过囿于当时物力、财力、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影响,官僚机构只延伸到县一级,为县以下乡村的“自治”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种自治只是形式上的自治,乡村自治的领导者—士绅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其身份的获得和维持严重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承认。士绅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庇护-服从”的关系,自皇帝而始形成的垂直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在基层乡村表现为在各地乡绅领导下互相隔绝的“蜂窝状”结构。对于普通农民来讲,他们既缺乏向外流动的资源,又缺少流动的机会,传统农村是“内向型”的(减少对外联系,追求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和仅以糊口为目的的生活倾向)。“猜疑和内讧及互不信任是内向型农村中社会关系的特点”。“互助合作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互相猜疑,使得合作不能超出按照某些刻板的互惠义务承诺的范围。缺乏相互间广泛的经济依赖与限制个人在村里地位的制裁结合起来,造成不信任和嫉妒。而且,个人间信任的缺乏部分地来自于并且强化了农民的家庭主义倾向。由于家庭是组织生产的纽带,所以它本来这种倾向就很强”([美]米格代尔,1996)。农民的社会网络基本是家庭的延伸,调整农民之间关系的准则是基于血缘关系上的伦理道德法则,因为资源的的稀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即使在家庭、宗族、乡邻内部这种冲突有时仍然非常激烈。但是,因为垂直向上流动机会的稀缺,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农民之间必须采取某种合作机制,来完成单一个体所无法完成的工作,权威集中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父权、夫权和族权手中,群体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属于迪尔凯姆所讲“机械团结”性质。压制导致稳定,但是压制也意味着反抗,农村貌似和谐的秩序之下掩盖着冲突的根源。
对于国家来讲,“国”只不过是“家”的放大和延伸,家庭里的父权延伸到整个国家政权皇帝成为最大的“家长”,皇帝之下各级官员又构成各地民众的“父母官”,层层“家长”对最底层的“草民”进行统治。这种状况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使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对于普通农民来讲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象征,“天高皇帝远”,普通农民眼里只有“家族”而无“国族”概念,只要完粮纳税服役后,“帝力于我何有哉”,而且在完成皇粮国税后,仍能保持“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农民就能心满意足,自认为赶上“太平盛世”、“皇恩浩荡”;另一方面,封建统治下,皇帝乃至各级官僚权力、财富和声望对广大小农具有深深的吸引力,除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动乱时期的造反称王以外,最常用的一种手段是利用家庭、宗族、师生等各种关系,为个人通过非正式渠道谋取私利。在以家庭为本位社会,这种先赋性资源成为决定条件下,个人的流动主要取决于因为出生就天然拥有的血缘关系网络,花费时间、精力去建立社团或者组织,并且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就会变得多余,并且导致“中国社会中的个体首先是天然地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不能选择的网络中。……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不用争取就能天然拥有,他在利用这一网络时无需考虑他的责任,而必须履行他的义务,他更多地会依赖性地滥用关系,而不会考虑家庭之外的另一套社会规范以及利用关系同这套规范是否相符,这是潜规则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翟学伟,2009)。
毛泽东时代对传统乡村社会资本的改造
清末新政以后,国家政权就不断努力向乡村进行渗透。但是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控制并不成功,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既缺乏中央权威的保护,也缺乏强大宗族的支持,孤零零的个体使他们面对强权时更加悲惨。巴林顿·摩尔写到:“中国的乡村,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将之与印度、日本甚至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乡村相比,就会发现前者明显缺乏内在的凝聚力。在中国的乡村中,很少有机会需要众多村民一起通力协作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从而形成团结的习惯,并培养起休戚相关的感情。中国的乡村更像是众多农民家庭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活跃的运转良好的社区”([美]巴林顿·摩尔,2013)。而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政权下乡、宣传下乡等扎实有效的农村工作,“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阻止抵抗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张鸣,2001)。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获得乡村巩固的、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endprint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通过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进程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领导人的首选途径。毛泽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快推进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进程,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一大二公”,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农民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强制纳入国家统一指挥体系,国家吞没了社会。“人民公社正是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影响了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首先是以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生产队集体劳动取代了家庭和家族组织的生产功能,并用正式的政权组织和党的系统深入农村,改变了原来的权威秩序;其次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不断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各种封建迷信和自私落后思想,用集体主义取代农民小家庭发家致富的梦想,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农民的民间信仰”(苗月霞,2008)。
从意识形态出发片面强调“一大二公”,虽然国家貌似建立了强大的制度网络社会资本,但是这种强制性的举动却破坏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农民通过退社、瞒产私分、自由买卖等“生产力暴动”的方式迫使国家的政策做出调整。就如研究农民问题著名学者斯科特所讲“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琐碎新法律等问题上冒险去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美]詹姆斯·斯科特,2007)。这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固定的领导者,没有明确纲领和口号的、但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卑微反抗行动,正如斯科特所比喻的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造成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以致于人民公社被迫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调整,组织网络的规模更加贴近农民传统的互惠合作网络,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这种古老的互惠合作单位重新成为乡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
毛泽东时代重构乡村社会资本的历史启示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现代化建设不可忽视农村社会资本的构建,但是社会资本绝非自上而下单单依靠国家政权能够单方建成的。正如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所讲:“全国和区域性政府机构强烈影响着个人追求长期发展目标的社会资本类型和范围。大规模的政府机构能够通过公民设法解决协作或集体行动问题,或使之变得更为困难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然而,当全国性和区域性政府接管大量公民活动领域的责任时,他们就会排挤进入这些领域的其他尝试。……他们就会迅速地摧毁社会资本的巨大存量”。“像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在实现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它并不是可由外部或者自上而下的过程创造的速成型式”([美]奥斯特罗姆,2003)。
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巅峰,标志着国家向农村的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即使全能型的国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的将任何控制和压榨手段强加给农民,农民采用各种方式和策略表达和捍卫他们的利益。“为了抵制危及其生存的、不得人心的国家政策,村民们首先诉诸固有的价值观和风俗,包括传统伦理(主要是生存权意识),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民间宗教信仰,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且易被利用的。然而,一旦国家在农村建立起行政及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村民们便逐渐转向使用政府允许的合法途径,运用官方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要求,使其行为在国家面前显得‘正当(rightful,亦即合法)”。因此,“1949年之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有力渗透,并没有必然地侵蚀和淘汰革命前的社会关系和行为习惯。……尽管乡村政治运动不断反复,以血缘亲属、邻里和私人友谊为基础的传统群体纽带,加上对个人利益得失的权衡,仍然决定着村中的人际关系,引发群众与干部关系上的憎恨、歧视现象以及庇护和派系之争”(李怀印,2010)。
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在乡村社会资本的转换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变革能够营造社会资本变化的外部情景,但是,制度可能有时是无效的,在社会资本的重构中,存在重要的公共角色的作用,但是谁来充当这个角色,是政府、社区还是公民群体组织,以及这个角色如何发挥作用,是通过国家强制、市场交易还是公民自愿,这些问题仍需大量思考。20世纪80年代去集体化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行,农村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对乡村社会资本的重构带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2.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J].社会,2009(1)
3.[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5.苗月霞.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社会资本分析[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6.[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
7.[美]奥斯特罗姆.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A].曹荣湘译.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C].上海三联书店,2003
8.[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M].法律出版社,201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