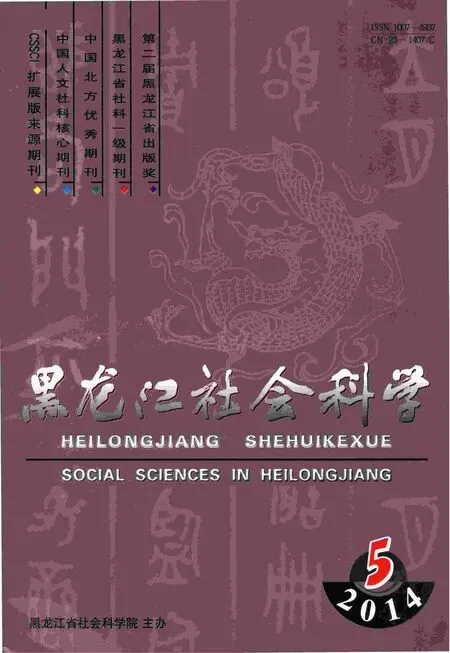日本女作家大庭美奈子的创伤叙事
田鸣
(外交学院外语系,北京100037)
日本现代女作家大庭美奈子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少年时代起便身处战乱,14岁时目睹广岛遭袭原子弹并在两周后被召集赴广岛灾区救援。作家日后在谈及这段经历时曾说:“当时目睹到的是语言无法言说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惨状,它们萦绕了我一生,成为我潜意识里时常浮现的意象”[1]。
那个夏天,我没有了语言。那个夏天的记忆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我开始行走时,苏醒的记忆遏阻了我的脚步,让我变成一具重新思考人类的骨桩[2]。
作家关于广岛原爆的这段记忆在其诸多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被表述,其中以发表于1977年的《浦岛草》最为引人瞩目,被日本评论界视为广岛原爆题材的代表作之一。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战争的反思,尤其是对核爆炸带来的战后后遗症乃至核开发与核利用问题的争论和质疑,都使得大庭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关注点。
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大庭美奈子因丈夫的工作关系,多年旅居美国阿拉斯加东南小镇锡特卡(Sitka)。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越战、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及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相继蓬勃发展,局势动荡不安,美国本土一些质疑现代文明、反主流文化的人以及世界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纷纷涌入阿拉斯加。小镇虽然自然条件严酷,但却有着湖泊、森林、峡湾、鲸鱼、熊、鹿等诱人的原始自然景观,原住民、移民等构成不同的人种、族裔,这片既有着浓郁的美国印第安风情又充满文化多样性的土地,令作家深深眷恋,在此旅居十数年间的生活经历及影响均成为她文学创作的珍贵财富。因此,阿拉斯加小镇被作家视为“第二故乡”[3],这段海外经历及影响自其成名作《三只蟹》起,几乎贯穿于她的整个文学创作。
一、创伤记忆
如前所述,作家少女时代的战祸记忆并亲历广岛遭袭原子弹和救灾经历,以及此后在文化流亡地阿拉斯加的漂泊均给予作家深远的影响。无论从作家本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述、还是从其作品文本里均可感受到,它们带给作家的是对生命的痛彻体悟和文化思考,且已然成为融于作家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自大庭美奈子创作之初起,这两段融于生命的记忆便在其笔下以多元的视角呈现。
纵观大庭文学,一方面,那段源于专制的法西斯暴力的战争创伤记忆,在其小说文本以及各种访谈、对话及随笔中被反复讲述;另一方面,两性关系中的女性人物灵与肉的挣扎,抑或置身异国的女性人物,以及她们被性别、少数族裔等多重身份覆盖下的边缘生存的孤独、漂泊的焦虑和身心的创伤亦是其作品的叙事主题。因此,可以说,在大庭的作品文本中,有关创伤记忆的叙事大致呈现为两类:一是对广岛原爆及战乱的讲述,另一类则关注了人物个体生存中的创伤记忆。
创伤(Trauma)一词源自希腊语,其最早的语义只将身体作为关注对象,即由某种直接的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19世纪末对创伤一词的关注开始从身体转向精神及心理。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的研究及其描述被认为是对当代创伤的理论性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开始聚焦创伤理论的研究,并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4]
目前,创伤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涉及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边缘群体、包括女性、儿童和少数族裔及退伍士兵等的创伤经历。如何再现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的创伤经历,通过他们的记忆修正和颠覆正统历史叙述,并帮助他们走出创伤,成为当代欧美创伤理论研究关注的主要方面[5]132-133。
由于创伤是灾难性事件给受害者带来的长远而深入的伤害和影响,因此创伤研究界便关注受害人除身体之外、在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即精神创伤。并认为:“精神创伤是人在受到伤害后,留给主体的记忆。他试图摆脱这种记忆,却又处于不断记忆和不断摆脱之中,精神创伤成为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6]而对于困扰精神创伤主体的这一心理状态,心理病理学家则指出,当一个人面临一种困扰自己的伤害,或他/她难以承受的思想情感时,由于无法整合太多或太过强烈的刺激,就会选择逃避伤害,转到与伤害无关的思想情感上去。于是,与伤害有关的思想情感就会被撇开,或与正常的意识相脱离,成为“固着的观念”。这些“固着的观念”就是创伤记忆[7]。
而就创伤记忆的特点,创伤理论的研究者指出:“创伤记忆有一些非同寻常的特点,他们不像成年人的普通记忆一样以文字的、线性的叙述被编码”[8]37;“它缺乏语言叙述和语境,通常被以栩栩如生的感觉和形象来编码”[8]38,即创伤记忆往往以视觉或听觉的非语言的形式复现。因此,为了让人们理解创伤,创伤书写便成为将创伤从视觉或听觉形式转化成文本形式的重要转译方式,成为回顾创伤事件和叙述个人创伤经历的主要媒介。鉴于“叙述是讲故事的行为或活动本身,而被表述出来的故事为之叙事”[9],因此,叙事在当代作为表现创伤的方式被广为运用。同时还鉴于“文学的言辞表达仍然是使创伤得以感知、使沉默得以听见的基础”[10],因此,文学作品的叙述功能便将创伤记忆与文学叙事联系在一起。
二、大庭美奈子的创伤叙事
(一)战争创伤的记忆
自少年时代起便身处战乱的作家,14岁时目睹的广岛遭袭原子弹及之后的灾区救援经历,对于一个正处于自我形成期、早熟且敏感的文弱少女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广岛遭袭原爆后触目惊心的一幕幕惨象,那份强烈的、甚至是“凌辱性的残酷体验”,究竟给大庭带来了怎样的打击和心灵的震颤?只要读一读作家的两篇随笔《地狱的配膳》和《亡灵》便可知悉。它们不仅改变了作家的人生,同时也成为萦绕作家一生的创伤记忆。在长篇随笔《亡灵》中,作家翔实地记叙了遭袭原子弹后被死亡的阴霾笼罩下的广岛惨象,及带给她的影响。在该随笔中作家述说道,因为广岛记忆在自己的内心之中过于巨大,常感窒息。那是一道“永不消失的心上疤痕”,所以,我对把它以赤裸的原貌写进作品深感畏惧。而“那些原爆意象则时刻涂抹着、改变着我的作品”。
西方文论对于造成创伤的根源指出:“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渗透了资产阶级家庭、工厂、战场、性/性别、种族/民族等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多层面,是现代文明暴力本质的征兆。它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性重复三大本质特征。”[11]117首先,与战争创伤有关的书写,特别是对于日本近代战祸、亦即作家本人亲身经历的战争创伤记忆的讲述,它们自始至终、直接或间接地贯穿于其早期至晚年的作品文本中。此外,作品不仅叙述日本曾经的战祸创伤记忆,还讲述其他民族也曾遭遇的战争创伤经历。即作家笔下关于战争创伤记忆的叙事呈现出多元的语境。作家最早叙述战争创伤记忆的作品是写于1954年的长诗《秋天》,诗歌中再现了她在广岛目睹到的遭袭原子弹的惨景。在其早期旅美三部曲《彩虹与浮桥》及《跳蚤市场》中,就通过作品人物之口谈及战争的创伤记忆。而在以广岛原爆为题材创作的《浦岛草》中,不仅战争带给多个人物的创伤记忆被表述于作品叙事里,连同灾难景象的一幕幕亦被再现其中。而且这些创伤记忆的书写一直延续到作家为该作品撰写的后记《〈浦岛草〉寄语》里。此外,《亡灵》及《地狱的配膳》则更可视为作家本人对广岛原爆灾区记忆再现的文本。写于80年代的短篇小说《我是鱼吗?》,以14岁少女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和已人到中年的现代人“我”的视角交替,叙写并再现了曾经的战乱中惊恐的一幕幕场景,以及我和家人内心种种绝望的思绪,及其这些创伤记忆带给我的思考。即便是在作家晚年写于病榻之上的《浦安和歌日记》中,战乱及广岛原爆的创伤记忆依然是其叙事主题之一,《八月忌》《江田岛》《八月的记忆》几篇便集中叙写了该主题。
“创伤主体不仅包括施暴者和直接遭受创伤的受害者,而且包括旁观者、救援人员”[11]124。与此同时,“创伤叙述是创伤复原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幸存者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创伤叙述不仅包括幸存者向治疗师或亲人讲述自己创伤经历,也包括书写叙述。”[5]136当年,曾在广岛原爆两周后便被动员前去救灾的大庭作为救援人员,同时亦是一个14岁的少女,无疑她也是遭受创伤者。因此,作为受创主体,大庭同样需要借助叙述记忆,需要通过反复讲述灾难场景,通过见证来抚平心灵的创伤。在旅美三部曲的下篇《跳蚤市场》中,因流产住院的女主人公左喜被医生告知因为原子弹防空演习的需要,病人应进入防空洞。左喜非但没有听从,还怒斥道:
你说什么?原子弹防空演习?!难道你真的以为原子弹的空袭是可以预防的吗?难道你觉得这种演习真的会有什么意义吗?我才不会离开病房呢!躲到哪都是一样的!我可是个活的证人。绝对逃不掉的!你在让我们参与防空演习之前,最好先看看有关原子弹爆炸的视频!
这里显现出的是作为灾难证人的左喜、亦是作家本人对原子弹带给人类的绝望及其见证。
而在其长篇小说《雾之旅》第一部《栃树与朴树》中,则有一段11岁的女主人公“我”对战争的讲述。那年夏天,“我”到京都妙高的表姐阿凤家小住,阿凤的小叔子繁带着他的低年级好友(后来成为我的男友和丈夫的)省三来玩,我和省三在去山上散步的途中,省三告诉“我”,他可能很快也要上战场了。对此“我”却冒出句听上去不大相干的话:“我讨厌看报!”继而“我”又述说道:
其实,在我心里这和战争关系大着呢!因为在学校,老师每天要让我们念报纸,可是报上天天就只有战争的消息,每天要为任课老师读报上登的:又在哪击落了几架敌机、击沉几艘军舰的消息,这让我讨厌上学、讨厌报纸!
自我上小学那年起,日本就一直在打仗。大人们动辄便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可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战争才是常态。而什么是没有战争的状态?什么是和平年代?则只有凭借我从大人讲的故事、凭借我从书本中去想象,那是梦想中的精彩故事。
《雾之旅》被视为作家的自传小说。而女作家的自传体写作通常也被认为:“是女性表现自我以及维护自我认同的最为恰当的形式,也是最为有力的形式”[12]。在这部充满作家主体认同的作品中,通过11岁少女“我”感受战争的视角,将作家本人对专制的法西斯强权意识形态统治的绝望,以及由此造成的创伤记忆讲述出来。
此外,在作家的创伤叙事中,除了上述作品以外,还有大庭与和自己有同样经历的创伤幸存者的共同见证及讲述。作品《蛆与蟹》起笔便写道:“在那个战争结束的夏天的记忆里,八月的阳光和原爆无法抹去”。在该短篇中,作家讲述了“我”旅居阿拉斯加时,在当地结识的一对年长“我”10岁的波兰夫妇并一起彻夜长谈彼此的战争创伤记忆。他们当年曾投身对占领波兰的纳粹抵抗运动,但由于运动失败双双被捕,并被送入德国人的集中营。在他们生命已经奄奄一息时有幸获救,后来两人再次重逢并组建了家庭。
我和他们相识于1959年,我们曾就十几年前彼此经历的广岛和纳粹集中营的记忆彻夜长谈。那残酷的一幕幕应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憎的事件。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彼此沉默着,我们各自整理着凌乱的思绪、时断时续地倾诉着,讲述着……迟疑着……,在心照不宣中交换着彼此的经历。即便再追问又能如何?只能令人绝望不已。
作品大段描述了这对波兰夫妇青年时期如何投身抵抗运动,以及集中营的非人待遇并后来流亡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当他们谈到集中营里枪杀囚徒的沉重话题时,夫人再也无法回忆下去,“她站起身来,走到钢琴前弹奏起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心理学家对于创伤的研究证实:“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亦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某位/些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然后,这一/些听众又能够真实地将这一事件向他人再次讲述”[13]。该作品不仅再现并重述了酿成创伤记忆的那些历史,同时也将幸存者们的创伤心境呈现出来。
1986年11月,应中国作协的邀请,大庭与数位日本作家访华。其间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翌年她以《南京》为题撰文。文中作家一方面谈到目睹史实后的情感变化及震撼,与此同时,更是直接呼吁日本政府应澄清历史真相并做出反省。文中还写道,某些日本人在谈及广岛和奥斯维辛时会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予以评论,但对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等同样的历史耻辱却不敢正视,极力回避[14]。显然,作家的这篇书写已不仅仅是对战争创伤的讲述,更是对日本官方史观的反思和质疑。
作为曾亲历创伤事件的作家,大庭美奈子以其多元视角,通过作家的个人化创伤书写,对于当年的战争暴行造成的创伤事件不但起到了见证作用,且对那段强权统治的历史也予以了有力的揭示。与此同时,还在对那段不仅使周边各国、同时也使本国普通民众基本权利遭侵犯的暴力历史的不断书写和阐释中、颠覆着代表处于统治地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所谓的官方历史观,并予以重新审视和思考。
(二)个体生存的创伤性经历
从前述战乱创伤的叙事可见,身为女性在其个体的生存之外,同时还要承担因专制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统治而造成的民族共同的创伤记忆。女性文学叙事中的创伤记忆,于历史及日常中的女性而言,除了她个人的经历之外,还来自于她“第二性”的性别身份,来自于历史及文化制度加诸女性的心灵桎梏及女性自身的无意识自我囚禁,同时还来自于女性的第二性特征。因此,在每一位女性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历程中,都有着不同的心灵与躯体的创伤性经历。
大庭在其随笔《鱼儿泪》中,曾对自己当年为何选择写作有过详述。即作家本人是于语言的苦闷并生存的绝望中决意写作的,而且作家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坦言道:“欲在置身的环境中确立自己的世界,就是要在不断地含冤饮恨中付出努力。为了能够让别人理解,所以我要自己讲述”[15]。这里,一方面表现出身为女性的大庭想成为自身叙事及历史主体的强烈欲望,还表明在作家的这一追求过程中,“含冤饮恨”的痛楚也伴随始终。而于作家心灵中的这些含冤饮恨的创伤性体验,无疑也被呈现于作品文本的叙事里。
纵观大庭美奈子的小说文本,诉诸作家笔端的女性人物们的个体生存,几乎每一人物都有着创伤性的经历,且这一经历均体现为精神与躯体、即灵与肉的双重创痛。无论是早期旅美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左喜,还是《三只蟹》的主人公由梨,以及作品《栂之梦》的主妇伸枝,其盲目的顺从及付出成为她最终精神崩溃的代价。在作品《蛀船虫》中,性无能、石女等几乎所有人物均有各自的创伤经历,作品尤其关注了性与生殖带给女性的创痛记忆。《旧物博物馆》则讲述了三个命运多舛的女性故事。俄罗斯裔的玛利亚,在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里曾经历两次婚姻,原本指望男人过一辈子的她,最终却孤苦一人漂泊至北美边远的海滨小镇寡居。日本女人阿雅,在日本的凄苦年代里嫁人并生养儿女,然而,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她却被心高气傲的丈夫抛弃。后来,阿雅认识了在基地工作的美国人拉斯,且随之漂泊北美。另一位苏性女士,其生父是日本人,母亲为朝鲜人,而苏本人则是在中国人继父教育下成长的。彼此共同的归属认同困惑及生存之悲哀,将人物们凝聚在一起,她们轮番讲述着各自的创痛记忆。《山姥的微笑》则叙写了女主人公自少女至晚年的忍辱负重直至病逝的一生。在讲述女性成长故事的作家自传体长篇小说《雾之旅》第Ⅰ部《通条花》一章中,主人公“我”在大学毕业时未婚流产的创痛经历,则更成为作家对一段女性困窘、带血含泪的个体生命经验的直接书写。
《浦岛草》不仅讲述了现实中的三个女性各自的生存焦虑,同时还回顾了家族历史中女性的生存及多舛的命运。《鸟啼兮》中,瑞希因幼年的心灵创伤而导致拒绝生育,甚至连作家自《雾之旅》起便开始讲述的“家族恶婆”、阿凤身上交织着的生存无奈与身心的悲苦也被铺叙其中。作家从早期的小说文本起,便在讲述日裔女性人物的同时,也对异域女性生存境遇予以关注。《跳蚤市场》中,美国家庭主妇佩缇的创伤性经历亦被叙写。佩缇在7年内生养了4个孩子,全身心投入家庭,却遭遇丈夫的外遇。她面临着离婚及子女抚养权和财产分割的烦恼。作家的这一视角在《海中摇曳的丝线》中,更是得到了集中体现。该作品关注了“我”在阿拉斯加结识的不同国籍的女性人物和她们各自的创伤性经历。纵观作家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伴随她们生存的不仅有欢笑,同时灵与肉的焦虑和思考也与她们的生存如影随形、相伴始终。许多时候,作家展示出的是她们身、心的苦痛记忆及其悲剧性命运。
倘若从作家的早期旅美三部曲及成名作《三只蟹》起,将其中的几部作品纵向连接起来分析,便可从中看到女性从少女到青春期、从恋爱到结婚、再经历怀孕生子,并在尽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后伴着种种的创痛步入更年期,最终病逝的、一个女人一生的创伤性经历。以下拟集中关注其中几部作品,对交织于女性人物生存中的灵与肉的焦虑进一步予以揭示。
三部曲中的左喜及《三只蟹》中的由梨,无论她们有着如何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无论她们怎样追求并展示她们女性的生命本能,都始终无法摆脱被多重身份覆盖的“他者”地位,及被主导意识形态边缘化的生存处境。这种窘迫的生存处境必然导致精神焦虑,即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以及边缘对中心的生存焦虑。与此同时,还表现为“这种焦虑不只是幻想暴力和强行进入的结果。女性焦虑从根本上是惧怕作为无抑制和无表述的客体的女性躯体”[16]421。因为“作为真实和直接经验的女性本质是弗洛伊德所分析的象征化过程中的盲点。在女性潜意识中共存着两个互不相容、各为异质的部分,也就是表述的部分和保持为‘黑暗陆地’的部分。”[16]421由此可知,女性的生理性焦虑是内在的,表述出来的部分只是少数,而更大的领域还处在黑暗当中。三部曲中的左喜,尽管在表层文本上看生活放纵、与多个异性有染。其实在其与异性间的欲望挣扎中,左喜的内心时常涌出“对与和自己不情投意合的异性丝毫没有交往的兴趣”等诸如此类的思绪。可见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交织着关于灵与肉的焦虑、思考和抗辩。白人讲师鲍曼的强势及其东方主义式的征服欲令她生厌,同样与白人同窗达尼埃尔之间,就因为她没能装出被征服的姿态而使他不快,令其与左喜发生激烈争吵,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令左喜心生不安与恐惧。和拉美留学生奇蔻的交往,一方面其被白人视为异己“他者”的边缘生存让左喜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同时他的放荡不羁亦让左喜醒悟到自己性别他者的身份。日本同乡岳的态度最使她安心和放松。然而,婚后岳的男性主体优越感及其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却与左喜的相左。在婚姻中,她的边缘身份的焦虑非但没有消解,还徒增了孤独与不安。在左喜的内心里,对于被制度给定的“男性天然优越感以及婚姻中他们的特权”及两性关系有着自己的种种抗辩,但这又是不能说出口的。同样,《三只蟹》中的由梨,也是因为有太多不能说出口或被迫保持沉默的思虑而焦灼不安,从而在生理层面出现了身体的不适,且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虽然她也曾与途中邂逅的异性男子交往,但在两人的交际中,她的“沉默”、她的“没有想说的话”仍处处呈现出她的压抑及不快。
在《栂之梦》和《山姥的微笑》中,以家庭主妇且是妻子和母亲角色出现的伸枝们的创伤经历则更为典型。《栂之梦》中的主人公伸枝,为丈夫和孩子全身心地付出着,而换得的却常是丈夫在她贫血及浑身不适时的“强行侵入”,甚而还有令门外孩子们惊恐的伴着她惨叫的家暴。对于常出现在丈夫脖子上的女人唇印,她则只能望而生怨。当她竭尽全力为丈夫争取来了调入更好职位的机会时,得到的却是丈夫的断然拒绝,以及女儿的离家出走。孤绝的自我焦虑终致使她精神失常。《山姥的微笑》中的“女人”遇到了使自己欢喜的男人,于是她出嫁了。而她的代价是一生讨男人的欢心,并顺从男人的各种要求。在一系列“没有道理可讲的不平等条约中”,她默默地为家庭奉献着一切,为丈夫恪尽职守。“女人”偶尔的疏忽或碰到有魅力的异性多说了几句时,便会招致丈夫的奚落。当丈夫生病时,“女人”心中便感不安,于是她又转做了丈夫的护士。“女人”因为有太多的要求要去服从,久而久之心生焦虑,内心孤独,患上了更年期综合征。后又因脑血栓昏迷不醒住进医院。照看病人一周下来,“女人”的丈夫和儿女开始各怀心事。一日在护士和女儿为她擦拭身体时,她的意识偶然清醒,在和女儿交换了最后一个眼神后,“女人”走了。确切地说,这是“女人”使尽浑身解数为她的家人做的最后一个努力——她让堵在喉咙中的唾液流进气管,从而窒息身亡。
综上所述,在作家的笔下,那些交织于女性灵与肉中的焦虑及其思考,那些呈现于文本中的创伤叙述均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即它们都与专制意识形态的统治及男性中心文化紧密关联。这些欲而不得的日常生活深层焦虑的叙事话语,构成了大庭笔下女主人公们的创伤经历和她们悲喜交集的故事。
[1] 年譜(自筆)——大庭みな子[M].东京:講談社,2000:553.
[2] 大庭みな子全集:第10卷[M].东京:講談社,1991:304.
[3] 大庭みな子全集:第24卷[M].东京:講談社,2011:485.
[4] 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Baltimore[M].MD:Johns HopkinsUP,1996:11.
[5] 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6] 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
[7] PIERRE J.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Felix Alcan[M].Paris:Societe,1973.
[8] HERMAN J.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1992.
[9] 马丁华.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6.
[10] HARTMAN G.'IraumaWithin the Limits of Literature[J].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2003,7(3):257-274.
[11] 陶家俊.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J].外国文学,2011,(4).
[12] 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54.
[13] SHAY J.Achilles in Vietnam:Combat Trauma and the Undoing of Character[M].New York:Touchstone,1994:4.
[14] 大庭みな子.南京[J].海燕,1987,(1).
[15] 大庭みな子全集:第3卷[M].东京:講談社,1991:222.
[16]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