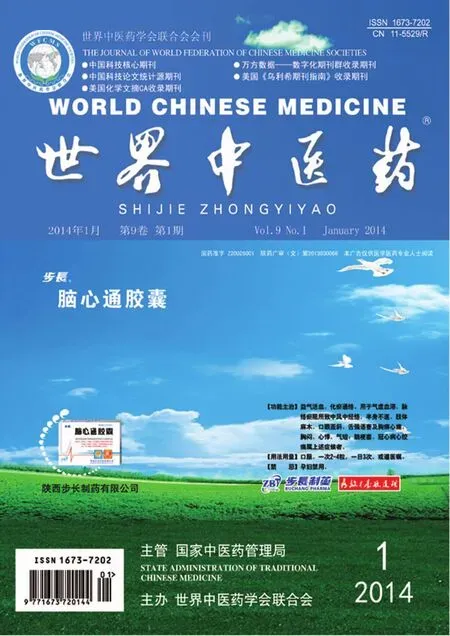蒲辅周方药配伍用量规律初探
王洪蓓 张 林 傅延龄
(1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医院中医科,北京,100044;2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100029;3北京中医药大学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100029)
配伍用量是方药用量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配伍用量比例可影响药效和制约药物毒性,影响药物有效成分的溶出,调整用量配比能够改变药物作用的方向[1-4]。配伍用量规律是蒲辅周方药用量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以《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中成人汤剂为研究对象,通过方中药物间量的关系,从方剂的配伍原则,八法的恰当运用,以及对药物偏性的制约几方面,总结蒲老配伍用量规律,现分述如下。
1 君臣佐使,各施其量
这是配伍用量的基本原则。蒲老更喜用“主辅佐使”,主药、辅药用量大,药味多,佐药、使药药味少、用量小。如产后血崩不止案(《蒲辅周医案-妇科治验》):一27岁产妇,产后血崩不止已50余天,症见面色苍白、目无神采、语言低缓、唇舌皆无血色、面目手足浮肿、肢体麻木不仁、肌肤甲错、小便失禁,舌淡苔白,六脉微细。此由产后流血过多,气血两虚,又兼冲任损伤,八脉无力统驭,气不能帅血,血不足以固气,已成危候。幸而患者尚能进食,胃气尚存,尤有运药之能,急以固气止血为务。以黄芪(一两)、党参(五钱)、白术(三钱)益气、强心、健脾,为主药;鹿角霜(一两)通督脉之气、阿胶(三钱)养肝肾之阴,杜仲(四钱)、续断(二钱)续络脉之绝,并强腰膂,为辅药;三七(三分)、蒲黄炭(三钱)涩血之源,以之为佐;恐止涩过甚,兼以香附(一钱)舒气之郁,以之为使。从以上药味数、用药量可见,主药、辅药(可认为即君药、臣药,在此为复君、复臣)药味多,用量重,而佐药、使药药味少,药量轻。突出该方建中气、固冲任为主的治则。一般认为君药是针对主病、主症、主因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药味少,用量大,但我们可以依据蒲老的用法把君药理解为君药组(复君),君药组中可以有君中之君、主中之主,如本案主药黄芪、党参、白术三味主药,黄芪、党参可认为是君中之君,主中之主,尤其黄芪,可以认为是三者之中最主要的君药。
2 八法应用,蒲老特色
蒲老强调以法治病,创造性地提出“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而八法的临床应用,是通过药物间配伍用量实现的。这是最具蒲老特色的配伍用量。尤其体现在汗法、温法、清法、补法的应用中。
2.1 汗法 “汗而勿伤”依配伍用量实现。汗法,是外感病初期有表证必用之法。汗之不及固无功,汗之太过亦伤表。大汗必伤阳,过汗亦耗液。汗而有伤易致变症蜂起。蒲老认为汗法辨证选方要适宜,方剂讲究配伍。关于配伍用量,蒲老认为麻黄汤为发汗解表之峻剂,而方中之甘草和内攘外,若使用恰当,亦可汗而勿伤。蒲老曾谈到一老年女患者患伤寒太阳表实证,曾用麻黄汤不解,而问于蒲老:“是否份量太轻,亦或未如您老之喜用葱白耶?”蒲老曰:“葱白固发表通阳之良药,但症结不在此。你方中用甘草几何?”答曰:“二钱”。余曰:“得之矣,如何得汗?麻黄甘草相去无几,必不得汗。”乃减甘草量,麻黄二钱,杏仁二钱,桂枝二钱,甘草五分,一剂即得微汗而愈。所以在麻黄汤应用时,麻黄与甘草的用量配伍恰当(麻黄要大于甘草用量,此案二者用量比例为4:1),才能起到既表邪得解又不伤正气的效果。
辨寒热、兼夹。外感风寒一般情况会逐渐化热倾向,但若表证仍在,即使已有化热情况出现,蒲老还是以解表为主,少佐清热之品,如《蒲辅周医疗经验》中风邪郁闭案,患者虽发热数日,咽痛,苔黄腻,但仍有恶风寒、头痛身痛、右脉浮数之表邪郁闭之象,故蒲老以杏苏散为主,只稍用黄芩3 g清里,在众多解表药中,可谓清热药的药味之少、药量之轻。
外感兼夹之证,若外邪未尽,纵有兼夹,仍宜疏解为主。如《蒲辅周医疗经验》感冒夹湿案,患者已感冒两周,虽有大便干燥、苔白黄腻之湿滞之象,初诊只以杏苏散3剂疏解立法,二诊虽热退咳嗽止,但鼻塞未除,外邪未尽,仍以疏解为主,只加用炒神曲6 g兼理肠胃,待三诊外邪已解时,才专主和脾消滞、清利湿热。
清热利湿勿忘阴液:在湿热为患的病证中,蒲老在大队清热利湿药中,往往少佐一味养阴药。如自汗一案、湿热一案、湿热二案(均出自《蒲辅周医案》)。自汗一案,患者本属阴虚肝热,其标则为暑湿遏郁,致湿遏郁而化热,湿聚热郁,三焦失调。治疗以祛暑利湿为主,用香薷、豆卷、豆豉、桑叶、菊花、滑石、茵陈等祛暑利湿、表里两解之药,兼顾肝阴,用一味石斛三钱,因蒲老认为石斛甘平,养阴而不滞邪,外感热病津伤者,尤多选用。他如湿热一、湿热二案,均为初诊即用石斛,从脉证上似无伤阴的表象,尤其舌象,三者舌象分别为:“舌质黯,苔厚秽腻”“舌质淡,苔薄白滑罩灰”“舌质红,苔微黄白腻”,可以说是无养阴的凭证。但蒲老在此少佐一味养阴药石斛,这一方面是蒲老治疗热病(外感热病、湿热病)重阴津的思想的体现,亦是蒲老“病因为本,症状为标,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辨证求本思想的体现,因热耗、渗利容易继发阴伤,一味养阴药即可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2.2 温法 温而勿燥。蒲老认为温法有温散,温热,温补之分。既有人参、黄芪、白术、甘草平和之温;也有附子、干姜、肉桂燥热之温。温法要掌握尺度:药既要对症,用也必须适中,药过病所,温热药的刚燥之性就难免有伤阴之弊。温药要掌握配伍。真寒假热,阴盛格阳,要用白通汤加童便、猪胆汁反佐温之。《伤寒论》“附子汤”中配用白芍就起温而不燥的作用;急救回阳的“四逆汤”有甘草,甘以缓之;《金匮要略》肾气丸是在水中补火,皆取温而不燥之意,故一般不能用纯温热之药拼凑起来去治病。(详见“辨药配伍用量”部分)
2.3 清法 寒而勿凝。清法是外感热病常用之法。蒲老认为,凡用清法,就须考虑脾胃,必须凉而勿伤,寒而勿凝。体质弱者,宁可再剂,不可重剂,避免热证未已,寒证即起之戒。临床若遇到狂躁脉实,阳盛拒阴,凉药入口即吐,则在适用之凉药中,佐以少许生姜汁为引,或用姜汁炒黄连,反佐以利药能入胃。热证用凉药,少佐热药一不伤胃,又能使寒药不凝滞,起到运药的作用。蒲老认为夏邦佐治白喉热证,以黄连解毒汤加僵蚕、附子是一苗头,“用附子者,用寒勿远热,驾诸药而不凝滞,反佐而能捣其巢,攻坚破结”。
2.4 补法 “补而不滞”依配伍用量实现。峻补、缓补涉及补药的用量多少。而蒲老认为补法的最高境界是达到“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即补而不滞。如补中益气汤中甘温的黄芪少佐陈皮以流通气机,防止黄芪致气壅的副作用,如眩晕一案,证属中虚脾弱夹痰,蒲老用补中益气汤加味,炙黄芪用四钱、陈皮用一钱五分,胸痹(心绞痛)案病情稳定后,以人参养荣汤以资巩固,其中黄芪用二钱、陈皮用七分。六味地黄汤中大量熟地配以适量的泽泻、茯苓,到达补而不腻、补中有泻的效果;而像补药、泻药用量相当的方剂又可以为补消兼施法中之法。
多项虚损,权衡孰重孰轻以施量。临床见到阴阳两虚、气阴两虚之时,又当权衡孰重孰轻。如《蒲辅周医案》眩晕二(高血压)案[1]患者4年来血压190~140/120~70 mmHg之间,证见头晕心悸,心烦懊憹。先生据脉沉迟,舌质不红,体胖肢胀,乏力溲频,诊为阳虚湿盛,即予附子汤加龙骨、牡蛎、杜仲、枸杞子、桑寄生、狗脊。初诊附子用4.5 g,5剂后二诊腰已不痛,头晕亦减,脉由沉迟转为沉细迟,蒲老辨为阳虚湿盛,阴亦不足,加熟地黄6 g益阴,而附子用量加大到18 g,又5剂三诊头晕又减,脉转弦缓,病势已减,故附子又减为4.5 g。15剂诸症尽除,血压正常。此案二诊时,原方似已见效,但此时蒲老结合脉证,尤其是脉象,断为不仅阳虚之象没有明显改善(仍为沉迟),而且出现了阴分不足之征象(沉迟兼细),此时蒲老虽立法阴阳兼顾,但仍以温阳为主,附子从4.5 g加至18 g,少加熟地黄6 g顾及阴分不足,5剂药后头晕及余症俱见好转,血压已降至正常(118/78 mmHg),尤其脉象由沉细迟转为弦缓,蒲老认为此时病势已减,仍以温阳益阴为法,但附子又减回4.5 g,熟地剂量不变,并增加滋肾润肺的枸杞子6 g,温阳益阴并重。从此案温阳益阴药的前后配伍用量变化看出,蒲老是通过权衡阳虚阴虚的孰重孰轻来确定两类药物的用量多少。当然这里也有考虑附子有一定毒性不宜大量久用的成分。又如《蒲辅周医疗经验》气液不足(低烧)案,患者低热两年余,既见自汗,头晕,身困,脉迟,舌淡的阳气不足之象,又有手足心热等阴液不足的表现,蒲老甘温益气与养阴同用,但以甘麦大枣汤加黄芪甘温益气为主,药味数及药量均重于养阴之品,突出了甘温除热法的治疗主线,同时而又顾及了阴液的不足。
另外,以回阳固阴立法的医案中,蒲老以固阴为主,固阴药药味多、药量重,而回阳(引火归原)药药味少、药量轻。如“热病转寒中(乙脑)”案一乙脑患者(29岁青年男性),因用寒凉之剂过甚,已由热中变为寒中,热邪被迫,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泻,药后邪热顿去而大虚之候尽露,见筋惕肉瞤,肢厥汗出,脉微欲绝,恐将阳脱,急以生脉加附、龙、牡回阳固阴,其中益气固阴的台党参、麦冬、五味子用量分别为一两、五钱、二钱,固脱的生龙骨、生牡蛎分别用八钱、六钱,而引火归原的附子用量2钱(6 g),剂量不大,尤其在大队益阴敛阴潜阳药中,并采用浓煎徐服不拘时,1剂而各症渐减。继进三才汤佐枣仁、石斛、阿胶养阴益胃,未及数剂而瘥。此案患者邪热去而现阳脱之象,此乃前期热邪耗阴,阴不敛阳,故益阴敛阴潜阳药为主,药味多,总用量超过3两,回阳之附子仅用2钱。又如“类中风”案,蒲老辨为五志过劳致肝肾真阴虚,真阳浮越于上,肝风将动。先生予育阴潜阳,佐附子引火归元、人参益气,回阳的附子用量每剂3钱(9 g),虽然3钱的用量已大于蒲老附子用量的平均值,但方中以育阴潜镇药为主,生龙骨、生牡蛎(打)各六钱、煅石决明八钱、灵磁石四钱、生玳瑁(打)三钱、生龟甲(打)六钱,共计33钱,从药量比例上看附子用量很小。10剂汤剂,眩晕基本消失。
在随证调量的过程中,药物间量的配伍关系也相应发生着动态变化。如阴虚阳亢的病证,初起平复亢阳,以重镇药为主,药味多,用量大,随着阳亢症状的好转,重镇药减少药味,减轻药量,益阴药则要逐渐增加用量。如类中风案。阳虚阴亦不足的病证,随着阳虚症状的缓解,补阳为主逐渐转向益阴为主,相应的补阳药的药量、药味减少,益阴药的药量、药味增加。又如眩晕二(高血压)案;湿热郁遏的病证,初起清热利湿药为主,随着热减,要逐渐增加养阴药药味、用量。
3 辨药配伍用量—制约药物偏性
药物在方剂中行使作用,但一些药物因其偏性或与病性(证之寒热)不符、或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需要通过恰当的配伍用量制约这种偏性。
黄芪:蒲老认为黄芪甘温,为补气要药。然其又有易致气壅的副作用,《本草经疏》中就有气实者勿用,胸膈气闭闷、肠胃有积滞者勿用,阳盛阴虚者忌之等说明。蒲老通过配伍用量,使黄芪补气而不致气壅,益气而不致伤津(阴),取药之用而弃其弊端。如蒲老认为补中益气汤补中有通,黄芪一钱,陈皮二、三分,以补为主,补药量重,通药量轻。如眩晕(美尼尔氏综合征)案(《蒲辅周医案-内科治验》[1]):属中虚脾弱夹痰,兼心气不足之证,以益中气、调脾胃为治,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味,炙黄芪用四钱,陈皮仅用一钱五分。又如气液两伤(肝炎后发热)案(蒲辅周医疗经验-内科治验):一肝炎后发热的男患者,发热已半月余,汗出如洗,不烦不渴,身倦语微,恶风寒,身疼痛,口不知味,胸胁不满。舌质艳红有裂纹,脉弦大按之无力。属热病汗出过多,卫气不固,气液两伤,治宜固卫养阴,蒲老用甘温复酸甘法,因阴伤较甚,故甘温偏燥的黄芪仅用6 g,并有玉竹9 g以顾阴津。用较小量的甘温补气的黄芪与较大量的甘寒养阴的玉竹配合使用,药后汗出、身疼大减,体温遂降,食纳知味。蒲老辨证施量而又顾虑周全,尽药之用而又制其偏弊,故病去而不伤正(阴)。
桂枝:蒲老认为桂性味辛温,桂枝走营血,舌红慎用。蒲老是通过桂枝与白芍的配伍用量来取其用、弃其弊。桂枝与白芍配伍使用在蒲老医案中见于桂枝汤,黄芪桂枝汤,桂枝汤合真武汤等,凡蒲老以调和营卫为法应用桂枝汤,即辨证为营卫失和,见于慢性心衰、腹泻、阳虚感冒、肝炎后发热、寒湿痹证两案、风湿病麻木、经行抽搐、产后受风、产后风寒湿痹证、产后恶露不尽、产后血崩不止、月经不调、痛经等病证,桂枝用量均小于等于白芍,且多为小于。如阳虚感冒案(《蒲辅周医疗经验-内科治验》)花甲某男,素来体弱,脾胃两虚,卫外不固,因劳逸失当,中气受损,复受风邪而感冒。蒲老以黄芪建中汤合新加汤,甘温建中,调和营卫,其中桂枝1钱半(4.5 g),白芍2钱(6 g)。又如“心悸(风湿性心脏病)案(《蒲辅周医案-内科治验》)患者并慢性心衰,下肢肿胀,胃气弱,蒲老以调和营卫温阳利水为法,桂枝汤合真武汤加味,其中桂枝八分,白芍一钱。但在产后风寒湿痹案(《蒲辅周医案-内科治验》)中,患者产后3月淋雨,虽值夏季,然腰部以下如瘫痪状,两腿疼痛不能移动,只能仰卧,不能翻身。蒲老辨为产后气血虚受风寒,与内湿搏结合而为痹。治以温经散寒、益气固表、调和营卫,以黄芪桂枝汤合术附汤加减为治。其中温经散寒用桂枝9 g,却不用白芍,因白芍酸寒恐妨碍附子桂枝温经散寒之力。3剂症减续以调和气血,并祛风湿,黄芪四物汤加桂枝、防风等祛风之品,桂枝既与白芍以和营卫,又入血分偕祛风之剂以温经祛风,桂枝芍药用量相等均为三钱,因方中尚有生地黄三钱,故不虑桂枝辛温动血耗血。蒲老虑桂枝辛温动血,制以白芍,但用量既不执着于《伤寒论》桂枝汤桂枝与白芍之比1∶1,亦不固定于《金匮要略》建中汤桂枝白芍之比1∶2,而是灵活运用,和营卫时用桂枝汤,一般情况下白芍用量略大于桂枝,但如病情需要,又可弃白芍而独用桂枝,全凭辨证用药、用量。
附子:蒲老认为附子辛温有毒,为临床温阳有效药物。蒲老强调附子使用要掌握配伍。认为《伤寒论》“附子汤”中配用白芍就起温而不燥的作用;急救回阳的“四逆汤”有甘草,甘以缓之;《金匮要略》肾气丸是在水中补火,皆取温而不燥之意。使附子温阳而不燥,助阳而不使阳亢,需配伍用量实现。如便血案(《蒲辅周医案-内科治验》):一大量便血58岁女性患者,证属中焦虚寒,脾阳失运,气不摄血因而便血之重证,服用黄土汤加味温养脾肾,其中用黑附子三钱温阳而“复健行之气,”附子用量为蒲老附子用量的较大剂量,又恐附子辛温动血,故佐黄芩二钱(6 g)苦寒监制,且又有熟地一两、阿胶五钱又制附子之燥。5剂后便血已很少。此案蒲老乃用仲景黄土汤加味,黄土汤原方重用黄土,余药分量均等,然蒲老根据病情,黄芩用量小于附子用量,使药不过热,但又与全方温养的治则一致,而与治疗方向一致的熟地、阿胶本身就可以制约附子燥烈之性。蒲老通过灵活施量,充分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而摒弃其弊端。
川芎及四物汤:四物汤,为“治一切血病通用之方”,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九·治妇人诸疾》,原方四药(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用量相等,蒲老则认为川芎量宜小,大约为当归之半,地黄为当归的二倍。这是源于蒲老对药物的深入了解,蒲老认为川芎“辛温,不宜重用久服。若使它药佐之,中病即止可也。”四物汤为养血和血之剂,当归与川芎配伍养血行血,但川芎辛温有动血之嫌,故药量宜小。当归与熟地黄配伍养血补血,而熟地黄质地重,故须多用才能起作用。如皮肤湿疹一案(《蒲辅周医案》)一78岁老妪,四肢湿疹,乃由脾湿化热,兼血燥生风,蒲老以养血清热,祛风除湿为法,其中归尾(一钱五分)、赤芍(二钱)、干生地黄(三钱)、川芎(一钱五分)、牡丹皮(二钱)、何首乌(三钱)、胡麻仁(五钱)、红花(一钱)养血活血,润燥清热,符合蒲老认为川芎量宜小,地黄为当归的二倍。该方突出了养阴凉血活血的作用,在四物汤的基础上,首先归尾易当归,赤芍易白芍,干生地黄易熟地黄,增加何首乌、胡麻仁养血润燥之品,突出了四物汤“养”“润”的一面,而牡丹皮和其后加用的丹参,是增加生地黄凉血活血的作用,因四物中归、芎性温,于血燥生风病性不利,故用生地黄、丹参一方面凉血活血,一方面又可佐制归芎之温燥。日1剂,共20剂后,疹渐消,痒亦大减。蒲老通过药物的选择与药量的变化,一方面制约了药物偏性,一方面结合病情突出了某一方面的治疗作用,四物汤的作用有了微妙的变化,切合病情,疗效明显。
[1]张广平,解素花,朱晓光,等.附子甘草配伍减毒增效/存效实验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2,19(6):31-34.
[2]涂瑶生,刘发锦,孙冬梅,等.黄连、吴茱萸配伍药对的HPLC指纹图谱研究[J].中成药,2011,33(1):5-9.
[3]王术玲,姚玉铿,曾建波.黄连-厚朴配伍比例对和厚朴酚、厚朴酚溶出的影响[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2):18-20.
[4]谢晚晴,连凤梅,姬航宇,等.中药量效关系研究进展[J].中医杂志,2011,52(19):1696-1699.
[5]中国中医研究院主编.高辉远等整理.蒲辅周医案(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第一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6]中国中医研究院主编.高辉远等整理.蒲辅周医疗经验(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第一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