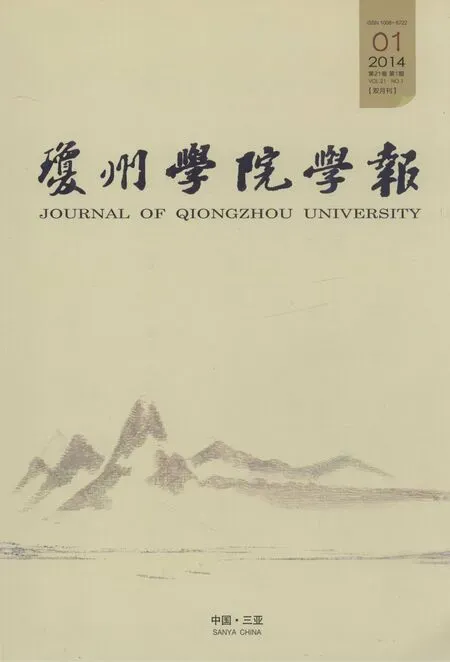司空图《诗品·悲慨》文本意义的二重阐释
朱 桦,匡梅普
(1.南岛视界杂志社 编辑部,海南 海口5701050;2.监利县第一中学,湖北 监利433300)
一
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837 -908)《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以诗论诗,探讨总结诗歌艺术风格规律,成就卓著,享誉古今中外,是旷世难得一遇的杰作。“悲慨”是其中第十九品,行世的解研文本,或拘于“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训诂功能,而缺失诗歌风格论意义的理论阐释。或探讨其诗歌理论内涵,往往因对文本基础性的理解、沟通乏力,致使理论阐释失却根基而流于飘忽,谬误甚多。笔者试图站在语言文学和诗歌理论的双重层面上,诠译文本,清除遮蔽,阐释它作为艺术作品和风格理论的二维思想主旨,力求较为全面、准确地拶揭“悲慨”诗的内涵意义。
晚唐社会,朝纲坏崩,政权旁落,皇帝像走马灯似地更换,社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奸臣当道、藩镇逞兵、忠良毁弃、生民涂炭,带给人们无穷的心灵重创。种种社会情形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罗根泽指出:“同时又以一方面社会丧乱,一部分的文人流落于江湖,或慷慨愤世,或优游肥遁;一方面都市发达,一部分的文人苟安于都市,或献诗宫廷,或声色自娱”[1]466。而由类似罗根泽所谓“慷慨愤世”诗人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情感主题,大都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生前途的悲观失望、哀伤叹息,充满不尽的苦闷与彷徨、忧虑与愤慨、凄迷与忧伤的悲慨色彩。而盛唐人那种豪爽、雄壮、热情、浪漫的精神风貌、广博胸襟、恢宏理想已荡然无存。如刘长卿、李嘉佑、韦应物、张继等大量诗人,面对残酷现实、苦难生民和烟梦人生,吟唱的都是些沧桑之感与沦落之悲,以及对世事无定、人生无常、现实无奈的怅然太息。大历诗人和韩孟派诗人更甚。孟郊诗中就处处充溢着怨、愁、忧、哀、苦、恨等之类伤感色彩浓重的字眼,悲愁咽呜之气不绝于缕。贾岛、李贺诗更不待言,即令著称当时的边塞诗人李益,其诗也同样浸透着幽怨凄凉、悲哀感伤之情。如《上汝州郡楼》诗云:“黄昏鼓角似边洲,三十年前上此楼。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社会动荡,时局剧变,反映到晚唐文学艺术作品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诗风从高亢昂扬向低迷消沉转变。如果说司空图《诗品》的前诸品,如“雄浑”、“豪放”、“劲健”等中,意在总结和揭示诗坛代表“盛唐气象”,即那些具有激越慷慨、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雄健豪宕、浑博宏深的思想情感境界,体现昂扬奋发、壮大蹈厉的时代风格。那么“悲慨”一品,则是司空图纵观诗歌艺术的流变,针对当时诗坛普遍苦闷徘徊、哀怨惆怅、凄迷感伤情怀风格特征,秉承“诗言志”的诗歌传统,站在风格理论建设高度,运用丰富想象力和卓越表现力,创作的一首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为主的优秀抒情诗,同时又是集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高度统一的优异之作,以此探讨并揭示“悲慨”诗风产生的生态环境、主客成因、表现主题和艺术特征。
二
司空图年青时就胸怀救时济世大志,积极进取,为文之外,孜孜以“探治乱之本”,冀成“万一之效”。
但因生逢衰乱之世,纲纪坏漏,朋党兴风作浪,危害朝政;藩镇逞兵,恣意作乱,加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仕途险象环生等因素,致使他一直救时无望,理想不竟,晚年在极度矛盾复杂的思想情感状态中,不得已隐忍故居的中条山王官谷。归隐后,他目睹家园被毁,饱尝贫病交加颠沛流离之苦,仍难舍国家倾危、生灵涂炭之忧。身为“当朝文学英特之士”和“忠臣节士”,内忧外患交炽,般般人生况味与复杂矛盾的思想情感激荡,一时义愤填膺,不能自持,唱出了这首壮怀激越、苍凉沉雄的慷慨悲歌。全诗共分三层解读。即首四句为第一层,中四句为第二层,末四句为第三层。
第一层,通过描写自然景象给诗人思想精神带来的影响,揭示“悲慨”诗风产生的外部环境和主客原因。
“大风卷水”,大风:古指西风。《诗·大雅·桑柔》:“大风有隧,有空大谷。”郑玄笺:“西风之谓大风。”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或指鸟名,古代传说中有恶鸟名大风。《淮南子·本经训》:“猴瑜、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从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考察之,“大风”作恶鸟名解,喻指结党弄权、摧残忠良、祸国殃民的朋党奸臣等凶猛的邪恶势力,但与“卷水”意境不合,故不取;若从自然现象出发联系下文考察,则本品中的“大风”应为狂风,俗称“龙卷风”。因为只有狂风,才能把水卷上天空,摧毁大树林木,也可喻当时的邪恶势力。故取其寓意将“大风”解作狂风,比较贴切。卷水,乃狂飙肆虐之状;“林木为摧”,是狂风肆虐的危害结果。狂飙卷水趁势而来,拔木折干。表面看似描写自然现象,实则影射唐末邪恶势力,肆意戕害国家栋梁,大批忠臣良相遭毁弃的现实。预示乱臣贼子肆虐下的国家政权大厦摇摇欲坠、行将坍塌的悲惨命运到来。广而言之,“大风卷水”也可喻指社整个会局势急剧动荡不安;“林木为摧”喻指生灵涂炭,黎民百姓生活如水火的情形。这既为下文诗人抒发思想、精神、心灵的苦闷不堪提供了依据,又揭示了悲慨诗风产生的外在的、客观的原因。
“意苦欲死,招憩不来。”意苦:心情痛苦。《全唐诗》作“意苦”。名词“意”是主语,形容词“苦”是谓语。“欲死”即“想死”,是补语。从语法上分析,是通顺的。《全唐诗》作“若死”,从生命实体着笔,不如作“欲死”从精神上形容为胜。意谓诗人思想精神苦闷到了极点,欲以一死方得解脱;期望招请友人来谈谈心,以纾解思想、精神和心理上的苦闷,可他却迟迟不来。根据诗人当时所处环境来看,暗示政治时局和社会形势非常严峻残酷,稍有不慎,即遭杀身之祸。对于诗人——这位“两朝美官”,曾被朝野“称奇”的高节旧臣,尽管已经归隐山林,朝中那些奸臣乱党仍不放心,时刻对其一举一动,予以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必欲寻找种种借口和理由除尽而后安。所以,时局险恶,或是因作者本人处境十分艰危,令友人不敢贸然前来;或是友人也深陷险境而不能前来。再不就是败局已成定数,无力回天,即是来了也于时无补,何必来谈?
同时也表现诗人因“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而产生的极度精神苦闷,这种精神状态是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对诗人影响作用的结果,揭示“悲慨”诗风的主观成因。因为“风格总是意味着通过特有标志在外部表现中显示自身内在的特性。[2]17故诗人“意苦欲死,招憩不来”——这种活着比死更难受,不如一死了之的情状,内在反映诗人对奸党乱臣那些邪恶势力兴风作浪,危害朝廷、摧残忠良行径的深恶痛绝,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重忧虑,对黎民百姓悲惨生活深切同情等思想情感。这样便与表象“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构成了一个有机因果链,使主体情思与客观表象融为一体。作者以托物寄情方式,形象生动地揭示出悲慨诗风形成的客观环境及其主体因素,与下文描写的“萧萧落叶,漏雨苍苔”形成首尾呼应,是作者“景外之景”、“韵外之致”的妙化,具有超越形象本身的含义,字字浸透着诗人真挚、灼热而悲凉的思想感情,是诗景与诗情的有机融合。
第二层,诗人采用迹近白描的艺术手法,描写艰危时局下的社会思想心理变化,揭示悲慨诗风的内在成因。
“百岁如流”,人一生不过百来岁光阴,就像流水一样转瞬即逝。此为感叹人生之短暂。“富贵冷灰”。“富贵”,旧时一般指当官发财的人生理想。根据司空图一生经历和思想文化修养状况等综合因素考察,此处解作建功立业比较符合其士子文人的身份、理想、情感和道德追求。意谓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像熄灭了的清冷灰烬,是理想不竟壮志未酬的感伤。“大道日往”,道,本义是道路。《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用于抽象意义,表示完成某一事件、行动,或达到某一目的途径方法。《庄子·达生》:“请问蹈水有道乎?”再引申为由规律或道理。《庄子·养生》:“臣之所好者,道也。”由规律道理再引申出两个意义:一是指思想、理论、学说。《论语·里仁》:“吾道以一贯之。”二是指美好政治理论思想纲领、方针、政策、路线、措施及其政治局面。《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大道,本品指最好的或优良的治国理论及其方略。《礼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往:下,滑坡,滑落,亡。意谓原本美好政治道德一天天坏崩丧失,“若为雄才”,即使是雄才大略的人又能怎么样呢?结合上文分析,这四句可以说由“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招憩不来,意苦若死”,给诗人带来的心理情绪反应,二者是因果关系。独立地看,前两句所表现出的生命感伤和理想冷漠的思想心理状态,实际上是后两句描写的“大道日往,若为雄才”的现状所致,前为果后为因,因果倒置。意谓国家病入膏肓、时局无可救药,雄才回天无力,暗示亡国之日即将来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性命不保了,个人生命岂能久长?政治大厦坍塌了,个人建功理想何以寄托?
不惟本诗作者如此。中晚唐士子文人面对政治的黑暗、社会的险恶、世风的谬戾,普遍都对社会人生产生了一种悲观、失望的心理情绪,而这种心理特征反映在众多诗歌作品中,大都陷于个人狭窄情感天地自怨自艾,所以诗格内敛、境界不高。司空图深刻洞悉并抓住了这一社会普遍心理及典型思想情感特征,由生命短暂之叹,进而理想不竟之慨,乃至与整个国家前途命运交织一起的深重之忧,拓而广之,拔而高之,形成了壮志难酬、大情难伸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效果的诗境。因而与其他诗人同类题材作品相比,就显得格局开阔,境界高大。
第三层,通过典型人物形象和典型环境生动细致的描写刻画,表现诗人壮怀激越而又凄苦、悲凉、矛盾的心理情感状态,从而最终完成悲慨诗风意境的铸造,揭示其美感特征。
“壮士拂剑,浩然弥哀。”描写壮士的表情(愤怒)和行为(拔剑),反映内在心理情绪的矛盾状态。一方面看,壮士愤怒地拔出宝剑,分明是一副义愤填膺,壮怀激越,甚至不惜生命也要铲除邪恶,扶大厦之将倾,解时势于艰危、救黎民于水火的形象。另一方面看,作者并不直接道出个中原因,而是以省减、跳跃之笔,直契壮士更加浩茫悲哀的心理状态。折射出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巨大反差,暗示时势已经到了无可救药地步,国家大厦坏漏到了无法修补的程度。壮士救世无望,大志难酬,所以才会有“浩然弥哀”的悲叹发出。
“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描写客观景物。其中“萧萧落叶”喻指国体涣散,贤良纷纷凋零陨落;“漏雨苍苔”:“漏雨”喻指国家大厦坏漏不堪,“苍苔”喻黎民百姓,映射国家衰败百姓生活凄凉惨景。回应壮士“浩然弥哀”,揭示其悲哀根本原因,为壮士心理情绪矛盾变化提供客观环境支持,并与前文“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共同构建全诗意境的圆环。而壮士情怀通过寒风萧萧,落叶纷纷;雨穿破屋,滴落苍苔这些景象描写的渲染烘托,便使得这首时代挽歌,更增添了令人悲之不已、哀之不绝的艺术震撼力效果。
面对行将灭亡的晚唐社会,诗人悲哀凄恻。但在心灵深处,尽管十分渺茫却仍还是希望能有雄才横空出世,整饬纲纪,扶大厦之将倾;有壮士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浪拯救斯民于水火。然而,即便是诗人心中的雄才、壮士横空出世,但大道沦丧,已然回天无力。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徒有一腔壮怀碧血,眼睁睁地等待末日来临。诗人内心世界与社会现实矛盾的巨大反差之下,产生出英雄无用武之地,丈夫有志不能伸的哀叹,何其动人!如同鲍照《拟行路难》描写的那样:“对案不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也只能浩叹壮志难酬。斯境之下的壮士,其实就是诗人的化身,其苍凉、悲愤、哀怨之情,着实令人动颜作色、回肠荡气。
三
司空图在构建“悲慨”诗风的全部过程中,总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和处理好主客关系,使个人的主观愿望、情思、审美意趣等的表现与社会的、自然的客观景象的描写达到高度和谐统一。因为这首诗兼具艺术作品和品评诗歌风格的双重属性,故其艺术特色也应围绕着两方面来分析。
(一)艺术风格特色
全诗思想情感内涵,既具有杜甫爱国主义诗歌题材,所表现出深沉、雄厚、郁结的基调,又兼有李白、高适浪漫诗富于激情、想象、自我色彩等。从而构成了全诗慷慨激热、沉郁悲壮、苍凉沉雄的风格特征,蓄积着震耳发聩、回肠荡气、催人泪下的强大艺术感染力。
第一、想象丰富奇特。善于再现自然景象、政治社会和时局形势,藉此营造诗情产生的客观环境。如“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本是自然奇特现象,运用夸张、隐喻艺术表现手法加以再现。作者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把狂风肆虐的毁灭性,与当时奸臣乱党兴风作浪,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破坏性进行沟通和联结,使得纯自然性的景象具有了社会属性。借助联想便可以洞见当时险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艰危的时局。置身此种现实情形之中,自然就会产生思想精神诸如苦闷、悲愤、郁结、压抑等之类的感受来。此外,在表现心理上,面对日益沦丧的“大道”,构建“雄才”形象以示时局艰危,而抒己回天乏术之慨;虚构“壮士拂剑”发己之“浩然弥哀”。“壮士”与“雄才”不过都是诗人自己的化身。
第二、以深刻感受和高度概括塑造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抒发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感情,因景生情,寄情于景,情景交浃。其中:以主体形象出现的个“我”——即“招憩不来,意苦若死”的艺术形象,是唐末那些具有倾向性和典型意义的,也即罗根泽先生所指“一部分流落江湖,或慷慨愤世”中的士子文人代表;以白描手法,表现“雄才”典型艺术形象心理,事实上反映了当时士子文人阶层的普遍心理;通过人物描写表现出的“壮士”艺术形象,其实就那些忠诚卫国将士的典型代表。
第三、语言高度洗练,内涵层次丰富、情节生动、境界高大;言虽尽而意无穷,滋味绵长,耐人寻索。
(二)风格理论特色
《悲慨》一诗,作为艺术作品,它是司空图诗歌理论的创作实践;作为艺术理论,它又是司空图诗歌理论中的一大风格建树。在有唐一代众多诗家侈谈“诗格”、“秀句”、“诗句图”的风气之下,司空图诗歌理论是具有超越性的,他的理论核心是“味外之旨”,其根本出发点之一,就是“存质以究实,镇浮而劝用”。对此,罗根泽先生的分析较为清明,以为司空图“一面以救世的志业移于诗,希望以诗转移世人的习性;一面以受不了社会的逼迫,逃到中条山王官谷的休休亭,不得不以诗寄托自己的生命。前者出于救世,后者出于避世,结果都趋于建立诗境。”[1]530
进而,罗根泽把司空图所建立的诗境视作“是超越人间世的极乐园,同时也是改善人间的理想国”[1]530,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据此认为司空图主张“诗贯六义,则讽喻、抑扬、汀蓄、渊雅,皆在其中矣。”[3]208淑世主义之说。而所建立的《诗品》诸如雄浑、冲淡……悲慨、形容等二十四种诗境是“充满逃避意味”的,似非确论。因为司空图隐忍之后的外在言行,与内在精神、思想、情感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状态,而占据统治地位始终不脱儒子功业。他晚年依然是佛、道其首而儒其业。其不食而卒,以身殉节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因此,遽然以其受不了社会的逼迫而隐忍中条山,他建立起包括悲慨在内的二十四诗境,便是“充满逃避意味”的,并非切实体谅古人心境之论。如同他在悲慨诗中表白的心迹那样:“大道日往,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分明是直面“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情形下,“意苦若死”的有志难伸、无可奈何,和大势已去的回天乏术,哪里有半点逃避意味掺乎其间?再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其实就是他在“立功”这一人生理想无望的现实情况下,转而以“立言”——另一种积极用世的方式和姿态,以致最终完成他作为士大夫人生境界的生动具体见证。古人是人不是神。我们不能把他视作“神”,更不能以“神”的标准来苛限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人!
无论司空图出于何种动因,其结果是建立起了迥异其趣的诗境,而诗境的建立无非是为了摹状、揭示其风格。“悲慨”一品从理论和创作双重层面,既实践他的“诗贯六义,则讽喻、抑扬、汀蓄、渊雅,皆在其中”淑世主义说,同时又申述了他的“象外”、“韵外”、“味外”三外说。其主要风格理论特色是以主“三外”说的象喻诗来体写悲慨风格:
1.以象征和隐喻表情达意,揭示主旨意趣
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与李生论诗书》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3]194,一并构成他的著名“三外说”理论。实际上,“象外”、“韵外”都是为其“以全美为工”的“味外之旨”服务的。前“两外”是后“一外”即“味外”的注脚。而“味外之旨”的指向,趋于王维、韦应物诗之“趣味澄夐,若清风之出岫”[3]189,追求的是意境含蓄,诗味澄夐。“悲慨”一品恰恰体现了他的这一审美要求。“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是自然之象;“招憩不来,意苦欲死”是人文之象。“壮士拂剑,浩然弥哀”是主体(人)之象;“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是客体(物)之象。当它们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映象出现在目击者的视野中时,因其本身具有真实、形象、多维度等特性,既可资传递人的某些态度和情绪,又能补充和强化语言符号在传意上某些不足;当它们通过诗人的审裁和构建以语言符号系统的“象”而存在时,它们所代表着人的某些态度和情绪,也就化为诗人并且代表着诗人的态度和情绪。这样,它们作为原象所表征的意义,是自然的“象内”之意。比如:“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就像我们今日所见巨大台风袭来,冲毁房屋田园、摧折林木等的情景一样。因为它的严重危害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之巨大,所以台风肆虐的结果代表着、实际也是传递着人类对之的愤慨、痛苦、悲哀等之类的心理情绪。诗人克服原象作为非语言系统缺乏组织结构性的不足,取其原象意,通过改造而成为变象时,它就是社会性的“象外之象”,带上了作者思想态度、心理情绪等蕴含其间,即具有延伸性的所谓象外意。于是,“大风”就演变成为表征强大邪恶势力的意符,“卷水”则是“大风”肆虐的情状。“林木为摧”,林木,在古人那里是用来修建房屋、桥梁等的主要材料。喻指国家、社会大厦的栋梁之才。广而言之,也可视为唐王朝的子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情形,系“大风”肆虐产生的危害的直接结果。这样,作者面对“大风卷水,林木为摧”的情形,所产生的思想态度、心理情绪等,借助人类心理情感的共通性也就可以想见并且体会得到。然而,作者并没有大肆渲染、铺排,而用高度浓缩、洗炼之笔,以“意苦欲死,招憩不来”寥寥几字,便把自己各种复杂而深刻的思想、心理、情绪和感受等蕴含于其间,使得诗味丰富而深长。作者以对自然的深刻领悟和高度艺术概括,来勾勒所表现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丰富性,又使得其诗意含蓄蕴籍,恰恰就是通过象征和隐喻的艺术手法建立象外之象而获得的。这也就是司空图本人所谓“诗贯六艺,则讽喻、抑扬、汀蓄、温雅,皆在其中矣”。
2.以建立因果关系来融铸悲慨诗风形成的主客因素,从而使诗境“近而不浮,远而不近”,饶有“韵外之致”的美感
全诗由客-主起兴,进而心理描写,直至诗境完成,可以说都是以因果关系建立起的有机链。因为有“大风卷水,林木为摧”的客观原因,才有诗人主观上“意苦若死,招憩不来”的精神苦闷;之所以令人产生“百岁如流,富贵冷灰”这种人生苦短、理想冷漠的心理情绪和叹息,是因了“大道日往,若为雄才”的现实无奈。而产生这种心理情绪恰恰又是主客原因导致的结果。至于“壮士拂剑,浩然弥哀”,也是因其目击“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的结果。统观全诗,因为“境中有人”,所以景物便有了生机和精神;因为“人在境中”,所以人的体性、情思、气质等内在特性,籍自然景物特性得到“强化和补充”。物我一气,交辉相映。这种诗境深契他本人“思与境偕”、“格在其中”的审美要求和原则。实际上,“思与境偕”作为“兴象说”、“发兴说”的继承发展,司空图更加注重形成诗歌风格主客因素的协调和平衡。悲慨诗风的生成即是如此,其主客因素自始至终是在因果链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仅从其物质外壳——诗歌语言运用的匀称性上即可一目了然,无须赘述。
那么,司空图为何要运用这种主客因素交融的平衡手段来构建悲慨诗风呢?我们知道,任何艺术作品,如果它的客观成分过多,则主观性愈少。由是之故,一方面,作品就会因为缺少生气,而流于呆滞枯槁,索然寡味;另一方面,作品识解、鉴赏起来就会变得很困难,给读者以“不知所云”的感觉。但如果是它的主观性成分过多,客观性成分就会愈少。如此一来,就会使得作品因其主观情思意绪过多而根基薄弱,致使诗风轻佻浮泛,或流于无病呻吟,或陷入矫情的滥觞。只有克服这种“过激”、“偏颇”带来的弊端,确保主客因素在诗风形成过程中的有机平衡和协调,才能使诗境具有“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3]193的审美效果,进而从中获得“味外之味”的美感。
全诗通过自然景象、精神心理、典型人物等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祸国殃民那股强大邪恶势力的无比愤慨,对国家时局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沉痛忧虑、极度苦闷,以及壮志难酬的万般无奈;彰显了诗人那不绝如缕、真挚灼热的救世情怀与磅礴气概。作者在严酷的现实和艰危的时局面前,既没有像他以前的诸如大历诗人一味地徘徊苦闷、哀怨惆怅、凄凉感伤;也没有像元和时期的一批苦吟诗人那样,因时代的阴霾、仕宦的坎坷、生活上的辛酸苦寒等陷入个人精神和肉体重创的自我天地之中不得自拔,使得作品思想情感郁闷低沉、境界促狭内敛。因作者冲破了个人自我狭窄天地,以丰富的想象、精当的构思、生动的形象、雄壮的气魄,表现出壮阔的胸襟、浓烈的情思、激越的音符、慷慨的气势而又万般的无奈。故而使得全诗意境深沉拓展、高昂开阔,具有震耳发聩、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这无疑是司空图对前人在相同或相似表现题材上的突破和创新,而这种突破与创新建立起来的悲慨艺术风格恰恰就是践行了他“三外”说诗歌理论的结果。
[1]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德]威克纳格.诗学·修辞学·风格论[M]//歌德,威克纳格,柯勒律治,等,著.文学风格论.王元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7.
[3]祖保全,陶礼天.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